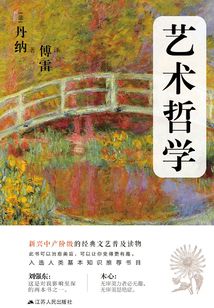
藝術哲學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譯者序
法國史學家兼批評家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自幼博聞強記,長于抽象思維,老師預言他是“為思想而生活”的人。中學時代成績卓越,文理各科都名列第一;1848年又以第一名考入國立高等師范,專攻哲學。1851年畢業(yè)后任中學教員,不久即以政見與當局不合而辭職,以寫作為專業(yè)。他和許多學者一樣,不僅長于希臘文,拉丁文,并且很早精通英文,德文,意大利文。1858-1871年間游歷英,比,荷,意,德諸國。1864年起應巴黎美術學校之聘,擔任美術史講座;1871年在英國牛津大學講學一年。他一生沒有遭遇重大事故,完全過著書齋生活,便是旅行也是為研究學問搜集材料,但1870年的普法戰(zhàn)爭對他刺激很大,成為他研究“現代法蘭西淵源”的主要原因。
他的重要著作,在文學史及文學批評方面有《拉封丹及其寓言》〔1854〕,《英國文學史》〔1864-1869〕,《評論集》,《評論續(xù)集》,《評論后集》〔1858,1865,1894〕;在哲學方面有《十九世紀法國哲學家研究》〔1857〕,《論智力》〔1870〕;在歷史方面有《現代法蘭西的淵源》十二卷〔1871-1894〕;在藝術批評方面有《意大利游記》〔1864-1866〕及《藝術哲學》〔1865-1869〕。列在計劃中而沒有寫成的作品有《論意志》及《現代法蘭西的淵源》的其他各卷,專論法國社會與法國家庭的部分。
《藝術哲學》一書原系按講課進程陸續(xù)印行,次序及標題也與定稿稍有出入:1865年先出《藝術哲學》(即今第一編),1866年續(xù)出《意大利的藝術哲學》(今第二編),1867年出《藝術中的理想》(今第五編),1868-1869年續(xù)出《尼德蘭的藝術哲學》和《希臘的藝術哲學》(今第三、四編)。
丹納受19世紀自然科學界的影響極深,特別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他在哲學家中服膺德國的黑格爾和法國18世紀的孔提亞克。他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無論物質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都可以解釋;一切事物的產生,發(fā)展,演變,消滅,都有規(guī)律可尋。他的治學方法是“從事實出發(fā),不從主義出發(fā);不是提出教訓而是探求規(guī)律,證明規(guī)律”[1];換句話說,他研究學問的目的是解釋事物。他在本書中說:“科學同情各種藝術形式和各種藝術流派,對完全相反的形式與派別一視同仁,把它們看做人類精神的不同的表現,認為形式與派別越多越相反,人類的精神面貌就表現得越多越新穎。植物學用同樣的興趣時而研究桔樹和棕樹,時而研究松樹和樺樹;美學的態(tài)度也一樣,美學本身便是一種實用植物學。”這個說法似乎他是取的純客觀態(tài)度,把一切事物等量齊觀;但事實上這僅僅指他做學問的方法,而并不代表他的人生觀。他承認“幻想世界中的事物像現實世界中的一樣有不同的等級,因為有不同的價值。”他提出藝術品表現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作為衡量藝術品價值的尺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征的有益程度,因為他所謂有益的特征是指幫助個體與集體生存與發(fā)展的特征。可見他仍然有他的道德觀點與社會觀點。
在他看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于種族,環(huán)境,時代三大因素。這個理論早在18世紀的孟德斯鳩,近至19世紀丹納的前輩圣伯夫,都曾經提到;但到了丹納手中才發(fā)展為一個嚴密與完整的學說,并以大量的史實為論證。他關于文學史,藝術史,政治史的著作,都以這個學說為中心思想;而他一切涉及批評與理論的著作,又無處不提供豐富的史料作證明。英國有位批評家說:“丹納的作品好比一幅圖畫,歷史就是鑲嵌這幅圖畫的框子。”因為這緣故,他的《藝術哲學》同時就是一部藝術史。
從種族,環(huán)境,時代三個原則出發(fā),丹納舉出許多顯著的例子說明偉大的藝術家不是孤立的,而只是一個藝術家家族的杰出的代表,有如百花盛開的園林中的一朵更美艷的花,一株茂盛的植物的“一根最高的枝條”。而在藝術家家族背后還有更廣大的群眾:“我們隔了幾世紀只聽到藝術家的聲音;但在傳到我們耳邊來的響亮的聲音之下,還能辨別出群眾的復雜而無窮無盡的歌聲,在藝術家四周齊聲合唱。只因為有了這一片和聲,藝術家才成其為偉大。”他又以每種植物只能在適當的天時地利中生長為例,說明每種藝術的品種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氣候中產生,從而指出藝術家必須適應社會的環(huán)境,滿足社會的要求,否則就要被淘汰。
另一方面,他不承認藝術欣賞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沒有客觀標準可言。因為“每個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別人的不同的趣味加以補足;許多成見在互相沖突之下獲得平衡,這種連續(xù)而相互的補充,逐漸使最后的意見更接近事實。”所以與藝術家同時的人的批評即使參差不一,或者贊成與反對各趨極端,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最后仍會歸于一致,得出一個相當客觀的結論。何況一個時代以后,還有別的時代“把懸案重新審查;每個時代都根據它的觀點審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徹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證實,便是有力的證實……即使各個時代各個民族所特有的思想感情都有局限性,因為大眾像個人一樣有時會有錯誤的判斷,錯誤的理解,但也像個人一樣,紛歧的見解互相糾正,搖擺的觀點互相抵消以后,會逐漸趨于固定,確實,得出一個相當可靠相當合理的意見,使我們能很有根據很有信心的接受。”
丹納不僅是長于分析的理論家,也是一個富于幻想的藝術家;所以被稱為“邏輯家兼詩人……能把抽象事物戲劇化”。他的行文不但條分縷析,明白曉暢,而且富有熱情,充滿形象,色彩富麗;他隨時運用具體的事例說明抽象的東西,以現代與古代作比較,以今人與古人作比較,使過去的歷史顯得格外生動,絕無一般理論文章的枯索沉悶之弊。有人批評他只采用有利于他理論的材料,擯棄一切抵觸的材料。這是事實,而在一個建立某種學說的人尤其難于避免。要把正反雙方的史實全部考慮到,把所有的例外與變格都解釋清楚,絕不是一個學者所能辦到,而有待于幾個世代的人的努力,或者把研究的題目與范圍縮減到最小限度,也許能少犯一些這一類的錯誤。
我們在今日看來,丹納更大的缺點倒是在另一方面:他雖則竭力挖掘精神文化的構成因素,但所揭露的時代與環(huán)境,只限于思想感情,道德宗教,政治法律,風俗人情,總之是一切屬于上層建筑的東西。他沒有接觸到社會的基礎;他考察了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卻忽略了或是不夠強調最基本的一面——經濟生活。《藝術哲學》盡管材料如此豐富,論證如此詳盡,仍不免予人以不全面的感覺,原因就在于此。古代的希臘,中世紀的歐洲,15世紀的意大利,16世紀的佛蘭德斯,17世紀的荷蘭,上層建筑與社會基礎的關系在這部書里沒有說明。作者所提到的繁榮與衰落只描繪了社會的表面現象,他還認為這些現象只是政治,法律,宗教和民族性的混合產物;他完全沒有認識社會的基本動力是在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
但除了這些片面性與不徹底性以外,丹納在上層建筑這個小范圍內所做的研究工作,仍然可供我們作進一步探討的根據。從歷史出發(fā)與從科學出發(fā)的美學固然還得在原則上加以重大的修正與補充,但丹納至少已經走了第一步,用他的話來說,已經做了第一個實驗,使后人知道將來的工作應當從哪幾點上著手,他的經驗有哪些部分可以接受,有哪些缺點需要改正。我們也不能忘記,丹納在他的時代畢竟把批評這門科學推進了一大步,使批評獲得一個比較客觀而穩(wěn)固的基礎;證據是他在歐洲學術界的影響至今還沒有完全消失,多數的批評家即使不明白標榜種族,環(huán)境,時代三大原則,實際上還是多多少少應用這個理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