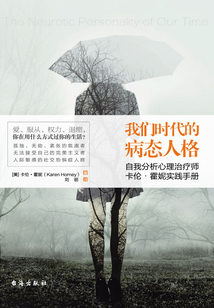
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
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序言
我之所以寫作這本書,其目的是為了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眾進行解讀,刻畫出他們內心的各種沖突、焦慮和痛苦,以及他們在個人生活和同他人交往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種障礙。這里,我要探討的不是哪種類型的病態人格,而是以不同形式出現在人們身上的性格結構。
我的研究重點在于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沖突,以及人們為消除這些沖突所作的嘗試;在于人們內心實際存在的焦慮,以及他們為抵抗這些焦慮所建立的防御機制。當然,看重實際處境,并不是說我對精神分析學家所說的,病態人格形成于童年時代的早期經驗的觀點持排斥態度。但是,我與精神分析專家的不同之處在于,我反對片面地把注意力聚焦在童年時代,而把人們后來的反應視為早期經驗的重演。我要指出的是,童年時期的經驗同后來的沖突兩者之間的關系,遠比一般精神分析專家所設想的要復雜得多。他們只注意到一種簡單明了的因果關系,然而實際情況卻是,盡管童年時代的經驗對于病態人格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可是它們卻并非導致后來各種心理障礙的唯一原因。
當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實際的心理障礙時就會發現,病態人格可以源自于偶然的個人經驗,也可以由我們所處的特殊文化環境造成。實際上,文化環境不僅為個人經驗增加分量和色彩,而且最終決定了它們的特殊形式。例如,一個人是有一位獨斷專行的母親還是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母親,是個人無法選擇的,然而只有在那些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我們才能夠看到這樣的母親出現。同時也正是因為存在著這些文化條件,這種經驗才會影響這個人以后的生活。
如此一來,曾被弗洛伊德當作病態人格形成根源的生物與生理因素,就馬上從主角淪為了陪襯。而這些次要因素產生的影響,只能通過分析大量精確的事實材料才能知曉。
因這種特別的思想傾向,我對病態人格中眾多基本問題進行了全新的解釋。盡管這些解釋涉及的領域廣泛、問題也各不相同,例如受虐狂問題,愛的病態需要的內涵,病態的罪惡感的意義等,但它們離不開一個相同的基礎,那就是認同且強調焦慮對產生病態性格傾向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很多解釋都與弗洛伊德的觀點截然不同,所以某些讀者可能會疑惑:這還是精神分析嗎?在這里,我要告訴大家,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取決于你是怎樣看待精神分析中最本質的東西的。假如你堅信精神分析全然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那一套理論構成的,那么,我在此處所提及的一切就不能夠算作精神分析。然而,假如你認為精神分析的本質在于探索無意識過程的作用和表現方式,并按照心理治療的形式將這些潛在的過程意識化,那么,我在此處所說的就算得上是精神分析。在我看來,如果只拘泥于弗洛伊德的理論,那么我們在對病態人格進行分析時就會只能看到弗洛伊德希望我們看到的那些東西,這只會讓我們故步自封。我相信,只有繼續鞏固弗洛伊德所奠定的基礎,才是對弗洛伊德偉大成就真正的尊敬,經由這種方式我們才能攜手完成精神分析的未來使命,促使精神分析既成為一種治療實踐,又成為一種指導性的理論方法。
這一說法也一并回答了另外一種可能會出現的疑問,即我的理論是否與阿德勒(Adler)式的理論同屬一類。不錯,我的理論同阿德勒曾經所強調過的某些觀點是有相似之處,但從根本上來說,我的理論還是以弗洛伊德為基礎的。實際上,阿德勒的理論恰好是一個最佳的例證,它說明:即便是對心理過程的頗具創造性的洞察,假如只是從片面的角度去探索,而不以弗洛伊德理論為基礎,也會變得枯燥乏味。
由于本書并不是以界定我與其他精神分析專家觀點的異同為目的,所以從整體上而言,我只把討論范圍局限在與弗洛伊德的觀點有重大分歧的問題上。
在此,我所提及的一切都是對病態人格進行長期精神分析研究所獲取的各種印象。為了證明我的理論不是無的放矢,我在書中列舉了很多詳實的例子,如此一來,就不可避免地使得敘述過程顯得有些冗長累贅。而事實上,即便沒有這些材料,專家乃至外行也仍舊能夠檢驗我的結論正確與否:假如他是一個擅長觀察的人,就可以將我的假設同他的觀察結果和經驗放在一起作對比,并根據對比的結果,來選擇是否拒絕或接受甚至是修正我所說的一切。
本書用詞力求簡潔。為了確保敘述清晰明了,我會盡量避免過多地討論細枝末節的問題,與此同時,我也盡可能不去使用過于技術性的專業術語,因為人們可能會過于依賴此類術語而無法進行清晰的思考。可是,這樣一來,很多讀者,尤其是外行,或許就會認為病態人格是一個淺顯易懂的問題,這個結論是錯誤甚至危險的。我們不得不承認,所有心理問題都必然是極其復雜與微妙的。假如哪位讀者不愿意接受這樣的事實,那么他最好還是不要讀這本書,否則他就會發現自己被越弄越糊涂了,同時還會因不能找到現成的公式而大失所望。
本書既是寫給那些對病態人格感興趣的外行看的,也是寫給那些以治療病態人格為職業,因而對本書所涉及的種種問題非常熟悉的人看的。這些人中不僅有此方面的專家,同時還包括教師、社會工作者,以及那些開始意識到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除此之外,我希望本書對具有病態人格的人自身也能產生某種積極的意義。假如這些人在原則上并不把心理學思想視為某種對個人的侵犯和強加的負擔而加以排斥的話,他往往能夠根據自身的切身感受,比其他人更敏銳也更準確地領略錯綜復雜的人類心理活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僅靠閱讀本書本身并不能讓他們擺脫病態人格的困擾;在所閱讀的內容中,他們或許更容易發現他人的影子,而非自己的影子。
我希望借此機會,表達我對本書編輯伊麗莎白·托德女士的感謝。至于其他那些我必須對其表示感謝的作家,我將在本書的正文中分別提到。此外,我特別要向弗洛伊德致以最誠摯的謝意,正是他為我們今天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工具。同時我也要向我的研究對象表示感謝,我對他們的了解都得益于他們的配合。
Karen Horney
卡倫·霍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