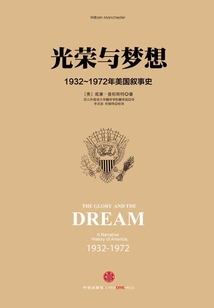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內訌不斷(1)
1951年1月4日,漢城(今韓國首爾)再次淪陷。共產黨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將美國軍隊阻隔在朝鮮半島中部的原州,破壞了聯合國軍的整條戰線。麥克阿瑟的第八集團軍新任司令、陸軍上將馬修·邦克·李奇微率領20萬人(半數為朝鮮當地人)對抗40萬中朝軍隊,結果“落荒而逃,自食惡果”,使得遠在華盛頓的國務卿艾奇遜也感到情緒低落。
聯合國軍戰線倒沒被沖垮。李奇微投入后備兵力,利用空中優勢,從兩翼迅速集結軍隊,緊緊堵住原州的缺口。1月中旬,即中國春節前夕,朝鮮的進攻勢頭已過。1月的最后一個星期,聯合國軍開始反擊。2月底,第八集團軍被打回漢城郊區。3月14日夜,李奇微重新占領漢城。兩個星期后,兩支大軍再一次在三八線上展開對峙,又回到三個月前的原點——單就這一點,也可以說又回到9個月前戰爭爆發之際的原點。
美國的這一代人仍在為“二戰”取得的勝利激動不已,又因近來順利登陸仁川的奇跡而沖昏頭腦,他們不可能平靜地接受這種僵持的局面。對于大部分美國人而言,僵持(鼓吹有限的目標以避免無休止的戰爭)就像異教邪說,聽來令人生厭。《生活》雜志的一篇社論表示,要拒絕與蘇聯共產主義“共存”,說那是“政治哄騙”,是“致命的謬論”。“院外援華集團”對美國政府不愿入侵中國東北不屑一顧,認為它們是在“姑息”,極端保守的共和黨人則認為艾奇遜號召克制的做法幾乎等于叛國。
戰前的孤立主義正經歷著一場不同尋常的改變。12月,33個師的中國軍人開始涌入麥克阿瑟的防護網。兩名孤立派曾公開表示要對朝鮮的遠征軍置之不理。12月12日,約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發表的演說中呼吁美國人:“做好你們自己分內的事,只在家園遭到威脅時再干涉。”12月17日,前總統胡佛聲援肯尼迪。他提出的理由是,在與共產黨軍隊進行的全球沖突中,美國軍隊不會永遠處于上風,但美國空軍和海軍可以控制海洋,保衛美國。他告誡美國人要安分守己,同時要喂飽“世界上饑餓的人民”,以及貫徹他解決國家危機不變的政策——平衡預算。
然而,敏感的孤立主義研究者注意到了一些新的變化。胡佛的單干假設并非像起初那樣孤獨,也不是僅限于西半球。他想“一邊以英國為疆界,另一邊以日本、臺灣[1]、菲律賓群島為疆界”,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接替胡佛擔任共和黨右翼領袖的塔夫脫在參議院亦做出同樣的讓步。塔夫脫表示,如果這些地區遭受襲擊而又能成功防衛,那么對于這些“民主島嶼”應予以保護。胡佛–塔夫脫主義,也可稱作美國堡壘主義或大陸主義,在新年到來之際,已被提議為代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的另一個選擇。在國會的這次討論中,選擇哪一個為最佳方案是主要議題。記者們紛紛稱之為“大辯論”。
當時,美國的當務之急是撥款建立4個師,這是杜魯門曾向北約做出的保證。1951年1月5日,塔夫脫告訴參議院:“國會從未批準給歐洲一支地面部隊的方案,我們也不應該不明就里地同意該計劃。”三天后,參議員惠里提出參議院第8號決議,反對在制定正式的國會政策前,向歐洲派遣地面部隊。2月15日,共和黨大部分議員簽署聲明,贊同胡佛的大陸主義。塔夫脫的對手們一心把他說成故意阻撓議案通過者。然而,他們不曾明白且塔夫脫也忽視的是,在塔夫脫身后支持他的是由憲法賦予發動戰爭權力的國會,并非白宮。塔夫脫并無意妨礙行政部門的工作。1月15日,塔夫脫宣布,他“已準備妥當,可與總統……或多數派政黨人士討論并制訂出方案,以獲得美國民眾的一致贊同和不斷支持”。但杜魯門并不打算與他人分享自羅斯福“百日新政”以來,通過許多先例而日漸擴大的總統權力。
按20世紀70年代的觀點來看,這次辯論最顯著的一點是,雙方都默認某些先決條件,但這些在20年后早已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了。無論是政治雄辯家還是國會都提倡“自由世界”——他們一致認為“自由世界”包括蔣介石盤踞的中國臺灣、李承晚的韓國、保大的南越、薩拉查的葡萄牙、法魯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廷、法屬阿爾及利亞、受軍事獨裁控制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亞洲的所有歐洲殖民地。大陸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都認為,運用美國的軍事力量是有益的。雙方無論誰獲勝,美國人民都會接受,他們不會組織游行和抗議,甚至連討論都不會有。所有辯論者都認為共產主義是龐大而單一的,有一個中央系統指導著他們從中國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紅色活動,因此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在任何地方進行的任何活動都是事先計劃好的,然后對所有的“自由世界”產生影響。當時,這種信念出奇地獲得了一致支持,杜魯門總統因此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在中南半島和西藏看到一種模式,其在時間上與朝鮮的進攻相吻合,我們把它們視作對西方世界的挑戰。這單單是共產主義者的挑戰,其目的在于增強大部分亞洲人民已平息的排外情緒。英國盟軍和歐洲的許多政治家都認為中國的行動旨在阻礙美國援助歐洲重建的計劃。
此次討論在以胡佛–塔夫脫為代表的共和黨人和以杜魯門–艾奇遜為首的民主黨人之間產生了本質上的分歧,但這還遠非黨派之爭。約瑟夫·肯尼迪仍是一名民主黨人,參議員喬治和道格拉斯也是民主黨人,兩人都認為在國會不支持的情況下,總統不得派遣士兵出國。另外,共和黨參議員洛奇和諾蘭則認為,參議院在原則上已支持北約,因此杜魯門能派出軍隊以實施計劃。托馬斯·杜威、厄爾·沃倫、哈羅德·史塔生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持北約。最后,一位未來的共和黨總統的證詞決定了辯論的結果。
這位證人就是艾森豪威爾。馬歇爾將軍對所謂的“集體安全”的必要性高談闊論,但其主張與羅斯福–杜魯門政策保持一致的時間太長了,所以被認為難以超脫戰爭之外,而艾森豪威爾則不同。圣誕節前一個星期,艾森豪威爾離開哥倫比亞大學,成為西歐軍事防御的最高指揮官。他對國會說,除了“重新武裝保衛西歐”,別無他法。他說,在歐洲人中,反對斯大林的呼聲高漲,他建議美國取得北約的領導權,主張更多的美國武裝力量進駐歐洲,而國會也不應限制其日后的增援力量。
塔夫脫抗議道,這樣會使事情“更加模糊不清、難以捉摸”,但辯論就此結束,他失敗了。詹姆斯·賴斯頓在《紐約時報》上評論道,艾森豪威爾擁有艾奇遜不具備的東西——“國內的政治支持”。此外,他還有“共和黨的支持,而這是自1950年春天威斯康星州共和黨人麥卡錫進入西弗吉尼亞州以來,國務院最缺少的東西”。惠里的決議案被否決了。4月4日,國會接受了另一方案,同意派遣4個師到歐洲駐扎。國會告誡總統,沒有“國會進一步的同意”,不得加派軍隊,但如今已無法阻止杜魯門了。
這是共和黨人過得極為艱辛的一個冬天。他們18年沒有執政了,并未意識到政治力量正在艾森豪威爾將軍那里聚集,而只看見更加灰暗的前景。當時,麥卡錫是黨內最出名的人。11月,他前往馬里蘭州鏟除米勒德·泰丁斯。這是一次不光彩的活動。共和黨內無足輕重的約翰·馬歇爾·巴特勒是泰丁斯的競選對手。麥卡錫與《華盛頓時代先驅報》支持巴特勒,煞費苦心地出版了只有一期的小報《記錄》。競選前夜,這份小報出現在馬里蘭州每戶人家的門口。報上是麥卡錫編造的攻擊泰丁斯的卑劣謊言,封面上是一張移花接木的假照片,顯示泰丁斯正與美國共產黨總書記厄爾·白勞德握手。泰丁斯因此失去4萬張選票而落選,在這之前,他可是被看作戰無不勝的。如果他被淘汰了,那么人人都有出局的可能。競選后的次日早晨,一位民主黨資深參議員環顧參議院的同事,問道:“喪鐘為誰而鳴?”然后冷冷地回答:“為君而鳴。”
接下來的一個月,華盛頓薩爾格雷弗俱樂部發生的一件事,顯示出林肯政黨的墮落程度之深。在知名專欄作家德魯·皮爾森33歲生日前夜的晚宴上,參議員尼克松離席,發現醉醺醺的麥卡錫正在男廁所毆打皮爾森。麥卡錫用皮帶抽打這位專欄作家的臉,譏笑道:“迪克(尼克松的昵稱),這一下是為你打的。”接著又說:“我想證明一種理論。如果用膝蓋使勁頂一個人的睪丸,血會不會從他的眼珠子里冒出來。”尼克松上前一步說:“讓我這個貴格會信徒來阻止這場架吧。”他拉著麥卡錫的胳膊說:“走吧,喬(麥卡錫的昵稱),該回家了。”麥卡錫說:“不,讓他先走,我可不會背對著這個人。”皮爾森離開后,麥卡錫告訴尼克松,他不記得把車停在哪里了。兩人在附近找了半小時,這位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員尋找車牌,而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則在黑暗中搖搖晃晃地跟在后面。尼克松找到車后,麥卡錫便急馳而去。對麥卡錫來說,最好是醒醒酒再開車,就像對共和黨的士氣來說,最好是別的共和黨人獲得千萬選民的擁戴。但共和黨別無選擇,很多年前黨內就已經沒有偶像了。
接著,春天來了,一切都變了。4月11日,杜魯門為他們帶來了一位受迫害的英雄。杜魯門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職務,讓大辯論演變為更大的辯論,觸發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作戰勝利日到12年后達拉斯事件[2]之間,美國最讓人大動感情的震蕩。
麥克阿瑟與艾森豪威爾不同,他不受士兵的廣泛愛戴,但人氣并非衡量將軍好壞的標準。論功績,同時代的將軍無人能及麥克阿瑟,他也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出色的指揮官。1918年,麥克阿瑟擔任駐法彩虹師師長,當時38歲的他是軍隊中最年輕的將軍。之后,他率領美國陸軍與日軍作戰,并以總統代表的身份治理戰后的日本。直到1951年,在許多美國民眾心中,他都有如神祇。在48年的軍旅生涯中,他學會了也實踐了軍人的一切美德,但唯一例外的是,他當不好副司令。
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在中國軍隊參戰后的那個冬天,麥克阿瑟在想些什么,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已喪失戰斗熱情。據曾任布雷德利將軍的副官,后任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高級軍事助理的切斯特·克里夫頓少將的說法,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在1月以軍事理由而非政治理由召回麥克阿瑟:“問題的關鍵在于麥克阿瑟失去了自信,并逐漸對下屬軍官和軍隊失去信心……但當他犯下不服從總司令命令的錯誤時(這一點證據確鑿),參謀長聯席會議輕而易舉地做出了決定。”然而,大部分華盛頓人懷疑總統是否有勇氣訓斥麥克阿瑟。4月11日,《華盛頓郵報》早報的標題為“國會獲悉,總統不會召回麥克阿瑟,但仍會訓斥他”。
當時,美國上下都知道了兩人之間的爭論。威克島戰役的精神早已被忘卻。12月初,麥克阿瑟開始在報紙上中傷總統,將言辭激烈的信件寄給《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周刊以及合眾社社長。杜魯門后來表示:“我本應該即刻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然而,杜魯門只是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警告麥克阿瑟,未經華盛頓同意,“不得擅自發布有關政策的言論,不得召開記者會或公開講話”。圣誕節后,總統寫信給麥克阿瑟,對其才能大加贊賞,同時委婉地提醒他,“就擴大敵對區域而言”,總統有責任“謹慎行事”。為確保麥克阿瑟明白這一命令,聯席會議的兩名首長柯林斯和霍伊特·桑福特·范登堡于1月12日飛往東京,在總部大樓將信交到麥克阿瑟手里,并告訴他,如果他需要,他們會做出說明。麥克阿瑟說不需要。接下來的兩個月內,麥克阿瑟不見任何記者。用國務卿艾奇遜的話說,麥克阿瑟“蓄意破壞政府的行動……破壞了一次他被告知的行動,這是對總司令的公然反抗”。
杜魯門認為該停戰了,進行和平談判的時刻已到。3月20日,他起草聲明宣布這一消息,并抄送給聯合國中的每一個美國盟國以作參閱,參謀長聯席會議將文件秘密送到東京。令他們詫異和害怕的是,麥克阿瑟竟然通知報社,并宣布他已準備好按自己的條件與交戰方進行談判。這破壞了杜魯門的計劃,卻又一事無成。麥克阿瑟提出的建議是全殲中國軍隊,正如沃爾特·李普曼直言不諱地指出:“任何政權都不會在生存問題上討價還價。”中國重申了自己對勝利的信念。和平攻勢還未開始就已然失敗,只留下氣急敗壞的總統。隨后,杜魯門寫道:“麥克阿瑟讓我別無選擇,我無法再容忍他不服從命令。”但在采取行動之前,又發生了一件事,使杜魯門忍無可忍——麥克阿瑟給國會議員喬·馬丁寫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