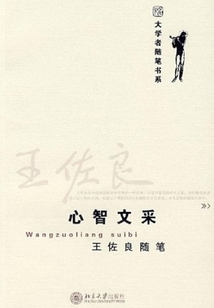
王佐良隨筆:心智文采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劍橋掠影記——1982年7月之游
真正是掠影。牛津只停留了一上午,劍橋也不過一夜一天。
然而能去還是比不去好。至少,我重溫了舊夢。
1949年8月,我離開牛津的時候,沒有想到能重來。現在,雖然隔了三十三年,我畢竟又出現在茂登學院的門口。
這是我當年做研究生時的所在,應該說是一個很熟悉的地方。然而我從“玫瑰巷”進去,居然把大門的朝向都弄反了。
一進門是傳達室。仍然是師生們取信的地方,一格一格的信架還在那里,但是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后來才在門口看見了一位女工,她點點頭,把我領到了總務長的房里。總務長是一位退役的中校,名叫亨特生。寒暄之后,他就陪我在學院各處看了一下,首先走進我當年住過的宿舍。
房間的內部現代化了,有一個白瓷洗臉盆,冷熱水俱全(過去,我們用小盆,每天早晨由管房間的工人送來一瓷瓶熱水,供刮胡子用)。但那面大窗子還在,窗外仍是那棵大梨樹,樹下是一片草地。記得我剛住進去的時候,詩人艾特蒙·勃倫登來看我,他指著那棵樹說:“春天這樹開滿白花,你會喜歡它的。”他原是這學院的教師,后來去了倫敦,這次偶然回來,聽說我是燕卜蓀的中國學生,因此主動來看我。我請他喝中國綠茶,他是我在學院宿舍里招待的第一個客人。
現在房里是另一代的學生了。我們向他道謝一聲,就走了出來。
然后走進新近重修過的教堂。這是牛津城最老的教堂之一,13世紀建的。外墻是淡黃色的石頭,已經一塊一塊重新換過,幾世紀風吹煙熏的黑跡沒有了。里面因無人而顯得寬大,橡木做的祭壇和桌椅之類發著典雅的光澤,但我更喜歡長窗上的彩色玻璃,它們拼出的圖畫是宗教故事,然而打動我的卻是那在幽暗中忽見光線透過紅藍黃綠等色玻璃而來的絢爛景象。
然后進了圖書館。只有一位教師管著,我問他那些用鐵鏈拴著的古書還在嗎。(中古時期的英國學生也有偷書的,所以圖書館里貴重書都用鐵鏈拴住,可以拿下來放在前面的長條桌子上讀,但拿不走。)在我當學生的時期,那樣的“拴鏈的書”還頗有一些。現在,這位管理員說:“還有,只是不多了,這里只留下一本做個紀念。”我記得三十年前的圖書館長是蓋羅德先生(H。W。Garrod)。他是古典文學專家,又是當時標準版《濟慈詩集》的編者,好像一直是單身,我常見他同學生在大樹下下棋。
接著是大廳。所謂“大廳”,是飯廳兼課堂。凡牛津正式學生,都一定要在所屬學院的大廳里吃上至少三個學期的飯。學校的飯天下一樣,總是大鍋菜,衛生而無味道。我們那時候正值戰后英國經濟緊縮,新上任的工黨政府厲行節約,主要食品也定量配給。我們學生去吃早飯時,每人手托一盤,上有一小塊黃油,一周的配給在此,得很吝嗇地、有計劃地吃。雞蛋也是每周配給一兩個,但是好心的英國同學常常從鄉下的家里或農場帶來一些雞蛋送給我吃。大廳里吃飯,有各種規矩,例如遲到或說了什么不雅的話要罰酒,總是先有人大喊:罰!罰!然后由受罰者出錢買啤酒,盛在一個很大的銀杯里讓大家傳著喝。院士們另在大廳上端一個桌子吃飯,桌子放在一個平臺上,叫做高桌。他們吃得比學生好,菜是另做的,有多種酒助餐,吃完之后還要一邊喝著葡萄酒,一邊各逞才智地談笑一番。
大廳四壁掛著歷任院長和重要院士的油畫像,師生們就是在這些歷史人物的注視下吃飯。我注意到有了幾張新的畫像。我當年的院長是一位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家,早已去世。新掛的像是他的繼任者,已經有兩三位了。
這樣周游一過,總務長又陪我在校園里走走。茂登學院的校園不大,但歷史久遠,一邊靠著古城墻,沿墻有一條路,叫做死人之路。這個名稱的來源我已忘了,現在我貪看的是那茂密的草地、大樹和花叢,想起了過去我在那里坐著看書的日子。
也就想到了我的導師F。P。威爾遜先生。牛津各學院往往文法理等學科都設,但又各有所長。茂登學院所長在哲學和英國語言文學。牛津的教授為數甚少,但有兩位英國語言文學教授就是屬于茂登的,當時威爾遜就是其一。另一位是研究中古英語,后來以寫多卷本古代傳奇小說出了大名的托爾金。威爾遜教授在英國學術界以外幾乎不為人知,但在英美文學研究界頗受尊崇。他是文學史家,是當時牛津大學出版社正在出版的多卷本《英國文學史》的兩個主編之一,又是版本學家,曾改編原由有名的版本學者麥開羅編的《戴克全集》。他寫的《莎士比亞與新目錄學》一書雖然篇幅不長,卻引起研究界的一致好評,因為在這里他把一個復雜的學術問題交代得十分清楚,重要的事實敘述得十分翔實,而又敘中有評,重點突出,同時文章又寫得典雅而有風趣,令人愛讀。
然而他寫的書不多,只有幾本講稿匯集,如《馬洛與早期莎士比亞》、《17世紀散文》、《伊麗莎白朝與詹姆斯朝》,都是薄薄的小書。他籌劃中的一本大書是上述牛津文學史中的十六七世紀戲劇卷,其中心人物就是莎士比亞,但是沒有寫完他就去世了。
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年約五十,衣著隨便,走路微跛(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傷所致)。牛津的教學主要靠各學院自己進行,大學無“系”,但為了日漸增多的研究生的需要,有一個英文部,附設一個圖書館。威爾遜當時就主管這個英文部,研究生入學、聽特設的專業課、參加合格考試(考五門專業課,筆試再加口試,考試及格才能寫論文),以至最后交論文安排口試(即答辯),都要經他批準。
我寫有關17世紀劇作家韋勃斯透的論文就經過他的指點。他告訴我,要注意歷代對這位劇作家的看法,但看法不一定只在評論文章里,還應注意他的劇本上演、改編、摘選等等的情況,因此他要我去查各種私人抄本、各代劇本目錄、劇院廣告等等。這類事看似瑣碎、枯燥,但一個研究者必須搜集一切有關材料,然后加以選擇。當然,更重要的是通過歷代作家、文論家對韋勃斯透的反應,追溯出歷代對于英國文藝復興時代詩劇的愛憎、迎拒的弧線,從而看出歷代的文學風尚,這樣就又揭示出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一個側面。另外,他說一個學者要寫得確實,但又要有點文采,例如能敘述圖書目錄和劇院廣告等十分枯燥的細節而做到眉目清楚,文字不枯燥才算本領。他自己的著作,特別是上面提到的《莎士比亞與新目錄學》一書,就做到了這一點。
我還記得,我的論文口試剛完,就接到他的信,問我考試經過,并要我去他家吃飯。像許多老一代的英國學者一樣,他寫信給朋友不用打字機,而且書法雅致。我去過他家多次,同他的夫人和女兒(也是讀英國文學的牛津學生)也都熟了。
現在他已過世,他的夫人和女兒又在哪里……我站在曾同他一起散過步的茂登校園內,感到惆悵。
托爾金也不在了,蓋羅德也不在了,當年的同學也星散了,這地方充滿了記憶,卻沒有一個熟人。等到總務長邀我進入小餐廳,我遇到了新一代的院士們,包括院長、教務長、現任茂登英國文學教授,還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有名的勃萊克威爾書店的老板貝索爾·勃萊克威爾爵士,他倒是我在1948年見過的。他告訴我他早已不管書店的事,現在是茂登學院的榮譽院士。他仍然愛說愛笑。“我今年九十四歲。”他說,“而蕭伯納只活了九十,將來我在陰間看見他,還得向他道歉去遲了。”而當榮譽院士呢,“只意味著我一直到死,在這里吃飯不花錢,如此而已”。
這是一次午餐會。每人自己動手。我取了熱火腿、色拉、餅干、奶酪、香蕉和葡萄,亨特生又給我端來一大杯冰啤酒。有人問我當年茂登的情況,有人問到中國和北京。我除了回答,也問英國文學研究和出版情況,例如牛津版《英國文學史》是否已經出全。約翰·凱萊(John Carey,現任茂登英國文學教授,常在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寫評論文章)說,還未最后出全,但早出的幾卷已在修訂。我又問,是否現在不興寫大部頭文學史了?(美國有人這樣說。)凱萊說,不然。據他所知,劍橋大學正在計劃編寫另一套多卷本《英國文學史》。
可惜這種吃飯場合,無法多談,而我下午還得去劍橋,只得匆忙吃完,就向院士們道別了。
這一次走出學院大門,我放慢腳步,回頭多看了幾眼。
走上大街,我的情緒起了變化。這條曾被稱為歐洲最高尚的街道的牛津大街仍是老樣,連那些賣紀念品的商店也仍然像以前一樣古色古香。恰好來了大批外國游客,在街上東張西望,猶如昔年暑假所見。這時候我就覺得牛津又屬于我了。我決心要做一兩件我過去愛做的事。去河邊漫步已不可能,徜徉大草地也無時間,想進包德林圖書館看看那美麗的亨弗萊公爵閱覽室怕已關門,于是走進大街中段的牛津大學出版社門市部——幸好它還在那里!趕緊買了一本《彌爾頓詩集》。出來,過街,經過一條叫做透爾的小巷,抵達寬街,對面就是勃萊克威爾書店,我又進去,匆忙瀏覽一下,買了一本牛津新版的《彭斯詩集》。
接著,直奔汽車站,看見英國文化委員會牛津辦事處的一位女士拿著票在等我,并且帶來了我的行李,這才喘息稍定,向她道謝之后就上了車。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后來想想,也許這樣倒好。如果多事盤桓,很可能記憶將多得無法承擔,真要變成感傷的旅行了。
到了劍橋,第一件事是去看老同學。
因為伊恩·杰克(Ian Jack)在那里。伊恩同我一起在牛津茂登學院做研究生,不久他結了婚,我幫他找房子,同他的妻子琪恩也成了好朋友。琪恩也研究文學,后來成了笛福專家,但前幾年同伊恩離婚了。伊恩現在是劍橋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他一聽說我來英國,就寫信約我來劍橋。幾天后,我到了蘇格蘭,剛進格拉斯哥的一家旅館,放下行李,就接到他的長途電話。三十年后第一次交談,他還是那樣熱情而又幽默。
他住在劍橋郊外。我坐出租汽車到達時,已是黃昏,他與夫人伊麗莎白在很大的花園里等我,旁邊一個四五歲的男孩在玩耍。
我們兩人對看了好久。三十年的逝水年華,兩個大洲的距離,那心情,真如彭斯所詠:
我們曾赤腳淌過河流,
水聲笑語里將時間忘。
如今大海的怒濤把我們隔開,
逝去了往昔的時光!
忠實的老友,伸出你的手,
讓我們握手聚一堂。
再來痛飲一杯歡樂酒,
為了往昔的時光!
一連串往事浮上心頭:他在課堂上寫小條子告訴我,勃萊克威爾書店來了一套路卡斯編的《韋勃斯透全集》,我一下課就趕緊跑去買下(他也對韋勃斯透有興趣,曾寫一文,題為《韋勃斯透是一個存在主義者么》,發表在著名文學理論家F。R。利維斯主編的《細察》雜志上);他第一次帶著琪恩來看我,琪恩是一位漂亮的蘇格蘭姑娘,但與始終不改蘇格蘭口音的伊恩相反,說一口純正的牛津英語;我們一起上牛津大街上某處一所古老而簡樸的小飯店,三人站在木樓梯上耐心地等待桌子;我們參加學生社團蘇格拉底學會,坐在地板上聽牛津名學者C。S。路易士雄辯滔滔地批判薩特的存在主義;我和伊恩騎自行車,隨著一群同學周游處處都是玫瑰花的牛津鄉下,每到一個小酒店就停下喝一大杯從木桶里汲出來的啤酒……
然而兩個人都還沒有衰老。伊恩的臉上多了皺紋,但頭不禿,滿滿的一頭白發,顯得雄邁。他告我他仍然每天騎自行車去講課。伊麗莎白年輕、和氣,看來很會持家,那天晚餐桌上的一大塊羊肉就是她自己烤的。孩子呢,很健壯,吃完了甜菜(黑莓加奶油),自個兒玩去了。
飯后伊恩把我讓進了他的書房,點起了一根小雪茄,我啜著咖啡和白蘭地。只在這時候,我們才像過去那樣談了起來。
彼此的工作,出了什么書,到過什么國家講學,劍橋文學教師中傳統派與革新派之爭,過去一些同學的近況,學術界、出版界的動態……
但是我心中有一個問題,遲遲不好提出。伊恩也終于覺察到了。
“琪恩?”他問。
“對了,她怎么樣?”
“她還在牛津,是圣休學院的院士。你知道,我們離了婚以后,仍然是好朋友。”
那么,又何必離婚呢?見證過他們婚后快樂的我,對這事總感到遺憾。如果我知道琪恩還在牛津,那么今天上午我是會去看她的。現在我聽了伊恩的話,只能默默地祝她幸福了。
第二天早上,陽光燦爛。我在所住的大學紋章旅館吃了早飯,就漫步街上,照著一張小地圖上的標記,去尋一些我想看的地方。過去我來過劍橋一次,住了兩天,但是現在連路也不認識了。好在這大學城不大,比牛津還小,尋找那幾所有名的學院還是不難的。
通過一兩條幾乎無人的小巷,我就到了國王學院。這是劍橋有名的地方,游客總要來看這所學院的教堂的。教堂立在一片剪得平整的草地之后,建筑的樣式莊重中帶靈巧,通體白色,被那片草地的綠色襯托得特別鮮明。它旁邊沒有零亂的小屋,草地又很大,草地邊上是康河,所以人人可見它的全貌,加上旁邊學院本身的一長排建筑,屋頂上塔尖林立,整個布局真是美極了。而且這地方幽靜中有生氣,河邊草坡上常有許多男女學生或坐或躺,河中則不時有人撐著小船而過。只不過我到的那天早上,大學已放假,所以更見幽靜廣闊,我一個人享有了這難得的清晨勝景。
教堂內部,也是令人流連。首先,全部是略帶沙色的白石砌成,因此堅固而又干凈。許多條哥特式的細長石柱組成了屋子的主要支撐,它們線條挺秀,像是直沖天庭,到了高高的頂上又交拱而成花格。同這種樸素美和高騰感相對照也相襯托的則是長窗上的彩色玻璃,其鮮麗,其絢爛,簡直動人心魄。1948年我在歐洲看過更大更老的教堂,當時另有一種心情;這一次,也許因為教堂剛經整修,我似乎更能欣賞這類宗教建筑的美學效果。
就是在這個優美的環境里,我訪問了弗蘭克·寇莫特教授(Frank Kermode)。他是我來英前提出想見的學者之一。幸好他還沒有休假,所以約好今天在此會面。
寇莫特是當今英國文學研究界的重要人物,著作甚多,我國學生熟悉的兩大卷的《牛津英國文學選》就是由他和另一人主編的。他與一般文學教授有兩點不同:一是他對流行法、德、美等國的新的文藝理論有興趣,自己也做出了貢獻;二是他除了研究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也注意現代主義及其以后的當代文學流派。
在前年劍橋大學解聘柯林·麥開勃的爭論中,他站在麥開勃一邊,因為劍橋之所以不喜歡麥開勃這位青年教師,正因為他講授了新派文學理論。劍橋的傳統派根深蒂固,爭論雖引起報紙和外面世界的注意,仍然以新理論派的失敗而告終。麥開勃去了蘇格蘭的一所大學,寇莫特自己雖然從倫敦轉到劍橋不久,也不得不讓出許多人認為是劍橋文學教師的第一職位——英王講座。
我在國王學院一間書房里見到了他,一個溫文爾雅、中等身材、臉容略顯瘦削的中年人。他首先向我道歉,說英國文化委員會通知他太晚,他只能擠出現在這個時間。我告訴他我并無特別事情找他,不過由于看過他的幾本書,既有訪英機會就想來看看他。他說我們也算有點因緣,原來我的導師威爾遜教授曾經擔任寇莫特在利物浦大學做的博士論文的口試人。
“當時,他對我還不錯。”寇莫特說,“不過他說我的文章缺乏文采。”
“對,老先生很注重這一點。他希望人人都寫得像他那本《莎士比亞與新目錄學》。”
這樣就談了開去。他問我都柏林開喬伊斯討論會的情況,聽說燕卜蓀也出席了,又問起老先生的近況。我問他最近在研究什么,也問了他對當前英國文壇的看法。他認為有幾個小說家不錯,其中有寫《白色旅館》的英格蘭作家D。M。多瑪斯和寫《午夜的兒童》的印度裔作家勒熙地。(這兩本書當時正在盛銷,我在倫敦聽到過許多人稱贊它們。)
他也問到北京學校的情況。所提問題之一,是喬治·奧威爾在中國有無人讀?我說,有的,例如他那篇《政治與英語》還曾列入大學教材。奧威爾的散文寫得好,而我們中國人是喜歡好散文的。
他忽然說:“我剛才接到英國文化委員會的一封信,就在你來之前幾分鐘。他們問我愿不愿意考慮去中國講學?”
我說:“你如能去,那就太好了。你會發現北京有不少學者愿意同你討論問題的。他們也同你一樣喜歡讀書、研究、教書、寫書,一直到編英國文學的選本。”
“選本?哦,我們那本‘牛津文選’正在修訂,準備出第二版。”
“當然,我們的選本規模小些,重點也不同,例如我們會包括威廉·莫里斯的《烏有鄉消息》。”
“完全應該。是一本好書。記不得為什么我們沒有選它。”
“那么,去吧?”
他有點躊躇。“今年秋天我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明年也早有約定了。也許1984年會有時間。”最后,他說:“當然,我是想去的。北京總是有吸引力的。”
來找他的研究生已在敲門。我站了起來,同他握手告別,幾乎想加上一句:你當然清楚,北京不只是一個城市,它是一種文化,正同牛津、劍橋是一種文化一樣。
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