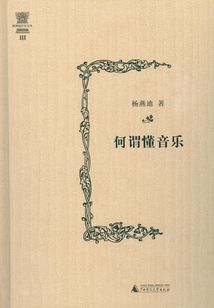
何謂懂音樂
最新章節(jié)
- 第66章 學(xué)術(shù)的生命感
- 第65章 音樂講解:個性比喻與技術(shù)觀察
- 第64章 “專業(yè)樂迷”自白錄
- 第63章 切入肌膚“鉛筆頭”
- 第62章 文匯音樂緣本文
- 第61章 春天的故事
第1章 序
近年來,我似乎一直處于“兩棲”狀態(tài):一方面從事所謂“學(xué)院派”的、“學(xué)術(shù)型”的研究和教學(xué),是為“專業(yè)”;另一方面則不斷應(yīng)約受邀為各類報刊和媒體寫作評論、散議和隨筆,屬于“業(yè)余”。按照慣例,前者一般比較“正襟危坐”,而后者應(yīng)該相對輕松和靈動。就寫作而論,這當(dāng)然是兩種相當(dāng)不同的行文感覺,所謂“兩棲”,指的即是這個意思。
筆者自忖,保持這種“專業(yè)”和“業(yè)余”同步進行的“兩棲”狀態(tài),一方面是順應(yīng)學(xué)院教師身份和社會音樂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我對自身定位的某種“有意為之”。我曾在自己的一本學(xué)術(shù)文集《音樂的人文詮釋》的后記中坦承:“音樂學(xué)和音樂學(xué)家,在中國的音樂生活和知識生活中,究竟處于何種地位,扮演何種角色,這個問題不僅困擾著當(dāng)時的自己,而且時至今日,依然還是一個不斷困擾自己的問題。”從這番話中可以看出,我近些年來念茲在茲的一個關(guān)切是,音樂學(xué)術(shù)應(yīng)該介入、參與甚至干預(yù)音樂生活。這一關(guān)切或許來源于我的音樂—文化信念:音樂雖是一種具有鮮明獨立個性的藝術(shù)語言表達方式,但它從來都沒有、也不可能在真空中運行——任何音樂都是歷史文化的產(chǎn)物,它的鳴響和運動一定承載著時代的脈搏、民族的基因、地域的風(fēng)俗、歷史的遺存和個人的創(chuàng)意。然而,在一般音樂聽眾甚至是專業(yè)音樂家的腦海里,對音樂的聆聽、接受和理解是否需要涉及上述的那些復(fù)雜的,有時是深奧的歷史文化維度?就國人的音樂意識而論,我覺得情況并不樂觀。就此而論,我認為音樂學(xué)家有責(zé)任、有義務(wù)為廣大的音樂聽眾(包括專業(yè)的音樂家)牽線搭橋——牽文化之線,搭歷史之橋,解讀音樂的文化內(nèi)涵,詮釋音樂的歷史意蘊。因此,學(xué)院派音樂學(xué)家的“專業(yè)”就其根本而言,其實與普通聽者的“業(yè)余”喜好應(yīng)該在某種程度上接軌。具體到我自己,以“專業(yè)”為倚靠的“業(yè)余”寫作也就順理成章。
那么,就普通音樂聽者和讀者而言,他(她)們?nèi)绻矏垡魳凡⒖释私庖魳罚瑥氖裁捶矫嫒胧肿顬橛行б沧顬橛腥ぃ课业目捶ㄊ牵环翉娜宋慕嵌惹腥胍魳贰K^“人文”,可以有各種各樣學(xué)理性的定義和解釋,在此暫且懸置不論。但總體說來,我以為“人文”即是與我們的“心靈”“精神”和“情感”最具關(guān)聯(lián)的那些范疇與話題——真善美,假惡丑,生老病死,愛恨情仇,喜怒哀樂……所有這些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guān)的人性課題和文化范疇,正是“人文”的要義所在,也是音樂永恒的表達母題。之所以特別強調(diào)音樂中的“人文”層面,是因為音樂本是一門高度技術(shù)化和極為感官性的藝術(shù)品種,這非常容易導(dǎo)致人們忘記和忽略音樂的人文性質(zhì)。在專業(yè)的音樂院校中,音樂往往被當(dāng)作專門化的技術(shù)訓(xùn)練,對此我們已經(jīng)非常熟悉——以至于熟視無睹;而在一般人眼中,音樂基本被等同于消遣性的放松娛樂,這當(dāng)然也無可厚非——因為音樂確乎具有這方面的功用。然而,在我看來,僅僅從技術(shù)的角度看待音樂,那是對音樂的歪曲(盡管如要真正理解音樂,沒有技術(shù)的支撐絕無可能);而僅僅從娛樂的層面感受音樂,那是對音樂的降格(盡管對音樂的感性體驗是一切音樂經(jīng)驗的基石)。僅就我個人切身的音樂體驗而論,音樂當(dāng)然從來不可能脫離技術(shù)肌理和感官直覺而存在,但音樂確乎又遠遠超越技術(shù)和感官,在最好的時候,它能以音響的方式(但并不排斥來自其他媒介包括各姊妹藝術(shù)的幫忙)呈現(xiàn)世界的真髓、表達人性的真諦。音樂之所以令人陶醉、讓人神往,其根本緣由正在于此——它與每個人的生命體驗緊密相連,并在最深刻的意義上讓聽者重新洞察世界和自己。故此,我有些偏好“音樂人文”這一概念,以至于我的博客名稱便是“音樂人文筆錄”,后來索性就以此名在《文匯報·筆會》上開了專欄……收在這三本文叢里的篇什,即是十多年來我在“專業(yè)”的研究和教學(xué)之外進行“業(yè)余”寫作的部分匯總,其中沒有收錄所謂的專業(yè)性學(xué)術(shù)論文(我的部分學(xué)術(shù)論文已收入另兩本文集——《音樂的人文詮釋》和《音樂解讀與文化批評》)。談到“專業(yè)”與“業(yè)余”之間的糾葛和關(guān)系,我倒想起巴勒斯坦裔的美國著名文化學(xué)者愛德華·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一書中曾有過非常尖銳的闡述。薩義德認為,當(dāng)今學(xué)院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挑戰(zhàn)中,首當(dāng)其沖便是“專業(yè)化”的壓力。雖然薩義德所指的“專業(yè)化”壓力與我們具體國情中的問題并非完全一回事,但他的立場和態(tài)度卻值得注意——薩義德希望用所謂的“業(yè)余性”(amateurism)來對抗學(xué)院派和學(xué)術(shù)圈中過分的“專業(yè)化”:“專業(yè)化意味著愈來愈多技術(shù)上的形式主義,以及愈來愈少的歷史意識。專業(yè)化意味著昧于建構(gòu)藝術(shù)或知識的原初努力,結(jié)果是無法把知識和藝術(shù)視為抉擇和決定、獻身和聯(lián)合,而只以冷漠的理論或方法論來看待……專業(yè)化也戕害了興奮感和發(fā)現(xiàn)感,而這兩種感受都是知識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在我看來,薩義德所抨擊的“專業(yè)化”中最致命的問題,正在于“專業(yè)化”的盛行導(dǎo)致藝術(shù)和知識中本應(yīng)有的人文性和生命感的喪失。那么,如何應(yīng)對?薩義德的策略是刻意為之的“業(yè)余性”——“所謂的業(yè)余性就是,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殺的興趣,而這些喜愛與興趣在于更遠大的景象,越過界線和障礙達成聯(lián)系,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不顧一個行業(yè)的限制而喜好眾多的觀念與價值。”
或許中國的情況和西方并不完全相同,我個人并不完全同意薩義德將“專業(yè)”和“業(yè)余”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和看法。就我所在的音樂學(xué)領(lǐng)域而言,“專業(yè)”和“業(yè)余”的統(tǒng)合,或者說,具有專業(yè)深度的“業(yè)余”和具備業(yè)余興味的“專業(yè)”,那是我理想中的愿景。就此而論,我希望自己的“業(yè)余”寫作并沒有背離“專業(yè)”的知識要求,甚至這其中有相當(dāng)成色的專業(yè)含量在。另一方面,我完全贊同薩義德的這一看法:“業(yè)余性”的關(guān)鍵在于喜愛和興趣的驅(qū)動。從事這些評論、散議和隨筆的寫作,當(dāng)然不可能是所謂研究課題的要求,也絕不屬于任何科研項目,它們的產(chǎn)生和產(chǎn)出確乎根源于我對音樂、對音樂人文性的體驗以及對文字如何表達這些體驗的喜愛和興趣。我想,既然自己不會脫離“專業(yè)”,也不會摒棄“業(yè)余”,在可預(yù)見的將來,大約還是會繼續(xù)處于“兩棲”狀態(tài)。而保持“兩棲”的動態(tài)平衡,并協(xié)調(diào)其中的關(guān)系張力,這對于我個人將會是特別的考驗,當(dāng)然也會是有趣的經(jīng)驗。
本文叢中《何謂懂音樂》一輯,所收的文論基本上均與所謂“學(xué)理”有關(guān),但行文的方式不是學(xué)術(shù)性的“論述”,而是隨筆式的“漫議”,如我對音樂審美、音樂理解、音樂創(chuàng)作、音樂表演、音樂價值判斷等問題的議論,以及對相關(guān)藝術(shù)問題甚至音樂學(xué)學(xué)科問題的思考。本來,這都是些相當(dāng)“古板”甚至“深奧”的話題,但我想試試能否用相對輕松的筆調(diào)來觸及——因為在我的想象中,這些文字的讀者是普通愛樂人。思考,以及與思考緊密相關(guān)的讀書,其實是帶有快感的,但在很多時候思考和讀書被搞得很無趣。本輯中所收錄的文章及相關(guān)書評和書序可被看作是我的某種個人努力——希望在思考和讀書過程中保持樂趣。我盡己之力,但做得如何,敬請讀者與行家批評指正。
這些文章原先大都發(fā)表在《音樂愛好者》《文匯報》《新民晚報》《讀書》等相關(guān)報刊上。承蒙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的熱心好意,編輯出版我的這套音樂文叢。在此謹表誠摯謝意!我的妻子趙小紅和女兒楊丹赫很多時候是這些文章的第一(或第二)讀者,往往在家人間常見的玩笑打趣中對我的寫作提出尖銳的修改意見。對這些意見,我有時虛心采納,有時也置之不理。但對她們多年來陪伴這些文字誕生過程中的耐心和親情,我愿表達發(fā)自內(nèi)心的真誠感謝。
楊燕迪
2013年11月于滬上書樂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