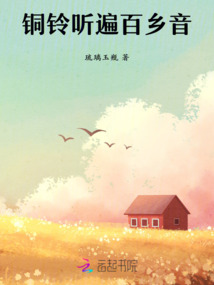
銅鈴聽遍百鄉音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騎樓底下的雜貨鋪
舊金山的晨霧總帶著股咸腥氣,像被太平洋的浪打濕的棉絮,懶洋洋地趴在都板街上。薛浩青推開“東西雜貨”的木門時,門楣上那串黃銅鈴鐺叮當作響——
鈴鐺是廣東佛山的老手藝,鑄著纏枝蓮紋,卻被前租客釘了塊英文木牌:
“BELLS FROM THE EAST”
他仰頭看了眼,伸手把歪了的木牌扶正,指尖蹭到積灰的紋路,像摸到了父親當年帶這串鈴鐺漂洋過海時,箱子里墊著的舊報紙。
“浩青仔,開門啦?”
對門“福記燒臘”的阿珍姐探出頭,手里還拎著剛出爐的燒鴨,油星子滴在她印著李小龍的圍裙上,
“今早的叉燒包剩兩個,給你留的。”
薛浩青接過來時,塑料袋在手里微微發燙。
“謝阿珍姐,”
他說著粵語,尾音卻帶著點英語的輕揚,
“昨天你說的那個美國客人,要找廣彩瓷碗裝沙拉的,我翻到個光緒年的,就是有點脫彩。”
“脫彩才夠味嘛!”
阿珍姐笑得眼角堆起褶子,
“那些鬼佬就愛這‘歲月的痕跡’,上次還有人要我用沙茶醬拌牛油果,說是什么‘fusion’。”
她轉身回店時,嗓門亮得能穿透霧靄:
“記得留著碗,中午讓我老公來拿!”
雜貨鋪里比街面暖些。
左手邊貨架擺著景德鎮的青花瓷,右邊卻是墨西哥的陶土骷髏頭,中間的玻璃柜里更雜:
民國的銅煙嘴挨著意大利的舊懷表,一本1950年的《紐約時報》墊在嶺南的端硯底下。
薛浩青把叉燒包擱在收銀臺——那收銀臺原是舊金山碼頭的老磅秤,他拆了秤盤改成臺面,邊緣還留著“1937”的刻字。
他剛用布擦完那只廣彩瓷碗,門鈴又響了。
進來的是住在隔壁街的羅西塔,墨西哥老太太裹著件印滿萬壽菊的披肩,手里攥著串佛珠,見了薛浩青就畫十字:
“親愛的浩,我女兒要結婚了,你說擺個什么能讓她像中國人一樣‘早生貴子’?”
薛浩青從貨架頂層取下個紅布包,打開是對醴陵窯的瓷娃娃,男孩手里抱著石榴,女孩捧著蓮子。
“這個,”
他切換成西班牙語,咬字比本地人還軟,
“石榴多子,蓮子諧音‘連生’,比送嬰兒床實用。”
羅西塔眼睛亮了,卻又皺起眉:
“可她未婚夫是猶太人,家里不喜歡偶像崇拜……”
“那就掛這個。”
薛浩青又抽出串紅繩編的花生掛墜,
“花生,落地生根,猶太人也喜歡多子多福,對吧?”
他想起小時候跟父親去猶太社區送貨,看到他們逾越節的餐盤里,苦菜旁邊總擺著烤花生。
羅西塔付了錢,臨走時塞給他塊杏仁糖:
“我孫兒說你們中國人過年吃杏仁糖,甜甜蜜蜜。”
糖紙是瑪利亞像,薛浩青剝開時,糖渣掉在他正在看的《申報》影印本上——那是1946年的報紙,父親的名字在招工啟事里,
“薛明遠,男,二十歲,懂粵語、英語,求碼頭雜工”。
霧散了些,陽光斜斜地照進來,在地板上投下窗格的影子。
薛浩青給自己沖了杯咖啡,用的是母親留下的意大利濃縮咖啡機,卻就著半塊叉燒包喝。父親生前總笑他“不中不西”,喝咖啡要放煉奶,吃包子要蘸番茄醬。
他那時不服氣,現在倒覺得,這味道像極了都板街的清晨——
早茶鋪子的蒸籠氣混著隔壁咖啡館的espresso香,旗袍店的銅扣碰著隔壁墨西哥餐廳的彩陶罐,叮當聲里,誰也沒覺得誰礙眼。
“叮鈴——”
鈴鐺又響了。這次進來的是個穿西裝的白人老頭,頭發梳得一絲不茍,手里捏著張泛黃的照片。
“請問,”
他的中文帶著濃重的倫敦腔,
“你認識照片上的人嗎?”
照片是黑白的,背景是雜貨鋪現在的門面,只是招牌上寫著“薛記南北行”。
穿長衫的年輕人站在門口,手里捧著個青花瓷瓶,笑得露出兩顆虎牙。薛浩青的心跳漏了半拍——
那是父親二十八歲的樣子,他在相冊里見過。
“他是我父親。”
薛浩青指著照片,
“1953年,他在這里開了家賣藥材和絲綢的店。”
老頭眼睛瞪圓了,從公文包里掏出個同樣的青花瓷瓶:
“這個!他當年賣給我祖父的,說是明代的,后來被博物館鑒定為……”
他頓了頓,似乎在找合適的詞,“‘非常精致的仿品’。”
薛浩青接過瓷瓶,指尖摸到瓶底的款識——“大明宣德年制”,但筆觸比真品飄了些。這是父親的手筆,他年輕時學過仿古瓷,來美國后靠這個貼補過家用。
“我父親后來再也沒賣過仿品,”
薛浩青輕聲說,
“他說,騙洋人一次,一輩子抬不起頭。”
老頭突然笑了:
“我祖父知道是仿品。他說,一個中國年輕人在異鄉,用祖傳的手藝換口飯吃,比真古董更有價值。”
他從錢包里抽出張支票,
“我想把這個捐給唐人街博物館,旁邊擺上這張照片,可以嗎?”
薛浩青看著他走出店門,背影融進街上的人流——
穿唐裝的老人提著鳥籠,戴頭巾的印度女人推著賣拉西的小車,穿滑板鞋的少年舉著奶茶,T恤上印著“孔子曰”和英文翻譯。
銅鈴又響了,這次是三個穿校服的孩子,背著印著“舊金山中文學校”的書包,吵吵嚷嚷要買辣條和泡泡糖。
“浩青哥,”
扎馬尾的女孩舉著本練習冊,
“‘鄉音無改鬢毛衰’是什么意思?老師說衰是cuī,不是shuāi。”
薛浩青想起父親臨終前,用含糊的粵語念這句詩,眼淚打濕了枕巾。
他拿起筆,在練習冊上畫了個鈴鐺:
“就像這銅鈴,不管在佛山還是舊金山,響起來都是叮鈴叮鈴,可聽的人心里,想的是不同的地方。”
孩子們似懂非懂地跑了,辣條的香味留在空氣里,混著咖啡香和遠處飄來的檀香。
薛浩青走到窗邊,看著街對面的關帝廟,香爐里的煙打著旋兒往上飄,與隔壁教堂的尖頂擦肩而過。
父親常說,這里的神佛都很忙,要管廣東人的生意,要護墨西哥人的平安,還要聽猶太人的禱告。
他低頭看了眼手機,是妹妹發來的視頻請求。
屏幕里,十歲的外甥女舉著幅畫:
“舅舅你看,我畫的都板街!有龍,有仙人掌,還有圣誕老人騎熊貓!”
薛浩青笑了,眼角有點發潮。他拿起那串銅鈴,輕輕晃了晃。
鈴聲穿過玻璃,落在騎樓下的石板路上,和早茶鋪子的吆喝、咖啡館的爵士樂、孩子們的笑鬧纏在一起,像條看不見的線,把東和西、舊和新、鄉愁和生計,都織進了舊金山的陽光里。
門又開了,鈴鐺聲混進個熟悉的嗓音:
“浩青,你要的陳皮到了,這次是江門新會的,比上次的甜些。”
是街角“藥材行”的林伯,手里拎著個牛皮紙包。
“謝林伯,”
薛浩青接過紙包,陳皮的清香漫出來,
“中午來吃叉燒飯,阿珍姐剛送了燒鴨。”
“又蹭飯?”
林伯笑罵著,眼睛卻掃過玻璃柜里的舊報紙,
“你爸當年啊,就是靠這陳皮,在碼頭換了個落腳點……”
薛浩青沒說話,只是拿起那只廣彩瓷碗,對著陽光看。
碗身上的纏枝蓮紋里,藏著點淡淡的鈷料痕跡——
那是父親后來補畫的,像給歲月的缺口,添了筆溫柔的補丁。
銅鈴在風里輕輕響著,像是在說,所有的異鄉,住久了,都會長出故鄉的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