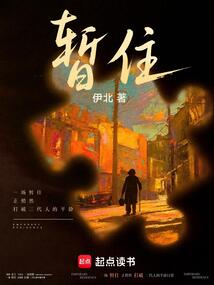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團圓居(一)
有福之人,不落無福之地。(《禪真后史》第十五回)
——代題記
來北京多少年了,姚婭思一直都非常強調自己的“地方特色”。事實上,在搬進大平層之前,他們家每個月都要吃一次臘肉,必須煙熏的那種,盡管婭思也下不了幾筷子,可只要一個臘肉,一個水芹菜擺上桌,那種故鄉的感覺就出來了。
婭思還喜歡喝那種鹽漬的菊花,以及不知名的野葉子,她說可以消炎,但許燕杰從來不信,并從科學和玄學兩角度駁斥她。
姚婭思依舊我行我素。
她對故鄉的吃食如數家珍,對老家的景點同樣竭力推薦,她家里還常備幾盆桂花,金桂、銀桂、丹桂、四季桂都有,雖說總是死了栽、栽了死,可她樂此不疲,因為老家的院子里曾經有那么兩棵,四季飄香。北京戶外種不了桂花樹,那就挪到室內,聊解思鄉之情。
總之,誰要敢說她老家不好,婭思一定第一個站出來反駁。
這些年,她還隨身帶著老家的幾件老家具,一件是床頭柜,她親爹親媽結婚時候打的,還有件書法作品,據說她們姚家老祖宗——可以追溯到清代了,手書的,三個大字:團圓居。裱好了,配上框,掛在玄關處。說是能辟邪。
最后就是太奶奶出嫁穿的刺繡衣裳,上面繡了個鳳凰。也是古董。婭思不時拿出來披著,不顧燕杰和楚楚大喊“詐尸”,堂而皇之在家里走來走去,她斥責兩位家庭成員不懂傳統,“你從哪來呀?沒有厚度,就立不住!”
她是要在北京立足的。
但有一次,女兒楚楚的一句話卻刺痛了婭思。女兒的口氣還挺不耐煩,“媽你別老把自己當鳳凰行嗎?全是瞎想,其實你就是個麻雀。”
于是那天,姚婭思發了好大火,末了,楚楚的爹,——許燕杰先生賠了個金鐲子她才善罷甘休。但冷靜下來想,姚婭思也不能否認女兒言論的正確性:是,他們本就是麻雀,只是借了羽毛。——學歷、職業、婚姻,都是他們的外衣,他們偽裝成鳳凰,闖入這個都市。可是,誰規定麻雀不能變鳳凰呢。只要勤加修煉,也會有出頭天。
雞窩里還能飛出金鳳凰呢。她要鳳凰頭上戴牡丹,好上加好。(反之,鳳凰也能降級,老話都說了,落毛的鳳凰不如雞)。
但她這個鳳凰要有特點。那么,老家的一切,就是她別具特色的羽毛。當然,這都是美好期盼,冷靜下來想,婭思認可燕杰的說法,他們既不至于成鳳凰,也不至于是麻雀,他們更像這城市里常見的灰喜鵲,用灰色的羽翼,調和著夢想的金色和現實的土色。
灰喜鵲體型中等,適應力強,能折騰,什么都吃,群居但獨立,叫叫嚷嚷。它們可不是沉默的族群。最重要的是,它們的灰色的,中間還夾著點藍和白,不搶眼,但耐看。盡管婭思談不上喜歡這種動物,可是也不得不承認燕杰的總結很精準。
灰喜鵲是留鳥,——一門心思留在這兒啦!婭思、燕杰跟它們一樣,都是要在北京扎根的。但正因為此,姚女士才對故鄉更加思念,這是一種姿態。
姚女士對故鄉,是濃濃一片愛,拳拳一片心,她差點沒成故鄉的代言人,雖然除了過年,她并不怎么回老家。
實際上,從高中畢業之后出來上學,然后一直讀到碩士,然后畢業,轉瞬也十多年了。她所熟悉的老家,還是大概二十年前的樣子,不過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距離,有了一種想象,老家在她眼里,似乎也蒙上了一層濾鏡,溫溫柔柔的、親親切切的,日常生活的血肉被剝離掉,剩下一下干枯的符號,仿佛木乃伊展覽。
這些符號對她特別重要,越是人在他鄉,就越需要這些符號。作為南嶺人,她的這些衣食住行,甚至方言,都作為一種屏障,一種反向的優越感,一下把她跟周圍的“庸脂俗粉”區別開來。她如此獨特,儼然北京地區的南嶺代言人,風風火火、轟轟烈烈。在這個賽博的年代,她堅信,地方的就是世界,越是本土,越是稀缺,越是好。
當然,這些年,婭思出門在外,單打獨斗,壓力還是很大的,但好在她自認是個幸運兒。
她的生活中有很多“一不小心”,都有點運氣的成分。運去黃金失色,時來鐵也生光。她就屬于那種平時不怎么起眼,十個人里頭能排個四五六,但一到關鍵時刻,卻鐵定能沖到一二三。她高考就“一不小心”發揮超常,考了個全校文科第三,報志愿也不含糊,她敢沖,撐死膽大餓死膽小,結果還真成了。
糊里糊涂歡天喜地來到北京,然后,一馬平川勇往直前,本科畢業后保送了本校讀碩士,這么一竿子撐到現在。順風順水。
既然讀了研,姚婭思的好勝心也漸熾了,必須留北京。本碩都是金融,雖沒有留學經歷,但婭思還是拼命擠進了一家國資銀行,先從柜臺做起,后來做到小組長,她覺得沒啥前途,又專做理財經理,做客戶。野蠻生長。說實話,在行里,婭思始終覺得自己跟孫悟空遇到銀角大王似的,身上背著一座山。一方面是業務上有壓力,要吸納存款,上面給指標,都是硬杠杠,她剛開始客戶有限。不像周圍那些有家世背景的留學回來的,盡管有的她看不上,覺得不學無術,可一到季度或者年終核算,人家找叔叔啊阿姨啊幫幫忙,窟窿一下就填上了。
她就沒這種幸運了。她的這些客戶,很多都是一個一個電話打下來的,一場一場見面維護下來的,是真心換真心,四兩換半斤,求爹爹告奶奶,沒一點水分。
就因為婭思那么“吭哧吭哧”,有些同事也看她不起,人家是洋的,她是土的,婭思被襯得沒辦法,索性橫下心來用了個“以毒攻毒,以土攻土”的法子,強調“地方特色”,強調唯一性。于是乎,老家南嶺則成了一種異域的訴說。還別說,有了這碗文化的酒打底,婭思的氣更足了,也能跟那些趾高氣昂的同事分庭抗禮了。
婭思也爭氣,在轉型當經理的日子里,她找到了許燕杰。北方人,農村出身,985高校畢業,一出來就在創業公司硬拼,從程序員做起,到管理崗,她認識他的時候,人家工資是她的兩倍。最關鍵是,燕杰作為高科技企業的人才,后發先至,拿下了戶口。這點就比她強。這是姚婭思進入銀行之后最大的痛,那些海外留學回來的,一來就能憑政策在北京落戶,不占公司的指標,她不行,一直沒解決,得等。
那些洋味兒婭思覺得沒什么,回都回來了,終究得落地,洋的最終還是變成土的,可戶口是實打實的呀!
婭思的婚事一直沒落定,戶口也是個重大因素。她沒戶口,那就得找個有戶口的。當初,婭思告訴自己:你得做個負責任的媽媽,不能讓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沒處落腳,不能堂堂正正站在這北京城。現在,她一激動起來,也容易跟女兒楚楚“苦口婆心”,——“知道媽媽當初為了你付出了什么嗎?要不是為你,我早就……”“早就什么?嫁入豪門?媽你能不能醒醒?”楚楚成大姑娘了,壓根兒不贊同這種敘述。
退一步講,燕杰也確實優秀,兩只眼睛離得近,透著機靈,腦門大大的,鼻梁高高的,雖然嘴巴有點小,但配著一個寬下巴,十足堅毅,一瞧就是晚運不錯。學歷沒話說,工作也好,人也踏實穩重,這些都是優勢。
婭思對許燕杰深入考察了,也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劣勢。比如,出身農村,是典型的鳳凰男。但有意思的是,他這么個農村娃,卻有機會去國外交流了一年。是真正的兼容并蓄,土洋結合。
許燕杰堅稱,在國外的生活費,都是自己在網上掙的(具體路子不詳),他號稱大學二年級之后就沒再問家里要過錢,他擺過地攤,開過小店,摸爬滾打,什么都干過,出道特別早,屬實的萬水千山走遍,苦盡了甘才來。他老家上頭有姐姐、哥哥,他是老三,后頭還有個妹妹。他娘走得早,他還有個老爹需贍養。不過談戀愛的時候,燕杰就跟阿月說了“你放心”。他說他爸將來不會來北京,哥哥姐姐管著老人,他就給點錢,還三令五申跟婭思“約法三章”:“咱倆在一起,那就是咱倆的事,別人老家那些人都摻合進來,到時候,你媽的事,你管,我也管,我爸這邊的事兒,我自己能弄明白了。”
聽著燕杰這么一說,婭思心里舒坦。雖然說是一回事兒,做又是另一回事兒,可這年頭,能把話擺在桌面上不易。放眼瞧瞧,別說不孝順的,就是孝順的,又能怎么顧老人呀!孩子們自己都顧頭不顧腚了。
燕杰這么說,也是因為婭思有個弟弟不大爭氣。他只能給婭思打氣。其實,連婭思的親媽胡愛茹女士都弄不清這倆孩子到底誰先來到這世上的。龍鳳胎,囫圇個,爭先恐后,泥石流似的誕生了。
針對這個世紀難題,姚婭思還專門回老家問過婦產醫院的老護士。老護士追憶似水年華,恍恍惚惚表示,當年,姚婭思是頭先出來的,姚議是腳先出來的,至于誰先落地,是不相上下,但根據眼見為實的原則,應該是婭思先面對這個世界,所以她當了姐姐。
哼!她姚婭思才懶得當這個姐姐呢!就因為快了那幾分鐘,一下就“長姐如母”,從小到大,她擔待了姚議多少呀!孔融讓梨那是家常便飯!婭思從小爭氣,處處要強,姚議就有點往下禿嚕了。同一個時辰出生,命數大不同。這事胡愛茹也找人看過,說是究竟是姚婭思大頭先落地,占了地利,福氣厚些。
確實,就讀書這事,婭思長驅直入,一直讀到碩士畢業沒打磕巴,姚議就沒這運道了。他在老家省城讀了個末流本科的美術專業,又四處晃蕩了一圈,怎么都不行,最后,索性要闖北京城,奔姐姐來。婭思一頭紫疙瘩。可終究是親的,人來了,少不得關照,少不得補貼,少不得操心。
在婭思眼里,弟弟一直就沒入流。最關鍵一點,屁股坐不住,毛躁,一會兒要開公司,一會兒上班,一會這個行業,一會兒那個買賣,弄砸好幾個項目,文化搞過,又要搞餐飲,實在不踏實、不務實。人過三十不學藝,都這個年紀了,還轉什么行!更何況,你姚議已經是有家的人了!他跟本科同學程娜一起來的北京,兩家湊錢,在燕郊弄了套小房,小兩口也算有落腳的地了。那就好好過日子,好好賺錢,別瞎折騰!不過,婭思也瞧不上程娜,這丫頭,看著老實,但透著固執,還死要面子、放不下身子,在她姚某人面前,都端著拿著,燕郊那房子,婭思攏共去過兩回,她實在懶得看弟妹那臉。還有,兩個人結婚后一直沒要上孩子,這也是婭思犯嘀咕的。究竟是不能生,還是不想生,她沒問過姚議。算了,兩個人都沒定性,現在要孩子也是麻煩,順其自然的好。
說到底,弟弟是親弟弟。她能批評,別人說,她就得護了。因此,每當許燕杰當面鑼對面鼓地找事兒,姚婭思立馬跟個母獅似的。呵呵,得有娘家人,姚議關鍵時刻還是跟她站在一起。不過最近,女兒楚楚卻被燕杰統戰過去了。許燕杰不說自己家里好,也不說姚婭思家里好,他就獨立。嶄新的獨立的中產家庭。
許燕杰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這年頭,誰是靠幫起來的,不都是自己努力嗎?家里幫過我們什么?我們欠誰的?誰也不欠!”這話說得盡管有些激烈,可從事實出發,婭思也不得不贊同。她父母原是化工廠的雙職工,她父親去世后,母親胡愛茹又找了個老干部牛叔。這些年,母親有自己的小家,逢年過節姚婭思和姚議回去的也少。
在母親再婚的問題上,姚家姐弟都有點保留意見,倒不是反對再婚本身,而是他們覺得,那個再婚對象,實在不怎么樣。廠里的老干部,頭多少年地里離休了,特別古板,跟不上時代,而且他的錢,也都被前面的老婆生的孩子攥著,胡愛茹只有個菜錢。干嗎伺候這老頭子!
但時間久了,婭思大抵明白了,老媽跟牛叔在一塊,一方面的確談得來,另一方面,牛叔也給她提供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氛圍,那種集體的,熱火朝天,工業大發展的時代的遺存。胡愛茹是從農村上來轉工人的,她一直以自己產業工人的身份驕傲。哪怕她只開過幾個月的航車,但只要在廠里,那就是個小樂園。
頭五六年地里,廠子徹底倒閉了。產業轉型,被收購了,這些污染嚴重的企業都遷往別處,原本氣派的廠房被夷為平地,婭思知道,那一天,胡大姐流了一夜的淚。打那時候起,姚婭思忽然開始祈禱牛叔長命百歲了。無它,牛叔活一天,胡大姐的小環境就存在一天。就這么一生一世也挺好。
然而事與愿違,老頭說病就病,說走就走了。婭思給聯系北京的醫院,花了不少錢,盡了做繼女最后的孝心。老頭臨了還擺了他們一道,房子沒留給胡大姐,錢早轉移了。胡愛茹大夢初醒,嚎啕大哭,但門一打開,又一臉堅毅,婭思看到如此狀態的老媽都害怕——真怕她一個想不開,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牛叔走了,胡愛茹原本就搖搖欲墜的世界,終于坍塌。她一輩子在工廠大院生活,現在,也該搬出來了。他們倒是不缺房子,老宅還有,過去一直姚議住著,胡愛茹搬回去即可。但心情卻沒辦法迅速調整。
端午回去,婭思一瞧老媽那狀態,兩個字,堪憂。現在馬上中秋,婭思跟燕杰商量著,打算把胡女士接到北京來,調整調整狀態,她也盡盡做女兒的孝心。
姚婭思跟許燕杰說這話的時候姿態是比較低的,很小心,很客氣,說“算暫住,看看情況”。結果燕杰卻大氣得很,直接說:“瞧你,這事哪用跟我商量,反正家里夠住,隨時都可以來呀!我本來也想問安排媽事呢,咱倆想一塊去了。”
姚婭思不曉得丈夫這話多少真心多少表演,但說實在的,又不是自己皮里的,頂多算半個兒,大面上能說出這話,夠可以了。而且時機也對,許燕杰最近心情不錯,他們剛拿下這三房一廳,還是個學區。讓胡大姐來,也是女婿展現實力的好機會,讓胡大姐也過過現代化的體面生活。
婭思還知道,燕杰一直憋著股氣呢。芥蒂出現在他們決定結婚,兩家大人碰面的時候。燕杰他媽走得早,燕杰他爸許天材又是北方農村大爺那種風格和見識,一張忽晴忽陰的臉,一口吸煙熏黑的牙,來了就拎個自家產的大南瓜,滿口土豆疙瘩式的語言風格,跟工廠大院來的胡大姐一比,著實太過接地氣了點。胡大姐半笑著問天材家里的情況,一年種多少地,收多少玉米,南瓜都這么大個兒?吃不吃得上豬肉?……外人聽著平平常常,可許燕杰不喜歡胡愛茹那種吊著的口氣。
調侃的,戲謔的,嘲弄的,那居高臨下的架勢,把他襯成劉姥姥了。
燕杰特別敏感,從小到大,他最抗拒的就是被人看不起。為胡大姐這態度,他跟婭思抗議過。婭思勸他:“反正兩家也不怎么能碰上面,菜瓜打鑼,就這一槌子。你別往心里去。”說著,眼一乜斜,半笑不笑地,“你爸什么樣你自己不也清楚么?”停了停,再說,“你自己不也往外摘么?”
現在,給老許家爭臉的時候來了。許燕杰下定決心要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現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