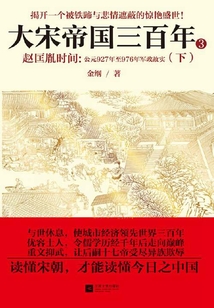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50章 附錄
- 第49章 斯人已逝,“誓碑”永恒(5)
- 第48章 斯人已逝,“誓碑”永恒(4)
- 第47章 斯人已逝,“誓碑”永恒(3)
- 第46章 斯人已逝,“誓碑”永恒(2)
- 第45章 斯人已逝,“誓碑”永恒(1)
第1章 偃武修文(1)
大宋立國伊始,老趙從地方收回司法權,制定《宋刑統》,提出著名的刑律方針: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除文明立法之外,他還巡視國子監,重視儒學,師法古圣,身體力行,教化天下,并對科舉進行了政策性調整,確保公平取士。國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軌。
“微行”遇冷箭
陳橋事件后,慕容延釗抵御北漢契丹來侵,前鋒已經駐屯真定(今河北正定)。太祖受禪后,當即派遣使者給慕容將軍帶去詔書,許以“便宜從事”,允許他根據前方形勢自行裁斷。慕容延釗于是巡視河北邊境,嚴加防范。北漢、契丹逡巡歸逡巡,覬覦歸覬覦,但聞聽慕容延釗大軍在前,未敢輕舉妄動。
不久,老趙等到了慕容延釗方面的來報,史稱來報的內容是:“契丹與北漢兵皆遁去。”他們聞聽老趙登基,已經不是后周幼主的天下,入侵中原之意頓消,再南下,已經沒有勝算,所以只好撤兵--或遁去。大宋新政初建,賴慕容將軍而安定了北境。慕容延釗被宋太祖授為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
公元960年2月,農歷正月,初春的日子,趙匡胤住進了原后周的禁宮。老趙幾乎來不及享用種種“帝王之樂”。他依舊過著那種簡易的日子。
心里想的卻是天下大事。老趙喜歡“微行”,以便于“陰察群情向背”。他大約想起了古來帝王“微服私訪”的故事,于是也常常“微行”。但這類行動給保衛工作帶來難度,于是有人勸諫他注意安全,帝王嘛,深居簡出為要。但老趙聽后大笑說: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過去周世宗見諸將長得方面大耳,有帝王之相者就借故殺之,我老趙終日侍奉在世宗左右,他也不能害我啦!沒關系,誰有這個帝王命格,任他自為就是,我老趙不禁!”
從此“微行”更加頻繁。但是“微行”雖然沒有遇到麻煩,第一次公開出行卻遭遇了襲擊。宋人朱弁《曲洧舊聞》,說太祖即位后,車駕初出,過一橋,忽然有飛矢來射黃傘。禁衛一時驚駭,老趙卻干脆敞開袍子,笑著說:
“教他射!教他射!”回到宮內后,左右力請捕賊,老趙不允,久之,亦無事。老趙此舉,很像大帝柴榮。當年,老趙跟從柴榮征淮南,克壽州城時,曾經親眼看到柴榮的鎮定。時壽州守將劉仁贍猿臂善射,發無不中。周世宗坐帳幄中觀戰士攻城,劉仁瞻覷見黃羅傘蓋旁的帳內有人,忖度就是柴榮,于是,從城上搭弓射之。說那箭鏃在御座前數尺就會降落。左右驚愕,都來諫請世宗避一避。柴榮說:
“要是一箭就射殺一個天子,天下還有天子嗎?嘁!”柴榮不但不避,還命左右將御座抬到剛才箭落處,等著繼續來箭。劉仁贍的箭又到了,結果又在幾步遠之外落地。這箭,傷不到周世宗。劉仁瞻知道后,將弓箭放下不再狙擊。他對左右說:“這是天意啊!不是我不能射中他!但吾世受國恩,兄弟之中行伍多人,如果不能治危捍敵,寧靜邊境,給君父帶來憂患,吾甚恥之!現在雖病但猶能奮力執戈,與諸君背城血戰,死于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以事二姓!”
這一段記載見于宋人龍袞《江南野史》。龍袞評論此事道:“以周世宗之神武確斷,當矢石而不懼。予觀自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這個評論不確,因為趙匡胤也是這樣的人。
老趙是真的相信天命在茲。他遇到敵對勢力放冷箭,卻沒有追緝刺客,確實了不起。想想如秦始皇博浪沙遭遇刺客,沒有搜索到刺客,竟然掃滅周圍多少平方公里的人煙,就知道老趙與嬴政不是一類人。所以我有一個說法:
同為皇權制度下的帝王,與同為民主制度下的總統一樣,良莠不齊;說帝王皆是混蛋,就跟說總統都是圣人一樣糊涂。人的豐富性決定了人的多樣性。以職業之不同而界定人性之不同,必生謬見。
老趙不追究暗殺團伙,不問何故何因,此即靜穆簡易。船山《宋論》,最為欣賞的就是老趙的行事簡易之風。蓋天下初定,特別需要休養生息,而“民之恃上以休養者,慈也、儉也、簡也;三者于道貴矣,而刻意以為之者,其美不終”。為君王能堅持“慈、儉、簡”三字,實為天下福音,但又不必刻意為之。在船山先生看來,漢代文景之治,兩代君王稱得起“慈、儉、簡”三字,但行事未免刻意,趙匡胤則全出于自心。船山先生認為宋太祖趙匡胤完全當得孔夫子“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之境。我贊同此議。
老趙有時會在后苑彈雀。有一次,臣下稱有急事請見。老趙趕緊扔下彈弓子來見臣下,但一看這位所奏不過是一個很平常的小事。于是大為光火,厲聲質問。這位失名的臣下(行事風格很像趙普)對曰:
“臣以為所奏之事再不急,也比在后花園彈雀子急!”老趙聞言更來火兒了,舉起身邊的斧鉞就撞擊臣下的嘴巴,結果撞下倆門牙來。這位臣下慢慢蹲下,將牙齒拾起來放入懷內。老趙氣未消,罵道:
“你這家伙藏那倆牙,是準備起訴我做呈堂證據嗎?嗯?”臣下對曰:“臣不能起訴陛下,但是自當有史官書之。”
老趙聽到這話,居然一下子就--覺悟了,連忙賜給他金帛慰勞。事實上,他是懼怕歷史。中國史,具有“類宗教”性質,讓人在作惡之前對身后之名有所忌憚。越是位尊德高之人越是懼怕歷史。位高而無德之輩,不信頭頂三尺有神明之輩,不怕歷史--他們什么也不怕。這個“彈雀”的故實,是可以考見趙匡胤內心“敬畏”的有趣案例。他不是一個“無所畏懼”的人。他內心有神明,可以從他每年都要做郊祀、祭太廟,敬告天地祖宗的事實得到證明;他終生敬天道,可以從他的自信坦蕩以及戒懼惕勵而行事的風格得到證明;他信奉儒學之春秋筆法,對歷史書寫有虔誠的敬畏,可以從“彈雀”故實得到證明。
一般來說,人在宇宙中的處境,省略了神恩、天道以及歷史感之后,就會成為一個徹底的無所畏懼者。但這種“無所畏懼”恰恰又是最為孤寂恐懼的。因為他的精神世界將為絕對的無助所支配,他的經驗想象世界徹底無援--神恩不來眷顧、天道不來垂注、歷史也與他絕緣,他將在“死了拉倒”的酸心硬語中孤零地走入虛無。虛無,給他隱秘、深邃的顫栗與恐懼。這是俗世的瘋狂、冷漠與麻木最實在的哲學背景。而內心有所敬畏的人,不會體驗虛無,因此他的精神世界豐富而又實在,在無限的想象中體驗絕對的超自然力量,不會顫栗、不會恐懼,因為他知道:他與神恩、與天道、與青史,同在。順便說一句:儒學,在引導帝王建構價值觀的方向上,很大程度是在培育他們內心--有所敬畏。
老趙有孩子氣,有軍閥氣,更有圣賢氣。知錯即改,看似容易,卻難于做到;特別是當場認錯。有錯不算錯,不改才是錯。所以《論語》中,孔子要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宋代大儒要說:“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二程粹言》)這種坦蕩,就是一種“剛”且“明”的圣賢氣象。只有內心保有敬畏的人,才可能自我培育起這種道德成果。我以此衡老趙,老趙當得。
老趙的“三條寶帶”
建國伊始,老趙率先做了三件事:從漕運和賑災開始解決民生問題;從政策改進開始解決偃武修文問題;從禮葬韓通開始解決士大夫道義問題。
東京汴梁是當時一大消費城市。帝室、百官、士庶、軍馬所需,大多仰仗于漕運。四方流往汴梁的各類物資,匡算下來,僅僅幾十萬士卒,每天就需要幾十萬斤口糧。史稱“歲漕百余萬石”,假定是一百六十萬石,就有近十萬噸的規模,每天必須有兩百噸糧食從外地運來。這還不算近百萬市民所需。而這些南方的糧食北上,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水運。所以河渠通暢,多年來都是執政至為關心的問題。老趙上臺伊始,往汴梁的幾條河道,因為戰爭,已經連年淤積,更需要浚治。就在第一次御前會議上,老趙提出了漕運問題的解決方案。
老趙之前,歷朝歷代,調集丁夫開挖河道,所有糗糧皆由河工自備。老趙認為此類歷史性盤剝過于苛刻。于是下詔,從此河工食用“悉從官給”,都由官方供應,且“著為令”,并且從此以后,成為一種制度性安排。
帝國的文明之象開始了點點滴滴的推演。當時的漕運,有汴河、惠民河、廣濟河、黃河四水,史稱“漕運四河”。
但黃河治理是另外的故事,實際上歷代所著力的是其他三條河。汴河,也稱“通濟渠”。隋煬帝時已經開挖,屬于大運河的一段,自洛陽西苑引兩條天然河水入黃河,再入汴水。然后循春秋時吳國開挖運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到淮水。主干在汴水,人工開挖,故也稱汴渠。
惠民河,在開封西南,大宋開挖的運河。廣濟河,是接收山東濰坊一帶收取租賦的漕運河道。先經由清河(也稱濟水)起運,跨黃河,過幾個州郡,進入廣濟河,由廣濟到達汴梁。這河,后周時已經開始治理,大宋繼續,先后引汴水、金水注入廣濟,與黃河勾連。河在開封城東,西流,經過今天的河南蘭考,到山東,注入梁山泊,下接濟水。因為河道拓寬至五丈,故又稱“五丈河”。工程不小,后周、大宋兩代人的時間都在“五丈河”上付出了汗水。
諸河都有淤淺的時候,尤以五丈河最為嚴重。于是老趙借春初的農閑季節,調集河工,大興力役,史稱開浚之后,“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才開始舟船通行便利,沒有了阻塞擁擠的現象。為了修治五丈河,老趙還常常要到治河現場去“督課”,親臨現場監督考核。最初,這些河工們是沒有口糧的,老趙看著一個個黑紅的脊梁在河道上起伏挖掘、穿梭來往,有了惻隱之心(史稱“上惻其勞苦”),特別下詔:每人每天給米二升,并命令天下各地的役夫,都要照此辦理。這個辦法一直貫徹大宋帝國始末。史稱“遂為永式”,于是成為永遠的規則制度。
修浚河道,解決了大汴梁城的日常用度問題,老趙也有得意的時刻。有一次,吳越國的國王錢俶入朝,向老趙進貢了一條“寶犀帶”,也許是由犀牛皮制作,嵌滿了珠寶的腰帶,老趙看過后,回過頭來對錢俶說:“我有三條寶帶,與你給我的這個不一樣。”錢俶很自信,認為“寶犀帶”乃是吳越國良工精心打造,世間罕有,于是請求老趙拿出那“三條寶帶”來開開眼。老趙笑道:
“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錢俶聽后,頓時明白了帝王之道在民生不在享用的大道理,不禁大為愧服。由此可見宋太祖趙匡胤的格局,遠不是錢俶這樣的國君可以達到的。
老趙踐祚的前一年,河北谷物豐收,導致谷賤傷農;老趙登基伊始,即下令“高其價以糴之”,高價收買農民手中的糧食,以此保障農民利益。
但中原諸道,有地方豐收,有地方絕收。老趙知道后,又派出使者到各地分賑鬧糧荒的州郡。
這是由政府介入而解決民用、戰備糧的儲備問題,是傳統中國的荒政(荒年政制)、良政之一。戰國時代的魏國、漢代初年,皆有此類設計,古稱“常平倉”。方法是:某地糧價低時,由政府適當提價收購;某地糧價高時,由政府適當降價出售。這類“金融政策”,既避免了谷賤傷農,也避免了谷貴傷農,應該是調節糧價、平抑市場、儲糧備荒以供官需民食的一項優良國策。
但這類工作操作起來有難度,故歷史上考察,并不經常施行。大宋帝國在太宗趙光義時代,完善了這個“常平倉”制度。大宋帝國的文明力量就在于:只要是利國利民之舉,幾代人都會為之努力,萬難不避。
元代佚名撰《宋史全文》引呂中議論老趙開倉放糧事,大意說:太祖甲辰即位,第二天乙卯日,即遣使往諸州賑貸。豈有得天下之初,要用這個來沽名釣譽的事嗎?上天惠民,應該遵從天命。當時之民,苦于干戈、賦斂、刑役很久了。為人父母,見子弟之饑寒,則萬難不避也要救助。太祖趙匡胤此舉,與周武王下車之后,就散財發粟給饑民,那種圣賢的仁愛之心,是一樣的。
我認為這不是溢美之詞。老趙賑災是常事。
翻看《續資治通鑒長編》就會發現,觸目皆是“賑災”“免租”的故實。我據該書統計,太祖一朝十七年,“賑”字出現二十四次,“蠲”字出現三十二次。“賑”是國家放糧給百姓;“蠲”是國家免收百姓租賦。這樣放糧、免收,國家自然就會減少收入,但這樣自動減少收入,實實在在給百姓利益的國家調控,每年要做三次以上。我在閱讀歷史記錄中,還沒有發現哪個朝代曾經有過這樣令人感動的民生政策。
乾德二年,更有一道詔書給地方長吏言:如果地方有災情,“即蠲其租,勿俟報”。如果遇到災害,正趕上收租,就要馬上蠲免,不必等到上報后批準。
這一德業,三皇五帝以來,不曾見有。尤為令人欽敬的是,這類德業,只在歷史記錄中夾帶提過,不僅帝王不再自我吹噓,大臣文人們也不做恭維逢迎之語,似乎:這事就應該這樣做!
大宋帝國“做好事”一向如此--從不做自我旌表。
盤剝尋租的惡性
官方的制造業場所稱為“場院”,地方的“場院”,除了由所在地直接調用租賦維持“場院”工作外,還由朝廷撥給糧草支持“場院”工作。等于“國稅”“地稅”都有一部分流入“場院”。“場院”工人多為軍人,屬于半軍方機構。但朝廷負責鹽鐵、戶部、度支的財務官三司使,下達的文件中又有規定:撥出的經費如果有“羨入”(盈余),可以上報朝廷,朝廷將據此而給“場務”官提成。這個法子五代以來一直如此施行。
宋初,有個地方官名叫張全操,他反對這個做法。他認為這樣將會助長“場務”官從中漁利。乾德四年,他給皇上上書說這個事。趙匡胤馬上下詔:
孔子有言:“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如果在規定之外還有盈余,這一定是對下屬的克扣所致。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余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這么多盈余,如果不是多倍收納民租,私減軍食,如何可以得到?要追問此事,不要頒行三司的做法。以后,除了官方規定的消耗數額之外,一切嚴加禁止!
“羨余”也即“盈余”,這個事,值得一說。這是歷來對地方官考核的指標之一。官方要組織國家力量經營各類制作,就要有預算。一般的預算都會做得比較公允,年底核算,一般都差不多用光。但場務官有時在組織地方租賦時,往往會“超指標”榨取,這樣就有了所謂的“羨余”。而朝廷鼓勵“羨余”并愿意從“羨余”中拿出一部分獎勵場務官時,場務官榨取百姓租賦就有了“動力”。朝廷如果不知道這個局面,那就是無能;如果知道,不來終止,那就是無道。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明知此事也睜一眼閉一眼。無論無能抑或無道,納稅人都要承擔這個被剝削的惡果。
史上對唐德宗時的“羨余”惡政記錄頗詳。大意說:德宗時國用不足,因此有專門聚斂的心思。地方藩鎮知道德宗的心思,就向朝廷進奉“稅外方圓”“用度羨余”來買好。其實,這個“稅外”的“方圓”
(就是孔方兄啦),以及“用度”的“羨余”,有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扣留“常賦”,假設:朝廷撥給一萬,他留三千;地方收取一萬,他報七千。這樣里外里,就有了六千的“方圓”或“羨余”。第二個部分是“增斂”,這一塊主要在“地稅”,假設:按規定要斂稅一萬,他斂一萬三千;如此,又有了三千的收入。總合起來,他額外尋租九千。這還不包括他可能克扣的工人報酬。但這九千,他并不完整上報為“方圓”或“羨余”,他報二千(史稱“所進才什一二”,進奉給朝廷的不過是扣留“常賦”和“增賦”的十分之一二);朝廷再返還給他一千作為獎勵;這樣,一年下來,他可以凈得八千。
這里的數字都是設想的,但路數就是這個路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