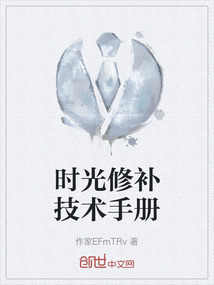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所以,我們活著到底有什么意義呢?”,當(dāng)小車嶼問(wèn)出這個(gè)問(wèn)題的時(shí)候,我沉默了很久,試圖從腦海里浮現(xiàn)的歷史過(guò)往中尋找到一個(gè)可以說(shuō)服自己的答案。我想起了柏拉圖的理想國(guó)和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想起了被火山灰掩埋的龐貝古城和被颶風(fēng)卷走的馬孔多,想起了無(wú)所不知的拉普拉斯妖和哥本哈根擲骰子的上帝,想起瓦爾登湖畔隱居的梭羅和紐約街頭游蕩的嬉皮士,想起哥譚陰影下的布魯斯·韋恩和打著響指的托尼·斯塔克,塞納河畔低頭沉默的小男孩和呼嘯而過(guò)的火車,聚光燈下尼克·凱夫驕傲的背影和黑石碑前大衛(wèi)·鮑曼滿臉的滄桑,所有的意象如同頃刻爆發(fā)的火山,噴濺在虛無(wú)縹緲的生命畫布之上,我看見在烈焰中咆哮的太陽(yáng),看見所有的星光無(wú)可逆轉(zhuǎn)地坍塌在遙不可及的奇點(diǎn),只剩下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片死寂。我想我需要給出一個(gè)答案,即使它根本沒(méi)有任何的意義,但是最終我還是告訴她:“我也不知道”。
也許我可以給出比這個(gè)好得多的答案,我可以試著跟她說(shuō)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愛,是我們值得為之奮斗一生即使失敗依然可以倍感欣慰的理想,但是也許我們需要的并不是一個(gè)振奮人心的說(shuō)辭,也許這個(gè)所謂的答案并不真的存在,也許我們需要談?wù)勥@個(gè)世界,談?wù)勱P(guān)于我們永遠(yuǎn)都在追問(wèn)卻注定無(wú)法得知的一切。
我想必須承認(rèn)的第一個(gè)現(xiàn)實(shí)就是,意義僅僅是存在于主觀意識(shí)中的一種信仰,人類為自身構(gòu)建了意義的概念從而避免心智在黑暗虛無(wú)的思想海洋中頹廢墮落。從柏拉圖時(shí)代開始,一直到浪漫主義興起之前的十八世紀(jì),哲學(xué)家們始終相信有一種高于現(xiàn)實(shí)存在的世界范式,無(wú)論是柏拉圖的理式世界,還是圣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亦或是托馬索·康帕內(nèi)拉的太陽(yáng)城,這些概念背后都隱含著相似的世界觀邏輯。在哲學(xué)家們看來(lái),現(xiàn)實(shí)世界不過(guò)是存在于理性中另一個(gè)完美世界的拙劣模仿,而人類作為唯一被賦予理性思考能力的動(dòng)物,自然也被賦予了特殊的使命,在這不完美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中運(yùn)用理性去分辨什么是絕對(duì)的正確,是必須被我們作為最高理想所追求的,而現(xiàn)實(shí)世界中所有的道德,美學(xué)都必須基于這種最高理想構(gòu)建。這種對(duì)更高存在的信仰和追求,激勵(lì)著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為之不懈奮斗,為人類構(gòu)建出了輝煌壯麗的文化,即使到了十九世紀(jì),這種思想在空想社會(huì)主義烏托邦思潮中依然興盛不衰。
在這種理性高于現(xiàn)實(shí)的論調(diào)之下,我們的生命或者說(shuō)我們的思想之所以能有真實(shí)的意義,是因?yàn)槲覀冇心芰Τ竭@無(wú)意義的現(xiàn)實(shí)之上去往更高的真理,去構(gòu)建一個(gè)代表絕對(duì)意義的理想國(guó),并為現(xiàn)有的世界指引方向。思想充當(dāng)了人類的引路人,這個(gè)理想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樣子其實(shí)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一種信念,相信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之上還有更高尚更偉大的超現(xiàn)實(shí)存在,只要我們相信在這個(gè)超現(xiàn)實(shí)中意義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即使現(xiàn)實(shí)世界毫無(wú)意義,也依然不能否認(rèn)人作為超現(xiàn)實(shí)世界信徒的意義。
也許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如此費(fèi)力去信仰一個(gè)虛無(wú)縹緲的超現(xiàn)實(shí)存在,而不是在眼前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尋找意義,盡管這種信仰的論調(diào)并不完美,在這種論調(diào)中似乎人類從來(lái)都不是處于舞臺(tái)中央的主角,只是一種實(shí)現(xiàn)更高意義的工具,我們需要關(guān)心的似乎也只是如何做才能成為一個(gè)更合格的工具。關(guān)于這個(gè)問(wèn)題,托馬斯·阿奎那告誡人們幸福來(lái)自對(duì)上帝的沉思,康德認(rèn)為人生的意義來(lái)源于對(duì)道德義務(wù)的履行,裴利提出人的使命應(yīng)該是造福大眾來(lái)說(shuō)明類似的觀點(diǎn)。
但是人類終究是不甘心僅僅作為工具而存在的,我們希望人類的存在自身就是具有意義的。這種思想上的覺醒由于尼采的超人哲學(xué)被廣為流傳,但是其實(shí)在更早之前,康德已經(jīng)做出了類似的論斷:人應(yīng)該被作為目的而不是手段。同樣的思想也出現(xiàn)在盧梭“人生的使命是能夠并且實(shí)際上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的論調(diào)中,又或者是邊沁的觀點(diǎn)“人生的使命在于獲得對(duì)自己和別人最大可能的快樂(lè)”。這種看起來(lái)有些老掉牙的結(jié)論并不能給人帶來(lái)太多心靈上的慰藉,尤其是當(dāng)我們發(fā)現(xiàn)盧梭對(duì)于人類本性近乎天真的樂(lè)觀態(tài)度并不符合現(xiàn)實(shí),邊沁的處世哲學(xué)在太多時(shí)候也顯得過(guò)于冰冷無(wú)情。
也許在很長(zhǎng)時(shí)間中我們都難以反駁的一個(gè)結(jié)論就是,如果拋棄了超現(xiàn)實(shí)的信仰,我們終究沒(méi)有辦法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找到人的意義所在,而我們卻需要這種意義的存在帶來(lái)生活下去的勇氣,但是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尋找意義真的注定會(huì)是徒勞無(wú)功的嗎?即使我們已經(jīng)擁有了理性和現(xiàn)代科學(xué)的各種思想工具。
科學(xué)主義的本質(zhì)是冰冷殘酷的,科學(xué)在根本上只接受兩類知識(shí),第一類是直觀的觀察結(jié)果,第二類是邏輯和數(shù)學(xué),科學(xué)無(wú)法接受那些僅僅是為了人文關(guān)懷而存在的信念。這里的問(wèn)題是,我們可以知曉物理學(xué)生物學(xué)化學(xué)上的一切,但是在純物質(zhì)的詮釋下我們總是會(huì)感受到意義的缺席。歌德在表達(dá)這種困惑時(shí)解釋說(shuō),就像生物學(xué)家把蝴蝶制作成標(biāo)本一樣,他們保留了一切,腦袋,身體,翅膀,所有的器官都還在,可是卻失去了最重要的東西——生命。
科學(xué)深諳人類自身的局限性,希望通過(guò)將這個(gè)過(guò)于復(fù)雜的世界切割成無(wú)數(shù)個(gè)我們可以理解的碎片,深入理解每一個(gè)碎片從而構(gòu)建出對(duì)整個(gè)世界的認(rèn)識(shí)。早在一千年以前,羅塞林就曾經(jīng)提出過(guò)類似的看法,他認(rèn)為“整體”本身并不存在,只是一個(gè)單詞而已,真實(shí)存在的是組成這個(gè)整體的各個(gè)部分。但是在考慮跟人類相關(guān)的各種錯(cuò)綜復(fù)雜的問(wèn)題時(shí)這樣簡(jiǎn)單化的觀點(diǎn)顯然并不正確,就像柏格森說(shuō)的,曲線不是眾多直線的集合,生命也不是由化學(xué)和物理元素簡(jiǎn)單組合而成。
時(shí)常被忽視的是,即使明白了每個(gè)部分的工作方式,也并不代表我們真的明白作為一個(gè)整體它們是如何運(yùn)作的,科學(xué)家們顯然也已經(jīng)意識(shí)到了這一點(diǎn),于是物理學(xué)開始研究起結(jié)構(gòu)和形式中涌現(xiàn)的意義,生物學(xué)家開始在蜜蜂,白蟻這類社會(huì)性動(dòng)物的生活方式中尋找超出個(gè)體之上的生存思維,同樣的思考在人文學(xué)科中也開始出現(xiàn),并且在二十世紀(jì)下半頁(yè)興起的結(jié)構(gòu)主義中達(dá)到巔峰。
梅拉妮·米歇爾在她的著作《復(fù)雜》中所指出的系統(tǒng)到達(dá)一定復(fù)雜程度之后自動(dòng)涌現(xiàn)出來(lái)的新特性,在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算法中有了更直觀的體現(xiàn),當(dāng)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模型的規(guī)模足夠龐大的時(shí)候,我們似乎已經(jīng)看到了真正智能的涌現(xiàn),而這種智能的特性在我們單獨(dú)研究網(wǎng)絡(luò)中的任何一個(gè)節(jié)點(diǎn)時(shí)都不可能在其中窺見哪怕一絲的痕跡。類似的,研究單個(gè)原子的行為并不能讓我們理解細(xì)胞的特性,研究細(xì)胞的行為也并不能讓我們理解高分子蛋白的特性,研究蛋白的行為也不可能理解人類。當(dāng)我們想要理解某個(gè)問(wèn)題的時(shí)候,簡(jiǎn)單拆分成更基礎(chǔ)的構(gòu)件在很多時(shí)候并不可行。
羅素在《哲學(xué)簡(jiǎn)史》中談到,哲學(xué)是關(guān)于未明確知識(shí)的思考,一旦這些知識(shí)被明確之后就會(huì)歸入具體的科學(xué)體系結(jié)構(gòu)。所以并不難想象,如今越來(lái)越多關(guān)于人生意義的問(wèn)題已經(jīng)逐漸成為認(rèn)知學(xué)家,心理學(xué)家或是生物學(xué)家的研究課題。達(dá)爾文的進(jìn)化論給這個(gè)問(wèn)題的研究帶來(lái)了強(qiáng)烈的思想沖擊,人們開始慢慢相信,人類并非凌駕于其他生物之上的神圣物種,除了像其他動(dòng)物一樣在環(huán)境中爭(zhēng)取自身的繁衍之外似乎也并不存在更高尚的意義。生物學(xué)的另一個(gè)沖擊來(lái)自于自私的基因理論,道金斯明確地指出,在人類進(jìn)化的舞臺(tái)上個(gè)體從來(lái)都不是主角,而不過(guò)是人體內(nèi)各個(gè)基因片段用來(lái)復(fù)制自身的工具,甚至在我們各種本能的情感和反應(yīng)之中都可以看出,真正決定個(gè)人行為的,并不是對(duì)本人是否有利,而是對(duì)體內(nèi)基因的復(fù)制是否有利。
雖然將人類視為微不足道的基因控制下的奴隸似乎令人很難以接受,但是更深入思考后不難發(fā)現(xiàn),似乎人類世界很多時(shí)候就是在這樣的原理之下運(yùn)作的。曾經(jīng)人們將個(gè)人繁衍后代的行為視為對(duì)自身生命的延續(xù),但是從來(lái)沒(méi)有人會(huì)真的覺得子女和父母是相同的個(gè)體,甚至他們往往一點(diǎn)都不相似,繁衍行為本質(zhì)上只是確保了個(gè)人體內(nèi)的基因片段被復(fù)制到一個(gè)新的個(gè)體中從而得到延續(xù)。所以我們更多看到的是父母會(huì)為了子女犧牲性命,而不是相反,因?yàn)閺幕虻睦嫔蟻?lái)看,父母作為基因的載具完成繁衍任務(wù)以后被認(rèn)為是可以犧牲的,而子女往往具有更高的基因傳播潛力,這種被我們盛贊的父母之愛背后也許只是基因功利性的算計(jì)而已。相同的邏輯在蜜蜂這一類社會(huì)性動(dòng)物身上能得到更為直觀的表現(xiàn),工蜂身上攜帶著與蜂后相同的基因片段,但是無(wú)法繁衍后代,因此犧牲工蜂的生命去保護(hù)蜂后的安全,盡管在工蜂個(gè)體的角度來(lái)看意味著死亡,但是在基因傳播的角度來(lái)看是有利的,工蜂體內(nèi)某個(gè)基因的利益戰(zhàn)勝了工蜂個(gè)體的利益,讓工蜂義無(wú)反顧地走向死亡。
基思·斯坦諾維奇在《機(jī)器人叛亂》中試圖為這種困境找到一條出路,聲稱人類是唯一能夠意識(shí)到自身被基因操控的物種,并且分析式思維的存在給了我們?nèi)ド髦厮伎疾⒎駴Q掉來(lái)自基因指令的能力,從而讓我們有機(jī)會(huì)逃脫基因的奴役。這也許是對(duì)的,但是從斯坦諾維奇舉出的種種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違抗基因的指令意味著與本能的對(duì)抗,也必然意味著痛苦的內(nèi)心掙扎,而這種掙扎的目的也不過(guò)是為了能夠選擇個(gè)體的利益而不是基因的利益,如果可以做到的話,也許我們可以聲稱自己是自由的,但是卻很難聲稱我們的生命就是有意義的。
從理性角度上看,似乎可以很輕易反駁絕大部分關(guān)于意義的論調(diào)。人類作為宇宙間一堆極其普通的分子組合形成的一個(gè)物理集合物,我們并沒(méi)有不言自明的原因可以標(biāo)榜自身的與眾不同,人類一直引以為傲的所謂靈魂,自由意志,可能也不過(guò)是物理規(guī)則下的并不神秘的必然產(chǎn)物。在得以窺見宇宙的浩瀚之后,即使如同生命這般非凡之物似乎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人類曾經(jīng)堅(jiān)定地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獨(dú)子,如今這個(gè)信念似乎也并非牢不可破,無(wú)論是外星智慧體存在的可能性,還是人類作為一個(gè)普通地球物種被祛魅,這種高高在上的獨(dú)特性都注定被一步步瓦解。而將時(shí)間尺度拉大到宇宙一百多億年的歷史后,甚至整個(gè)人類存在與否,對(duì)宇宙的大爆炸和未來(lái)的冷卻或坍縮都不會(huì)有任何的影響,我們究極一生完成的,不過(guò)是宇宙歷史中終將被遺忘的一個(gè)瞬間,這并不是一個(gè)可以讓人感到欣慰的結(jié)論。作為一個(gè)個(gè)體的人,我們?nèi)绾卧谡麄€(gè)宇宙的視角中尋找到存在的意義?而如果個(gè)體的人并不存在意義,那么作為個(gè)人與個(gè)人之間的聯(lián)結(jié)(比如愛)是否就能存在超越個(gè)體存在更深層的意義,就像一堆看似無(wú)意義的腦神經(jīng)元,相互連接起來(lái)卻產(chǎn)生了令人驚嘆的智慧?
理性主義很難對(duì)這些問(wèn)題給出讓人滿意的答案,即使我們像古時(shí)候的哲學(xué)家一樣,相信真的存在一個(gè)完美的理想世界,即使我們真的可以推動(dòng)現(xiàn)實(shí)朝著理想世界無(wú)限逼近,但是,如果無(wú)法確切知道現(xiàn)實(shí)世界本身存在的意義,那么現(xiàn)實(shí)是否接近理想世界又有什么意義呢?就像我們?cè)陔娪啊懂惔卧斂汀分锌吹降囊粯樱瑹o(wú)論主角生活的世界多么真實(shí)完美,在發(fā)現(xiàn)世界邊緣的時(shí)候一切的信仰都會(huì)崩塌,如果我們尋找不到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意義,終究有一天我們也會(huì)看到這個(gè)世界的邊緣。
在理性主義看來(lái),似乎理性本身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理性主義者也堅(jiān)信可以將世界的意義這一終極命題的答案在此基礎(chǔ)之上構(gòu)建出來(lái)。但是十八世紀(jì)浪漫主義的大肆興起似乎也表明了理性主義并不能給人類的心靈帶來(lái)足夠的安慰,科學(xué)精神開始質(zhì)疑這些所謂不言自明的邏輯起點(diǎn),人們希望得到更有說(shuō)服力的推理基礎(chǔ),希望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理性這個(gè)抽象的概念。
隨后代替理性被推上神壇的概念變成了自由意志,越來(lái)越多的人開始相信,我們的自由意志決定了我們的存在和現(xiàn)實(shí)現(xiàn)實(shí)就是有意義的,盡管自由意志這個(gè)概念本身也充滿了可疑性。如果所有的想法都產(chǎn)生自大腦中腦電波的物理過(guò)程,我們所謂的自由意志又是否真實(shí)存在?我們的一切想法和決定會(huì)不會(huì)只是我們身體內(nèi)的物理狀態(tài)決定了必然會(huì)發(fā)生的現(xiàn)象?
笛卡爾試圖用一種簡(jiǎn)單粗暴的二分法來(lái)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認(rèn)為雖然人的身體本身是物理的存在,但是在人腦松果體里面居住著一個(gè)與物理世界無(wú)關(guān)從而也不被物理規(guī)律決定的靈魂,這個(gè)靈魂的存在使人類得以擺脫物理宿命論的操縱。費(fèi)希特也表達(dá)了類似的思想,認(rèn)為意志或自我不是事物之一,不是跟隨物理定律被確定的,而是自由的,自我決定的活動(dòng)。但是這種說(shuō)法更多表達(dá)出來(lái)的只是他們的愿望而不是現(xiàn)實(shí),現(xiàn)在越來(lái)越多的生物學(xué)和心理學(xué)實(shí)驗(yàn)已經(jīng)表明,人類意志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理智和自由,無(wú)論是下意識(shí)反射性的瞬時(shí)反應(yīng),還是經(jīng)過(guò)深思熟慮的信仰或觀點(diǎn),實(shí)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會(huì)被外界環(huán)境所影響,人們并不真的理解為什么他們腦子里會(huì)有某個(gè)想法。
同時(shí),雖然也有另一些人試圖通過(guò)量子力學(xué)將世界歸結(jié)成一片混沌,從而逃脫命定論并且給自由意志留下了空間,但是身處這片混沌之中似乎并不能真的讓我們的境遇有所好轉(zhuǎn),人們并不喜歡生活在一個(gè)完全無(wú)法被理解,只能觀察卻不能解釋的世界中,而量子力學(xué)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個(gè)世界。如果我們的確處在這樣一個(gè)混沌的世界中,即使我們所謂的自由意志成立,它又是否有足夠的說(shuō)服力去證明人的意義?
在思考這些問(wèn)題之前,也許還有一個(gè)更基本更重要的問(wèn)題,真相是否真的重要?是否我們最關(guān)心的其實(shí)并不是真相,我們需要的僅僅是一個(gè)可以讓自己安心的結(jié)論,關(guān)乎人生意義的問(wèn)題會(huì)不會(huì)并不是關(guān)乎對(duì)錯(cuò),而是關(guān)乎信仰,關(guān)乎我們內(nèi)心愿意認(rèn)可并且從中得到慰藉的說(shuō)辭?所有哲學(xué)家都希望找到一個(gè)真相來(lái)證明我們活著是有意義的,但是如果真相是冰冷殘酷的,我們是否依然想要奮不顧身地去追尋?如果知識(shí)和真相本身并不能帶來(lái)幸福,我們究竟應(yīng)該成為痛苦的蘇格拉底,還是幸福的豬?是否真的會(huì)有一個(gè)叫做“人生意義”的東西靜靜地在等著我們?nèi)グl(fā)現(xiàn)?
叔本華認(rèn)為人是意志的奴隸,因此并不存在所謂自由而且更高層次的意義。尼采也無(wú)情地表示,關(guān)于人生意義的提問(wèn)本身就是身體或者精神軟弱的表現(xiàn)。馬赫的“思維經(jīng)濟(jì)”理論則是直接告訴我們,根本不需要浪費(fèi)時(shí)間去思考人生意義的問(wèn)題。維特根斯坦也告訴我們這些問(wèn)題都不過(guò)是語(yǔ)言上的陷阱。也許他們才是對(duì)的,也許只要保持沉默,這些問(wèn)題也就都不存在了。
“可是活著一點(diǎn)意思都沒(méi)有。”,小車嶼漫不在意地說(shuō)著,仿佛她早已知曉了一切,根本沒(méi)有留給我任何反駁的空間。
“可能確實(shí)是這樣的吧,但是生命中總會(huì)有那么一些瞬間,它們是如此的美好,以至于遇上的時(shí)候你會(huì)覺得,無(wú)論之前承受過(guò)多少的苦難,為了這一刻都值得了。”
我想我從來(lái)都不擅長(zhǎng)鼓勵(lì)別人,特別是在我自己也完全無(wú)法理解的問(wèn)題上,使用一些自己都不確定是否可信的詞匯,這會(huì)讓我顯得很蠢。暗示別人的經(jīng)歷太少并不是一個(gè)很明智的選擇,這無(wú)形中產(chǎn)生了一種身份上的優(yōu)越感,于是突然之間,你不再是她的朋友,不再是那個(gè)會(huì)對(duì)她感同身受的人,你變成了她的老師,變成了冰冷教條的無(wú)腦搬運(yùn)工。同樣的原因也成為了康德反對(duì)同情和憐憫的關(guān)鍵所在,對(duì)一個(gè)人平等的尊重遠(yuǎn)遠(yuǎn)比所有你能給出的幫助更重要。人們都喜歡優(yōu)越感,特別是面對(duì)比自己年紀(jì)小的人,而大部分時(shí)候,這種優(yōu)越感不過(guò)是一種可悲的虛榮心。
我很慶幸她并沒(méi)有反駁我,也許她也明白,應(yīng)該給這個(gè)自大的成年人一個(gè)臺(tái)階可以下,雖然我從來(lái)都沒(méi)有辦法告訴她,到底是哪些瞬間,到底如何評(píng)估苦難是否值得,甚至我從來(lái)沒(méi)有辦法回答最初的那個(gè)問(wèn)題,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兩千多年前,蘇格拉底在面對(duì)這些問(wèn)題的時(shí)候說(shuō)出了流傳至今的名言“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wú)所知”,兩千多年后,我們的處境沒(méi)有絲毫的改善,甚至信仰的力量前所未有的薄弱。然而,有一件事我們依然可以確信的就是,所有的經(jīng)歷,所有的思考,最終都不會(huì)是徒勞無(wú)功的,我們不會(huì)甘愿當(dāng)一頭快樂(lè)的豬。又或者重要的并不是答案,重要的是我們?cè)?jīng)思考過(guò)什么。就像羅伯特·波西格跨越美國(guó)大陸的摩托車之旅,所有的美好從來(lái)不是關(guān)乎終點(diǎn),而是關(guān)乎一路上的微風(fēng),烈日和所有肖陶擴(kuò)對(duì)心靈的洗禮。
我想是時(shí)候開啟一趟穿越思想的旅程了,雖然我并沒(méi)有一輛摩托車,但至少我有個(gè)愿意聽我喋喋不休的小車嶼,還有一把曾經(jīng)心愛的木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