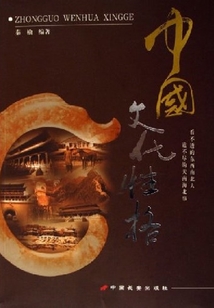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38章 閩南文化——一種文化,牽動兩岸心(5)
- 第37章 閩南文化——一種文化,牽動兩岸心(4)
- 第36章 閩南文化——一種文化,牽動兩岸心(3)
- 第35章 閩南文化——一種文化,牽動兩岸心(2)
- 第34章 閩南文化——一種文化,牽動兩岸心(1)
- 第33章 青藏文化——神秘的高原,神秘的臉(4)
第1章 燕趙文化——一個“混血”的文化(1)
在中國走向世界以前,祖國大陸的主要文化,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農耕文化,一種是游牧文化。而這兩種文化又此消彼長,相生相克。燕趙之地就是這兩種文化之間的緩沖地帶,所以有人認為燕趙文化是這兩種文化的混合體,又稱他是一個“混血”文化。
一、燕趙文化的地理區劃
燕趙文化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是在燕趙區域內產生的一種地方文化。但是我們對于燕趙區域的劃分,不能僅僅依據戰國時期燕、趙兩國的疆域來劃分,一是因為戰國時期在燕、趙兩國中間還有另外一個大國中山國存在,二是因為燕、趙兩國自己的疆界也常因戰爭的勝負而變化不定。
同樣,燕趙區域也不能以今河北省的省界為界線。今河北省又別稱燕趙,其省界大體與戰國燕、趙二國疆界相合。然而一般所理解的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個大致區域內持續存在的文化特征,其地域的區分往往是比較模糊的自然區分,因為歷史上持續存在的文化特征絕不會由人為的行政區劃而截然分開。今河北省的行政設置開始于1928年,由直隸省改為河北省,至今不過只有幾十年的歷史,因此用河北省這一行政區劃來涵蓋以往數千年的文化發展也是不夠確切的。特別是在河北省行政區劃的四圍之內還獨立出了北京市和天津市。
有人認為北京自西周初年分封燕國以來,經歷遼代的南京(燕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明代的北京、清代的京師,是六朝古都,這種說法不夠精確。因為在分裂狀態下一國之都的性質和意義與統一狀態下全國的首都是不相同的,以往幾千年間曾經作過分裂國家都城(包括臨時都城)的地方數不勝數,周代燕國的都城其性質和意義都與趙都邯鄲相差無幾,而這一類的大小都城在河北省境內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出30個以上。只是到了明代以后,北京成為全國的首都,才具有了與以往不同的性質和意義,它的歷史和文化確實不再與任何一處地方的區域性歷史和文化相同。所以自近現代以來北京史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不再和河北省的歷史、文化研究混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將燕趙文化等同于河北省的文化,就會給對元代以前北京的研究帶來不便。
尤其是自元朝以來,歷經明、清幾朝,北京都作為京都,燕趙區域也隨之成為京畿重地。在這三朝將近700年間,燕趙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都有了明顯的變化,這時期的燕趙區域和漢唐時期以全國首都長安、洛陽為中心的關中地區和河洛地區一樣,已不再是一個地方性區域,而是一個五方共居的以及代表中央的區域了。
因此,可以以今黃河來劃分燕趙區域的南部界線,這也是切合實際的。當然黃河的河道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但自漢代以后,黃河雖屢次變遷,但基本上是自砥柱東流入海,與今黃河走向大體相符。
燕趙區域的地理區劃是以今黃河為它的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脈為它的西界和北界。從當代人的空間概念來看,燕趙文化的地理范圍包括現在的河北全境及山西、山東、河南、遼寧、內蒙的部分地區。在京津文化形成以前,京津地區也屬于燕趙文化的范圍。
燕趙文化它是一種平原文化。
燕趙地勢開闊,沃野千里,兼有三面天然屏障,自古以來就是人文薈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而在漢代之前,北中國的第一大水脈黃河流向比現在靠北,那時的黃河繞太行山流經燕趙大平原,最后在碣石山一帶入海。于是黃河一方面成為燕趙戰略上的南部天塹,另一方面也是農業富庶的重要保證。那時候,北中國是整個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之一,在各個領域里扮演了歷史的主角,三秦、燕趙、齊魯等北方區域都是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后來美麗富饒的長江以南區域那時還是地廣人稀、火耕水褥的陰濕蠻荒之地。經濟重心的全面南移是唐朝后期到五代時期的事。
另一個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燕趙人中融入了大量驃悍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新鮮血液。那道被當作中國文化象征的萬里長城,在燕趙北部的懷來、萬全一線一直沿燕山山脈橫亙至秦皇島海濱,遠遠看去仿佛一條蜿蜒的巨龍。今天,當我們站在被稱作燕趙鎖鑰的山海關下,明代狀元蕭顯徘徊三日后寫就的“天下第一關”五個蒼勁大字已經引不起我們的陶醉之感。雄闊的萬里長城從來就沒有成為北中國不可逾越的軍事屏障,從戰國、西漢到明代,固若金湯般的長城被修了一次又一次,但游牧人的鐵騎照樣踏破城闕屢屢南進,江山永固、海內晏請的愿望只是不切實際的夢幻空花而已。
燕趙文化也就成為一塊農耕文化,發育得相當完善,并以儒家文化為中心,成為中國與游牧文化通向交匯的前沿陣地。在中國,農耕文化以中原文化和黃河文化為主體。以農耕文化為中心建立的封建王朝,都極力防止以草原部落和東北關外文化為代表的游牧文化的南移。而游牧文化又有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極力南移,并在全國建立了兩個統一的封建王朝:元朝和清朝。這兩種文化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溫文爾雅。燕趙文化正好夾在這兩種文化中間,所以有人認為燕趙文化是一個“混血”的文化。胡服、朝服、洋服,燕趙文化經歷了無數次的歷史變奏,無數次的滄海桑田。
另外,燕趙的土地是遼闊的,但也是相對貧瘠的,這個地方的農業在漢代黃河未改道之前曾經一度繁榮,但比不上山東、關中,南北朝以后便不得不依靠運河把南方大量的糧食運過來。五代以后它的經濟與南方相比已大為遜色。到了20世紀上半葉,林語堂用“簡單的思想和艱苦的生活”來描繪這里的百姓。
在歷史上,由于要適應燕趙寒冷的溫帶氣候和相對艱險的生存環境,人們就必須具備堅強的體魄和堅毅的品質。正如孟德斯鳩在1748年所指出:“土地貧瘠,使人勤奮、儉樸、耐勞、勇敢和適宜于戰爭,土地不給與的東西,他們不得不以人力去獲得。土地肥沃使人因生活寬裕而柔弱懶惰,貪生怕死。”因此,為什么在中國歷史上,北方同南方的戰爭中南方人常遭失敗呢?孟氏的話提醒了我們。
二、慷慨悲歌與好氣任俠
20世紀前期,弗洛伊德的高足奧地利心理學家榮格一生都在強調“集體無意識”的巨大影響力。在他看來,每個人一生的行為都受到背后一只無形大手的控制,這支大手就是長期以來積淀在傳統中具有文化同構特征的綜合價值觀念,它是人文地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文化特征上看,燕趙區域也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這就是慷慨悲歌、好氣任俠。
“慷慨悲歌”一語可以用來形容各個地區的人物和現象,但是在歷史上,它是由燕趙區域而產生的,是以燕趙區域為典型的。在其他區域,慷慨悲歌并沒有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而在燕趙區域,慷慨悲歌卻已是普遍的特征和特殊的標志。這一特征從理論上建構了燕趙文化的個性特征,鞏固了燕趙文化的區域概念,使燕趙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區別開來。
從時間上,慷慨悲歌文化的特征在戰國時期形成和成熟,在隋唐時期仍然為人們所稱道,到明清時期其余音遺響不絕如縷,前后持續2000余年,確已形成了悠久而穩定的傳統。所以,燕趙區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趙區域的文化特色。這也是即不同于中原,關隴,又不同于齊魯,江南的特點。
1.齊魯多鴻儒,燕趙饒壯士
大歷史學家司馬遷說:“燕趙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然而燕趙大地還蘊含了無限的優雅之氣與閑散的情調,以及太多太多的無奈和苦難。
燕趙與江南比起來,“正像是黃酒之于白干,稀飯之于饃饃,鱸魚之于大蟹,黃犬之于駱駝”。
燕趙文化充滿著一種悲壯之美。燕趙人多有一股俠義之氣,秉性率真,性格直率,充滿著骨氣和血性。
燕趙文化有自己的文化性格。
燕趙文化世代傳承,存在著一種尚武遺風。在燕趙文化里,散發著個人英雄主義的濃香,充滿著文化的悲劇之美。
戰爭、尚武、俠義、壯士渲染的是文化上的悲壯。燕趙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角色是一個悲劇的角色,燕趙文化充滿著歷史的悲劇美。燕趙的人以生命去告訴世人什么是正義,以死去證明人生的價值,讓正義戰勝邪惡。燕趙文化里的人物命運大都以備注的死來結束一生。燕趙文化是在歷史的大悲壯中展開的,尤其在民族危亡、國破家亡、戰事頻頻的動蕩時期,燕趙文化總是表現出一種崇高的風骨,一種頂天立地的英雄氣概。
歷史上的燕趙曾是奇俠、豪客、英雄、土匪、流氓、大頭鬼的樂園,是中國英雄主義的源頭和男子漢的降生之地。
燕趙多悲風、多義士。一句“燕趙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令我們胸中的塊壘沉郁,百感交集。
荊軻刺秦,壯懷激烈。荊軻是歷史上一位著名的俠士,《史記·刺客列傳》中共記載了五位俠士,荊軻是其一。公元前27年,燕國派刺客荊軻以獻圖為名入秦宮刺殺秦王,秦王慢慢展開地圖,結果圖窮匕現,荊軻拿起匕首向秦王猛刺,然而未刺及秦王,結果為秦王所殺戮。壯士之名,流芳千古。“荊軻刺秦”的典故就來自于他只身一人行刺秦始皇。司馬遷說:自豫讓之后四十余年而有聶政,自聶政之后二百二十余年而有荊軻。數百年間僅區區五人,可見在司馬遷眼中稱得上俠士的都是不世出的大英雄。
燕趙文化多有一股俠義之氣。什么是俠?俠就是不君不臣,不偏不倚,自成一家。俠士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既不遵從國君之命,也不遵從世俗的觀念,而只遵從自己獨有的價值標準。俠士并不單單只尚武,他們也十分注重讀書。在古代,士是讀書人的稱謂,那些稱得上是俠士的人都讀書有成,文武兼通,并不單只習武。俠士重信義,言必信,行必果,一諾千金。俠士注重德操,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議論別人的短處,“交絕不出惡聲,去國不潔其名”。他們注重名譽,不是沽取虛名,而是為了證實自己的絕對完美、絕對自信。他們幫助別人時報一答十,不是出于對別人的關心,而是為了證實自己有存在的價值和承諾的力量。他們不在意成敗,不吝惜生死,不是因為輕視生命,而實在是因為太熱愛生命。生命有兩種,茍且偷生自欺欺人是沒有意義的生命,矢志不移獨立自存是有意義的生命。俠士愛惜的是有意義的生命,所以他們都意志堅強,“立意皎然,不欺其志。”為了保全這個志向,他們就會在需要的時候不惜生死,所以像程嬰、侯贏、田光、樊於期、夏扶甚至在完成使命之后也要自殺而死。生不茍合,死不茍且,死法和生法同樣重要。做俠士最重要的不是敢于去和強敵拼死,而是敢于在值得的時候自己殺死自己。
由于俠士有自己特殊的價值標準,國君不認同他們,因為他們擾亂國家法令,私設刑罰。普通人也不認同他們,因為他們活著不求財利,死時不惜生命,全然不可效仿。只有他們自己少數幾個人之間相互認同,但也都是默認于心,從不明說。這樣的一種人生確實稱得上是白虹貫日、感天地而泣鬼神!
俠士必須是刻苦砥礪,孤介獨行。只有田光能請出荊軻,而田光自刎身死。只有樊於期的人頭能使秦動容,而樊於期果然甘心授首。夏扶只因不能同行,就在車前刎頸以壯行色。黃金投龜,燴千里馬肝,斷美人之手,荊軻面不改色。然而荊軻來到燕國肯定不是因為希圖燕太子丹的黃金、館舍、車騎、美女,別人可能是,他決不可能。他知道提一匕首以入強秦的后果,早已預存必死之心。何況田光、樊於期、夏扶已先他而死,荊軻更是義無反顧。但他入秦又不是為了太子丹一人一國的私利,他是為他自己平生的志向。荊軻說:“心向意,投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狂狷”了。
易水送行,高漸離擊筑,荊軻作歌,眾人無不動容,而荊軻升車而去,終不回顧,看似無情。荊軻已死,魯勾踐悲痛自悔,說:“從前我還怒叱他,他會以為我是什么人!”這幾位俠士志向之高之烈以及他們之間心意的默然契合,都已達到無以倫比的境界。荊軻之悲壯在于,義士壯烈,以燕國的興亡為己任,明知行刺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仍奮然前行,置生死于不顧。“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中國歷史上還有比這更悲涼、更凄美、更蕩氣回腸的背影嗎?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荊軻的壯舉,中國的公元前三世紀將會平淡許多。
燕地以慷慨悲歌為特征的文化的形成,不是社會正常發展和社會繁榮的結果。社會正常發展與社會繁榮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揚的大國之風,燕趙文化則是一劍以當百萬之師的偏鋒奇鋒。燕地苦寒卑弱,因此它的文化也就自傷自怨,剛烈悲壯。“慷慨悲歌”中的慷慨,又寫作忼慨,忼又寫作亢,本指咽喉。在聲樂上,慷慨是情緒激昂、聲音高亢的歌唱方式。悲歌也是專有所指的一種歌唱風格,在《燕丹子》中有“為壯聲”、“為哀聲”的描寫,其悲壯之情可以由荊軻《易水歌》中“易水寒”、“不復還”數語具體印證。在心理上,慷慨悲歌是一個情結,是由經濟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導致的一個情結。這個情結經過一種壯烈的撞擊,發生逆轉,出現升華,于是就化育成為慷慨悲歌的性格。
在謀刺秦王的過程中,太子丹和荊軻之間也有一種契合。這二人的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又缺一不可。太子丹的精誠與荊軻的奇志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產生出的激變,就形成和成熟了燕趙文化“慷慨悲歌”的獨特風格。慷慨悲歌或燕趙悲歌自戰國秦漢以來已經成為固定的成語,人人皆知,但是對它作深一步解釋的人并不多,唯有袁褧《楓窗小牘》中說道:“秦威大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以自虹貫日,和歌變徵。”這個解釋準確而深刻地道出了燕趙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
燕昭王的報復伐齊和燕太子丹、荊軻的謀刺秦王,標志著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
2.武勇任俠與陽剛之美
燕趙文化武勇任俠的特征形成于戰國時期,以趙武靈王的胡服尚武為最主要標志。趙國的文化源出三晉,而晉國正是中國古代法家智慧與武勇任俠風尚的發源地。早在遷都邯鄲前后,趙氏之中就已接連出現了幾位俠士。趙朔時,趙氏遇到大難,同宗四位大夫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都被滅族,于是趙氏門客中出了公孫杵臼和程嬰二人,保護趙氏遺孤。公孫杵臼問程嬰:“抉立孤兒和殉難而死哪個更難?”程嬰說:“死容易,扶立孤兒更難。”公孫杵臼說:“那么你來努力做這件難事,我做容易的,先讓我來死。”于是公孫杵臼殉難而死,以掩護程嬰。程嬰則帶著孤兒趙武藏匿山中,十五年后,趙武重新被立為大夫,程嬰繼續在左右保護他。又過了數年,趙武長大成人,舉行了加冠禮,程嬰便毫不遲疑地自殺而死,為的是到地下向公孫杵臼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