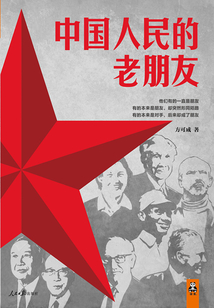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 第34章 參考文獻著作類:
- 第33章 附2 那些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國家
- 第32章 附1 數(shù)讀老友
- 第31章 與一個時代作別(1980年至今)(5)
- 第30章 與一個時代作別(1980年至今)(4)
- 第29章 與一個時代作別(1980年至今)(3)
第1章 理想照耀友誼(1949年之前)(1)
他們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來到中國。
他們結識了中國人,接觸了中國共產(chǎn)黨,并且站在了當時還很弱小的紅色力量這一邊——這成為他們后來被稱為的主要緣由。
這份友誼伴隨著共產(chǎn)黨的成長壯大,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芒。
這份理想指向一個獨立、民主、沒有腐敗、沒有壓迫的新中國。
站臺的一次偶然相逢
兩人都沒有想到,日后他們會因為中國而結為畢生的忠誠朋友和合作伙伴,并且被賦予一個相同的重要稱呼——“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不過顯然,在他們相逢的1929年夏天,這兩位“老朋友”還是兩個世界里的人。
1929年6月,張家口。
一列火車正從這座位于河北西北部的城市緩緩駛出,一路向西,沿平綏鐵路開往綏遠的薩拉齊。
乘坐這趟火車是件苦差事。連年的軍閥混戰(zhàn)導致民生凋敝,人們營養(yǎng)不良,就連火車也跑不動了——因為機車和車廂保養(yǎng)不善,行駛速度極慢。從北京到張家口短短200公里的距離,竟花了一天一夜。從張家口開出后,前方的旅程還有三個晝夜。
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這趟火車雖然是載人的客車,用的卻是無頂?shù)呢涇囓噹每蛡兌甲诘匕迳稀M局胁磺捎錾洗蟊┯辏w在車頂?shù)钠婆?布完全無法抵御雨水的入侵,車廂內(nèi)又濕又悶,擁擠而骯臟。
這些車廂就像是彼時中國的一幅縮影——潦倒破敗的環(huán)境中擠滿了饑腸轆轆的窮人,正駛向一個目的地,但速度極其緩慢,叫人看不到希望。
中國的西北部更是如同人間地獄,天災頻仍,人禍不斷,連年的旱災導致的饑饉已經(jīng)奪去了不少人的生命,而已經(jīng)成為家常便飯的土匪搶劫、軍閥混戰(zhàn)、稅吏橫征暴斂、地主巧取豪奪更讓人失去最后的希望。在列車行駛的目的地綏遠,1929年開始的一場大饑荒正吞噬著200萬條生命。
不過,并非所有人都生活得如此不堪。這趟火車駛離張家口時,掛上了一節(jié)環(huán)境舒適、設備齊全的專用車廂,里面只坐了兩個人。用今天的話來說,那是一節(jié)“VIP車廂”。
這趟同時掛著最破舊車廂和最豪華車廂的列車在鐵道上走走停停。如此怪異的情景,也好似貧富差距驚人的中國。
火車在一個小站長時間停車時,破舊車廂里的旅客紛紛下車透氣。32歲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隨人流走向站臺,他想下車吹干自己被雨水淋濕的衣服——那皺巴巴、濕乎乎的卡其襯衫和短褲讓他看起來狼狽不堪。
24歲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也下了車。站臺上的人群中,他完全是一個格格不入的異類,這不光因為他是外國人,更因為他乘坐的是那節(jié)VIP車廂,因此衣物十分整潔服帖,神情也與那群愁苦的以農(nóng)民為主的旅客全然不同。
兩位外國人都發(fā)現(xiàn)了對方,走到一起寒暄起來。
這是艾黎與斯諾的第一次見面,但他們只匆匆交談了幾句。兩人都沒有想到,日后他們會因為中國而結為畢生的忠誠朋友和合作伙伴,并且被賦予一個相同的重要稱呼——。
不過顯然,在他們相逢的1929年夏天,這兩位“老朋友”還是兩個世界里的人。
當時,斯諾的身份是《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的助理編輯和記者,這份報紙由美國人在上海創(chuàng)辦,讀者包括在華外僑和海外關心中國的外國人,影響力頗大。南京國民政府的交通部邀請斯諾在中國鐵路沿線進行旅行采訪,通過他的報道宣傳中國的旅游,讓西方人相信到中國旅游是可行、安全和舒適的。
不論這樣的宣傳是否屬實,起碼,斯諾的鐵路之旅是安全而舒適的。他不僅享用了VIP車廂,還有一名姓胡的官員專程陪同,擔任向?qū)Ш头g。
但斯諾感興趣的不僅僅是沿途的旅游風光,否則他不會選擇去綏遠。這位天生具備強烈好奇心的記者不希望成為單純的傳聲筒,他想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一切,當他抵達張家口后,發(fā)現(xiàn)西邊正遭受著可怕的災難。在他的堅持之下,他們的VIP車廂才得以掛在艾黎乘坐的那列載人貨車后面,一起朝受災嚴重的旱區(qū)進發(fā)。
在站臺相遇后,斯諾邀請艾黎去他的VIP車廂坐坐,享受享受舒適的設施,但那位姓胡的官員看了一眼艾黎,便傲慢地拒絕了他的要求。
艾黎絲毫不感到慍怒,他很高興地回到農(nóng)民伙伴中間,坐在地板上搖晃到了薩拉齊。在那里,他將參與國際賑災委員會的救災行動,修筑一條灌溉渠。
和出身中產(chǎn)階級家庭的斯諾比起來,艾黎與底層民眾走得更近,他并不認為自己返回那骯臟的貨車車廂是什么羞辱。
這與艾黎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關。艾黎的父親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認為只有國營工業(yè)化農(nóng)場才是解決土地問題的出路。他從小受到的教育是尊重教會,但他卻摒棄了教會。他不讓自己的孩子上主日學校,說這是因為他不愿在孩子自己能作出決定或理解人生之前把信仰強加于他們。
“我相信宇宙間有神主宰著生命與演變,但我不信基督是上帝生的兒子,他只是人類一位偉大的領袖。我喜歡進教堂去唱和聽美麗的圣詩,卻不會背教義,不過我還是信基督的教導的。”艾黎的父親說。
艾黎的母親則不僅治家有方,還是早期在新西蘭爭取并獲得女性普選權的婦女之一。正是由于他母親等人的努力,1893年,新西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批準婦女享有普選權的國家。
這樣的家庭背景似乎注定了艾黎的一生將要獻給社會運動,也注定了他與底層民眾具有天生的親密感,關注農(nóng)民和工人的生存狀況。
另一個有趣的細節(jié)是,艾黎的名字“路易”帶有反抗帝國主義的意味——那是他的姑媽根據(jù)一個名叫路易·曼尼亞波托的毛利族首領的名字起的,此人在19世紀60年代毛利人的土地戰(zhàn)爭中奮力抵抗英國軍隊,最終成為傳奇人物。
艾黎和斯諾最終也將成為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傳奇人物。在此后的歲月里,他們彼此的友誼將愈來愈深;同時,他們也將愈來愈深地卷入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被中國改變,并改變中國。
31年后的1960年,作為中美恢復外交關系的前奏,斯諾重訪中國,那一次的訪問,他的身份正是定居中國的路易·艾黎的私人客人。1929年夏天小站站臺上的相遇只是一個開端,波瀾壯闊的畫卷正緩緩鋪開,為艾黎,為斯諾,也為中國。
路易·艾黎是個古怪家伙
誰能想到,中國人迎接這位日后將成為老朋友的新西蘭人的第一件“禮物”居然是唾沫!
在1929年的那一次站臺相逢中,斯諾對艾黎的印象是“古怪的家伙,但很有趣”。
艾黎的確有些古怪。比如,他終身未婚,不少人對此也曾有過種種猜測。他的秘書呂宛如則透露,艾黎并非有意選擇獨身生活,“多少不同國籍的女性仰慕他的品德和才干,大多因志雖同而道不合,最后止于做終生好友。他自己也并非沒有中意的人,但年輕時他認定,在革命中,一個人不該有家室之累,有家室而不能給家人帶來幸福,會有愧于心。一年又一年,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如果呂宛如所言不虛,那么另一個問題又來了:艾黎為何會執(zhí)著于中國的革命,并因此放棄成家,在所不惜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后文中再逐漸揭開。
其實,對于那些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來中國的外國人來說,他們在自己同胞的眼里或多或少都有些奇怪。尤其是艾黎這樣自告奮勇、只身一人來中國的,就更少見了——起碼,像斯諾那樣的記者來華時肩負著采訪報道的使命,更不用提來做生意的商人,來傳教的傳教士了,而艾黎來中國,并沒有受到任何組織的委派。
1927年4月21日,這位古怪的30歲青年抵達上海。此前,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歐洲戰(zhàn)場經(jīng)歷了生死考驗。戰(zhàn)后,這位老兵回國辦牧場,每天要花上16小時砍灌木、架圍欄、修公路、趕牲畜,還要自己種菜、擠奶、燒火做飯。由于戰(zhàn)后新西蘭經(jīng)濟形勢惡化,他的生活十分艱苦。
就在牧場經(jīng)營無以為繼,不得不關閉的那一年,艾黎經(jīng)常從報刊上讀到關于中國的消息,獲悉革命的情況。那時,中國的事態(tài)已經(jīng)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革命的消息也吸引了艾黎,行事風格雷厲風行的他立馬決定去中國。
本來,他只辦了為期6個月的簽證;結果,他卻在這個遙遠的國度生活了整整60年。很多年后,當路易·艾黎步入晚年的時候,他說,是中國給了他生活的目的,一個值得他為之奮斗的事業(yè)和內(nèi)容日益豐富的歲月。
的確,如果沒有來中國,艾黎也許會在新西蘭的鄉(xiāng)間度過一生,偶爾在某個閑暇的午后回憶一戰(zhàn)時期的崢嶸歲月。
但是因為與中國結緣,他的晚年被榮譽所籠罩。艾黎贏得了眾多的榮譽頭銜,包括作家、詩人、社會活動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教育家、中新關系架橋人、英女王社會服務勛章獲得者、北京市榮譽市民、甘肅省榮譽公民以及各種榮譽學位。他還得以與中國最高層的領導保持密切聯(lián)系,成為許許多多中國人尊敬的對象。
不過,如果將這些榮譽簡單理解為“幸運”,歸結于年輕時代的一次“撞大運”,顯然是不公允的。來中國的外國人絕不止路易·艾黎一個,為什么命運如他的人少之又少?
最重要的原因,是少有人像這位古怪的新西蘭人一樣,身上流淌著親近底層民眾和厭惡侵略、破壞的血液,對中國與中國人懷有如此濃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更少有人像他一樣,憑著老兵的堅韌和老農(nóng)的踏實,為中國無私工作幾十年,試圖改造這個積弊已深的古老國家。
改造的前提是理解。對于外國人來說,理解中國和中國人,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艾黎抵達上海時,遭遇的第一件事就讓他費解。
當時,他先去了澳大利亞,然后坐了6個星期的船抵達香港,再從香港出發(fā),在上海十六鋪碼頭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個中國最大的港口居然沒有海關,也沒有邊防檢查,不用辦任何手續(xù),外國人可以隨意在這個國家通行。
更離奇的是,艾黎在碼頭獨自行走的時候,一個碼頭工人看見他,便面露慍色。當他走過這位碼頭工人身旁時,工人忽然站起來,朝艾黎臉上吐了口唾沫!
好在艾黎并沒有發(fā)作,他只是在心里想:“這可是件怪事!這個國家可真特別!”他擦掉唾沫,快步離開了碼頭,住進了四川路的一家小客棧。
后來他才明白,當時上海有許多外國軍隊,中國工人因此具有強烈的排外意識。
雖然艾黎日后逐漸被中國人所接納、信賴、喜愛,但這一幕一直留在艾黎的腦海里,也成為他理解中國的一個入口。
誰能想到,中國人迎接這位日后將成為老朋友的新西蘭人的第一件“禮物”居然是唾沫!此后,艾黎遭遇了更多超乎想象的事情,這位古怪的年輕人開始與這個古怪的國家深入接觸。
上海見聞
“他們在無蓋的鉻缸旁操作,周圍沒有排除含毒水汽的裝置。
傷口腐蝕到肉里,手腳上有一個個‘鉻孔’。”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五方雜處,華洋共居,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
艾黎卻敏銳地發(fā)現(xiàn),這座樂園是畸形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只不過是為富人、權貴以及擁有特權的外國人所享受而已,普通民眾的生活極其悲慘——這部分人的生存狀況恰恰是艾黎最關心的。
上海的貧富懸殊令艾黎感到吃驚。在市區(qū)幾條主要的道路上,車水馬龍,建筑高大宏偉,一派繁榮的景象,但一旦深入城市的“毛細血管”之中,很快就會發(fā)現(xiàn)那迷宮般縱橫的里弄狹窄,擁擠,臭氣熏人,大街小巷到處都是乞丐。
“那里每個人都吐痰——上海95%的人似乎都患慢性黏膜炎。”在回憶錄中,艾黎這樣寫道。
艾黎生活的地方有著豪華的俱樂部,時髦的汽車,訓練有素的仆役。但是,他卻將時間和感情大量投入了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居住的街巷里。
起初,艾黎在公共租界的消防處工作,他不喜歡跟單位的官員們談話,唯獨喜歡檢查工廠,因為這樣可以深入擁擠、發(fā)臭的陋巷里的車間,直接接觸工人。他的同事們不明白,為什么艾黎要花那么多時間去學中文,甚至還學上海話?
1932年,消防處所在的工部局成立工業(yè)科,艾黎調(diào)任工廠安全督察長,專門負責檢查租界內(nèi)工廠的安全設施。
這一新職位算是徹底發(fā)揮了艾黎的特長,也符合了他的興趣。然而,這項工作卻讓艾黎極其痛苦,因為他親眼目睹了太多殘忍的場景。
由于工廠的安全措施很差,事故經(jīng)常發(fā)生。農(nóng)村來的青年工人經(jīng)常穿著肥大下擺的褲子和寬袖口上衣干活,他們的衣服時常被卷入擺得過于密集的機器。因為疲勞過度,許多工人的手指不慎被沖床切斷。還有一次,橡膠廠因為硫化器引起爆炸,460名女工受害。
最讓艾黎感到痛苦的,是童工們在“黑工廠”里的遭際。
在當時的繅絲業(yè)體制下,許多孩子不過八九歲,卻要每天在煮繭的大槽前站上足足12個小時。他們手指紅腫,兩眼因睡眠不足而布滿血絲,眼皮沉得像鉛。工頭手里拿著鐵絲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來回走動。如果童工把一根絲理錯了,工頭就用開水燙他瘦弱的胳膊作為懲罰。
其他工廠的勞動條件不見得比繅絲廠好。搪瓷廠里普遍發(fā)生銻中毒,制作電池鉛板的工廠則盛產(chǎn)鉛中毒。
“我還記得那些日夜站在拋光盤前的孩子,他們疲憊不堪,手腳上沾滿了金剛砂粉、汗水和金屬粉末,真是可憐!”艾黎后來回憶說,“他們在無蓋的鉻缸旁操作,周圍沒有排除含毒水汽的裝置。傷口腐蝕到肉里,手腳上有一個個‘鉻孔’,在那種糟糕透頂?shù)膭趧訔l件下幾乎是治不好的。孩子們無可奈何地操作,勞動時間之長令人難以相信,根本談不上最起碼的人權。
他們瘦小的軀體為活命而掙扎,好讓老板有暴利可圖。在國民經(jīng)濟已經(jīng)崩潰的情況下,各種工業(yè)使得為謀生而掙扎的青老年工人更加困苦……”
作為工廠安全督察長,艾黎能做的卻非常有限,他只能從技術上對工人們的勞動條件稍加改善。比如,他曾去嘉定的一家工廠參觀那里抄襲來的日本式總煮沸系統(tǒng),并將其帶回上海,在所有的繅絲廠里推廣使用,以減少工房里的蒸汽,降低室溫。
但更根本性的東西是艾黎無法改變的,比如包身工制度。在艾黎看來,工業(yè)就像是一場戰(zhàn)爭,勝利的總是工廠主。
這樣的經(jīng)歷和這樣的看法為艾黎后來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伏筆。因為渴望看到工人境況的改變,他開啟了“工合”計劃,而他與共產(chǎn)黨人的惺惺相惜更是順理成章。當時,上海的工人們已經(jīng)受到延安正在組織進行抗日戰(zhàn)爭的鼓舞,一些工人出走,參加了革命軍隊。
當艾黎正為工人們的安全奔忙時,斯諾也在上海——作為當時的外國在華政治經(jīng)濟中心,上海是外國人聚集的地方,甚至在根本上更像是一座外國城市。在斯諾看來,上海是“迷人的、令人銷魂的老所多瑪和蛾摩拉”。
上海的罪孽在哪里?這位年輕的美國記者與艾黎所見略同:巨大的不平等,殘酷的剝削,工人們慘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