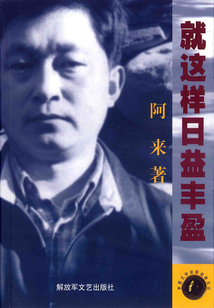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太陽攀響群山的音階(1)
在詩歌與小說之間(序篇)
必須承認,對我來說,所謂散文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
我知道詩是什么,也知道小說是什么,但我肯定無法明晰地表達散文這種文體該是什么。詩是我文學的開始。而當詩歌因為體裁本身的問題,開始限制自己作更自由更充分表達的時候,我便漸漸轉向了小說。而且,在這兩個方面,我都有著相當的自信,但是說到散文,我就真的不知道該說些什么了。
散文是那么多種,那么多類,那么多不同的文本與方式。比如蘭姆與蘇東坡,其間的差異絕非是東西方文化的不同,作家個性不同那么簡單的理由便可以說明。再比如寫《陶庵夢憶》的張岱與寫《野草》的魯迅。當然,還有更多不是散文家寫出來使人無可歸類便指稱為散文的好文章,使我們進入的時候像是進入一個藏書數十萬冊,但沒有分類索引上架的寶庫,只好四處淺嘗輒止,雜食而不得要領。所以,當出版社盛情相邀出一本散文的時候,我是十二分地婉辭過的。原因是自己雖然也有一些介于小說與詩歌之間的感性文字,但我不知道它們是不是應該稱為散文。因為讀者看到的這一輯東西,如果說有一個統一的標識,便是它的藏文化背景。除此之外,它們在寫作方式上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第一輯里如《銀環蛇》、《野人》和《魚》等篇什,是我漫游時的記錄,寫成詩不合適,又非完全虛構的小說。也就是說,主要脈絡都是作者實在的經歷,只不過在細節或者在氣氛上多了一些虛構。過去也是作為小說發表的,現在編輯看了,說也算是散文,我也找不出反對的理由。最有意思的是《聲音》二篇,湖南《新創作》雜志親自派人來索稿,我便應命寫了,本意中寫的是一篇小說,或者說自認為寫的是一篇小說,只不過投寄時沒在題目下作一個說明:此篇是小說。結果就被當成散文發表。事后,編輯還打電話來說,本來預留了前面的小說版面,沒想到寄去的是散文,于是,便把大半本雜志的版面重推了一遍云云,我也沒有聲辯。
再就是前年應邀參加“走進西藏”叢書的行走與寫作。走了一趟西藏,結果卻全寫的故鄉四川藏區阿壩,寫了更多的回憶而不是發現。叢書出來后,據說這一本評價還不壞。這個不壞,不是藝術水準上的評價,而是說寫得真賣,有干貨,有個思想著的阿來在里面。其實拉拉雜雜的二十萬字,能夠立起來,全靠那數萬平方公里構造雄偉的地理骨架。媒體炒作這些書和一些類似的書時起了一個名字“行走文學”。這是個命名時代,出版商中有人都可以開起名公司了。這個名字初聽之下,我也覺得其妙無比。并沾沾自喜地捧著印著這種字樣的報紙入睡,但早上醒來,猛然清醒:什么文學又不是行走的文學而是禪坐著的文學?但自己的確無力再給一個新的名字。這次,托責任編輯從《大地的階梯》里挑一些比較獨立的段落來湊一個半個印張。與天寶商量時,我又一次困惑,這是散文嗎?接踵而至的又一個困惑是,如果不是散文又是什么呢?一個準社會學者的田野考察筆記?但這種好筆記難道就不是散文?于是,又一次想打退堂鼓。但是,編者曉之以理再加動之以情。說這套書是四個因茅公稿酬捐獻才有的這個大獎的得主的,三缺一,不成樣子。我所在的成都是一個麻將城市,我也偶爾上場把自己的財運交給賭神支配一回兩回。知道四方桌子缺了一邊,難看。但我湊上去了,還是難看。對方,王安憶,剛從文的時候,還拿著她的書給女朋友說,將來我也要寫這樣子的書,這些年,光是她那些讀書心得,光是她探究小說之道的文章,就是上海女人從張愛玲那里一路下來很莊重齊楚的樣子了。上手,張平,反腐斗士,是可以在《南方周末》的時評裊開專門欄目那一路數的武林高手。下家,王旭烽,承她陪游過一次西湖,那四處隨意的掌故點染,讓我把張岱的《西湖夢尋》忘得一干二凈,又坐在湖邊茶樓里經她引領著學了如何吃茶,光是一眼西湖與兩杯龍井,就可以褪盡我這個小小書商的俗氣。今天,藏著她奉送的一罐武陵山珍,說是茶中極品,偶爾嘗過兩次,卻不得門徑,你說,這圈麻將如何開打?
好在,滿世界寫狗屁文章的人都盡拿西藏做著幌子,很入世的人拿政治的西藏做幌子,很入世又要做出很不入樣子的人也拿在西藏的什么神秘,什么九死一生的游歷做幌子,我自己生在藏地,長在藏地,如果藏地真的如此險惡,那么,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如果西藏真的如此神秘莫測,我活著要么也自稱什么大師,要么就進了精神病院。但至今,我算賬沒有出過千位數以上的錯誤,出門沒有上錯過飛機,處世也沒有太錯認過朋友。所以,上了這桌子,摸了一手花色很雜的牌也暗暗喜歡,不是為一手壞牌喜歡,而是喜歡一種東西本身那種喜歡。喜歡文字表達的那種喜歡。
還必須說的一句是,我這輩子可能永遠弄不懂真正的散文是什么樣子,也不打算弄懂這種文字該是什么樣子(模式?),至多,我所知道的散文很寬泛之處在詩歌與小說這兩個王國之間的游擊地帶,但這種無從定義的文字多多少少還是會寫下去的吧。
離開就是一種歸來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我從一座小寺廟里出來。住持讓手下惟一的年輕喇嘛送我一程。他把我送出山門,并把我寄放在門房的小口徑步槍交還給我。
下午斜射的陽光照耀著蒼黛的群山,蜿蜒的山脈把人的視線延伸到很遠的地方。山下奔涌不息的大渡河水也被陽光鍍上了一層因爍不定的金光。
我對這個年輕昀嘛說“請回去吧。”
他的臉上流露出些依依不舍的表情,說讓我再送送你吧。
我知道這并不意味著通過這四五個小時的訪問,我們之間已經建立起了多么深厚的友誼,這是不可能的。在我做客的大部分時間里,我都在跟他的上司一這座山間小寺的住持喇嘛爭論。因為一開始他就對我說,這座小廟的歷史有一萬多年了。宗教從誕生之初,就具有對日常生活的超越能力。但很難設想產生于歷史進程中的宗教能夠超越歷史本身。于是,我們就開始爭論起來。這個爭論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而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那時,這個年輕喇嘛就坐在一邊。他一直以一種恭敬的態度為我們不斷續上滿碗的熱茶,但他的眼睛卻經常從二樓狹小的窗口注視著外面的世界。
現在,我們來到了陽光下面。強烈的陽光刺得人有些睜不開眼睛。我們踏入了一片剛剛收割了小麥的莊稼地。剩下的麥茬發出許多細密的聲響。那個年輕喇嘛還跟在后面。我還看見,那個多少有些惱怒的住持正從二樓經堂的窗口注視著我。我在他的眼里,是一個真正異端嗎?
我再一次對身后的年輕喇嘛說:“請回去吧。”
他固執地說:“我再送一送你。”
我在剛收割不久的麥地里坐了下來。麥子堆成一個一個的小垛,四散在田野里。每一個小垛都是一幢房子的形狀。在這一帶地方,傳統建筑樣式都是碉樓式的平頂房子。而這種房子式的麥垛卻有一道脊充當分水,帶著兩邊的坡頂。在這片遼闊山地里,還有一種小房子也是這么低矮,有門無窗,也有分水的脊帶著兩邊的坡頂。那就是裝滿叫做“擦擦”的泥供的小房子。這些叫做擦擦的東西,一類是寶塔狀,一類則像是四方的印版,都是從木模里模制出的泥坯。這些泥坯陳列在不同的地方,是對很多不同鬼神的供養。
麥地邊的樹林與草地邊緣,就有一兩座這種裝滿供養的小房子。
而地里則滿是麥子堆成的這種小房子。
這時,坐在我身邊的小喇嘛突然開口說:“我知道你的話比師父說的有道理。”
我也說:“其實,我并不用跟他爭論什么。”但問題是我已經跟別人爭論了。
年輕喇嘛說:“可是我們還是會相信下去的。”
我當然不必問他明知如此,還要這般的理由。很多事情我們都說不出理由。
這時,夕陽照亮了一川河水,也輝耀著列列遠山,一座又一座青碧的山峰牽動著我的視線,直到很遼遠的地方。
年輕喇嘛瞇縫著雙眼,用他那樣的方法看去,眼前的景象會顯得飄浮不定,從而產生出一種虛幻的感覺。
“其實,我相信師父講的,還沒有從眼前山水中自己看見的多。”
我的眼里顯出了疑問。
他臉上浮現出一絲猶疑的笑容我看那些山,一層一層的,就像一個一個的梯級,我覺得有一天,我的靈魂踩著這些梯子會去到天上。這個年輕喇嘛如果接受與我一樣的教育,肯定會成為一個詩人。
我知道,這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對方也只是說出自己的感受,并不是要與我討論什么。這些山間冷清小寺里的喇嘛,早巳深刻領受了落寞的意義,并不特別傾向于向你灌輸什么。
但他卻把這樣一句話長久地留在了我的心上。我站起身來與他道別請向你師父說得罪了,我不該跟他爭論,每個人都該相信良己的東西。
我走下山道回望時,他的師父出來,與他并肩站在一起。這時,倒是那在夕陽余暉里,兩個喇嘛高大的剪影,給人一種比一萬年還要久遠的印象。
一小時后,我下到山腳時,夜已經降臨了。
坐上吉普車,發動起來的引擎把一種震顫傳導到整部車子的每一個角落,也傳導到我的身子。我從窗口回望山腰上那座小小的寺廟。看到的只是星光下一個黝黑的剪影。不知為什么,我期望看到一星半點的燈光,但是,燈火并未因為我有這種期望才會出現。
那座小廟的建立很有意思。數百年前的某一天,一個犁地的農民突然發現一面小山崖上似乎有一尊佛像顯現出來。到秋天收割的時候,這隱約的印跡已經清晰地現身為一尊坐佛了。于是,他們留下了一名游方僧人,依著這面不大的山崖建起了一座寶殿。石匠順著那個顯現的輪廓,把這尊自生佛從山崖里剝離出來。九百年來,人們慢慢為這座自生佛像裝金裹銀,沒有人再能看到一點石頭的質地,當然也就無從想像原來的樣子了。
在藏區,這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
在布達拉宮眾多佛像中,最為信徒崇奉的是一尊觀音像。這不但是因為很多偉大人物,比如吐蕃國歷史上有名的國王松贊干布就被看成是觀世音的化身。而是因為這尊觀音像也是從一段檀香木中自然生成的。只是在布達拉宮我們看到的這尊自生觀音,也不是原本的樣子了。
這尊自生觀音包裹在了一尊更大的佛像里,里面到底是什么樣子,我們只能自己進行判斷或猜想了。
從此以后,我在群山中各個角落進進出出,每當登臨比較高的地方,極目遠望時,看見一列列的群山拔地而起,逶迤著向西而去,最終失去陡峻與峭拔,融人青藏高原的壯闊與遼遠時,我就會想到這個有關階梯的比喻。
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比喻。
一本有關藏語詩歌修辭的書中說,好的比喻猶如一串珠飾中的上等寶石。而在百姓日常口頭的表達中,很難打撈到這樣的寶石。我有幸找到了一顆,所以,經常會在自己再次面對同樣自然美景時像撫摸一顆寶石一樣撫摸它。而這種撫摸,只會讓真正的寶石煥發出更令人迷醉的光芒。
當然,如果說我僅憑這么一點來由,就有了一個書名,也太弱化了自己的創造。
我希望自己的書名里有足夠真切的自我體驗。
大概兩年之后,我為拍攝部電視片,在探秋十月去攀登過一次號稱蜀山皇后的四姑娘山。這座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就聳立在距四川盆地不過百余公里直線距離的邛崍山脈中央。我們前去的時候,巳經是水冷草枯的時節。雪線正一天天下降到河谷,探險的游客已斷了蹤跡。只在山下的小鎮日隆的旅館墻上留下了“四姑娘山花之旅”一類的浪漫詞句。
上山的第四天,我們的雙腳巳經站在了所有森林植被生存線以上的地方。巨大巖石的陰影里都是經年不化的冰雪。往上,是陡峭的冰川和藍天,回望,是一株株金黃的落葉松,純凈的明亮。此行,我們不是刻意登頂,只是盡量攀到高丁點的地方。當天晚上,我們退回去一些,宿在那些美麗的落葉松樹下。那天晚上下了一場大雪。早上醒來,雪遮蔽了一切。樹,巖石,甚至草甸上狹長的髙山海子。
我又一次看到被雪覆蓋的山脈一對列走向遼遠,一直走到與天際模糊交接的地方。這時,太陽出來了。
不是先著到的太陽。而是遽然而起的鳥類的清脆歡快的鳴叫一下就打破了那仿佛亙古如此的寧靜。然后,眼前猛地一亮,太陽在跳出山脊的遮擋后,陡然放出了萬道金光。起先,是感覺全世界的寂靜都匯聚到這個雪后的早晨了。現在,又覺得這個水晶世界匯聚了全世界的光芒與歡唱。
“太陽攀響群山的音階。”
我試圖用詩概括當時的感受時,用了上面這樣一個句子作為開頭。從此,我就把這一片從成都平原開始一級級走向青藏高原頂端的一列列山脈看成大地的階梯。
從純粹地理的眼光看,這是把低海拔的小橋流水最終抬升為世界最高處的曠野長風。
而地理從來與文化相關,復雜多變的地理往往預示著別樣的生存方式別樣的人生所構成的多姿多態的文化。
不一樣的地理與文化對于個人來說,又往往意味著一種新的精神啟示與引領。
我出生在這片構成大地階梯的群山中間,并在那里生活,成長,直到36歲時,方才禽開。所以選擇這個時候離開,無非是兩個原因。首先,對于一個時刻都試圖擴展自己眼界的人來說,這個群山環抱的地方時時會顯出一種不太寬廣的固守。但更為重要的是,我相信,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片大地所賦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會因為將來紛紜多變的生活而有所改變。
有時候,離開是一種更本質意義上的切進與歸來。
我的歸來方式肯定不是發了財回去捐助一座寺廟或一間學校,我的方式就是用我的書,其中我要告訴的是我的獨立的思考與判斷。我的情感就蘊藏在全部的敘述中間。我的情感就在這每一個章節里不斷離開,又不斷歸來。
作為一個漫游者,從成都平原上升到青藏高原,在感覺到地理階梯抬升的同時,也會感覺到某種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當你進入那些深深陷落在河谷中的村落,那些種植小麥、玉米、青稞、蘋果與梨的村莊,走近那些山間分屬于藏傳佛教不同流派的或大或小的廟宇,又會感覺到歷史,感覺到時代前進之時,某一處曾有時間的陷落。
問題的關鍵是,我能同時寫出這種上升與陷落嗎?
當云南人民出版社這次活動結束的時候,各路同行會師拉薩,新聞發布會召開時,租來作為會場的地方,竟然有一尊佛教中文藝女神央金瑪的塑像。這種情境當然只會在西藏出現。那么,就讓這尊女神保佑我,賜給我足夠的靈性與智慧,來達到我的目標吧。
當我成人之后,我常常四出漫游。有一首獻給自己的詩就叫做《三十周歲時漫游若爾蓋大草原》。
記得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我們嘴唇是泥,
牙齒是石頭,
舌頭是水,
我們尚未口吐蓮花。
蒼天啊,何時賜我最精美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