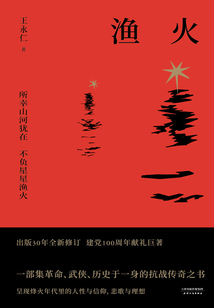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鐵飛還鄉
一
中國人沒有不知道水泊梁山的。水泊梁山八百里,何等壯美!可惜歷經滄桑,今日的水泊梁山只剩下四十五萬畝面積的東平湖。它的南面倒是有一個很大的湖泊,一碧萬頃,浩如煙海,地跨蘇魯兩省八縣,口銜徐州銅山,尾系古城濟寧。方圓千里的湖面,蘆蕩如云,碧荷接天;島嶼星羅棋布,兩岸山巒起伏;夏秋群魚歡躍,冬春大雁野鴨成陣。
相傳,商紂王的庶兄殷微子曾隱居此地。他死后就埋葬在湖南部的一個美麗的湖心島上,此島因此得名微山島,此湖也就叫微山湖了,當地人也叫它微湖。
微山湖素有“日出斗金”之稱,“微湖收,養九州”。但微山湖并非理想的安息之所。古往今來,每遇戰亂,群雄并起,烽火連年。世人都說:“天下未亂湖先亂,天下已平湖未平。”
一九三七年底,日寇大舉南侵,微山湖亂得越發不可收拾……
幾場風雪過后,微湖一片悲涼蕭索的景象。一行行大雁南飛,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消息:日軍兵渡黃河,占領省城濟南,韓復榘率十萬大軍不戰而逃,日軍沿津浦鐵路南下,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轉眼間,占泰安,下兗州,進濟寧……大好的山東河山相繼插上了太陽旗。
連日來,從濟寧潰退下來的官兵不停地向南滾動,蕩起的塵埃,把昔日明凈的微湖遮得灰蒙蒙的。急促的腳步聲、叫罵聲、車馬的喧鬧聲和女人的尖叫聲、孩子的哭聲混雜成一片。
起初,他們還敢沿著湖邊的公路成行成隊地走,后來,鬼子飛機一炸,中央軍就像黃河決了口似的離開公路,野坡里、小路上到處都是三五成群的敗兵。他們到處拉車牽驢,翻箱倒柜,沿途的村莊都被攪鬧得不安寧。老百姓叫苦連天,氣得直罵:“白養活你們這些‘遭殃’軍!鬼子還沒到,就腿肚子朝北了,丟下老百姓不管,還有臉來搶東西!”
傍晚,一團人馬開進湖邊的谷亭鎮,士兵亂紛紛地敲門砸鎖,四處尋找吃飯、休息的地方,頓時谷亭像滾了鍋似的,人哭鬼叫,雞飛狗咬。折騰了一夜,黎明時分剛剛平靜了下來,突然又被一陣亂槍驚動。官兵們如驚弓之鳥,提著槍就往街上跑,東邊的往西跑,西邊的往東跑,究竟發生了什么事,誰也不知道。
這時,一位魁梧彪悍的軍官從一家大門樓里跳出來,他手里提著匣槍,大步流星地向東走,在亂兵中沖開一溜胡同,沒有人敢攔他,也沒有人敢問。他那張棱角分明的臉繃得鐵緊,目光像兩把刀子,叫人望而生畏。他叫王鐵飛,原是該團三營八連的連長。三天前,在撤離濟寧的戰斗中,他被提升為營長,奉命據守草橋口,掩護全師撤退。他帶領全營官兵浴血奮戰,有效地阻擊了鬼子,完成了掩護任務。當他們要撤退時,已撤到橋南的周團副下令炸毀橋梁,切斷了他們的退路。三營面臨絕境,拼死抵抗,堅持到天黑,子彈打光了,才跳河泅水轉移。因為天冷,士兵都穿著棉衣,一跳進水里便寸步難行。鬼子居高臨下,用機槍掃射,百十號人就這樣慘死在河里。全營官兵僥幸活命的只有王鐵飛和七八個士兵。他們相擁大哭,發誓要找周團副算賬,為死難的弟兄報仇。
王鐵飛說:“周團副要置我于死地,早有預謀,這一次不過是他的借刀殺人之計,叫弟兄們也跟著我受連累。不殺此賊,我誓不為人!不過,你們不要再為此事冒險,砸了自己的飯碗。”
大家七嘴八舌地說:“這是大家的事,怎么能讓營長去冒險?”
王鐵飛擺擺手:“殺死周團副還不像踩死個螞蟻一樣容易?弟兄們用不著擔心。再說,他知道我還活著,我不殺他,他也要殺我。大家犯不著都跟著受連累。”
王鐵飛在兩小時前,悄悄地來到谷亭,他打聽到周團副正和幾個親信在一家地主宅院里喝酒。大門緊閉著,他越墻而過,摸到窗下,只聽屋里有人說:“王鐵飛這一死,黃少雄就沒有得力的幫手了,趁這個時候把他宰了,你就是我們的團長了。”
“別忙,等他睡熟了再下手。嘿嘿,明兒個我當了團長,你們幾位就是營長了。”
王鐵飛怒火萬丈,一腳踹開房門,躍了進去,炸雷似的大吼一聲:“周亮!見你的鬼去吧!”說著“嘩啦”就是一梭子,周團副和幾個親信頓時倒在了桌下。王鐵飛走過去,踢了周團副一腳,在他腦袋上又補了一槍,這才轉身往回走。王鐵飛突然出現在街上,他那殺氣騰騰的樣子,使士兵們立刻猜到剛才槍響的原因。
“快抓住他,抓住他呀!團副被他打死了!”一個渾身血跡的人從大門樓里爬出來,聲嘶力竭地喊叫。他是一營二連的連長,周團副的親信。他這一叫,證實了大家的猜想。沒有人理睬他,反而主動地讓開道,任王鐵飛自去。周團副一死,誰愿意與王鐵飛為難,自找麻煩?
二連長見士兵們不聽他嚷嚷,只好掙扎著爬起來去找團長黃少雄。
二
王鐵飛走出谷亭鎮,折向通往湖邊的小路。突然從后面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他不慌不忙,繼續往前走,聽到后面的馬蹄聲近,猛一轉身,同時甩手一槍。那騎在馬上的人急忙把頭一低,帽子被打飛了。他勒住馬,大叫:“不要開槍,是我!”
王鐵飛一看是團長黃少雄,便站住腳,把槍插回腰間,等他走近了,冷冷地問:“你想押我回去?”
黃少雄哈哈一笑,跳下馬來,親熱地拍著王鐵飛的肩膀說:“老弟干得好!除了我一塊心病。走,到那邊喝兩杯。”他指了指路對面的燕來酒店。
“不!我沒有工夫。”王鐵飛依然冷若冰霜。
“你這是怎么啦?信不過我?”黃少雄驚異地望著他。
“那倒不是。周團副是你的對頭,我殺了他,你自然高興,不會與我為難。但他叔是你的頂頭上司,周師長怪罪下來,你如何交代?”
“球!”黃少雄壓低了聲音說,“你再幫我一把,把他那幾個親信爪牙全干掉,周師長抓不到把柄,就沒咒念了。”
“我沒那個興趣。恕小弟不恭,告辭了。”
黃少雄急忙拖住王鐵飛一只胳膊,懇切地說:“你既然執意要走,我不留你,但咱們兄弟一場,臨別總得喝三杯吧。”
王鐵飛不好再推辭,隨他走進酒店。他朝店里望了一下,見一男一女兩位顧客已經占據了東邊的一張桌子,像是逃難的官員,桌下放著兩只皮箱。他倆在西邊一張桌子邊坐下。
等了好大一會兒,不見店家來。黃少雄不耐煩,啪啪地拍著桌子,罵道:“媽了個巴子,店里的人都死絕了!”
店家聞聲慌忙跑出來,點頭哈腰地說:“長官,實在對不起,不是小子不愿孝敬二位,小店實在沒有什么東西了。連日里過兵……”
“媽的!你向老子訴苦?老子的部隊可沒動你一根草棒!快拿酒來,少廢話!”
“長官,酒真的沒了,不信,你自個兒去找。”店家見過世面,知道如何應付搶吃搶喝的國軍,擺出一副愛莫能助的樣子。
“啪”一聲,黃少雄把匣子槍拍在桌上,向對面桌上斜了一眼,指著店家的鼻子罵道:“媽了個巴子,有他們吃的,就有我吃的。你小子耍滑頭,還得學三年!別找不素靜。”
店家嚇得臉色慘白,不敢吭聲了。王鐵飛掏出幾塊銀元扔給他,和氣地說:“快去吧,別惹團長生氣。”
店家見錢眼開,連聲道謝著退了回去。不一會兒,便從里面捧出一壇老酒,又端來四樣菜。
他倆對菜似乎沒有什么興趣,只要有酒就滿足了。黃少雄要了兩個大茶杯,斟得滿滿的。
“來,干!咱們兄弟一場,臨別喝個痛快,還不知今生能否再見。”黃少雄見王鐵飛真的要走,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揚脖子把酒灌下去。
一大杯酒落了肚,黃少雄的話稠了:“老弟,說句實話,為私為國,我都不該放你走。為私,你是我的好幫手,有你在,遇到什么硬仗、惡仗,我都不怕;為國,你是一員難得的虎將。現在國難當頭,正是用人之時……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啊!”
“為國,我寧愿戰死在沙場。可是上頭畏敵如虎,一味地后撤,叫人寒心。我沒臉再穿這二尺半。吃糧當兵,不為國出力,反去禍害百姓,我們有什么臉面去見家鄉父老?”
“英雄氣概!英雄氣概!”黃少雄苦笑了兩聲,“可是,真的要抗日,談何容易?沒有飛機大炮能打勝仗嗎?”
“怎么不能?人家八路軍在山西平型關不是打了個大勝仗嗎?!”
“區區小勝頂什么用?”黃少雄很不以為然,“我認為當務之急,是避其鋒芒,保存實力,等待盟國的援助,到那時,日本人不攻自退。”
聽到這里,王鐵飛把酒杯“砰”的一聲蹾在桌上,氣呼呼地說:“退讓、等待!等到什么時候?日本人已經占領了小半個中國,你還做‘等待盟國援助’的夢?軍隊不戰自亂,四散而逃,實力何存?什么盟國,去他娘的蛋吧,他們關心的只是瓜分中國。要救中國,只能靠我們自己,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靠民眾的大團結!”
“你從哪里學來的這一套?”黃少雄驚訝地望著他,“難怪周團副密告你是赤色分子,說出話來同共產黨如出一轍。”
王鐵飛哈哈大笑:“如果主張積極抗日就是共產黨,那么,我也算一個!”
“哎呀!你小聲點好不好?”
“怕什么?現在國共兩黨合作了,再想剿共可不得人心了。”王鐵飛毫無顧忌,嗓門更高了。
“好了,不談這些。何必這么憂國憂民?老弟,你今后打算怎么辦?”
“回老家,捕魚撈蝦,打野鴨子。”
“日本人打到家門口上來,你能在家里安心打魚?”
王鐵飛面紅耳赤。是的,國難當頭,匹夫有責,像他這樣的血性男兒決不會坐視不理。可是,下一步如何走,他不知道。想起剛才黃少雄說他是共產黨,他覺得可笑。此刻,他倒真希望找到個共產黨,問問該怎么辦。他認識一個共產黨人,不過,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黃少雄見他沉默不語,認為他又回心轉意,便挽留說:“你覺得回家有難處,就留下來吧。像你這樣的猛將,將來前途不可估量!”
“前途?什么前途?”王鐵飛不屑地哼了一聲,“國民黨軍隊腐敗無能,我早就待夠了!開弓沒有回頭箭,我走定了!”
黃少雄無限惋惜地搖搖頭說:“好吧,我把營長的位置給你留著,等你回頭想回來……”
“謝謝!”王鐵飛打斷他的話,決然地說,“我不會回來的!”
三杯酒喝干了,王鐵飛起身告辭。黃少雄從腰里掏出一個錢袋,放在王鐵飛面前。
“老弟,這是五百塊大洋,其中三百塊是我代你保存的積蓄,二百塊是老哥的一點心意。”
王鐵飛執意不肯收。黃少雄惱了:“你不收下,叫我出門挨槍子。”王鐵飛只好收下。
黃少雄笑了,拍著他的肩膀說:“這才像朋友。快走吧,我知道家鄉有位俊姑娘等著你,我留不住你。”
三
王鐵飛迎著早霞來到湖邊的渡口,見一只小船停泊著,船家正躺在船艙里睡覺。他走過去,把船家叫醒了。
“勞駕,搭你的船過湖到南壯去。”
船家伸了個懶身,拉下破氈帽,露出半邊臉來,上下打量一下王鐵飛,沒好氣地說:“哼,窮當兵的,俺不侍候。”
“你別怕,我可以先付給你船錢。”
“俺怕個啥?老天是老大,俺是老二。你們這號人,俺就是不載。”船家說罷,往船艙一躺,不再理睬他。
王鐵飛頓時火冒三丈,真想過去給他一腳,但他還是忍住了,去尋找另外的船只。可是,他在渡口上下來回走了幾趟,再沒有找到第二只船,只好又折回來。他正暗自盤算如何說服船家,忽聽得有人叫:“李老歪,別他娘的挺尸了,快來接接孤家。”
喊話的是燕來酒店的店家。
“喲,是錢掌柜的,什么風把你吹來了?”船家跳下船,一瘸一拐地迎上去,從店家手里接過兩個沉甸甸的皮箱。
店家的身后跟著一男一女。男的五十歲上下,身穿狐皮袍,頭戴水獺皮帽,腳上是一雙直貢呢的兔耳大棉鞋,他面目清癯,兩鬢斑白。那女子二十上下,穿著一件入時合身的花旗袍,楊柳細腰,粉白的臉蛋,一雙明眸,透著十二分俊秀。王鐵飛認得,正是在燕來酒店碰到的那兩位顧客。
“這位老爺要到戚城去,你小心地侍候。”
“錢掌柜的,你交我辦的事幾時出過差錯?”
“路上好走嗎?”那位老者有些不放心。
“老爺,坐我的船,你就把心放在肚里,保你一路平安。”船家李老歪滿臉堆笑地說。
王鐵飛隱在一旁的蘆葦叢里把這一切看在眼里。只等他們上了船,剛要離岸,他分開蘆葦,急跑了幾步,一縱身躍上船頭。
船家吃了一驚,看清了來者,立即暴跳起來,掄篙便打,喝了一聲:“你給我下去!”王鐵飛紋絲未動,船家反被震倒在船上。
“你這個人好不通情理,我又不白坐你的船,何苦要趕我下船?”
李老歪爬起身來,正要發作,只聽錢掌柜的在岸邊道:“李老歪,你小子瞎了狗眼,這位長官腰里有的是錢,出手大方得很,虧不了你。”
李老歪的臉上立刻堆起笑來,向王鐵飛作了個揖:“長官別見怪,俺有眼不識泰山,請艙里面坐。”
聽話聽音,察顏觀色,王鐵飛已明白這兩個家伙不是好東西。他故意把錢袋拿出來,在李老歪面前晃了晃說:“你小子把眼睜大點兒,這是五百塊大洋。”說罷,王鐵飛走進船艙。
那長者起身讓座,很客氣地說:“請坐吧。讓我們認識一下。我叫楚天章,她是我女兒筱蘭。”顯然他對王鐵飛有好感,很高興有這樣一位旅伴。
出于禮貌,王鐵飛也做了自我介紹,但他語氣很冷淡。他出身于貧寒的漁民之家,對闊佬總是看不順眼。
“你的老家在哪里?”
“湖東南壯。”
“南莊?”
“不,是南壯,”王鐵飛糾正說,“是壯志的壯。”
“哦,那是鼎鼎有名的村莊……”
王鐵飛打個哈欠,閉上了眼睛。
“怎么,你困了?湖上的風冷,當心著涼。”
“不怕,我的身子是鐵鑄的。”王鐵飛說罷,索性躺下來。沒有興趣和他談下去。
王鐵飛確實困了,一躺下來便呼呼入睡。船艙本來就不大,王鐵飛那魁梧的身軀一躺下來,便占據了絕大的空間,楚天章父女被擠到角落里。在生人面前,尤其是當著一個年輕姑娘的面就這樣四仰八叉地躺下去,是很不禮貌的。楚天章并沒有怪他,反脫下皮袍蓋在他的身上。
太陽偏西了,小船駛進了一片蘆蕩,只聽一聲呼哨,從斜汊里躥出一條大船,攔住小船的去路。七八個實槍荷彈的湖匪立在船頭。
“喂!李老歪,運的什么貨?”
“兩個肉票,一個花票。”
兩船靠攏了,從大船上走過來三個湖匪,堵住了艙口,同時嘩啦嘩啦拉響槍栓。
“快出來!”一個麻臉湖匪兇暴地命令。
“湖匪!”楚天章驚叫了一聲,站了起來,用身子擋住女兒筱蘭,顫聲地問,“你們要干什么?”同時伸出一腳,踢了踢還在熟睡的王鐵飛。王鐵飛沒有動。
“少廢話!快出來!不然老子一槍崩了你!”另一個粗壯的湖匪威脅說。
“這里有兩箱東西,你們都拿去,放我們走。”楚天章抑制著內心的恐懼,佯裝鎮靜地說。
聽說有東西,那麻臉立刻放下槍,走進船艙,一腳正踩在王鐵飛身上。王鐵飛一躍而起,飛起一腳,將他踢出艙外。站在艙口的粗壯的湖匪躲閃不及,也被砸倒了。另一個湖匪還沒弄清怎么回事,王鐵飛已躍出艙外一把奪過他手里的槍,同時伸出另一只大手扼住了他的脖子。李老歪見勢不妙,抽出一把尖刀向王鐵飛刺來。王鐵飛急閃身,那把尖刀不偏不斜插入湖匪的心窩,湖匪慘叫一聲倒下了。李老歪驚得目瞪口呆。王鐵飛大怒,劈胸一拳將他打下船去。
這時那粗壯的湖匪已爬起身來,舉槍正要向王鐵飛射擊,不想留在大船上的湖匪已經開了槍,差點射中他的腦袋。王鐵飛趁機就地一滾,躲進了船艙,順手將那麻臉湖匪拖進來。麻臉湖匪胸口挨了重重的一腳,疼痛難忍,哪還有力量抵抗。
槍彈飛蝗般地向船艙里射來,王鐵飛、楚天章、筱蘭都伏在船艙里不敢動彈。王鐵飛從腰里拔出匣槍,指著麻臉湖匪的腦袋,厲聲地說:“叫他們別打槍!要不,我就對你不客氣。”
麻臉湖匪嚇得渾身哆嗦,可著嗓門喊:“別打了!我……我是張麻子。”
槍聲果然停下來,只聽湖匪們狂叫:“快把張麻子放出來!”
“朋友,你們先閃開道,讓我們過去,我就放了他。”王鐵飛大聲說。
“娘的!你殺死我們兩個弟兄,還想逃命嗎?”
王鐵飛冷笑一聲,說道:“那是你們自己不長眼,誤殺了自己的人,我要是有心殺你們,早就用槍一個個把你們都點了。”
“你小子死到臨頭還敢吹大牛?!”
“你們到底閃不閃開?”
“不閃!”
“好!我先把張麻子點了,再收拾你們。”
張麻子一聽要殺他,殺豬般地嚎叫起來,指名道姓地破口大罵:“劉禿子,你個天殺的,你不閃開,要送老子的命嗎?”
大船上的湖匪嘀咕了一陣,把大船退回了汊道,閃開了路。
王鐵飛對楚天章說:“請你幫個忙,把外面那幾把槍撿回來。”
楚天章明白王鐵飛的用意,是為了防備湖匪的突然襲擊。他剛要動身,筱蘭卻搶在了前面,鼓起勇氣說:“爸,讓我去。”
“你?”王鐵飛懷疑地望著她。
她把頭一低,鉆出了艙口,不一會兒,便把槍拖了回來。
王鐵飛沒有想到這位弱不禁風的小姐竟會有這樣的膽量,稱贊道:“好,有種!會打槍嗎?”
“會!”楚天章、筱蘭一起回答。
“好!一人拿一支,隱蔽好。咱們得防備他們狗急跳墻。”王鐵飛說罷,把張麻子一手提起來,他向外面望了一下說,“還得勞你的駕,把我們送上岸去。可是,你要搗鬼,我的槍子可長著眼。不信,你看——”王鐵飛抬手一槍,一只野鴨子從天空中掉了下來。
張麻子驚恐地瞪大了眼睛,連聲說:“不敢,不敢!”
小船駛出了蘆蕩,慢慢向湖岸駛去。大船在后面不遠的地方跟著,但不敢靠近,也不敢開槍。他們看到王鐵飛的槍法那么準,真的打起來,不但張麻子小命難保,他們也占不了便宜,只得乖乖地把他們送上岸。
王鐵飛一看,東邊不遠就是戚城了,便對楚天章父女說:“不送了,你們走吧。”
“天這么晚了,你同我們一起去戚城吧,那里有我的表哥馮淵。”筱蘭搶著說,不知為什么她的臉紅了。
王鐵飛笑了笑說:“謝謝你們的好意,我還要連夜趕回家去。”
“急什么?住一夜,明天一早再回家也不遲。”楚天章也懇切地挽留他。
“不!我離家四年多,每時每刻都在思念親人,怎能不急?”
楚天章點了點頭,打開手里的皮箱,取出一對貓眼玉石,雙手捧送給王鐵飛,說道:“你救了我們父女,無以為報,就把它送給你做個紀念吧。”
王鐵飛的臉陡然變色,冷冷地說:“楚先生,你小看我了。”
楚天章一愣,這對貓眼玉石價值千金,他竟不為所動,心里贊嘆:“這才是真正的英雄啊!”連忙道:“失敬!失敬!你既不肯收,老朽只好收回了。今后有用著老朽處,當竭力相助。”
王鐵飛見小船已經離去,那湖匪的大船反而飛快地向岸邊駛來,便催促楚天章父女快走。他操起留在身邊的一支槍,瞄準大船桅桿頂部的篷索打了一槍,篷索應聲而斷,帆篷唰地落下來。大船失去了動力,停止不動了。他這才從容地離開了湖岸。走不多遠,只聽湖匪喊道:“你小子不要燒包,有種就報出你的名字來!”
“爺爺的名字叫王鐵飛,家住在戚城南,郗山北,微湖岸邊的南壯村!十五歲爺爺下濟寧州打過擂,十八歲大鬧戚城,坐過牢,當過兵,殺過東洋鬼子。你小子算什么東西?”
王鐵飛氣壯如牛,聲震四野。湖匪聽到他的名字再也不敢作聲。微湖上下,誰人不知,何人不曉,大名鼎鼎的王鐵飛!
四
王鐵飛五歲隨父習武,經過十年苦練,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本領在微湖首屈一指。他十五歲那年,適逢一貫道道首張天虎霸占運河碼頭,包辦航運,還在濟寧州太白樓下立擂,聲言“腳踢四方好漢,拳打五路英雄”,擂臺擺了十天,不知多少好漢毀在他的手下。張天虎氣焰更加囂張,自恃武功高強,搶男霸女,無惡不作。王鐵飛少年氣盛,瞞著父親,毅然登臺打擂。小鐵飛以武當絕技九宮神行掌,擊敗了不可一世的張天虎,從此名揚武林,被譽為“鐵掌小雷神”。
一九三二年夏天,“鎮街虎”劉哮林剛當上滕縣八區的區長,便以保護湖產為名,強令封湖,禁止湖漁民打蓮割葦。秋收時節,由政府組織采割,五五分成。禁令像一塊巨石投在平靜的湖面上,立刻激起軒然大波。
微山湖歷來是“免征地”“屯水區”,是萬民就食的地方。蓮藕、蘆葦自生自長,自古以來任人采割。沿湖的漁民,一無漁具,二無土地,全靠打蓮扒藕、割葦罱草維持生計。要封湖,“混窮的”只好像魚鷹一樣扎起脖子等死了。
戚城地下共產黨的負責人張光華挺身而出,組織發動上萬名湖漁民暴動,聚集了數百只漁船,架起鴨槍,趕走了劉哮林的水上封湖隊。湖漁民又涌進戚城游行示威。劉哮林竟命令警察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群眾,當場就有七八個倒在血泊里,張光華也身負重傷。王鐵飛怒火萬丈,率領青年敢死隊與警察展開殊死搏斗。憤怒的群眾像大海的怒濤,把警察摧垮了。他們又沖進劉府,痛打了劉哮林。這時,韓復榘的手槍旅趕來鎮壓,為掩護群眾疏散,張光華、王鐵飛和幾十名群眾被捕。
國民黨當局為平息民憤,不得不將劉哮林撤職,取消了封湖。一些被捕的群眾也陸續被取保釋放。但由于叛徒的出賣,張光華身份暴露,作為共產黨“要犯”被押往濟南。王鐵飛雖不是黨員,但因領頭“鬧事”,被判處五年徒刑,關進了滕縣大獄。不久他便越獄逃跑,到江西去投奔紅軍。不料紅軍早已北上,他只得再回山東,到濟南府去探聽張光華的下落。但他身無分文,一路上打拳賣藝糊口,歷盡艱辛,終于到了濟南。不想張光華又被押往南京。他有家難歸,只好去當兵……一晃就是四年。
王鐵飛回憶著往事,心情激憤,恨不得一步趕到南壯……
微山湖東岸,有一個蘆葦、荷花環抱的漁村。全村百十戶人家散居在一塊蒲扇似的孤島上,村東有一座玉帶似的石橋與陸地相接。橋下有一條小河,上通古運河,下連微山湖。
這就是王鐵飛的老家南壯。為啥叫南壯?說來話長。
這里原是一片荒草灘,清乾隆年間,有一位叫王窮的大漢流落到這里,他一貧如洗,全靠兩只手扒藕、割葦子為生。這一年,乾隆下江南,龍船到此擱淺。上百個纖夫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前進半分。王窮見了心下不忍,從葦垛上抽下鐵扁擔,往船底一插,輕輕一推,龍船便滑出了淺灘。乾隆又驚又喜,想留他御前聽用。王窮搖搖頭,裝聾作啞,擔起小山似的葦垛,揚長而去。乾隆問不出他的名字,以南下所見的第一位壯士,賜他封號“南壯”。事后,四鄉父老齊來祝賀,王窮反而不悅,又不好違了圣意,推說皇帝封的是這片新開的家園。你道他為何不高興?
原來他是位武當派的大俠,當年原是“紅花會”中一位響當當的人物。“紅花會”是反清的秘幫,以匡復漢家江山為己任,與清廷勢不兩立,后來乾隆厲行鎮壓,終于瓦解冰消。王窮隱姓埋名,來到這里隱居,娶妻生子。后來一些難民也陸續來此定居,人口繁衍,便形成了現在的村莊。由于他不肯接受乾隆的封號,人們便把這個村莊稱為“南壯”了。
王窮是南壯的驕傲。南壯人秉承祖訓,代代習武。而習武之風所以能夠經久不衰,還有另一個原因。這微湖的漁民因生產方式和所用漁具的不同,結成了“賣載幫”“大網幫”“槍箔幫”“罱網幫”四大漁幫。南壯的漁民皆屬于“賣載幫”。“賣載幫”主要靠裝載運輸、長途販運為生。冬季冰封不能行船時,便操起鴨槍打野鴨子。在那個弱肉強食的舊社會,你若不會點武藝,想在江湖上裝載行船,等于拿著小命做兒戲。不要說土匪強盜一路搶劫,光是那沿途的關卡、碼頭層層剝皮也夠人受的。從濟寧到徐州,僅這一段運河上就有二十四閘,閘閘有“閘官”。雁過拔毛,魚過揭鱗。船到碼頭,什么“靠岸稅”“貨物落地稅”“停泊稅”等等,名目繁多。所謂“貓子[1]上了岸,無罪三分過”,對湖漁民任意打罵罰款。所以每次裝載行船,他們必須攜帶武器,結伙成幫,集數十只,甚至上百只船一起行動,如出征一般,隨時準備拼斗。
到了眼下這個動亂的年頭,官府的苛捐雜稅加了又加,像山一樣壓得人們透不過氣來。各路的牛毛司令也來要糧要錢,說個沒有,就放火燒你的村子。連那些零星的“刀客”也來訛詐。有一天,南壯就收到了十幾張要糧要錢的條子。這不是成心要人命嗎?!大家都來找王老大商量怎么辦。
王老大是王窮的第七代長孫,王鐵飛的父親。他是村里的保長,也是湖漁民中賣載幫的幫主,名叫王志遠,但人們都尊稱他王老大。王老大自幼就在微湖、京杭大運河上裝載行船,走南闖北,經多見廣,深受人們的敬重。
“把村子封起來!”王老大說出他的主意,“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南壯人不是好欺侮的!”
“咱們光有鴨槍、抬桿,能頂得住嗎?”有人提出異議。
“我已經把家里的船賣了,從川軍逃兵手里買來了三支‘漢陽造’,一箱子彈。”王老大胸有成竹。
大家又驚又喜,又為王老大擔憂:“船賣了今后你指望什么養家糊口?”
“火燒眉毛,顧眼下要緊。等年景平穩了,大家再幫我排船。”王老大說。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王老大把村里的青壯年都組織起來,天天操練,日夜守衛。把鴨槍、抬桿架在石板橋頭,封住進村的唯一通道,又將大小船只齊刷刷泊在湖岸,以便應付不測。
這一天,湖匪杜二海領著手下的嘍啰來要錢,錢沒要到,反賠進去七八個弟兄、五條槍。杜二海落荒而逃,眾湖匪方知南壯的厲害,再不敢來找麻煩。南壯一下子又多了五條槍,群情振奮,索興拉起了“保家自衛團”,一不做,二不休,管你是官家、兵家、匪家,無理索要捐稅糧錢的,一概不交。
這一下可惹惱了劉哮林。劉哮林人稱“鎮街虎”,是戚城一霸。戚城是微湖首屈一指的大鎮,劉哮林原是滕縣八區的區長,管轄著半座戚城鎮,四個大鄉,四十八個村莊。反封湖斗爭后他被撤職查辦,但不久他又花錢活動,恢復了職務。人心不足蛇吞象,他一心想做微湖霸主。前些日子,他糾集了一百多條槍,打起“抗日救國軍第八團”的旗號,自封司令。南壯竟敢在他的勢力范圍內另立山頭,這還得了?更何況那王老大原是他的冤家對頭,一旦羽毛豐滿,必成心腹大患。他立即派衛隊長胡空帶兵馬去南壯收繳槍支。
“使不得!使不得!”參謀長孔玄連忙阻攔,“南壯是一片孤島,易守難攻。來硬的,恐怕占不了便宜。”
“那你說怎么辦?”劉哮林心里不痛快。
孔玄如此這般,說出他的韜略。劉哮林的臉上露出笑容,吩咐孔玄如計照辦。這孔玄生得干癟瘦小,獐頭鼠目,軍事上狗屁不通,肚里的歪點子卻是不少。他長著一張算卦先生的嘴,能把死人說活,活人說死。
當天下午,孔玄騎著個毛驢來到南壯,一見到王老大就稱兄道弟地說:“志遠兄見義勇為,率眾拒匪,為民除害,兄弟十分敬佩。劉司令特派我前來慰問。”
“不敢當。”王老大不熱不冷地說,“參謀長有話不妨直說。”
孔玄干笑了兩聲:“劉司令想與你聯合抗日,委任你當副司令。明天,請你把人和槍帶到戚城,接受改編。從今以后,南壯一切捐稅可以免除。”
王老大冷笑道:“劉哮林要是眼紅我們這幾條槍,就讓他來拿吧。我可不眼熱那個副司令。”
“別誤會!劉司令是一片好意。你要是執意不肯,惹惱了他,恐怕……”
“送客!”王老大憤憤地打斷孔玄的話,把手一擺,揚長而去。
孔玄被晾在那兒,沒人再理睬他,只好悻悻而去。人們望著他的背影,不禁大笑起來。
王老大知道劉哮林不會善罷甘休,一面組織村民們嚴加防范,一面將老弱婦孺轉移到船上去,以防不測。
五
就在這個緊張的夜晚,有一個人突然出現在村東的運河堤上,立刻引起了放哨的注意。那人打量著月光下的南壯,村子里寂靜無聲,但村西湖邊的漁船上燈火點點,人聲喧嘩。他邁開大步,飛身下堤,眨眼間便來到石板橋頭。忽見柳枝一擺,飄下兩片黃葉,卻又無風。他立住腳,把背上的長槍摘下來,靠在橋頭,不再往前走了。
這時從歪脖子老柳樹上“嗖”地跳下一人,照準他的腦門一刀劈去。只聽“咔嚓”一聲,劈個正著,那人連“哎喲”都沒喊,就栽進橋下水里去了。仔細一看,卻原來是半截橋欄漂在水上。他正要掄刀再砍,卻聽見那人叫自己的名字:“毛二旦,你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了。”
聽對方叫出自己的名字,他一愣,仔細打量一番,撲上去,驚喜地大叫:“鐵飛哥,是你!”
兩人緊緊地摟抱在一起。他倆同歲,從小在一起長大,秉性相投,情同手足。分別四年,一旦相聚,有多少話要說。但王鐵飛心情急切,問明了村里最近的情況,便把長槍留給毛二旦,讓他好好地看守著村口,急匆匆向村里走去……
家近了,鐵飛反而停住腳,打量著這臨水而立的院落:荊條編織的籬笆墻,錯落有序的草屋,挺拔高聳的鉆天楊,一切還是那么熟悉,那么親切。他輕輕地踱進小院,向堂屋走去。
堂屋門半掩著,一位瘦弱的老媽媽正跪在堂前的蒲團上,雙手合十,默默地禱告著什么。桌上擺著香爐,青煙縷縷。桌后的條幾上放著一盞豆油燈,燈火照亮了正墻上懸掛著的岳王神像。上有“還我河山”四個剛健的大字,鐵飛認得是二弟銀飛的手筆。想不到僅僅四年,他的字畫有這么大的長進。二弟自幼多病,身單力薄,有此神筆妙手,也不負父親的一片苦心了。父親長在亂世,年輕時參加過義和拳,與八國聯軍打過仗。他一不敬神,二不信鬼,唯獨敬仰精忠報國的岳飛,他給三個兒子取名為“鐵飛”“銀飛”“金飛”,希望他們長大成人之后能效法岳飛,為國盡忠。
這時母親正為兒子虔誠地禱告,突然覺得一只有力的手將她攙起,一個熟悉的聲音喊道:“娘,我回來了!”
母親回頭見是鐵飛,就臉色慘白地倒在兒子寬闊的胸上,閉上了眼睛。
“娘,是我,我是鐵飛呀!”鐵飛把母親扶到椅子上坐下來,跪倒在她的面前。
母親一雙顫抖的手胡亂地摸著兒子的頭發、臉頰、耳朵……哭著說:“你是鐵兒,你是俺的鐵兒!你到底回到娘的身邊了……”
“娘,我回來了,你老人家應當高興才是。”鐵飛忍著淚安慰母親。
母親撩起衣角拭去淚水:“乖孩子,快站起來,讓娘好好看看你。”
這時從門外蹦進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一手拿著魚叉,一手提著兩條大鯉魚,他忽閃著一對大眼睛望著鐵飛,問母親:“娘,這是誰呀?”
“憨小子,連你大哥都不認識了?”
“大哥?大哥回來了!”小金飛樂得一蹦三尺高,扔下手里的物件,雙手攀住鐵飛的脖子。
鐵飛把弟弟舉起來,驚喜地說:“三弟長這么高了。我教你的鴨行拳還記得嗎?”
小金飛掙脫了鐵飛,不以為然說:“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戲,俺現在跟爹學六合拳。”說著,他就要比畫。
鐵飛笑道:“不忙不忙,等有工夫,我再考你的武藝。”他轉向母親問道:“有東西吃嗎?我餓壞了。”
“哎呀!你看我,光顧著高興。”
母親慌忙去做飯,不想與急急趕來的王老大撞個滿懷。
“哎喲!你這死老頭子,進門也不吭聲。”
王老大顧不得答話,撲上前來抱住鐵飛,上上下下看了一遍,激動地說:“俺這不是做夢吧?真的是鐵兒回來了?”
王老大將兒子按在一條板凳上,忙不迭地詢問起來:“這些年你是怎么熬過來的啊?”
王鐵飛訴說了這幾年的經過,王老大聽了,沉思著說:“你回來得正是時候,這兩天風聲緊得很,劉哮林那龜孫想找咱們的茬兒。咱們村小人少,就那么幾條破槍,俺正愁不好對付。”
“怕什么!讓他來吧,我正想找他算賬哩!”鐵飛氣昂昂地說。他里里外外掃望了一下,問:“銀飛呢?”
“前幾天他就到湖西去了。”
“去湖西干啥?”
“聽說張光華從監獄里放出來了,回到老家張莊,正在組織什么抗日義勇軍。銀飛不知從哪里聽到的信兒,就約合著幾個同學投奔他去了。也不知現在找到了沒有。”
鐵飛忽地站起來:“那我明天也去湖西看看。”
“別忙,明天還有件頂要緊的事要你去辦。”
“什么事?”鐵飛不解地望著父親。
“到戚城去,先看看玉蓮。”
“玉蓮?玉蓮她怎么啦?”鐵飛急切地問。
“四年來,她一直等著你,不知流了多少淚,受了多少苦。像她那樣百里挑一的姑娘,在這動亂的年頭,守到二十一歲,不容易呀!快商訂個日子,把她娶進家來。”
父親的一番話,使他聯想起與玉蓮初會的甜蜜、鬧戚城同斗警察的深情、蘆花蕩絮語曼曼的溫馨、定婚時的海誓山盟。
王老大見兒子一言不發悶頭兒想什么,就把煙袋鍋往桌腿上一磕,說:“喂,俺說了半天,你聽到沒有?為啥一聲不吭?難道你把玉蓮忘了?”
“怎能忘了?”鐵飛漲紅了臉,“我明天就去。”
“這才對!”王老大笑了,拍了他一巴掌,又教訓道,“別看你是俺兒子,要是對不住玉蓮,俺第一個不答應!不過,你明天到戚城去,要當心,不要驚動了劉哮林那個龜孫。”
說到這兒,突然屋外傳來一陣笑聲:“哈哈,老遠就聞到香味,我當是大叔來了什么貴客,原來是鐵飛老弟回來了!你真是福大命大……哈哈!”
門口出現一個黑發油頭。他二十多歲,一副上寬下窄的醬色猴臉,淡眉下有一對圓麗靈活的眼睛,閃爍著狡黠、捉摸不定的幽光。他一手拿著啃了一半的煎魚,一手拎著半瓶白酒,耳朵上還夾著一根紙煙。
鐵飛認出是鄰居喬葦,販鮮魚的,此人能說會道,大秤買,小秤賣,會搗鬼做假。鐵飛對他沒有什么好印象,但還是站起來向他打招呼。
這時母親用托盤端上菜來,是紅燒魚、水熗蝦、炒鴨蛋、調藕片。
“呀!這么多好吃的東西。”喬葦大驚小怪地嚷叫著,“你這位得寵的‘太子’,大嬸把你捧上天了。”他像一只饞狗似的聞著菜,露出滿口細密而尖利的牙齒笑著。
“快吃吧,飯菜都要涼了。”王老大提醒他們。他不喜歡這個油嘴滑舌的鄰居。他收拾起桌上的東西,帶著小金飛走了。
母親把酒菜擺好,拉了條凳子坐在鐵飛的對面,一邊納鞋底,一邊守望著兒子。
鐵飛餓極了,顧不得喝酒,狼吞虎咽地吃著。喬葦不用人讓,自斟自飲,細細地品味,好像他是這里的主人。他邊吃邊評論:“嘖嘖,大嬸的手藝好極了,菜到嘴里滿口香,只是酒味太辣,配不上。喏,幾時能喝上你的喜酒?我可等得有些心急了。”
“我也想早一點。等辦喜事時,我想請朋友都來,當然也忘不了你。”
“好極!越快越好。要不,我真擔心夜長夢多會有什么變故。”
“你這是什么意思?”鐵飛停住了筷子,注視著對方。
“噢,沒有什么。”喬葦吞下一杯酒,“白玉蓮姑娘是戚城有名的美人兒,誰見了不愛?我敢打賭,圍著她打轉的小伙子不下一打。”
“真的嗎?”鐵飛微笑著,但微笑里含著不安。
“姑娘總是愛攀高枝的,而戚城有錢有勢又漂亮的公子哥有的是。”
“玉蓮不是那種人。”鐵飛不愿聽人非議他所鐘愛的人,玉蓮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位純潔高尚的姑娘。
“哈哈,鳥兒關進籠子才飛不了。姑娘過了門,才算是自己的媳婦。”
鐵飛把碗筷一推,瞬時沒有了食欲。
喬葦酒足飯飽,打著飽嗝,告辭而去。
注釋
[1]貓子:舊社會對湖漁民的侮辱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