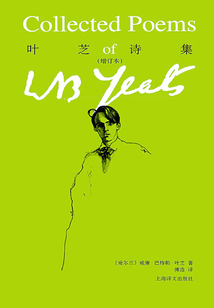
葉芝詩集(增訂本)
最新章節
- 第22章 注釋
- 第21章 附錄
- 第20章 最后的詩(1938—1939)[1063]
- 第19章 選自《在鍋爐上》[1051]
- 第18章 新詩(1938)[953]
- 第17章 帕內爾的葬禮及其它(1935)[904]
第1章 前言
一
我翻譯葉芝的緣起在別處已有所交代,茲不贅言。迄今為止,不算散見于各種書刊和網絡的零星發表和轉載乃至盜版外,計出版《葉芝抒情詩全集》(中國工人出版社,1994;1996年。譯詩374首)、《葉慈詩選》(英漢對照,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2001年。自選譯詩169首)、《葉芝詩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修訂譯詩374首)、《葉芝詩精選》(英漢對照,華文出版社,2005年。他人代選譯詩43首)、《葉芝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自選譯詩321首;劇本1部;短篇小說2篇;散文1篇)、《葉芝抒情詩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自選譯詩199首,包括新增譯詩4首)、《葉芝詩選》(時代文藝出版社,2012年,自選譯詩146首)、《葉芝詩選》(英漢對照,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5年。自選譯詩157首)等八種譯著。其中,華文版《葉芝詩精選》是由書商策劃并選編的,內容未經我過目,所選篇什既不代表葉芝創作,也不代表拙譯作的精華;時代文藝版《葉芝詩選》的責任編輯極不負責,我仔細校改過的校樣返回后,竟完全未用,而是用錯誤百出的第一次排版直接付印了,聽說同系列(外國經典詩歌珍藏叢書)其它詩選也是同樣遭遇。
凡我經手的,每次再版,我都要對照原文逐首逐字修改譯文。越是流行的篇什修改的次數就越多,遠多于再版的次數。我曾半開玩笑地對學生說:葉芝人稱“自我批評家”,對詩藝精益求精,幾乎每首詩都是改了又改,直至一字不易的完美。能給別人改稿的是編輯,能給自己改稿的才是大師。我只是努力向大師看齊,譯(藝)無止境,我的譯文迄今為止還沒有完全令我自己滿意。你們要學文學翻譯,只需把拙譯的新舊各版拿來對照著原文來比對研讀,肯定會有所得。不傳之秘即在其中矣,唯有心者得之。不過,在研讀之前,如果自己也先試譯一遍,效果會更好。我不怕獻丑,只當是現身說法,為翻譯事業做犧牲吧。
此次增訂,除《葉芝抒情詩全集》原有的374首譯詩又修改一過外,還新譯了葉芝生前未發表過的早期詩作38首,加上選自評論小冊子《在鍋爐上》中的3首詩,共得譯詩415首。本書雖仍未囊括葉芝所有詩作,但仍是現有收錄篇什最多的漢譯葉芝詩集了。
二
學界一般認為,葉芝早期詩藝主要受英國詩人埃德蒙·斯賓塞和珀西·比舍·雪萊的影響,但在他正式發表的作品中卻難覓例證。他的第一本詩集《烏辛漫游記及其它》(1889)主要是寫愛爾蘭題材的,只有部分涉及古印度和古希臘題材。誠如他在1925年所說:“許多詩,當然是那些關于印度或牧人和牧神題材的詩,肯定作于我二十歲以前,因為從我在那個年紀開始寫《烏辛漫游記》那一刻起,我相信,我的題材就變成愛爾蘭的了。”
1995年,斯克里布納圖書出版了喬治·伯恩斯坦整理編輯的《月下:威廉·巴特勒·葉芝未發表的早期詩》一書,收錄葉芝作于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詩作三十八首。這些葉芝生前因種種原因秘不發表的詩稿印證了學界的看法,其中有不少作品的確有模仿斯賓塞和雪萊等前人的明顯痕跡,大多抒寫遙想神仙英雄騎士淑女之類的思古幽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已開始表現愛爾蘭和詩人私生活題材了。
少年學藝階段不免模仿借鑒。葉芝還喜歡改寫來自蓋爾語或其他語種的作品譯文,有時甚至難免剿襲之嫌而為人詬病。《靜靜的在達吉斯坦河谷》一詩即據俄國詩人米哈伊爾·萊蒙托夫的《夢》改寫而成,較諸原詩,內容和措辭幾無二致。《泉水中一個靈魂》顯示了斯賓塞的影響,敘事詩《羅蘭爵士》則從題材到形式都亦步亦趨追摹斯賓塞。《烏辛漫游記及其它》出版后,葉芝曾寄給前輩英國詩人威廉·莫里斯一本。莫里斯以寫歐洲古典神話和中古英雄題材的敘事詩見長,見了他說:“你寫我這一類的詩。”于是乎對他大加獎勉,并答應為他寫書評。《流寇的婚禮》也是這類敘事詩之一,只不過場景設在了十七世紀的愛爾蘭,反映了葉芝在1885年結識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領袖約翰·歐李爾利之后的題材轉向;寫法則采用主人公對女友說話的戲劇獨白形式,較以第三人稱視點敘事的《羅蘭爵士》更具抒情性。《你懂的我的歌》、《灰發老人》、《谷地》、《狂風吹打的碉樓》也都是以愛爾蘭為場景的富有幻想色彩的小品。《居普良》、《日出》、《潘》則仍有古希臘的典故或意象或題材殘留。葉芝一貫反對在詩中采用現代工業意象,也許因此之故而獲評“無須是現代主義者而最現代”。《遮面的話音與黑暗的發問》中的有軌電車可以說是葉芝詩中絕無僅有的現代寫實形象,詩人生前未公開發表此詩也許就是因為其風格異乎尋常吧。《路徑》和《有關前世的夢》無疑是寫給葉芝的單戀對象茉德·岡的。《路徑》的結尾兩行與收入詩集《葦間風》(1899)的《他冀求天錦》一詩的最后兩行不無相似之處,甚至二詩的整體構思亦屬雷同,后者應該是基于前者的改作或重作。《有關前世的夢》含有紀實成分,頗涉隱私,不免令人聯想到葉芝在晚期詩作《他的記憶》(1926)中類似地珍藏的私房話。此詩的末行則可以為其另一首差不多作于同時的名詩《在你年老時》(1891)的末尾兩行半作注腳,比較而言更清晰地勾畫了“頭戴繁星冠”的愛神丘比特形象,并點明無緣之人不受愛神眷顧的寓義。
葉芝晚年自稱:“我們是最后的浪漫主義者——曾選用/傳統的圣潔和美好、詩人名之為/人民之書中所寫的一切內容、/最能祝福人類心靈或升級/詩作的一切作為主題正宗”(《庫勒和巴利里,1931》),這些早期詩作就是最好的證據。
三
瀏覽網頁時,偶然看到讀者評論另一種拙譯說:原作者的語言是海,譯者的語言只是池塘,不禁啞然失笑。這是說,譯者比原作者的詞匯量差遠了嗎?誠然,這可能是事實,但量化就是決定優劣的惟一標準嗎?在實際語篇中,兩種不同語言的詞匯量是不好相比的。從理論上講,除非譯者大量省略、合并,把近似的表達都譯成同樣,逐字對譯的譯文和原文的詞匯量應該是大致相當的。我猜想,他(她)的意思更可能是說,原文的文體華麗繁復,而譯文的文體樸拙單純吧?實際上,我在翻譯的時候,心中總是為讀者著想的,生怕用詞太生僻,太文雅,不合時宜,讀者看不懂。可現在有一種不正之風,推崇綺靡、生僻甚至怪異詞藻。例如今年高考,據說又有一位考生用文言文寫作文得了高分,其用詞之艱澀生僻令閱卷老師都汗顏拜服。實際上,在韓愈提倡“惟陳言之務去”的古文運動之后,古人也不會寫那樣佶屈聱牙的偽漢賦風或尚書體了;即便有,也不能算是好文章。我大學三年級初譯葉芝,楊周翰先生評曰:“太文雅”;趙蘿蕤先生指點曰:“要直譯”。可見,掉書袋、弄詞藻、尚文雅、喜意譯是初學者易犯的毛病,而初學者還自以為是優點呢。
最近,詩歌翻譯雜志《光年》編輯提問:作為譯者,有何經驗和體悟可以分享?我簡答如下:
學國畫,除書法基礎外,先學工筆,后學寫意是正途,否則易失之狂野粗陋。學譯亦然,應先求精確,以直譯為主,熟練后自會變通。以意譯為主,不是初學,就是外語不夠好,否則就是狂妄。
我常說,翻譯沒什么訣竅,只要兩種語言都好,都達到熟悉各種文體,能自由創作的水平即可,那么翻譯只是換一種說法而已;
不能全程使用純原文詞典(科技術語除外)做翻譯,說明翻譯水平還不夠高;用純原文詞典翻譯才是真正的翻譯;借助源語——譯語詞典的翻譯一半功勞應歸于詞典編纂者;
喜用華麗詞藻、成語、熟語、生僻語、陳腔濫調的文學用語,甚至生造詞語,都是初學者的表現;
譯后最好放一段時間再看,不要急于拿出去發表。人說翻譯是遺憾的藝術。我早年發表太快,后來譯著一有機會再版就修改,改無止境。自己能修改自己的譯作,是翻譯水平提高的標志,創作也是同樣;
我對譯詩的要求是:不增一字,不減一字,不錯一字,字字有著落;
譯者如演員,好的譯者應該是性格演員,千人千面;壞的譯者是本色演員,千人一面。譯者應隱身在譯作后面,而不應突出到譯作前面。曾見有譯者把莎士比亞也譯成現代自由詩模樣,這就近于埃茲拉·龐德所為了;
譯者憑借譯作說話,猶如創作者憑借原作說話。然而,文學評論者可以不懂創作,翻譯評論者卻不可不會翻譯,否則難以令人信服。然而,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弄不好會得罪人,甚至引火燒身。也許最好的評論是提供自己的譯文。
以上體悟,自己也并非時時處處都做得到,做得好,只因自己是過來人,愿與從譯(藝)同道共勉而已。總之一句話:寧拙勿巧。
我已故的武術老師常說:聽過不如見過,見過不如做過,做過不如錯過。就翻譯而言,我更多是個實踐者,而不是研究者。我做過,錯過,改過。
傅浩
2017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