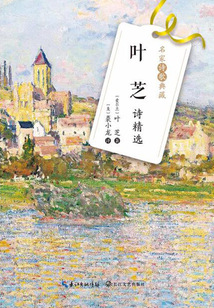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本前言 “把詛咒變成葡萄園”的詩歌耕耘[1]
裘小龍
威廉·勃特勒·葉芝(1856—1939),愛爾蘭現代著名詩人,192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葉芝對我國廣大讀者來說,雖然算不上太陌生,卻依然被了解得不夠深入。因為要了解一個偉大的詩人,尤其像葉芝這樣的詩人,既充滿了種種矛盾,又在漫長的創作生涯中寫出了不乏有機整體性的作品,就需要從相對來說的整體視角上來認識他的作品。葉芝自己作過一個比喻,作品就像一棵樹那樣成長、發展,根還是同一的根,但花與葉會呈現種種變化。
要了解葉芝的作品,我們得首先了解他的生平與作品之間的復雜關系。在用英語寫作的現代詩人中,葉芝大約是從他富有戲劇性的個人經歷中挖掘得最多、最成功的。然而,他又迥然不同于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詩人;如果說浪漫主義詩人的特點之一就是圍繞著“自我”抒情,葉芝的自我抒情卻充滿了現代意識和感性。他為詩中的自我戴上了不同的“面具”——這在后來被稱為“面具理論”;他同時又把自我和周圍的一切染上了一層層神秘甚至神話色彩,仿佛形成了內在的底蘊。作為后期象征主義的一個代表人物,他那一套獨特的象征主義體系也使他的自我內涵大大豐富、復雜了。因此,需要從這“有機整體”中個人化與非個人化層面來把握他的生平與作品。
葉芝出生于都柏林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父親是拉斐爾前派的畫家,喜歡把自己對文學藝術的一些獨到見解灌輸給兒子。童年時代的葉芝是幸福的,常常隨著家人去愛爾蘭北部的斯萊哥鄉間度假。當地迷人的風光,樸實又粗獷的農民,尤其是那種種廣為流傳的民間傳說,在葉芝幼小的心靈上激起了陣陣火花。還在很早的時候,他就對愛爾蘭鄉間盛行的神秘主義產生了興趣。1884年,葉芝進了藝術學院,但不久就違背父親的愿望,拋棄了畫布和油彩,徑自一心一意地寫起詩來了。他的處女作發表在《都柏林大學雜志》上,詩中清新的詞句,特別是愛爾蘭鄉間特有的神話意識,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
1887年,葉芝全家遷居倫敦。他結識了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和摩利斯等人,受到他們風格的感染,加入了詩人俱樂部。同時,他參加了當時著名的神秘主義者巴拉弗斯基夫人的一個“接神論”團體,還在這方面作了一些實驗,寫了一部題為《神話和民間故事》的著作。
1889年,葉芝與美麗的女演員茅德·岡相遇。關于他第一次見到茅德·岡時的情形,他后來曾這樣寫過,“她佇立窗畔,身旁盛開著一大團蘋果花;她光彩奪目,仿佛自身就是灑滿了陽光的花瓣。”她不僅苗條動人,還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愛爾蘭爭取民族自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這在詩人的心目中自然平添了一輪特殊的政治理想光暈。他在《當你老了》詩中贊美她“有著朝圣者的靈魂”,“朝圣”指的就是她所爭取的民族自治運動事業。他對茅德·岡是一見鐘情,更一往情深,但她卻一再拒絕了他的求婚。他對她的一番癡情始終得不到回報,“真像是奉獻給了帽商櫥窗里的模特兒”。她在1903年嫁給了愛爾蘭軍官麥克布萊德少校,這場婚姻后來頗有波折,甚至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可她十分固執,甚至在自己的婚事完全失意時,依然拒絕了葉芝的追求。盡管如此,葉芝對她抱有終身不渝的愛慕,他一生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也就充滿了難以排解的痛苦。
不過,對于詩人來說,一次不幸的愛情并不意味著詩歌創作的不幸。按照著名心理學家榮格的說法,詩人往往在他的無意識中需要這種不幸來寫出深沉的詩篇。痛苦出詩歌,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在數十年的時光里,茅德·岡不斷地激發起葉芝的靈感;有時是激情的愛戀,有時是絕望的怨恨,更多的時候是愛和恨之間復雜的張力。葉芝擺脫不了她,從葉芝最初到最后的詩集里,都可以看到她在葉芝心目中的不同映照。
而且,葉芝也或多或少是在她的影響下,進一步參加了愛爾蘭的政治斗爭。愛爾蘭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在當時是個比較復雜的歷史現象,人們對此持有不同的理解和態度。像茅德·岡這樣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主張通過暴力、流血的斗爭來實觀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只是手段和目的常常難以統一,他們采取的行動有時也導致了相反的結果。葉芝對此頗不以為然,但他后來又覺得,這些民族主義者的抗爭為愛爾蘭帶來了英雄主義的氣氛,達到了崇高的悲劇精神。這種矛盾的態度在葉芝的詩作中有充分的反映。在他自己看來,更重要的卻是通過作品來喚醒人民的民族歷史意識,他事實上也是更多地用他的作品參加了這場斗爭。這個時期,他的作品中出現了更遠大、壯麗的地平線。
1894年,葉芝遇見奧莉維亞·莎士比亞夫人,這也是對他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女人。奧莉維亞長得十分嫵媚,賦有一種古典美,她與葉芝很快就發展起熾熱的激情。葉芝在這段日子的抒情詩中有不少大膽、直露的描寫,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說是他們關系的折射。奧莉維亞曾考慮與葉芝結合,后因故未能如愿,但他們還是一直保持真摯的友誼。
1896年,在葉芝的生活道路上又出現了一個對他具有重要意義的女友,劇作家格雷戈里夫人。如果說茅德·岡給葉芝提供了創作的素材和激情,奧莉維亞·莎士比亞夫人給了葉芝生活中的溫柔和寧靜,格雷戈里夫人則為葉芝成為一個大詩人創造了寫作和生活的條件。出身貴族的格雷戈里夫人,賦有一種為貴族社會中的上層人士充當藝術保護人的責任感。她發現葉芝才華橫溢,于是充當起了保護人的角色。她在愛爾蘭西部擁有一座莊園(即葉芝詩中頻頻提到的柯爾莊園),她請葉芝到那里度假,使他能在那里安心從事創作,并讓他接觸到貴族社交活動,擴大、豐富了他的生活圈子。此外,她還慷慨地給了葉芝經濟援助,使葉芝不用像其他詩人那樣靠賣文度日。葉芝后來滿懷感激之情地說過:“對于我,她是母親、姐妹、兄弟、朋友;沒有她,我就無法認識這個世界——她為我動搖的思想帶來一種堅定的高尚性。”另一方面,格雷戈里夫人的影響反過來也加深了葉芝帶有貴族主義色彩的保守觀點。柯爾莊園成了一種有著無比美好的過去,但此刻就要消逝的存在的象征。甚至在葉芝后來圍繞拜占庭主題寫成的一些詩里,也因此流露出了對在貴族社會統治下的藝術家生活的留戀。
1904年,葉芝、格雷戈里、沁孤等人一起創辦了阿貝劇院,葉芝任經理,并為劇院寫了許多關于愛爾蘭歷史和農民生活的戲劇。在這些戲里,有不少用詩體寫成的“歌”,頗有獨特的韻味,后來也被收進了詩集。同一時期他還寫了一些明快、優秀的詩篇。在他看來,這是喚起愛爾蘭民族意識,從而贏得民族自治的重要途徑。葉芝和他友人的這些創作活動,后來被稱為“愛爾蘭文藝復興”,成了愛爾蘭文學史上的重要一頁。
從1912年到1916年,當時尚未成名的美國現代派詩人艾茲拉·龐德斷斷續續地為葉芝擔任助手工作。現代派正在西方詩壇崛起,龐德是現代主義詩歌的一個狂熱鼓吹者。據批評家的說法,龐德使葉芝的創作實踐更接近了現代派的傾向。不過,葉芝自己對此也是一直在摸索之中,他匯入現代派這股潮流,接著成了中堅人物,其實是必然要走出的一步。
葉芝在1917年轉而向茅德·岡的養女伊莎爾特莎·岡求婚,遭拒絕,翌年娶喬治·海德·利斯為妻。婚后,葉芝在離莊園不遠的地方買下了一座傾頹的古塔,把它修復后,攜帶妻子住了進去。黯黑而浪漫的古塔,在他詩意的想象中,與其說是一處棲身之所,還不如說是一個象征。殘破的塔頂仿佛象征他的時代和自己的遭際,塔的本身卻體現著往昔的傳統和精華。詩人攀上塔內的旋梯,從塔頂上向下俯瞰,沉思冥想,寫了不少以塔為主體象征的詩。
1921年,愛爾蘭獲得了自治領地位,葉芝出任自治領參議員,合家搬到都柏林居住。1923年他獲諾貝爾文學獎,在斯德哥爾摩受到了人們的熱情歡迎;他在獲獎答辭中謙虛地將自己的成就說成是愛爾蘭作家集體努力的結果,并再次提到了一些神秘主義詩人對他的影響。晚年的葉芝雖然得參加種種社會活動,但創作始終不衰,寫出了最為成熟的作品。他這時已成了英國詩壇上的執牛耳者,與現代派詩人有著更廣泛的接觸,還主編了《現代牛津英國詩選》。現代派詩歌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獲得了長足進展,葉芝在現代派詩人中也越來越多地顯示出了一種獨特的影響。
從1931年起,他的健康狀況開始漸漸衰退,不過他仍堅持寫作,出了幾本詩文集子。1938年初,他因腺瘤動了一次手術,可他在作品中反而更迸發出一股激情,甚至是浪漫主義激情的火焰,“當我奄奄一息時,我還會躺在床上想著我青春歲月中虛度的夜晚。”
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故人星散了,詩人自己也快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他回首往事,感慨萬端。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他對自己是懷疑的、不滿的,“我尋找一個主題,但總是徒勞。”在他的一生中,又有多少是自己想做而確實做成的呢?他的激情在思考中凝聚著,升華成一首首深刻的詩。1939年初他病逝,在最后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人們能體現真理但不能認識真理……抽象之物不是生命,處處都存在矛盾。”他的詩,卻絕非什么抽象之物,而是充滿了強盛的生命力,留在了他的身后。
國外的評論家常把葉芝的詩歌創作分成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的變化都與他個人經歷有間接或直接的關系,可以結合起來看,但我認為,更主要的還應該結合著詩人意識和詩學形式上的變化來看。
葉芝開始他的創作時,統治英國詩壇的仍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后期浪漫主義。詩人雪萊和布萊克等都對葉芝產生過影響。但到了十九世紀末,盛極一時的浪漫主義在英國已成了強弩之末,隨著社會危機的進一步深化、惡化,那種僅僅強調直抒個人情懷的詩篇,顯然無法對時代面臨的種種復雜問題作出有力的回答。在內容上,這些詩往往只是風花雪月的俗套,或是言之無物,或是無病呻吟;在形式上,傳統的抑揚格過分追求音韻的整齊,顯得圓熟而無新意,而在字面和格律上過分雕琢的要求,也給詩寫作帶來了很大的局限性。葉芝初期的作品多少也有這方面的不足。不過,他的作品由于大多取材于斯萊哥鄉間的生活經驗,從而獲得了一種獨特的逼真、清新的色彩。如《茵尼斯弗利島》一詩,就常被人認為是葉芝最富浪漫主義情調的代表作,但詩中出現的一些意象卻具體、硬朗,不同于當時流行的空洞陳腐的詩風,沒有局限在寫爛了的那一套上,反而充滿著民間文學中質樸的生氣。在作品里有時也會出現一種逃離現實的傾向,這也可以理解,畢竟,愛爾蘭面臨的眾多難題令人沮喪,個人生活中的挫折使他絕望。在稍后一段時間里,唯美主義詩風同樣對他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傳統的“歡樂的英格蘭”無法再作二十世紀田園詩的背景了,詩人只能懷著夢似的憧憬去找遠離塵囂的烏有鄉。不過,葉芝轉向了愛爾蘭民間的神話傳說去尋找出路,這在一方面突破了時間的局限性,讓凝聚著人類幾千年共同經驗的神話同時凸現著古今的共同性和不同性;也使詩有了莊嚴的歷史感和集體無意識深度。不少作品的力量正是來源于民族心理淀積。《誰和費古斯同去》就是這樣一篇成功地運用神話原型抒情的代表作。詩人對于理想世界的渴望,在神話傳說中的一個人物身上得到了折射,古代的人與現代的人有著本質上相同的向往,體現了愛爾蘭民族始終堅持著的“形而上”的追求。喬伊斯《尤利西斯》中的斯蒂芬,一想到母親就想到這首詩,從這一個例子中亦可以看到詩在愛爾蘭民族心理結構深處中所引起的共鳴。葉芝歌唱神話傳說中的英雄,固然主要是為了用過去的光輝幻象照亮現時的不幸,有些詩卻因此蒙上一層薄薄的神秘主義面紗。總的說來,這一時期的神秘主義成分在詩中所占的比例還是較小的。
1899年他來到都柏林。愛爾蘭民族自治運動的高漲,為他詩歌創作激發起了新的激情。在形式上,他開始追求一種雄渾有力、自然奔放的風格,為自己的詩在各個不同階層都贏得了讀者。他的語言一反當時流行的后期浪漫主義詩的雕琢和浮華,把十分流暢、清晰、富有活生生表現力的口語寫進詩里。雖然詩體大多還是沿用傳統的格律形式,卻是別出心裁地舊瓶裝新酒,成功地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種種復雜經驗。這段時間里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的“面具理論”的實踐。葉芝寫了大量似乎是從第三者角度抒情的抒情詩;這些第三者的形象與葉芝本人迥異——有乞丐、小丑、姑娘、老人,甚至擬人化的玩偶,等等。在以單一角度的自我抒情為主的浪漫主義詩歌中,從第三者(即某一個“他”)角度作出的抒情偶爾也是有的。葉芝詩中的第三者,卻并不是葉芝觀察的一個外在的對象,而是葉芝的第二自我、第三自我,或者說“準自我”。說得簡單一些,葉芝融入了這些對象;葉芝成了乞丐,成了小丑,成了粗漢。這些第三者形象的所說所作所思,正是葉芝處于這些人的地位時會說會作會思的。葉芝仿佛戴起了角色面具,在面具后抒情。詩中依然有詩人的聲音,但詩人的聲音和面具的聲音形成復調,反映了內心的矛盾性和豐富性。作品不再是單聲部的,而是多聲部的。按照現代心理學的研究,人們在面對父母、師長、雇主、情人等不同的對象時,其實也會進入截然不同的心理狀態,幾乎像是換了一個人,戴上了假面具似的。這樣的例子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其實并不少見。但是,到底哪一種“面具”是人真正的自我呢?似乎很難說。現當代心理學家還認為,如果一個人真正認為自己是另一個人,他或許可以發掘出他性格潛在的、卻被忽視了的另一面。現代派作家對人的幾重性格的發掘研究,更匯入到葉芝這一探索之中。對于渴望著新經驗的詩人來說,這自然也更使面具理論趣味盎然了。
《乞丐對著乞丐喊》就可以作一個例子。詩中的說話者是一個老乞丐,自然無法與葉芝畫等號,但乞丐卻用辛辣的語言吐出了葉芝自己所說不出口的一些想法。這些想法也許在葉芝腦海深處或者潛意識中閃過,但作為一個成名的詩人,他卻無法直接寫進作品。戴上面具后,真正融入乞丐的本體,許多先前不曾有過的思想、感受甚至經驗,也都逼真地涌上筆端,更從另一角度反映了心靈的豐富性,擴大了詩的表現領域。
同時,葉芝還把這些“面具”人物放到充滿戲劇性的處境中——或是一場爭吵,或是一次約會;而在這種戲劇性處境中的一個甚至兩個、三個人物都可能是葉芝的一部分自我,這就使作品具有更生動的深刻性。《英雄、姑娘和傻瓜》里三個人物處于一場“形而上”的爭吵中。他們各自顯露真實性格,不同的自我被刻畫得淋漓盡致;傻瓜在一旁發感想,有一種痛苦的幽默感,頗有莎士比亞戲劇中丑角的意味。有時這種丑角其實也是葉芝自我嘲諷、自我拆臺的那一部分人格。無疑,詩很難離開抒情主體即自我,但經過了這樣的“面具”處理,多少達到了主客觀之間的平衡,增添了充滿張力的強度。
葉芝自己說過,他的作品的特點是發出了“個人的(獨特的)聲音”,但他又認識到,僅僅是晚期浪漫主義那種個人的聲音無法構成作品的有機整體。在他早期的創作實踐中,他還發現沉溺于自己“個人的聲音”有著變為“個人的傷感”的危險。這樣,詩就不會去反映現實世界,而是陷入各種各樣的自我憐憫和自我陶醉。“個人化”成了“個人詩”,只是讓詩的表現領域越來越狹隘。在二十世紀初,由于人的異化危機加劇,詩人(個人)作為宇宙中心的浪漫主義概念的幻滅,“個人化”的詩也確實很難寫得好。另一個較葉芝稍晚的著名詩人艾略特,同樣主張“非個人化”的理論。雖然艾略特更強調這樣一點:詩不是詩人個性的直接流露,而是不帶個人感情色彩的技巧追求。但是葉芝與艾略特在反對個人直接抒情上異曲同工,葉芝關于“面具”的一些想法與寫法對以后的詩人也產生了影響。
1918年左右,葉芝詩中的象征主義技巧有了長足進展。從廣義上說,象征作為一種創作技巧早已有之,但在現代派詩歌發展史中,象征主義是最早崛起的有宣言、有理論的一個流派,也是最重要、最有收獲的一個階段。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象征主義詩人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主張與寫法;葉芝同樣也創建了他自己的一套象征主義體系。他的散文著作《幻象》對此作了專門的闡述。在他的一些作品中,月亮的運動和盈虧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總象征:月明、月暗、月圓、月殘,都體現了葉芝向往的變化中的統一。簡單地說,葉芝的象征也就是圍繞著主觀和客觀、變和不變的辯證關系展開的。這在葉芝看來,簡直是貫通天人,奧妙無窮,可以用來解釋世界的歷史和人類的命運。從真正的哲學意義上說,這種象征主義體系不免有幼稚的地方,但它滿足了他藝術創作的需要。在他這一時期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是旋轉的樓梯(或輪子)和傾頹的塔尖(或屋頂)。旋轉多少帶有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內涵,塔尖則往往意味著殘破的現代,然而廢墟上也會出現新生的理念。他那帶有貴族色彩的唯心史觀,使他在塔尖上是往后看的,因此拜占庭成了葉芝想象中藝術家的樂園。與此同時,他的象征主義體系又摻進了不少神秘主義的東西。在《幻象》中,他還畫過兩個交叉在一起的圓錐形圖案,一邊是“陽”,旁邊注著“空間、道德、客觀”;一邊是“陰”,旁邊注著“美感、時間、主觀”。它們代表了每個個人、每個國家,每個時代中的矛盾的成分,兩者都是存在的、互相轉化而又受到空間和時間影響、決定。葉芝把什么東西都囊括進去,仿佛冥冥之中先驗地有著這樣的圖案,一切都有了注定的開始和結局。
《麗達和天鵝》就是一首體現了葉芝獨特的象征主義的名詩。按照葉芝神秘的象征主義體系,歷史每一循環是兩千年,每一循環都是由一位姑娘和一只鳥兒的結合開始的。我們公元開始的兩千年是由瑪麗和白鴿(即圣靈懷孕說)引出,而紀元前的那一循環則由麗達和天鵝的結合產生。在希臘神話中,眾神之王朱諾變形為天鵝,使麗達懷孕產了兩個蛋,蛋中出現的是海倫和克萊斯特納。海倫的私奔導致了特洛依戰爭,而克萊斯特納和奸夫一起謀殺了阿伽門農。詩把麗達與天鵝的結合作為歷史的開端來寫,在“毛茸茸的光榮”和“松開的大腿”之后,卻呈現了“燃燒的屋頂和塔巔”。批評家們對詩中豐富的象征內涵眾說紛紜:有的認為葉芝的歷史透視觸及了人類歷史最根本的因果問題,也有的提出這里涉及到了人性、獸性、神性等復雜關系所形成的一個整體史觀。自然,將一首富有深度的詩局限于一種解釋并不足取,也不一定要把它作為一種歷史的解釋來讀,不同的讀者自可有不同的理解。其他一些詩,如《第二次來臨》等也都是從具體形象寫起的,但因為有了象征感,也就有了一種獨特的歷史感。
葉芝晚期的作品有一部分恢復到簡潔、豪放、粗獷的風格。一些組詩用民謠體寫成,仿佛詩人真回到了斯萊哥鄉間那些樸實的平民之中。較突出的是一組圍繞似乎瘋瘋癲癲的鄉下老婆子“瘋簡”寫成的詩。也可以說,此時的葉芝是戴上一個“老傻瓜”面具了。在一個人有限的生涯中,怎樣來最后看待“傻”與“不傻”,或者說“對”與“不對”呢?這是晚年的詩人回首往事時所面臨的問題。瘋簡的一些話似乎粗俗,但她是過來人,尤其在愛情上,她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知道愛情需要靈魂和肉體的統一。她老年的智慧更有一種酸蘋果似的澀味,一些漫不經心的話里其實充滿了深刻的反嘲。人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激情總是會受挫的,然而人又不能少了激情,正像黑格爾所說過的那樣,“沒有激情一切都是完不成的”。瘋簡充滿激情,又能嘲笑自己的激情,實際上達到了新的認識的高度。瘋簡這個形象包含了老年葉芝對生活的態度,一種既不同于浪漫派、也不完全等同于現代派的態度。
在他去世前兩個月,在一首題為《在本布爾本山下》的詩里,葉芝寫下了自己的墓志銘:“向生活,向死亡/冷冷看上一眼,/騎士啊,向前。”詩篇充滿激情,但又是包含在冷靜的認識里的激情,這也正是葉芝在文學上不懈追求的一生的寫照。
我們前面已談到,葉芝從事詩歌創作的歲月,正值英國詩壇經歷了滄桑變遷的年代——后期浪漫派、唯美派、象征派和現代派。葉芝在每個時期里都寫出了優秀的作品,取得了獨特的成就,這在現代英國文學史上可謂絕無僅有。
原因之一,可以說是葉芝兼收并蓄的創作實踐,也可以說是開放性的創作實踐。他從浪漫主義中走來,進入現代主義,卻始終保持了浪漫主義的一些特色。他知識淵博,算得上一個學院派詩人,但他的作品一直帶有民間文學的氣息。他反對把藝術作為廉價的宣傳品,可他自己卻又為愛爾蘭爭取民族自治運動寫出了輝煌的詩篇。難怪有的評論家至今驚訝于這樣一個事實:作為現代主義的著名代表詩人,在現代主義業已退潮的今天卻依然屹立著,令人贊嘆、深思。
西方有些評論家因此把葉芝稱為最大的、也是最后一個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抒情詩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狹義的現代派詩歌中,傳統概念上的“抒情”似乎成了一種格格不入的東西,甚至出現了“嘲抒情”和“反抒情”。法國著名作家馬爾羅摹仿尼采“上帝死了”的說法,宣稱“人死了”;意思是說,人在現代社會遇到異化危機,人已不是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性和荒誕性,弗洛伊德學說中關于人無法理解自己潛意識中一切的說法,都使傳統概念中的“人”動搖了;在浪漫主義幻想中作為“人類立法者”的詩人的地位也同樣崩潰了。許多現代派詩人有意識地在否定的形式中看待一切“浪漫”的事物;按照這種形而上的探索,世界是如此荒誕、無人情、非理性。于是,詩人一味個人化的抒情,就顯得膚淺和天真了。他們想當然的一個沖動反應就是用冷漠對冷漠,用荒誕對荒誕。現代西方社會中人性造成的扭曲和異化,也就這樣在現代派詩歌中得到了某些深刻的反映,但又畢竟不是全面的反映。從歷史的角度看,事物往往是螺旋式地發展的,有了一種否定,必將進入否定之否定。葉芝的獨特性恰恰在于沒有采取那種“見樹不見林”的否定。他在愛爾蘭人民的追求和斗爭中看到了人類感情的更高向往,盡管這條道路充滿挫折,但還是要走下去,不能在路旁永遠耽于幻滅、冷嘲和絕望。人道主義的理想不僅僅需要從否定的形式(如現代派)中表現出來,也需要在肯定的形式中繼續發展,因此也就應該存在這樣的抒情作品。葉芝用抒情來維護個人內心中殘剩的情感和尊嚴,盡管同時也對他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用自己的聲音作出了批判。于是,葉芝的抒情詩也就成了現代派反抒情傾向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對立面。這有它的歷史合理性。時代變了,人們的感受方式變了,抒情的方式更要變,變成一種更高形式的抒情。葉芝正是這樣吸收和發展了現代派的某些技巧,為詩歌創作不斷開拓出了新的領域。
當然,葉芝能這樣做,還由于他自身的客觀條件,也可以說是他的偶然性。當代蘇格蘭詩人紹利·麥克蘭在題為《葉芝墓前》的詩里就寫過這樣的句子——“你得到了機會,威廉,/運用你語言的機會,/因為勇士和美人在你身旁豎起了旗桿。”這里的“英雄”指的是愛爾蘭爭取民族自治運動的志士仁人,“美人”則是茅德·岡。他們引導著葉芝投入當時正義的斗爭,因此也就在這時代中獲得了他為之奮斗的信念,而這種信念(旗桿),對大多數現代派詩人來說,卻是可遇不可求的。愛爾蘭爭取民族自治運動的崇高性,使得愛爾蘭的精神氣氛不同于歐洲其他國家,用葉芝自己的話來說,也就是愛爾蘭有著“英雄的悲劇”的高度,這對葉芝的創作無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自然,一個詩人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時代,而在于他怎樣把自己出生的時代中的際遇最成功地寫入詩篇。
英國現代著名詩人奧登也寫過一首題為《懷念葉芝》的詩,其中有兩行這樣寫道:“辛勤耕耘著詩歌/把詛咒變成了葡萄園。”這里,奧登是從葉芝遭遇的不幸方面來著墨的。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葉芝一生中的“詛咒”,無論在個人生活或時代氛圍中都可謂多矣,但他恰恰是從這一切中寫出了輝煌的詩篇。因此,正像瑞典皇家學院主席哈爾斯特龍在授予葉芝諾貝爾獎的授獎詞中所說的那樣:“把這樣一生的工作稱為偉大,是一點不過分的。”
注釋
[1]語出英國現代著名詩人奧登(1907—1973)詩:《懷念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