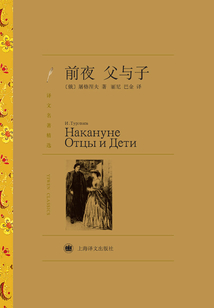
前夜 父與子(譯文名著精選)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譯本序
在世界文學(xué)中,也許很少有人像屠格涅夫那樣,作為一個(gè)小說家,卻不愧為抒情詩人;而作為抒情詩人,他又是現(xiàn)實(shí)主義者。他的詩神,溫文爾雅,但卻不是高居于奧林帕斯山上,不食人間煙火。他的筆端傾瀉的不只是“愛情、人世的悲哀、淡淡的哀愁、自由的熱烈頌歌、生之歡樂的陶醉”;而主要是“飛馳中”的社會(huì)生活的重大現(xiàn)象,是這些現(xiàn)象的藝術(shù)反映。
從十九世紀(jì)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俄國,正處于資本主義關(guān)系逐漸茁壯和封建農(nóng)奴制面臨崩潰的時(shí)代。與這個(g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條件相適應(yīng),貴族活動(dòng)家已喪失其歷史作用,代替他們,民主主義平民知識(shí)分子出現(xiàn)在社會(huì)舞臺(tái)的前景。屠格涅夫在這段時(shí)期的創(chuàng)作,正好是當(dāng)時(shí)歷史的紀(jì)錄。他以反農(nóng)奴制傾向的特寫集《獵人筆記》進(jìn)入文學(xué)之林,接著他以《羅亭》宣告了貴族知識(shí)分子成為“多余的人”的判決,又以《貴族之家》唱出了貴族階級(jí)“黃金時(shí)代”消逝的挽歌。在這以后,社會(huì)上在等待著,屠格涅夫下一部小說將以什么人為主人公呢?果然,屠格涅夫不負(fù)所望,在自己新作中,塑造了平民知識(shí)分子的“新人”形象,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由新的活動(dòng)家來推動(dòng)的歷史趨向。這就是放在我們面前的《前夜》(1859)和《父與子》(1861)。就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成就來說,兩者可算是他創(chuàng)作中的雙璧。
遵循形象思維的藝術(shù)規(guī)律,以生活為“藝術(shù)的永恒淵源”,是屠格涅夫的創(chuàng)作原則。他從不“從觀念出發(fā)”來“創(chuàng)造形象”,總要有“活人來做依據(jù)”,但又不是依樣葫蘆,而是把生活“升華為詩的理想”。他力求把握生活的“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透過“偶然性的變幻”捕捉到時(shí)代的典型。《前夜》中英沙羅夫的原型,是一個(gè)姓卡特拉諾夫的保加利亞愛國者,他曾在莫斯科大學(xué)讀書,一個(gè)少女愛上了他,跟他一起去保加利亞,后來他們一度回到俄國,不久他在威尼斯病故[1]。屠格涅夫從友人那里得到關(guān)于他的記載,敏銳地從他身上看到自己“要找尋的主人公”,自己在構(gòu)思中的那個(gè)“對(duì)自由懷著朦朧而又強(qiáng)烈的渴望的葉琳娜愿意為之委身的主人公”。那是在一八五五年。但只有到了農(nóng)奴制改革的“前夜”,當(dāng)他在俄國生活中看到英沙羅夫那樣的人物的時(shí)候,才在作品中塑造他的形象,使之成為“新時(shí)代的預(yù)言者”。《父與子》里巴扎羅夫的原型是某縣醫(yī)生德米特里耶夫。屠格涅夫一次在旅行中與他邂逅,深深為他的鋒利獨(dú)到的見解而吃驚,從這里敏銳地感覺到那時(shí)“剛剛產(chǎn)生、還在醞釀之中、后來被稱為‘虛無主義’的因素”,抓住了六十年代民主主義平民知識(shí)分子的特性。他心中孕育著這個(gè)形象,并不斷地概括“巴扎羅夫們”以及所熟悉的貴族友人的品性,終于創(chuàng)造出“父”與“子”的典型,反映了當(dāng)時(shí)兩種歷史力量的斗爭。可以說,凝視當(dāng)前現(xiàn)實(shí)的現(xiàn)象,深入了解其底蘊(yùn),敏捷地抓住時(shí)代的脈搏,藝術(shù)地加以反映:這一切正是屠格涅夫之所以成為大作家的主要原因。
下邊談?wù)劇肚耙埂泛汀陡概c子》寫作時(shí)期的作者的思想狀況。屠格涅夫?qū)儆谫F族自由主義者,這是眾所周知的。貴族自由主義者是資產(chǎn)階級(jí)化了的貴族,在四十年代剛出現(xiàn)時(shí)尚有其進(jìn)步的意義。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在消滅農(nóng)奴制問題上,他們同民主主義者還是基本一致的。一八五五年以后才開始發(fā)生了變化。克里米亞戰(zhàn)爭的失敗,暴露了俄國專制農(nóng)奴制度的腐朽。于是,“被活埋了的俄國”“睜開眼睛”從墳?zāi)估镒吡顺鰜恚ㄋ顾鞣蛘Z),社會(huì)上各個(gè)階層都感到改革的必要,農(nóng)民起義的浪潮也日益高漲。新皇亞歷山大二世被迫宣布準(zhǔn)備實(shí)行農(nóng)奴制改革,并且稍稍放寬書刊的審查。社會(huì)上出現(xiàn)了空前活躍的氣氛,當(dāng)時(shí)輿論的大膽曾使剛從流放回來的謝德林感到驚奇。但是,如果說在尼古拉一世(他死于一八五五年)的高壓統(tǒng)治下,自由主義者對(duì)沙皇政府還抱著對(duì)抗的情緒,那么現(xiàn)在,在表面上“自由”的氛圍中,在新的革命形勢(shì)下,卻漸漸趨向同政府妥協(xié)了。面對(duì)農(nóng)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道路的問題,他們同革命民主主義者產(chǎn)生了分歧。革命民主主義者主張把土地?zé)o償?shù)胤纸o農(nóng)民,寄希望于農(nóng)民革命。自由主義者雖然也同意分配土地,卻要收取大量贖金;他們害怕革命,擁護(hù)沙皇“自上而下”的改革。到了一八六一年二月農(nóng)奴制改革法令頒布,其欺騙性質(zhì)暴露以后,兩派“越來越清楚地、明確地、堅(jiān)決地分開”[2],形成了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而自由主義者也開始變成一種保守的以至反動(dòng)的力量了。這個(gè)歷史的交界,也是屠格涅夫思想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折點(diǎn)。
一般說來,屠格涅夫的思想演變同自由主義者可說是亦步亦趨的。但是正像個(gè)性不能完全包括于共性一樣,屠格涅夫也不能完全歸結(jié)為自由主義者。而且作為作家,他在創(chuàng)作中所表現(xiàn)的思想又有其矛盾的地方。的確,屠格涅夫像有人指出的那樣,具有啟蒙者的某些特點(diǎn)。例如,“強(qiáng)烈仇視”農(nóng)奴制,“熱烈擁護(hù)”全盤歐化,“衷心相信”農(nóng)奴制廢除“就會(huì)有普遍幸福”并“促進(jìn)這一事業(yè)”[3]。但是,屠格涅夫只是“溫和的啟蒙者”,他的出發(fā)點(diǎn)是資產(chǎn)階級(jí)人道主義,他只是同情人民而不是站在人民一邊,帶有明顯的人道主義雙重性。一方面,在他看來,農(nóng)奴“應(yīng)該享有人權(quán)”(加里寧語),他同情農(nóng)奴制下農(nóng)奴備受欺壓的無權(quán)地位,揭露壓迫農(nóng)奴的貴族地主,包括自由主義者(從《獵人筆記》到《前夜》、《父與子》);另一方面,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在談到改革前夜需要的英雄人物時(shí),特地注明“不是指的人民”,他認(rèn)為革命的因素不存在于人民身上,而“只存在于有教養(yǎng)階級(jí)的少數(shù)人之中”。一方面,他“真誠地”希望農(nóng)奴制改革與一般自由主義者不同,他看到貴族地主在“表面上情愿(改革)的后面隱藏著極度頑固——既恐怖又吝嗇”,他慶幸農(nóng)奴制改革“不會(huì)后退”,他憂心忡忡,唯恐貴族農(nóng)奴主阻撓改革,希望通過科學(xué)和文學(xué)喚起俄國進(jìn)步力量支持政府實(shí)現(xiàn)這個(gè)“皇上的高尚意圖”;另一方面,他畏懼農(nóng)民革命,深恐“革命發(fā)生,全部貴族都將被絞死”,認(rèn)為“我們不應(yīng)通過這條道路前進(jìn)”。思想立場上的這些矛盾,終于導(dǎo)致了他同革命民主主義者及其刊物《現(xiàn)代人》的徹底決裂。
《前夜》和《父與子》正好寫成于作家思想創(chuàng)作轉(zhuǎn)折的前夕,從這里可以看到他當(dāng)時(shí)的思想矛盾的折射。一般認(rèn)為,屠格涅夫在《父與子》里取得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勝利,但這也只是因?yàn)樗拿艿乃枷胫蟹e極因素占了上風(fēng)。作為作家,屠格涅夫不同于他的文學(xué)界自由主義的友人德魯日寧、安年科夫、包特金等人。他們都受過別林斯基的熏陶。德魯日寧等人在五十年代,早就成為純藝術(shù)的鼓吹者;而屠格涅夫,特別在創(chuàng)作中,仍然基本上遵循別林斯基的遺教,忠實(shí)地反映客觀現(xiàn)實(shí)。固然,在一八六二年以后,屠格涅夫也有過唯美主義的傾向(如《夠了》和《幻影》),也公開誹謗過革命民主主義者(如《煙》),但他的立場是動(dòng)搖的、矛盾的。他始終沒有陷入反動(dòng)陣營,也沒有像皮謝姆斯基、岡察洛夫、列斯科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卷入“反虛無主義小說”的逆流。
如果說,評(píng)價(jià)作家的立場,不能離開他的作品,那么,分析作品的思想,則主要應(yīng)著眼于藝術(shù)形象。
杜勃羅留波夫關(guān)于《前夜》曾經(jīng)寫道:“他(屠格涅夫)意識(shí)到,以前的英雄已經(jīng)完成了自己的事業(yè)……就決定放棄他們,從某些片斷現(xiàn)象中抓住生活新要求的趨勢(shì),試行站上今天進(jìn)步運(yùn)動(dòng)所循以實(shí)現(xiàn)的道路上。”[4]小說的布局正好體現(xiàn)“以前的英雄”為“新人”所代替的過程。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舒賓和伯爾森涅夫。舒賓具有藝術(shù)家的氣質(zhì)和才華,機(jī)智而樂觀。但是他玩世不恭,沉湎于個(gè)人的幸福。對(duì)于藝術(shù),他也只是隨興之所至,當(dāng)作玩樂,而不愿下苦功夫。與他不同,伯爾森涅夫嚴(yán)肅、好學(xué)、鍥而不舍。他不為世俗的樂趣而動(dòng)心,熱烈追求學(xué)術(shù)上的成就。他常常感到個(gè)人幸福同責(zé)任感的矛盾,但他善良,他可以為責(zé)任而犧牲個(gè)人的幸福。不過,伯爾森涅夫也只是不能高飛的燕雀,他的可憐的理想無非是當(dāng)一名教授,他脫離生活而遁入古代文化。饒有意思的是,在《前夜》初稿中,他談到過“人民”、“真理”等字眼,在定稿時(shí)作家都給刪掉了。
在俄國十九世紀(jì)三十年代,許多人曾醉心于藝術(shù),而在四十年代,則曾迷戀于學(xué)術(shù)。舒賓和伯爾森涅夫所向往的正好一個(gè)是純藝術(shù),一個(gè)是純學(xué)術(shù)。他們作為五十年代的貴族優(yōu)秀人物,已經(jīng)沒有他們前輩羅亭那樣追求崇高理想的激情了。他們不是農(nóng)奴制改革“前夜”所需要的。時(shí)代的英雄只能是平民知識(shí)分子的代表,這就是英沙羅夫。
英沙羅夫是保加利亞富商的兒子,他的祖國被土耳其人占領(lǐng),父母都遭土耳其人殺害。他立誓要洗雪國恥家仇,內(nèi)心燃燒著為解放祖國而獻(xiàn)身的感情的火焰。他堅(jiān)強(qiáng)果斷,沉著寡言,講究實(shí)際,言行一致。他目標(biāo)明確,心不旁騖。他外表羸弱,卻蘊(yùn)藏著勇士般的力量。他將整個(gè)身心獻(xiàn)給祖國解放事業(yè),準(zhǔn)備為此犧牲一切,包括愛情,如果它妨礙他的事業(yè)的話。他能團(tuán)結(jié)同胞,并在他們中間享有信任和威信。如果說舒賓恣縱感情而獵逐幸福,伯爾森涅夫遵循理智而有強(qiáng)烈責(zé)任感,那么對(duì)英沙羅夫說來,個(gè)人追求和社會(huì)責(zé)任是和諧一致的。這是社會(huì)地位使然,他的國恥家仇是連結(jié)在一起的。
《前夜》反映的是改革的“前夜”。社會(huì)必須改革,這個(gè)問題深深激動(dòng)著屠格涅夫。改革有賴于“自覺的英雄性格”[5]。他清醒地看到,在貴族中,即使是優(yōu)秀分子,也不能肩任這樣的歷史任務(wù)。要尋找“新人”。這種“新人”,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一八五八年曾在文章中提到,他們?cè)谏钪幸泊_實(shí)已經(jīng)出現(xiàn),雖然還是罕見現(xiàn)象,其代表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等民主主義平民知識(shí)分子。屠格涅夫從生活中得到啟示,就以平民知識(shí)分子代替貴族活動(dòng)家作為文學(xué)的主人公,明確地表達(dá)了歷史發(fā)展的要求和趨向,并在俄國文學(xué)史上打開嶄新的一頁。這是他在思想上和藝術(shù)上的不朽成就。但是這種成就不僅僅由于他的藝術(shù)敏感,而主要由于他的“藝術(shù)上的自我否定”,他“強(qiáng)迫自己的審美感,遷就于固執(zhí)的……高尚的心靈傾向”,而使貴族的優(yōu)秀代表在精神上為英沙羅夫所戰(zhàn)勝。[6]可是事情還有另一個(gè)方面。英沙羅夫是保加利亞人,目標(biāo)是解放祖國,他要與之斗爭的是外部的敵人,是土耳其占領(lǐng)者。而當(dāng)時(shí)俄國社會(huì),像杜勃羅留波夫說的,需要的是俄國的英沙羅夫,要反對(duì)的是內(nèi)部的敵人,即以沙皇為首的農(nóng)奴主和專制農(nóng)奴制度。因此可以說,英沙羅夫同當(dāng)時(shí)俄國的需要還是有一定距離的。這也不是屠格涅夫藝術(shù)上的失算,而是由于他的思想立場的限制。屠格涅夫以人道主義來反對(duì)農(nóng)奴制,他只渴望“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贊成革命。他所隱憂的不是這種改革的有名無實(shí),而是貴族頑固派的阻撓改革,因而認(rèn)為,俄國需要團(tuán)結(jié)有教養(yǎng)階級(jí)一切進(jìn)步力量同農(nóng)奴制斗爭,而人民則只能跟隨前進(jìn);這就需要像英沙羅夫那樣的人物,團(tuán)結(jié)包括“最貧苦的農(nóng)民和乞丐在內(nèi)”的“保加利亞人”以爭取“整個(gè)民族的解放”。這也就是幻想以民族解放代替社會(huì)革命,以各階級(jí)的聯(lián)合來代替農(nóng)奴反農(nóng)奴主的斗爭。不僅如此。對(duì)于英沙羅夫,他的態(tài)度也是矛盾的。他推崇他的高尚和愛國主義,卻不完全同情他的革命理想和行動(dòng)。他把英沙羅夫看作堂吉訶德[7],也就是雖然忠于理想,但卻是徒勞無補(bǔ)的。因此,不僅沒有表現(xiàn)英沙羅夫的行動(dòng),使其在那“戀愛應(yīng)當(dāng)讓位給公民活動(dòng)的地方”就中斷了生命;而且通過舒賓所塑造的兩個(gè)英沙羅夫塑像,表明作家自己對(duì)他又愛又憎的兩種感情。正因如此,作家不能滲透到這個(gè)人物的心靈:英沙羅夫做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都是一個(gè)沒有答案的謎,以致這個(gè)藝術(shù)形象的輪廓有點(diǎn)模糊。
從形象豐滿來說,應(yīng)推女主人公葉琳娜。她是中心人物,不僅情節(jié)圍繞她而展開,所有人物的優(yōu)缺點(diǎn)也由她來衡量——“自覺的英雄性格”就是通過她來選擇的。她有性格形成的歷史。父親是空虛的卻不嚴(yán)厲的自由主義者,使她能養(yǎng)成自由的性格;母親多愁善感,因丈夫不忠實(shí)長期感到壓抑,又孕育了葉琳娜同情心的幼芽。但這種同情心主要還是由社會(huì)培養(yǎng)出來的。她常常夢(mèng)見貧苦的人,正像杜勃羅留波夫指出,當(dāng)時(shí)俄國社會(huì)中“一切優(yōu)秀事物不都是在這一類印象中成長和得到鍛煉的嗎”?她渴望積極的行動(dòng),不僅做好人,還要做好事。她單獨(dú)成長,習(xí)慣于冷靜分析,具有獨(dú)立思考的能力。庸俗無聊的家庭使她感到孤獨(dú)和苦悶。她早就憧憬?jīng)_出這個(gè)無形的樊籠,缺乏的只是一個(gè)可以信賴的理想人物給她指明道路。舒賓雖有才華卻華而不實(shí),伯爾森涅夫雖然淵博卻目光短淺,更不用說庫爾納托夫斯基,此人雖然干練而講實(shí)際,但卻那么庸俗!她所傾心的只能是英沙羅夫那樣既有崇高理想又能腳踏實(shí)地的實(shí)踐家。“解放自己的祖國!”她從這句“偉大”的話里看到自己所探求的理想的體現(xiàn)。屠格涅夫以描寫少女著稱,而葉琳娜則是他筆下最完美的形象。要知道他的少女形象是以理想見勝,但是娜達(dá)莎(《羅亭》)或麗莎(《貴族之家》)所憧憬的卻只有理想的形式,而葉琳娜的理想才獲得具體的內(nèi)容。英沙羅夫像磁石那樣吸引了她,她多年潛伏的感情像春潮那樣奔涌出來。通過日記作家縷述了她的隱秘的心理活動(dòng),讓她弄清了自己的情感。她果敢堅(jiān)決,主動(dòng)地三次訪問了英沙羅夫。社會(huì)的輿論只配受她蔑視,家庭父母是她早要掙脫的羈絆;英沙羅夫要回祖國,等待著他們的是貧困、艱險(xiǎn)和屈辱……這些絲毫也不能阻撓她前進(jìn)。她愛上他,就無保留地把自己同他的命運(yùn)連在一起。可以說,到此為止,這個(gè)形象是鮮明的、完整的。而下文卻稍稍有了變化。“歡樂極兮哀情多!”在他們結(jié)合后,作品的情節(jié)急轉(zhuǎn)直下。但是,作家似乎不忍他們這么匆匆地喝完了人生的苦酒,給他們安排了威尼斯之行。在這水都,作家以其詩意盎然的抒情筆觸抒寫了他們甜蜜的可卻是曇花一現(xiàn)的幸福,馬上又以神秘的悲觀主義的語調(diào)暗示了他們不幸的未來。“我有什么權(quán)利得到幸福呢?”“我們凡人,可憐的罪人”……面對(duì)上帝、大自然而感到軟弱無力,這給葉琳娜的形象蒙上不協(xié)調(diào)的色彩:須知她不同于麗莎,沒有宗教的情緒。但葉琳娜仍然是堅(jiān)定的,她忠于愛情,矢志不移。在英沙羅夫病故以后,還到保加利亞去當(dāng)起義者的志愿看護(hù),“忠于他的終生事業(yè)”。
應(yīng)該指出,葉琳娜的形象,不是作家的杜撰,而是時(shí)代的典型。在她身上,洋溢著當(dāng)時(shí)俄國革命形勢(shì)形成前夜的社會(huì)氣氛,表達(dá)了當(dāng)時(shí)俄國婦女解放運(yùn)動(dòng)的要求,概括了當(dāng)時(shí)前赴塞瓦斯托波爾擔(dān)任志愿看護(hù)的貴族婦女的忘我精神;而她同貴族環(huán)境的脫離又反映了俄國進(jìn)步青年的轉(zhuǎn)向民主力量。屠格涅夫從這些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出發(fā),使其同改革的“前夜”聯(lián)系起來,從而使這個(gè)形象更為充實(shí),更有意義。但是,葉琳娜在威尼斯突然襲來的哀愁的預(yù)感,她的相信宿命論和懷疑自己幸福的權(quán)利等等,不是來自形象發(fā)展的邏輯,而是作家所素有的悲觀哲學(xué)的表現(xiàn)。這種悲觀哲學(xué)不僅像有人認(rèn)為的那樣,是由于作家“對(duì)他周圍現(xiàn)實(shí)的不滿”,而且是沒有前途的階級(jí)的思想的反映。而在這里,還表現(xiàn)了作家對(duì)婦女解放和參加政治生活的權(quán)利的懷疑。
葉琳娜和英沙羅夫的形象是交相輝映的。他們的愛情的基礎(chǔ)是崇高的理想,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男女之愛。不過,葉琳娜的理想是有賴于英沙羅夫而得到明確化并付之行動(dòng)的。因此只有英沙羅夫才是當(dāng)時(shí)俄國所需要的“新人”、英雄。這就是為什么杜勃羅留波夫寄希望于他,說隨著葉琳娜的出現(xiàn),俄國的英沙羅夫也很快出現(xiàn)了。
小說引起了當(dāng)時(shí)兩個(gè)陣營的不同反響。上流社會(huì)攻擊葉琳娜形象輕浮、“不知羞恥”,“體現(xiàn)了破壞因素”,并主要因作品的“政治主題”而加以根本否定,說它“從頭到尾都是虛假和錯(cuò)誤的”,有人還譏笑說,這個(gè)“前夜”“任何時(shí)候也不會(huì)有明天”。屠格涅夫因此幾乎要“付之一炬”。[8]而在另一陣營那里,杜勃羅留波夫在他寫的《真正的白天何時(shí)到來?》一文里,卻很歡迎英沙羅夫和葉琳娜形象。他只是惋惜英沙羅夫不是俄國人,固然他知道這是由于俄國的政治條件妨礙這種人物發(fā)展。但卻仍然認(rèn)為,俄國要有自己的英沙羅夫,并且他也行將出現(xiàn)了。“前夜離開隨之而來的白天總是不遠(yuǎn)的”。
杜勃羅留波夫這里作出的是革命的結(jié)論,暗示俄國處于革命的“前夜”,并且必須同專制農(nóng)奴制度作斗爭。這是屠格涅夫所害怕而不能接受的。他從審查官那里看到此文的手稿后,強(qiáng)烈要求《現(xiàn)代人》不刊登它。但后者沒有聽從他而把文章發(fā)表出來。他同《現(xiàn)代人》雜志社在農(nóng)民解放問題上久已分歧,這件事以及隨之發(fā)生的一些誤會(huì),促使了彼此間的最后決裂。屠格涅夫多年以來作品都給《現(xiàn)代人》發(fā)表,而《前夜》和后來的《父與子》,在寫作過程中就預(yù)定交給《俄羅斯通報(bào)》。這是自由主義保守派的刊物,從六十年代初起,代表反動(dòng)的農(nóng)奴主利益,同《現(xiàn)代人》激烈論戰(zhàn)。為這個(gè)刊物撰稿,是屠格涅夫思想立場重要變化的表現(xiàn)。
《父與子》寫于農(nóng)奴制改革法令頒布前后。身經(jīng)激烈的思想斗爭,作家的頭腦更清醒了。各階級(jí)協(xié)調(diào)一致的幻想已經(jīng)消散,革命民主主義者同自由主義者兩個(gè)陣營間的鴻溝終于展現(xiàn)在眼前。這也就是“父”與“子”的沖突的社會(huì)內(nèi)容。
小說一開始,屠格涅夫就把主人公放到同他格格不入的環(huán)境里,使他的性格以至作品的沖突迅速地展開。巴扎羅夫是平民知識(shí)分子,“祖父種過地”,他的一雙紅色的手說明他自幼勞動(dòng)過。他同阿爾卡狄是彼得堡大學(xué)的同學(xué),現(xiàn)在到后者的貴族莊園里去度暑假。在科學(xué)、藝術(shù)、哲學(xué)、道德……以至社會(huì)制度和一般的原則等問題上他和巴威爾都有正相對(duì)立的看法。很快就爭論開了,但這是對(duì)方挑起的,他卻為此打哈欠,覺得無聊。他不是熱衷于宣傳的羅亭,他重視的是實(shí)際行動(dòng),現(xiàn)在則是做科學(xué)實(shí)驗(yàn)。他冷靜、自信,在論爭中只用簡單幾句話,準(zhǔn)確有力地?fù)魯?duì)方,又能不動(dòng)聲色,不像巴威爾那樣失去自持。這是因?yàn)樗袌?jiān)定的信念,從高處俯視對(duì)手,顯示出他的優(yōu)越性。這種優(yōu)越性在后來決斗的場面里表現(xiàn)得最為充分。他是一個(gè)虛無主義者。他否定一切,對(duì)一切持批判態(tài)度。當(dāng)巴威爾問他是否“不僅(否定)藝術(shù)、詩歌,而且有……”的時(shí)候,他沉著地肯定說:“一切”,以致巴威爾說:“說得多可怕。”由于審查制度,屠格涅夫不能說得更清楚些,但卻已經(jīng)意味深長地表明,所反對(duì)的是整個(gè)社會(huì)制度了。當(dāng)然,虛無主義的價(jià)值是相對(duì)的,視所否定的對(duì)象而定。巴扎羅夫否定專制農(nóng)奴制度,因此這否定是含有積極意義的。他也不光是否定,尤其不是為否定而否定。他破壞一切,只是因?yàn)槭紫鹊谩鞍训孛娲驋吒蓛簟薄R簿褪钦f,他破壞是為了建設(shè),這破壞也是建設(shè)性的。當(dāng)然,可能性不等于現(xiàn)實(shí)性,破壞本身還不就是建設(shè)。巴扎羅夫說:建設(shè),“那不是我們的事情了”。可見他沒有積極的綱領(lǐng)。[9]因此,作為虛無主義者,他并沒有像作家說的那樣,就意味著是“革命家”。他只是過渡的典型。這并不是說,他們的論爭就沒有政治意義了。上面說過,巴威爾因?qū)Ψ椒穸ㄒ磺卸械娇膳隆K硪淮斡謫枺喊驮_夫是否也否定日常生活中“公認(rèn)的法則”?這無疑暗示著國家、財(cái)產(chǎn)、法律以至教會(huì)等等。巴扎羅夫不直接回答而反問道:這是“在審問嗎”?巴威爾的臉色不禁為之變白,因?yàn)槠渲泻姓蔚臐撆_(tái)詞。這場斗爭已達(dá)到劍拔弩張的地步,它是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上兩個(gè)陣營斗爭的鮮明反映。在基爾沙諾夫莊園里兩個(gè)陣營具體而微地呈現(xiàn)出來:一方面是巴扎羅夫,還有家仆和農(nóng)民孩子們,巴扎羅夫以民主態(tài)度贏得他們的喜愛;這里也包括費(fèi)涅奇卡,她喜歡他平易近人,并因他在“吵架”中把巴威爾“弄得團(tuán)團(tuán)轉(zhuǎn)”而悄悄高興。另一方面則是巴威爾兄弟、卜羅科菲奇,以至阿爾卡狄。
的確,巴扎羅夫是被作為革命民主主義者的代表人物來描寫的。他的一些觀點(diǎn),例如反對(duì)僵死的“原則”;否定責(zé)任感和內(nèi)心追求的矛盾;批評(píng)人民的消極面;認(rèn)為人與人“就像一座林子里的樹木”彼此相似;認(rèn)為精神上的病來自不健全的社會(huì),隨社會(huì)的改造而消失等等,都可以從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那里找到類似的表述。另一些觀點(diǎn)固然概括自別的人,例如只相信感覺而不相信理論概括,來自庸俗唯物論者;否定普希金以至整個(gè)藝術(shù),來自民主主義作家尼·烏斯賓斯基;而這兩者又都接近皮薩烈夫的觀點(diǎn)。不過,屠格涅夫客觀地反映這些觀點(diǎn),卻并不完全贊成。最明顯的如他在書簡中談到,尼·烏斯賓斯基否定普希金幾乎是“發(fā)了瘋”,他顯然是抱著反感把這些論點(diǎn)概括在巴扎羅夫形象上的。這是很自然的。屠格涅夫在生活中雖然也承認(rèn)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某些優(yōu)點(diǎn),但卻因政治觀點(diǎn)不同,而同他們決裂;在小說中,他也不能完全同情巴扎羅夫。他的態(tài)度是矛盾的。他讓巴扎羅夫取得對(duì)巴威爾的精神上的勝利,但卻把巴扎羅夫看作虛無主義者,在他身上只看到破壞因素。盡管如此,由于上述觀點(diǎn)符合于巴扎羅夫的性格,沒有破壞形象的完整性;而這些觀點(diǎn)又大都是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在當(dāng)時(shí)是進(jìn)步的,因此不以作家的意志為轉(zhuǎn)移,并沒有貶低形象。這也正是屠格涅夫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勝利。遺憾的是,事情還不限于此。
《父與子》可以分為兩個(gè)部分。在后一部分,在巴扎羅夫和奧津左娃的關(guān)系上,他這個(gè)形象是被歪曲了的。我們并不認(rèn)為,作家不應(yīng)讓他愛上貴族夫人,更不同意說這一愛情是為了表現(xiàn)他的愛的能力,即人性。問題也不在于屠格涅夫總愛把人物放到愛情中考驗(yàn)。問題在于這個(gè)形象的變化是反常的,不符合其發(fā)展的邏輯的。巴扎羅夫開頭以其觀點(diǎn)大膽?yīng)毺囟龏W津左娃,但漸漸卻遷就她,屈服于她的影響,改變了否定一切的態(tài)度,動(dòng)搖了自己的信念。他為此苦惱,感到詫異并引以自嘲。他過去以出身人民而自豪,為他們斗爭,現(xiàn)在卻悵惘地感到,人民即使住上白凈房子,他自己身上已經(jīng)長滿牛蒡了。他過去認(rèn)為,要是因?yàn)槭ァ芭说膼邸倍倚膯蕷猓退悴坏谩澳凶訚h”,而現(xiàn)在卻因愛情挫折,失去意志力而陷入頹唐的境地。他的死是偶然的,卻有其必然性。固然,這種必然性的社會(huì)原因是當(dāng)時(shí)歷史條件不能讓他有所作為;但其心理原因卻是因身死之前,早已“心死”了。他后來的狂熱工作,只是為的填補(bǔ)心靈的空虛。他甚至懷疑俄國是否需要他。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回憶他否定一切、凌厲無前的氣概,幾乎成了銀樣镴槍頭。他認(rèn)為自己是“巨人”,要“干一番事業(yè)”,但這“巨人”的事業(yè)卻只是要死得像樣些,悲壯些!
在《父與子》的長期修改過程中,屠格涅夫是舉棋不定的。他受到各方面的影響,主要因卡特科夫(《父與子》發(fā)表在他主編的《俄羅斯通報(bào)》上)的壓力而貶抑巴扎羅夫[10]。但有關(guān)奧津左娃的愛情這一重要情節(jié)卻出自原來的構(gòu)思。通過這個(gè)情節(jié),作家企圖揭示巴扎羅夫的理論觀點(diǎn)經(jīng)不起生活的考驗(yàn),證明他作為一種社會(huì)力量,沒有前途。這是作家的階級(jí)心理的局限,在他看來,革命運(yùn)動(dòng)前途渺茫,注定是悲劇性的。也正因此,他不能了解巴扎羅夫的心理,也不認(rèn)為其后繼有人。我們看到,巴扎羅夫一如英沙羅夫,內(nèi)心是封鎖著的,不為我們所窺見的;他遭到農(nóng)民的奚落;他在全書的形象體系中是孤軍作戰(zhàn),沒有志同道合的戰(zhàn)友,他說的“我們?nèi)藬?shù)并不……那么少”也只是句空話:要知道,阿爾卡狄這個(gè)門徒很快就改了宗,西特尼科夫和庫克希娜則只是“子輩”的漫畫化而已。所以總的說來,屠格涅夫是不喜歡巴扎羅夫的,[11]雖則他多次為自己辯解,說決非詆毀子輩,說自己熱愛巴扎羅夫,同意他的許多觀點(diǎn),并曾為他的死哭過,這一切只能說明其思想深刻矛盾,巴扎羅夫形象的矛盾就是其具體體現(xiàn)。
與巴扎羅夫?qū)镜氖前屯枴K皇琴F族的敗類,而是他們中的翹楚。這樣,意義深刻得多。作家說:“我的整個(gè)中篇小說是反對(duì)作為先進(jìn)階級(jí)的貴族的”,“奶油尚且不好,何況牛奶。”[12]巴威爾是貴族保守派。他內(nèi)心空虛,年輕時(shí)追逐一個(gè)由嬌縱而變得反復(fù)無常的公爵夫人,失敗后就終身萎靡不振。他不僅蔑視人民,心目中也沒有祖國。從談吐到服飾,都在炫示英國氣派。他自負(fù)貴族身份,維護(hù)所謂原則,即貴族和舊制度的精神支柱。他強(qiáng)烈感到巴扎羅夫的威脅和同他的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有意挑起論爭。他平時(shí)看起來很正直,儼然一個(gè)騎士,而在決斗中,從動(dòng)機(jī)到行動(dòng),他的卑劣渺小暴露得淋漓盡致。同巴威爾的好斗不同,尼古拉是溫和的自由主義者。他缺乏自信、軟弱、多愁善感,喜愛詩歌和音樂,為大自然景色而陶醉。他在農(nóng)業(yè)中實(shí)行一些改革,但他莊園中仍然是一片敗落景象。他希望接近青年人,承認(rèn)他們有些優(yōu)越,為自己一代人的過時(shí)而惆悵。他害怕巴扎羅夫的觀點(diǎn),卻并不持?jǐn)硨?duì)態(tài)度,常以調(diào)解者身份出現(xiàn)。在這些方面,帶有屠格涅夫的某些成分,所以作家說:尼古拉“就是我……”[13]然而作為農(nóng)奴主,他同農(nóng)民在利害關(guān)系上是對(duì)立的。如所周知,“父”與“子”的矛盾并不發(fā)生在父輩和子輩之間。阿爾卡狄是農(nóng)奴主的孝子。他在聽到尼古拉因土地將要分給農(nóng)民而把森林出賣時(shí),惋惜的是森林而不是農(nóng)民。青年人的熱情曾使他受到巴扎羅夫的吸引,但這是外鑠的、暫時(shí)的。他參與論爭,多半是炫耀新觀點(diǎn),并不怎么理解其深刻涵義。他很快就為卡契雅所“改造”,也就是還他本來面目。他樂于“擺脫”他青年導(dǎo)師的影響,正像卡契雅樂于擺脫姐姐的控制那樣。比較復(fù)雜的是奧津左娃。她聰明、優(yōu)雅、大方,閱歷很深而并不世故,獨(dú)立自主而不依傍別人。她又冷又熱,主要是冷靜自持。她興趣很廣,但卻沒有為特殊的興趣而迷醉。她并非沒有激動(dòng)的剎那,她的想象有時(shí)也能越出日常道德許可的范圍,但這只是一閃即熄的火花。她像蝸牛一樣,總是愛縮回到自己的安樂窩里。她同巴扎羅夫之所以暫時(shí)互感興趣,是因?yàn)槟巧狭魃鐣?huì)太庸俗太空虛了,以致相形之下,他們卻有某些共同之處,例如都厭惡庸俗,都是“怪物”。然而她是“悠閑的”、“享樂主義的太太”[14],最怕打亂生活中的安寧,決不會(huì)愛上巴扎羅夫。巴扎羅夫的父母是一對(duì)好人。通過他們,表現(xiàn)了巴扎羅夫性格的一個(gè)側(cè)面。他同父親的“小人物”的處世態(tài)度格格不入,他對(duì)雙親冷漠生硬,但卻懷著熾熱的深沉的愛。他離家之前不敢貿(mào)然告別,躊躇了一整天,唯恐父母感到傷心。就在彌留時(shí)刻,他還叮嚀奧津左娃說:“還請(qǐng)安慰我的母親……”小說在《俄羅斯通報(bào)》發(fā)表時(shí),卡特科夫就因這句話有利于巴扎羅夫而給刪去了。全書以這對(duì)衰老的雙親慟哭于巴扎羅夫的墓前而結(jié)束。作家施展其擅長的抒情之筆表示了對(duì)自己主人公的哀悼和愛撫,同時(shí)又重彈了他那面對(duì)大自然無能為力的悲觀論調(diào):“啊,不!不管那顆藏在墳里的心是怎樣熱烈,怎樣狂暴,怎樣反抗”,墳上的花卻“寧靜地”敘說“那個(gè)‘冷漠的’大自然的偉大的安息”,以及“永久的和解同無窮的生命”!
不,“永久的和解”只是作家的幻想!當(dāng)時(shí)現(xiàn)實(shí)中的斗爭是那么激烈,《父與子》對(duì)它的反映是那么及時(shí),作家的態(tài)度又是那么矛盾,以致小說問世,“像火上澆油”[15],激起了席卷俄國思想界的空前激烈的論爭,而且像梅里美說的,兩邊都不討好,兩邊都予以責(zé)難。在反動(dòng)陣營,早就有人建議把手稿燒掉,指責(zé)作家“在極端分子面前降下旗幟”[16];而現(xiàn)在則有人說巴扎羅夫的形象是“對(duì)《現(xiàn)代人》的崇拜”[17],有人說作家身上“完全沒有骨頭”[18]。而在另一陣營,大部分青年對(duì)作家表示憤慨,《現(xiàn)代人》的安東諾維奇認(rèn)為小說是對(duì)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惡毒誹謗。由于巴扎羅夫的早死同剛剛逝世的杜勃羅留波夫巧合,而他們的思想觀點(diǎn)又多類似,當(dāng)時(shí)也確實(shí)有人把杜勃羅留波夫叫做“虛無主義者中的虛無主義者”,因此包括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內(nèi)很多人都認(rèn)為小說是在攻擊杜勃羅留波夫。對(duì)《父與子》表示歡迎的只有皮薩烈夫及他所主辦的《俄羅斯言論》。在《巴扎羅夫》一文中,皮薩烈夫肯定巴扎羅夫是“我們年輕一代的代表”,說“巴扎羅夫們既有知識(shí)又有意志,思想和行動(dòng)熔成堅(jiān)實(shí)的統(tǒng)一體”。他及其同仁因?yàn)椴患南M谧罱陂g的農(nóng)民起義,因而認(rèn)為,巴扎羅夫之死也是因?yàn)樵诋?dāng)時(shí)條件下無法表現(xiàn)其怎樣生活和行動(dòng),而只能“表現(xiàn)他是怎樣死的”。他指出作家的思想同創(chuàng)作之間的矛盾:“在創(chuàng)作巴扎羅夫時(shí),屠格涅夫想粉碎他,結(jié)果卻充分地給他以公正的敬意。”[19]這同后來的赫爾岑的看法完全一致。赫爾岑說:屠格涅夫原意不是夸獎(jiǎng)巴扎羅夫,而是想給“父輩做點(diǎn)有益的事”。結(jié)果卻“不是鞭撻兒子,而是抽打了父輩”[20]。也就是說,這是藝術(shù)真實(shí)的勝利。
如果說作家屠格涅夫,在思想上是瑕瑜并見,瑕不掩瑜;那么在藝術(shù)上則是獨(dú)步一時(shí)[21],別開生面。他的小說藝術(shù),表現(xiàn)于性格塑造、環(huán)境描寫、情節(jié)結(jié)構(gòu)和語言風(fēng)格上的共同特點(diǎn),可以說是簡潔和樸素。但這么概括卻未免籠統(tǒng)了些。顯然,屠格涅夫的簡潔,不是粗獷,是細(xì)膩而又不流于纖巧;他的樸素不是古拙,是淡雅而又保持其深度。他的作品不像寶石那樣璀璨奪目,而像水晶那樣清澈而很少雜質(zhì),像碧玉那樣溫潤而饒有含蓄。
屠格涅夫與岡察洛夫適成鮮明的對(duì)比。如果說后者擅長工筆畫,那他就是用勾勒法。在人物刻畫上,岡察洛夫愛作詳盡的但卻是靜態(tài)的描述,屠格涅夫則主要借助于對(duì)照與反襯。在《前夜》里,英沙羅夫和舒賓、伯爾森涅夫以至庫爾納托夫斯基都是互相烘托出來的;同時(shí)他們又在同葉琳娜的關(guān)系以及葉琳娜在對(duì)他們的不同態(tài)度中各自顯出自己的特色。《父與子》寫對(duì)立的陣營,主要是用反襯法。巴扎羅夫和巴威爾的反襯不僅見于思想觀點(diǎn)、言論舉止、待人接物方面,而且也見于外表和服飾上。借助于這些方法,并抓住典型特點(diǎn),因而著墨不多,勾勒出鮮明的性格。他刻畫個(gè)性的另一特色是不作瑣碎的心理分析。他對(duì)列夫·托爾斯泰過于細(xì)致的心理描寫,是頗有微詞的。一般說來,托爾斯泰寫心靈辯證過程;屠格涅夫則只寫心理變化的結(jié)果,而且往往還不是心理本身,而是在行動(dòng)上的表現(xiàn)。葉琳娜聽到英沙羅夫失蹤的消息,“沉到了椅子里”,可又“竭力裝作冷淡”,這寫出了她已愛上英沙羅夫,但又怕被人發(fā)現(xiàn)的復(fù)雜心情。巴扎羅夫同奧津左娃采集植物歸來,向阿爾卡狄說聲:“早安!”事實(shí)上當(dāng)天他們已見過面,這說明他心不在焉,而且反映了他同阿爾卡狄和奧津左娃的微妙關(guān)系。巴威爾單獨(dú)在費(fèi)涅奇卡房間里,仔細(xì)觀察四壁的一切,當(dāng)聽到隔壁有人聲時(shí),卻隨手拿起一本殘書,這表明他對(duì)費(fèi)涅奇卡很感興趣而又加以掩飾。奧津左娃同巴扎羅夫談話后,在入睡前想到他,自言自語地說了“這個(gè)醫(yī)生是個(gè)古怪的人”和“這個(gè)醫(yī)生真是個(gè)怪人”兩句話,“伸一伸腰,微微一笑”,就睡著了。足見她很冷靜,沒有什么激情。這些都可說是傳神之筆,主要在于抓住人物在剎那間心理變化的基本特點(diǎn)。當(dāng)然,屠格涅夫不像有些人說的,不會(huì)直接寫心理演變過程。像葉琳娜的日記(這里的心理描寫是斷斷續(xù)續(xù)的)、她等待英沙羅夫來告別以及向英沙羅夫表白了愛情后回家等幾段描寫都很出色。在第三十三章末,葉琳娜的思想進(jìn)展,使人想起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贊賞的托爾斯泰的《兩個(gè)驃騎兵》那個(gè)片段。描繪肖像,屠格涅夫力求平淡,力求符合性格,不加以虛假的美化。前者如奧津左娃:鼻子“略有點(diǎn)兒肥大”,膚色“并不十分白凈”;后者如葉琳娜:“嘴唇緊閉”,“下頦稍顯尖削”,“步履迅速”等等。而且他避免單純的敘述,常常表現(xiàn)于人物的觀感之中,從而同時(shí)表明人物間的關(guān)系。葉琳娜的肖像最初由舒賓談到,巴威爾的外表首先是巴扎羅夫注意到,奧津左娃的體態(tài)主要是阿爾卡狄看到,費(fèi)涅奇卡的外表描寫,一次是出現(xiàn)在巴威爾之前,另一次是談到巴扎羅夫喜歡她的時(shí)候。
人物在其中活動(dòng)的生活環(huán)境的描寫,在屠格涅夫確是惜墨如金,主要還是視性格而定。我們沒有看到葉琳娜房間是怎么樣的,雖則作家寫到“強(qiáng)烈的陽光射入她的房里”。要知道她厭惡自己的家,不會(huì)關(guān)心房間的陳設(shè)。作家寫到英沙羅夫的房間:“寬大,幾乎空無所有……房間里的一隅放著一架小床,另一隅則有一座小小的沙發(fā)”,幾乎只占一行,寫出了主人儉樸和講究實(shí)際的性格。費(fèi)涅奇卡的房間寫得比較詳細(xì),這主要為了寫巴威爾對(duì)她的注意,一切陳設(shè)是通過他的眼睛看到的。
屠格涅夫是世界文學(xué)中的風(fēng)景畫大師。《前夜》第一章里的景色,的確是色、聲、香兼而有之。察里津諾和威尼斯的畫面更顯得清奇、輕靈而迷人。但是,也正好在風(fēng)景描寫上,最顯示出作家的藝術(shù)分寸感。他使這些描寫嚴(yán)格服從于性格刻畫或情節(jié)開展的需要。在《父與子》里,尼古拉從涼亭里看到的景色就是為了這二者。巴扎羅夫不愛藝術(shù)美,也不愛自然美,把自然看作“工廠”,因此在他出場的時(shí)候,作家?guī)缀鯏R下了畫筆。甚至在他拜訪奧津左娃時(shí),莊園前的參天古木和夾道樅樹也只作了干巴巴的交代。只有當(dāng)他坐在奧津左娃的房間里,傳染上“一種隱秘的激動(dòng)”時(shí),他才感到“柔和的”黑夜里“那清爽的露天空氣的芬芳”,“一陣陣沁人肌膚的清涼夜氣”,聽到“夜的神秘的細(xì)語聲”。還有一次,那就是在決斗前,“清涼的早晨”、“晶瑩的露珠”和“百靈的歌聲”,這些自然景色之所以映入他的眼簾,只是由于他心情坦然,很像彼喬林赴決斗時(shí)欣賞曙光的心境:“我不記得有哪一天早晨,天空更加蔚藍(lán)、空氣更加清新!”[22]作為社會(huì)心理小說,屠格涅夫的長篇的特色之一是寫思想沖突,寫人物論爭。這些長篇結(jié)構(gòu)相當(dāng)簡單,主要由幾次產(chǎn)生重大后果的論爭構(gòu)成,《父與子》特別如此。屠格涅夫的小說,情節(jié)進(jìn)展特別迅速。在幾乎相同的篇幅里,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還沒有從沙發(fā)上起來,《父與子》的沖突已經(jīng)全面展開了。屠格涅夫從不追求表面的效果:不寫復(fù)雜緊張的情節(jié),不寫引人入勝的故事,不寫過分感傷的甜膩的場面,不寫回腸蕩氣的哀傷的插曲。寫愛情主要是理想的激情,寫決斗卻帶有喜劇味道,寫死也顯得平平常常。總之,屠格涅夫有其獨(dú)特的韻致,可以說是妙質(zhì)天生,淡雅宜人。
作為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屠格涅夫?qū)φZ言的基本要求是“簡潔、確切和樸素”。但他的成就不止于此。他不乞靈于奇僻的詞匯,不追求鮮明的色彩,他擯棄雕琢的表現(xiàn)法,避免冗長的復(fù)合句。他的語言是那么平易近人,而又那么生動(dòng)、優(yōu)美和清新。在俄羅斯文學(xué)中,屠格涅夫是首屈一指的語言大師。列寧在贊嘆俄羅斯語言時(shí),決非偶然地首先提到他。
屠格涅夫的抒情筆觸可說是獨(dú)擅勝場,不過他也很有分寸。他絕不作過多的不必要的抒情旁涉,沒有浪漫主義那么高昂的調(diào)子,始終保持其客觀的態(tài)度。他也不隨處使用抒情,例如,在人物中,洋溢著抒情氣息的,不是英沙羅夫和巴扎羅夫等形象,而是“屠格涅夫的少女”,像葉琳娜就閃耀著詩意的光輝。在自然畫面中,他的抒情也總是同人物的感受密切相關(guān)。總的說來,他的抒情的特色是帶有一種淡淡的哀愁,一種悲觀的情調(diào)。
屠格涅夫有一句名言:“米羅的維納斯也許比羅馬法或(一七)八九年的原則更要無疑得多。”[23]他顯然錯(cuò)了。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就是明證。難道《前夜》和《父與子》不是因其反映當(dāng)代社會(huì)斗爭而為我們所欣賞,而他的《夠了》或《幻影》等作品,不是因其為唯美主義而早已消失在忘津嗎!當(dāng)然,這不是說,屠格涅夫的藝術(shù)就不值得重視了。顯然,《前夜》和《父與子》的不朽仍有賴于其藝術(shù)力量,有賴于思想和藝術(shù)的統(tǒng)一。否則,我們今天就不去讀它們,而單單研究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論文了,這里的真理比屠格涅夫的小說確實(shí)“要無疑得多”。不,我們是需要借鑒屠格涅夫的藝術(shù)的。加里寧很幽默地說:“凡是不想使自己作品產(chǎn)生社會(huì)影響的人,他自然就不需要屠格涅夫。”[24]愿我們的無產(chǎn)階級(jí)作家三復(fù)斯言!
陳燊
注釋:
[1]這里根據(jù)《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有關(guān)的考證。屠格涅夫自己在為1880年版的長篇小說集的《前言》中談到這件事,但比較簡略。
[2]《列寧全集》,第17卷第105頁。
[3]參閱《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127頁。
[4]引自《真正的白天何時(shí)到來?》,見《杜勃羅留波夫文集》,第6卷第105頁。下文提到的他的話均引自這篇文章。
[5]《屠格涅夫全集·書信集》,第3卷第368頁。
[6]這是當(dāng)時(shí)一個(gè)否定《前夜》的批評(píng)家說的話,參見《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第537頁。
[7]屠格涅夫的《堂吉訶德和哈姆萊特》一文發(fā)表于《前夜》之后幾個(gè)月,但開始寫作于1856年。在這兩個(gè)作品發(fā)表后不久,有人就認(rèn)為英沙羅夫體現(xiàn)了屠格涅夫所理解的堂吉訶德的精神。
[8]這些意見分別參見《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第530頁、第505頁和第524頁。
[9]在《父與子》初稿中,巴扎羅夫曾對(duì)奧津左娃談到:“必須從消滅一切舊事物開始”。要燒掉“無用的宿草”,“如果土壤里力量沒有消耗完了,它就會(huì)使其雙倍地成長”(見《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第458頁)。這是巴扎羅夫唯一的有建設(shè)性的話,屠格涅夫后來把它刪掉了。
[10]有人認(rèn)為,屠格涅夫害怕兩方面的攻擊,動(dòng)搖于兩者之間,時(shí)而對(duì)這方,時(shí)而對(duì)那方作些讓步。但總的傾向是貶低巴扎羅夫。這也不僅由于卡特科夫的壓力。以后在出版單行本時(shí),雖曾作過一些有利于巴扎羅夫的修改,但有些地方卻一仍其舊。
[11]《父與子》原有題詞:中年人對(duì)年輕人說,“您具有沒內(nèi)容的力量”,后來刪去。屠格涅夫在1861年10月致卡特科夫的信,也不無同情地引用了后者關(guān)于巴扎羅夫的貶詞。在1862年4月致費(fèi)特的信中,說自己也不知道,是愛巴扎羅夫,還是恨他。
[12]《屠格涅夫全集·書信集》,第4卷第380頁。
[13]《屠格涅夫全集·書信集》,第4卷第380頁。
[14]分別參見《屠格涅夫全集·書信集》,第4卷第381頁和第5卷第12頁。
[15]分別參見《屠格涅夫全集·書信集》,第4卷第381頁和第5卷第12頁。
[16]安寧科夫《文學(xué)回憶錄》,第477頁。
[17]《屠格涅夫全集·書信集》,第4卷第382頁。
[18]《屠格涅夫全集》,第8卷第606頁。
[19]參見《皮薩烈夫文集》,第2卷第8頁、第21頁、第45頁、第48頁。
[20]《赫爾岑全集》,第20卷第1分冊(cè)第339頁。
[21]在《前夜》成書以前,屠格涅夫已是公認(rèn)的俄國最著名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稱他為“俄國文學(xué)的榮譽(yù)”,赫爾岑稱他為“當(dāng)代俄國最偉大的藝術(shù)家”。
[22]見《當(dāng)代英雄》(萊蒙托夫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第398頁。
[23]《屠格涅夫全集》,第9卷第119頁。
[24]《加里寧論文學(xué)》,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第9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