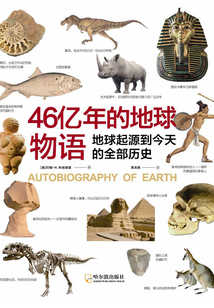
46億年的地球物語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13評論第1章 恢宏大計(jì)(1)
年復(fù)一年,在貌似死寂的星球上,沖突四起,矛盾更迭,留下了萬物逆旅的痕跡。這些痕跡中,有些屬于動物和植物,有些則屬于它們腳下的泥土。
一、地球與生命的更迭
世界和平之夢牢牢地扎根于人們的心中,但對于造物主而言卻無關(guān)緊要。他是建筑師,規(guī)劃和建造了宇宙這個龐大的劇場;他也是導(dǎo)演,為劇場中的每一個演員安排各自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從一開始便制訂的恢宏的計(jì)劃——那個在紛亂中徐徐展開的地球歷史——億萬年來從未發(fā)生過太大的變更。隨著時間的流逝,生命的演出在地球的大舞臺上幕起幕落,歷經(jīng)滄桑。但倘若因此便認(rèn)定世界麻木不仁,那只是因?yàn)槟銢]能看清真相。年復(fù)一年,在貌似死寂的星球上,沖突四起,矛盾更迭,留下了萬物逆旅的痕跡。這些痕跡中,有些屬于動物和植物,有些則屬于它們腳下的泥土。
通常,一個人很難對那些事不關(guān)己的紛爭有所體會。當(dāng)他轉(zhuǎn)身凝視繁星滿天的夜空,遙望地平線上綿延不絕的群山時,他的心中或許充滿了寧靜與祥和。詩人們時常被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拋棄,遂無休無止地吟唱著林間的寂靜,吟唱著河流的平緩,吟唱著對自然世界無以復(fù)加的滿足。然而,殊不知,大自然同人類的靈魂一樣多災(zāi)多難。人類能從煩悶的自然中得到啟示,使自我的煩悶歸于安寧,如此福分絕非理性之果,而是另有他因。
那些見多識廣的人或許會以批判的眼光鄙夷這種自我陶醉,其實(shí)大可不必。人類的思維包含著許多不同的層次,沒有必要因?yàn)橹獣粤嗣篮檬挛镏律顚哟蔚恼嫦啵头艞墝γ篮帽旧淼母兄托蕾p。人類生活的演出不過是宇宙大舞臺上短而又短的一幕。盡管這種認(rèn)知不可避免地會挫傷人類一貫高傲的自尊,卻依然包含些許有益的成分。至少,人們可以一次次地暫時忘卻心中的重?fù)簦ミx擇聆聽自然的悸動。
在人類發(fā)展的早期階段,一些人已經(jīng)逐步認(rèn)識到,地球不僅僅是一片可供撫慰煎熬生活的怡人景色——它不能被草草定義為人類的棲息之所,也不只是一面用以映照人類自身情緒的明鏡,而是一部用異國文字撰寫而成的戲劇,時刻引誘著人們將其翻譯成各自的語言。和自然界中的所有其他事物一樣,地球也書寫了自己的歷史,并且,在無數(shù)“譯者”的共同努力下,這部歷史巨著的主題已經(jīng)鋪展開來。
當(dāng)早期人類撥開籠罩內(nèi)心的迷霧并著手探尋真相時,幾乎沒有一種想法能準(zhǔn)確地闡明地球發(fā)展的來龍去脈。公元前的數(shù)世紀(jì)間,學(xué)者們醉心于謹(jǐn)小慎微的自然觀測,為大膽地提出各種有關(guān)世界的起源、歷史和構(gòu)造的假說而陶醉不已。東方和古希臘的哲學(xué)家們無疑是這些學(xué)者中的典范。他們提出了千奇百怪的宇宙演化學(xué)說,其中絕大多數(shù)源自虛構(gòu)的神話故事與宗教傳說。古希臘詩人赫西奧德的觀點(diǎn)古老而獨(dú)特,他認(rèn)為宇宙脫胎于一片原始的混沌,接著,天空鋪展開來,繼而高山聳起,海洋匯聚,最后才輪到諸神出場(略顯姍姍來遲)。就連一向講求實(shí)際的古羅馬人也更傾向于以一種詩意而不是理性的方式來探索自然。公元1世紀(jì),古羅馬哲學(xué)家盧克萊修的學(xué)說風(fēng)行一時,他認(rèn)為地球內(nèi)部存在一個空洞,洞內(nèi)布滿了在黑暗中奔流的江河,雄奇的峽谷、巨穴與山崖,以及一股股將火焰吹上地殼的狂風(fēng)。學(xué)者們的想象常常富有戲劇性的矛盾與沖突,這似乎意味著早期人類必定無福消受真相的出演。
無法否認(rèn),一些古老的觀點(diǎn)確實(shí)在某種程度上與晚期的理論存在吻合之處。無非,前者帶有猜測性,而后者則歷經(jīng)數(shù)世紀(jì)緩慢而艱辛的探索和歸納。這樣一來,當(dāng)一位古代思想家不經(jīng)意間言中的啟示被現(xiàn)代科技所證實(shí)時,便會有人將他的成就歸結(jié)于某種超自然的洞察力。這些人有意無意忽視的事實(shí)是,該思想家的其他假說大都荒誕不經(jīng)。當(dāng)幻想者在思緒的海洋中遨游時,偶然會在無意中登上真相的沙洲。然而一些人卻對這種可能置之不理,他們沉湎于神秘主義帶來的快感,樂于使思想的晴空遍布斑駁的陰云。
而諸如亞里士多德、斯特拉波[1]、塞涅卡[2]這樣的偉人,其姓名之所以被鐫刻在地球科學(xué)的歷史長廊上而久不褪色,正在于他們孜孜以求,試圖以一己之力描繪出地球發(fā)展的脈絡(luò)。然而,他們的理論貢獻(xiàn)一方面有所建樹,一方面也零碎而分散,并且時常夾雜著神話與傳說。實(shí)際上,盡管古典時代不乏有識之士,盡管思想自由曾長時間地免于教會和公共輿論的壓制,那時的人們似乎依然不具備從事科學(xué)研究的品質(zhì)。唯有在艱苦辛勞、枯燥無味的鉆研中掙扎過后,人們才可能了解自然的真相,收獲豐碩的果實(shí)。文學(xué)和藝術(shù)可以憑借古典時代的寬松氛圍而茁壯成長,科學(xué)的發(fā)展卻必須一再等待,直到世人愿意為解開它的謎團(tuán)而付出更多的汗水。
這個等待注定遙遙無期。羅馬帝國的崩潰卷起陣陣陰云,戰(zhàn)爭、革命、迫害此起彼伏,學(xué)術(shù)研究在一個貌似文明的世界中一步步走向窒息的邊緣。各種文化活動也日漸式微,只得黯然隱入修道院的高墻。科學(xué)借此覓得安身之所,卻在數(shù)世紀(jì)間慘遭遺棄。然后,阿拉伯人來了。他們從厚厚的塵土中拾起昔日的榮光,使得早期學(xué)術(shù)免遭湮滅的命運(yùn)。不僅如此,阿拉伯人還憑借著自己強(qiáng)烈的求知欲和刻苦的鉆研,促進(jìn)了古典時代科學(xué)文化的發(fā)揚(yáng)與傳承。然而,他們大力發(fā)展了數(shù)學(xué)、天文學(xué)、醫(yī)學(xué)和生物學(xué),卻唯獨(dú)對地質(zhì)學(xué)漠不關(guān)心。地球科學(xué)歷經(jīng)近千年的黯淡,直到文藝復(fù)興時期才重獲一線生機(jī)。待到它沖破陳腐的神學(xué)與種種荒誕臆測的堅(jiān)壁,19世紀(jì)已然來臨。那時,人類終于隱約察覺到,地球的發(fā)展過程正是一部永恒法則的執(zhí)行筆錄;也只有在那時,人們才真正開始解出那些記載著時空軌跡的神秘文字。
二、地球的歷史
終于,厄謝爾[3]主教的創(chuàng)世理論開始受到輿論的動搖。人們懷疑,他的計(jì)算之所以將地球歷史的開篇定于公元前4004年,更多地是出于對宗教的虔敬,而非對真理的向往。17世紀(jì)末,詹姆斯·赫頓[4]提出,對現(xiàn)實(shí)的、正在發(fā)生的地球歷史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地球的種種過往。自此,推算和證明地球的古老年歲便有了方向。人們很快發(fā)現(xiàn),任何試圖精確地以年為單位度量地球歷史的做法,其荒謬性都不亞于用品脫計(jì)算太平洋的肚量。
無法歷數(shù),當(dāng)年加利福尼亞一株株幼小的秧苗,究竟經(jīng)歷了多少年才成長為如今參天挺立的紅杉林。然而,以地質(zhì)年代的觀點(diǎn)來看,即便是這些古老生命所經(jīng)歷的數(shù)千年的光陰都只不過是短短的一瞬,以至于無法在地球飽經(jīng)滄桑的面龐上增添哪怕是一道不起眼的褶痕;圖坦卡蒙古墓的發(fā)掘一度使人類為自己過去的輝煌文明而熱血澎湃,而放眼地球歷史的大背景,卻不得不承認(rèn),圖坦卡蒙只是一位現(xiàn)代君主,他和我們之間數(shù)十世紀(jì)的時間間隔誠然不足為道。
盡管從表面上看,地球的自然環(huán)境似乎平靜而穩(wěn)定,然而它作為太陽系中的一個獨(dú)立星體,自誕生的那一刻起,其內(nèi)部就激蕩著各種猛烈的沖撞。這些沖撞大都波及甚廣、持續(xù)不斷,卻也因?yàn)榘l(fā)生得十分緩慢而不易被肉眼察覺。多年來,詩人們吟詠著亙古不變的山巒,贊美著大自然的永垂不朽。然而,隨著地質(zhì)科學(xué)的發(fā)展,人們很快就意識到,山巒并非亙古不變。總有一天,最巍峨的山峰也會崩碎、倒塌;或許在另一天,傾倒的峰巒又會重新隆起。而所有的山脈的崩立成壞,都只是發(fā)生在地質(zhì)年代的時間碎片中罷了。山脈如此,其他的地理要素也是一樣。我們今日的所見所聞,不同于昨日的過往,也將不同于明日的未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是真正恒常不變的。
假設(shè)我們可以在五千年以后來到自己最愛的山間或是海邊的度假勝地,地理的變遷依然是難以察覺的,頂多也就是那片飼養(yǎng)鱒魚的小湖被沉積物淤死,或者被一條小溪排干。我們也可能會注意到,原先在我們的海邊小屋半英里開外入海的溪流,那時已經(jīng)改道在小屋邊入海了。但如果屋子原先是建在低平寬闊的沙灘上,我們很可能就只能在距離海岸線半英里外的水底找到它了。然而,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下,肉眼所能觀察到的變化卻微乎其微。盡管雨雪風(fēng)霜千年來不知疲倦地侵蝕著巖層中的高地,山地的形態(tài)基本上不會發(fā)生顯著的變化,海岸地貌的總體格局也會和五千年前大體相當(dāng)。
如果我們把五千年換成五百萬年,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地球的滄桑巨變將足以使我們驚愕不已。山脈可能會被蠶食得只剩下一個小土堆,甚至被夷為平地,以至于無法留下任何遺跡可供憑吊其昔日的壯麗。海洋則可能對陸地大舉進(jìn)犯,使原本焦燥的土地慘遭淹溺。陸地上棲息著千奇百怪的動植物,水中的生物也與今天的大不相同。甚至當(dāng)我們遇見自己的后代,也會因?yàn)閷Ψ揭呀?jīng)變異得過于離奇而質(zhì)疑他們的物種科別。地球歷史學(xué)的研究者們深知這些變化曾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因而也就沒有理由否認(rèn)它們將會在未來延續(xù)下去。
地球歷史的開端,要從它獲得大氣層和原始海洋算起。海水的鹽分是經(jīng)由陸地上的河流入海而積累起來的。一開始幾乎所有的海水都是淡的。于是,地質(zhì)學(xué)家們嘗試著通過測算河流對海洋鹽分的貢獻(xiàn)速率來計(jì)算海洋的壽命。早在1715年,埃德蒙·哈雷[5]便提出了這種測算的可行性。然而,直到1899年,學(xué)者們才收集到足夠的數(shù)據(jù)來進(jìn)行實(shí)際的計(jì)算。在那一年,愛爾蘭物理學(xué)家喬利[6]將估算出的海水鹽分總量除以估算出的年均河流鹽分貢獻(xiàn)量,從而計(jì)算出海洋的存在大約歷經(jīng)97600000年的歷史跨度。其他科學(xué)家也提供了一些測算結(jié)果,其中大多數(shù)人都將海洋的成長歷時定于1億年左右。
即便是數(shù)以億計(jì)的數(shù)據(jù)依然明顯低估了現(xiàn)實(shí)。事實(shí)上,陸地的海拔比以前大多數(shù)時期都要高得多,河流進(jìn)而也就更密集、更洶涌,并且搬運(yùn)了更多從陸地上侵蝕而來的鹽分。這意味著當(dāng)下河流的鹽分貢獻(xiàn)速率過高,不能用來簡單替換歷史上的速率,依此推算出來的海洋壽命也一定被大大低估了。然而,要了解河流過去向海洋貢獻(xiàn)鹽分的速率則是難上加難。
再退一步說,就算海洋的現(xiàn)時壽命真的可以得到確定,在海洋形成前就存在的巖石圈的年齡也依然是個未知數(shù)。地球原先經(jīng)由母體太陽的放射物質(zhì)撞擊匯聚而成,而迄今在人們可以探測到的所有地殼巖層中都沒能留下有關(guān)地球形成時期的記載。所幸我們可以斷定,形成時期應(yīng)早于任何可探測到的巖層所記載的地質(zhì)時期,那些巖層在大氣和液態(tài)水出現(xiàn)后才開始形成。天文學(xué)家普遍認(rèn)為這個形成時期至少持續(xù)了大約5億年。年以億計(jì)足以使我們的想象備受沖擊,卻遠(yuǎn)遠(yuǎn)無法表達(dá)海洋的古老和莊嚴(yán),至于它那高貴而神圣的基床,則躑躅在更為湮遠(yuǎn)的年代之中。
除了鹽分,入海的河流還會從陸地運(yùn)來大量的泥沙。每年,數(shù)不清的數(shù)以噸計(jì)的巖石圈沉積物都會在大河們的入海口找到歸宿。僅尼羅河每年就在其三角洲沉積約5000萬噸的巖屑。然而,就算我們一輩子依河而居,也不會發(fā)現(xiàn)河谷有任何拓寬的跡象。河谷的確日漸拓寬,但由于拓寬的速度過慢,人在短短的一生中注定無福見證可觀的變化。實(shí)際上,河流不僅會拓寬河谷,最終還會使大面積的流域歸于平地。以現(xiàn)在的侵蝕速度,密西西比河要在圣路易斯附近顯著地帶拓寬河谷,大約需要100萬年;如果要夷平整個密西西比河流域,則需要長達(dá)數(shù)千萬年的時間。已經(jīng)有充分的證據(jù)表明,現(xiàn)在陸地上的許多平坦區(qū)域,正是由河流年復(fù)一年的侵蝕所形成的。這樣一來,根據(jù)河流在地球上存在的時間來推算,也可以證明地球的誕辰應(yīng)該大大早于厄謝爾所認(rèn)為的公元前4004年。
在地質(zhì)演化的歷史上,流水和其他侵蝕陸地的力量不僅僅將成堆的巖屑傾入大洋,也會將沉積物保存在一些較淺的近陸海盆中,這些海盆上的海水年復(fù)一年地溶蝕著陸地。沉積物不斷地堆積、壓實(shí)、抬升,從而儲存下來,形成了沉積層。沉積層不斷積累,其平均厚度如今已經(jīng)超過65英里。然而,堆積作用的速率在地球各地差異甚迥,整個過程發(fā)生的時間也十分漫長,以至于任何試圖對這個時間做出精確推算的猜想都顯得荒誕不經(jīng)。
地質(zhì)學(xué)家隨即將目光轉(zhuǎn)向山脈。大量證據(jù)表明,山脈形成和抬升的速度之慢異乎尋常。最有力的證明,便是那些橫跨流域山脈而奔涌的河流,它們幾乎每時每刻以與山脈抬升相同的速度切割著山脈。哥倫比亞河就是其中的典型。它曾流經(jīng)一片未來將成為喀斯喀特山脈[7]的平坦區(qū)域。盡管山脈逐年抬升,河流切割山脈而形成的谷道幾乎與早先的河道毫無偏差。如今,哥倫比亞河自如地流過喀斯喀特山脈的中央,其雍容大度一如山脈存在之前。我們知道,河流侵蝕河道的速度是十分緩慢的,因此不難推出,這條不舍晝夜的河流所流經(jīng)山脈的抬升過程也同樣慢條斯理。在地球的歷史上,無數(shù)巍峨的高山都曾經(jīng)歷聳起與跌落的輪回,我們無法精確地以年為單位確定其經(jīng)歷的時間跨度,但是我們知道,那時間一定很長很長,一直延伸到想象難以觸及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