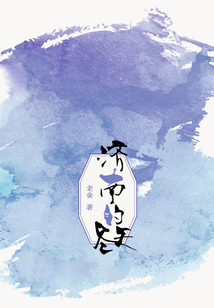
濟(jì)南的冬天
最新章節(jié)
- 第29章 夢(mèng)想的文藝(6)
- 第28章 夢(mèng)想的文藝(5)
- 第27章 夢(mèng)想的文藝(4)
- 第26章 夢(mèng)想的文藝(3)
- 第25章 夢(mèng)想的文藝(2)
- 第24章 夢(mèng)想的文藝(1)
第1章 濟(jì)南的冬天(1)
春風(fēng)
濟(jì)南與青島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個(gè)設(shè)若比作穿肥袖馬褂的老先生,那一個(gè)便應(yīng)當(dāng)是摩登的少女。可是這兩處不無(wú)相似之點(diǎn)。拿氣候說(shuō)吧,濟(jì)南的夏天可以熱死人,而青島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濟(jì)南也比青島冷。但是,兩地的春秋頗有點(diǎn)相同。濟(jì)南到春天多風(fēng),青島也是這樣;濟(jì)南的秋天是長(zhǎng)而晴美,青島亦然。
對(duì)于秋天,我不知應(yīng)愛(ài)哪里的:濟(jì)南的秋是在山上,青島的是海邊。濟(jì)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的草色在黃綠之間,松是綠的,別的樹(shù)葉差不多都是紅與黃的。就是那沒(méi)樹(shù)木的山上,也增多了顏色——日影、草色、石層,三者能配合出種種的條紋,種種的影色。配上那光暖的藍(lán)空,我覺(jué)到一種舒適安全,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的躺著,躺到永遠(yuǎn)。青島的山——雖然怪秀美——不能與海相抗,秋海的波還是春樣的綠,可是被清涼的藍(lán)空給開(kāi)拓出老遠(yuǎn),平日看不見(jiàn)的小島清楚的點(diǎn)在帆外。這遠(yuǎn)到天邊的綠水使我不愿思想而不得不思想;一種無(wú)目的的思慮,要思慮而心中反倒空虛了些。濟(jì)南的秋給我安全之感,青島的秋引起我甜美的悲哀。我不知應(yīng)當(dāng)愛(ài)哪個(gè)。
兩地的春可都被風(fēng)給吹毀了。所謂春風(fēng),似乎應(yīng)當(dāng)溫柔,輕吻著柳枝,微微吹皺了水面,偷偷的傳送花香,同情地輕輕掀起禽鳥(niǎo)的羽毛。濟(jì)南與青島的春風(fēng)都太粗猛。濟(jì)南的風(fēng)每每在丁香海棠開(kāi)花的時(shí)候把天刮黃,什么也看不見(jiàn),連花都埋在黃暗中,青島的風(fēng)少一些沙土,可是狡猾,在已很暖的時(shí)節(jié)忽然來(lái)一陣或一天的冷風(fēng),把一切都送回冬天去,棉衣不敢脫,花兒不敢開(kāi),海邊翻著愁浪。
兩地的風(fēng)都有時(shí)候整天整夜的刮。春夜的微風(fēng)送來(lái)雁叫,使人似乎多些希望。整夜的大風(fēng),門響窗戶動(dòng),使人不英雄的把頭埋在被子里;即使無(wú)害,也似乎不應(yīng)該如此。對(duì)于我,特別覺(jué)得難堪。我生在北方,聽(tīng)?wèi)T了風(fēng),可也最怕風(fēng)。聽(tīng)是聽(tīng)?wèi)T了,因?yàn)槁?tīng)?wèi)T才知道那個(gè)難受勁兒。它老使我坐臥不安,心中游游摸摸的,干什么不好,不干什么也不好。它常常打斷我的希望:聽(tīng)見(jiàn)風(fēng)響,我懶得出門,覺(jué)得寒冷,心中渺茫。春天仿佛應(yīng)當(dāng)有生氣,應(yīng)當(dāng)有花草,這樣的野風(fēng)幾乎是不可原諒的!我倒不是個(gè)弱不禁風(fēng)的人,雖然身體不很足壯。我能受苦,只是受不住風(fēng)。別種的苦處,多少是在一個(gè)地方,多少有個(gè)原因,多少可以設(shè)法減除;對(duì)風(fēng)是干沒(méi)辦法。總不在一個(gè)地方,到處隨時(shí)使我的腦子晃動(dòng),像怒海上的船。它使我說(shuō)不出為什么苦痛,而且沒(méi)法子避免。它自由的刮,我死受著苦。我不能和風(fēng)去講理或吵架。單單在春天刮這樣的風(fēng)!可是跟誰(shuí)講理去呢?蘇杭的春天應(yīng)當(dāng)沒(méi)有這不得人心的風(fēng)吧?我不準(zhǔn)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個(gè)地方去“避風(fēng)”呀!
想北平
設(shè)若讓我寫一本小說(shuō),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yàn)槲铱梢該熘抑赖膶懀汩_(kāi)我所不知道的。讓我單擺浮擱的講一套北平,我沒(méi)辦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覺(jué)太少了,雖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廿七歲才離開(kāi)。以名勝說(shuō),我沒(méi)到過(guò)陶然亭,這多可笑!以此類推,我所知道的那點(diǎn)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愛(ài)北平。這個(gè)愛(ài)幾乎是要說(shuō)而說(shuō)不出的。我愛(ài)我的母親。怎樣愛(ài)?我說(shuō)不出。在我想作一件事討她老人家喜歡的時(shí)候,我獨(dú)自微微的笑著;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時(shí)候,我欲落淚。言語(yǔ)是不夠表現(xiàn)我的心情的,只有獨(dú)自微笑或落淚才足以把內(nèi)心揭露在外面一些來(lái)。我之愛(ài)北平也近乎這個(gè)。夸獎(jiǎng)這個(gè)古城的某一點(diǎn)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愛(ài)的北平不是枝枝節(jié)節(jié)的一些什么,而是整個(gè)兒與我的心靈相粘合的一段歷史,一大塊地方,多少風(fēng)景名勝,從雨后什剎海的蜻蜓一直到我夢(mèng)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積湊到一塊,每一小的事件中有個(gè)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個(gè)北平,這只有說(shuō)不出而已。
真愿成為詩(shī)人,把一切好聽(tīng)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鵑似的啼出北平的俊偉。啊!我不是詩(shī)人!我將永遠(yuǎn)道不出我的愛(ài),一種像由音樂(lè)與圖畫所引起的愛(ài)。這不但是辜負(fù)了北平,也對(duì)不住我自己,因?yàn)槲业淖畛醯闹R(shí)與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與脾氣里有許多地方是這古城所賜給的。我不能愛(ài)上海與天津,因?yàn)槲倚闹杏袀€(gè)北平。可是我說(shuō)不出來(lái)!
倫敦,巴黎,羅馬與堪司坦丁堡,曾被稱為歐洲的四大“歷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倫敦的情形;巴黎與羅馬只是到過(guò)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沒(méi)有去過(guò)。就倫敦,巴黎,羅馬來(lái)說(shuō),巴黎更近似北平——雖然“近似”兩字要拉扯得很遠(yuǎn)——不過(guò),假使讓我“家住巴黎”,我一定會(huì)和沒(méi)有家一樣的感到寂苦。巴黎,據(jù)我看,還太熱鬧。自然,那里也有空曠靜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曠;不像北平那樣既復(fù)雜而又有個(gè)邊際,使我能摸著——那長(zhǎng)著紅酸棗的老城墻!面向著積水潭,背后是城墻,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葦葉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樂(lè)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適,無(wú)所求也無(wú)可怕,像小兒安睡在搖籃里。是的,北平也有熱鬧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極拳相似,動(dòng)中有靜。巴黎有許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與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溫和的香片茶就夠了。
論說(shuō)巴黎的布置已比倫敦羅馬勻調(diào)的多了,可是比上北平還差點(diǎn)事兒。北平在人為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sh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qū)不遠(yuǎn)。這種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經(jīng)驗(yàn)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shè)備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圍都有空閑的地方,使它們成為美景。每一個(gè)城樓,每一個(gè)牌樓,都可以從老遠(yuǎn)就看見(jiàn)。況且在街上還可以看見(jiàn)北山與西山呢!
好學(xué)的,愛(ài)古物的,人們自然喜歡北平,因?yàn)檫@里書多古物多。我不好學(xué),也沒(méi)錢買古物。對(duì)于物質(zhì)上,我卻喜愛(ài)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種費(fèi)錢的玩藝,可是此地的“草花兒”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錢而種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么,可是到底可愛(ài)呀。墻上的牽牛,墻根的靠山竹與草茉莉,是多么省錢省事而也足以招來(lái)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黃瓜,菠菜等等,大多數(shù)是直接由城外擔(dān)來(lái)而送到家門口的。雨后,韭菜葉上還往往帶著雨時(shí)濺起的泥點(diǎn)。青菜攤子上的紅紅綠綠幾乎有詩(shī)似的美麗。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與北山來(lái)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棗,柿子,進(jìn)了城還帶著一層白霜兒呀!哼,美國(guó)的橘子包著紙;遇到北平的帶霜兒的玉李,還不愧殺!
是的,北平是個(gè)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產(chǎn)生的花,菜,水果,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從它里面說(shuō),它沒(méi)有像倫敦的那些成天冒煙的工廠;從外面說(shuō),它緊連著園林,菜圃與農(nóng)村。采菊東籬下,在這里,確是可以悠然見(jiàn)南山的;大概把“南”字變個(gè)“西”或“北”,也沒(méi)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這樣的一個(gè)貧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點(diǎn)清福了。
好,不再說(shuō)了吧;要落淚了,真想念北平呀!
吊濟(jì)南
從民國(guó)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濟(jì)南住過(guò)四載。在那里,我有了第一個(gè)小孩,即起名為“濟(jì)”。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無(wú)論什么時(shí)候我從那里過(guò),總有人笑臉地招呼我;無(wú)論我到何處去,那里總有人惦念著我。在那里,我寫成了《大明湖》,《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和收在《趕集》里的那十幾個(gè)短篇。在那里,我努力地創(chuàng)作,快活地休息……四年雖短,但是一氣住下來(lái),于是事與事的聯(lián)系,人與人的交往,快樂(lè)與悲苦的代換,便顯明地在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地印劃在心中;時(shí)短情長(zhǎng),濟(jì)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鄉(xiāng)。
它介乎北平與青島之間。北平是我的故鄉(xiāng),可是這七年來(lái),我不是住濟(jì)南,便是住青島。在濟(jì)南住呢,時(shí)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不放心濟(jì)南的新家。好在道路不遠(yuǎn),來(lái)來(lái)往往,兩地都有親愛(ài)的人,熟悉的地方;它們都使我依依不舍,幾乎分不出誰(shuí)重誰(shuí)輕。在青島住呢,無(wú)論是由青去平,還是自平返青,中途總得經(jīng)過(guò)濟(jì)南。車到那里,不由的我便要停留一兩天。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名勝,閉了眼也曾想出來(lái),可是重游一番總是高興的:每一角落,似乎都存著一些生命的痕跡;每一小小的變遷,都引起一些感觸;就是一風(fēng)一雨也仿佛含著無(wú)限的情意似的。
講富麗堂皇,濟(jì)南遠(yuǎn)不及北平;講山海之勝,也跟不上青島。可是除了北平青島,要在華北找個(gè)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閉塞,而生活程度又不過(guò)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屬濟(jì)南了。況且,它雖是個(gè)大都市,可是還能看到樸素的鄉(xiāng)民,一群群的來(lái)此賣貨或買東西,不像上海與漢口那樣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穩(wěn)立在中國(guó)的文化上,城墻并不足攔阻住城與鄉(xiāng)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與神情,在這里是不易找到的。這使人心里覺(jué)得舒服一些。一個(gè)不以跳舞開(kāi)香檳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這里自自然然會(huì)感到一些平淡而可愛(ài)的滋味。
濟(jì)南的美麗來(lái)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還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繞郭。可惜這樣的天然美景,和那座城市結(jié)合到一處,不但沒(méi)得到人工的幫助而相得益彰,反而因市設(shè)的敷衍而淹沒(méi)了麗質(zhì)。大路上灰塵飛揚(yáng),小巷里污穢雜亂,雖然天色是那么清明,泉水是那么方便,可是到處老使人憋得慌。近來(lái)雖修成幾條柏油路,也仍舊顯不出怎么清潔來(lái)。至于那些名勝,趵突泉左右前后的建筑破爛不堪,大明湖的湖面已化作水田,只剩下幾道水溝。有人說(shuō),這種種的敗陋,并非因?yàn)楫?dāng)局不肯努力建設(shè),而是因?yàn)樗麄儛?ài)民如子,不肯把老百姓的錢都花費(fèi)在美化城市上。假若這是可靠的話,我們便應(yīng)當(dāng)看見(jiàn)老百姓的錢另有出路,在國(guó)防與民生上有所建設(shè)。這個(gè),我們卻沒(méi)有看見(jiàn)。這筆賬該當(dāng)怎么算呢?況且,我們所要求的并不是高樓大廈,池園庭館,而是城市應(yīng)有的衛(wèi)生與便利。假若在城市衛(wèi)生上有相當(dāng)?shù)脑O(shè)施,到處注意秩序與清潔,這座城既有現(xiàn)成的山水取勝,自然就會(huì)美如畫圖,用不著浪費(fèi)人工財(cái)力。
這倒并非專為山水喊冤,而是借以說(shuō)明許多別的事。濟(jì)南的多少事情都與此相似,本來(lái)可以略加調(diào)整便有可觀,可是事實(shí)上竟廢弛委棄,以至一切的事物上都罩著一層灰土。這層灰土下蠕蠕微動(dòng)著一群可好可壞的人,隱覆著一些似有若無(wú)的事;不死不生,一切灰色。此處沒(méi)有嶄新的東西,也沒(méi)有徹底舊的東西,本來(lái)可以令人愛(ài)護(hù),可是又使人無(wú)法不傷心。什么事都在動(dòng)作,什么可也沒(méi)照著一定的計(jì)劃作成。無(wú)所拒絕,也不甘心接受,不易見(jiàn)到有何主張的人,可也不易見(jiàn)到很討厭的人,大家都那么和氣一團(tuán),敷敷衍衍,不易捉摸,也沒(méi)什么大了不起。有電燈而無(wú)光,有馬路而擁擠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都沒(méi)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
按理說(shuō),這層灰色是不應(yīng)當(dāng)存到今日的,因?yàn)槲遑K案的血還鮮紅的在馬路上,城根下,假若有記性的人會(huì)閉目想一會(huì)兒。我初到濟(jì)南那年,那被敵人擊破的城樓還掛著“勿忘國(guó)恥”的破布條在那兒含羞的立著。不久,城樓拆去,國(guó)恥布條也被撤去,同被忘掉。拆去城樓本無(wú)不可,但是別無(wú)建設(shè)或者就是表示著忘去煩惱最為簡(jiǎn)便;結(jié)果呢,敵人今日就又在那里唱?jiǎng)P歌了。
在我寫《大明湖》的時(shí)候,就寫過(guò)一段:在千佛山上北望濟(jì)南全城,城河帶柳,遠(yuǎn)水生煙,鵲華對(duì)立,夾衛(wèi)大河,是何等氣象。可是市聲隱隱,塵霧微茫,房貼著房,巷聯(lián)著巷,全城籠罩在灰色之中。敵人已經(jīng)在山巔投過(guò)重炮,轟過(guò)幾晝夜了,以后還可以隨時(shí)地重演一次;第一次的炮火既沒(méi)能打破那灰色的大夢(mèng),那么總會(huì)有一天全城化為灰燼,沖天的紅焰趕走了灰色,燒完了夢(mèng)中人灰色的城,灰色的人,一切是統(tǒng)制,也就是因循,自己不干,不會(huì)干,而反倒把要干與會(huì)干的人的手捆起來(lái);這是死城!此書的原稿已在上海隨著“一·二八”的毒火殉了難,不過(guò)這一段的大意還沒(méi)有忘掉,因?yàn)槊看斡墒欣锏缴缴先ィ倳?huì)把市內(nèi)所見(jiàn)的灰色景象帶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會(huì)起了憂思。湖山是多么美呢,卻始終被灰色籠罩著,誰(shuí)能不由愛(ài)而畏,由失望而顫抖呢?
再說(shuō),破碎的城樓可以拆去,而敵人并未曾退出;眼不見(jiàn)心不煩,可是小鬼們就在眼前,怎能疏忽過(guò)去,視而不見(jiàn)呢?敵人的醫(yī)院,公司,鋪戶,旅館,分散在商埠各處。哪一個(gè)買賣也帶“白面”,即使不是專售,也多少要預(yù)備一些,余利作為婦女與孩子們的零錢。大批的劣貨壟斷著市場(chǎng),零整批發(fā)的嗎啡白面毒化著市民,此外還不時(shí)的暗放傳染病的毒菌,甚至于把他們國(guó)內(nèi)穿殘的破褲爛襖也整船的運(yùn)來(lái)銷賣。這夠多么可怕呢?可是我們有目無(wú)睹,仍舊逍遙自在;等因奉此是唯一的公事,奉命唯謹(jǐn)落個(gè)好官,我自為之,別無(wú)可慮。人家以經(jīng)濟(jì)吸盡我們的血,我們只會(huì)加捐添稅再抽斷老百姓的筋。對(duì)外講親善,故無(wú)抵制;對(duì)內(nèi)講愛(ài)民,而以大家不出聲為感戴。敵人的炮火是厲害的,敵人的經(jīng)濟(jì)侵略是毒辣的,可是我們的捆束百姓的政策就更可怕。濟(jì)南是久已死去,美麗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