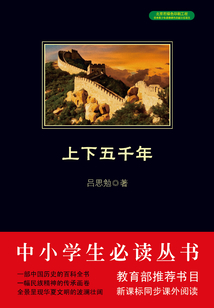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84評論第1章 緒論(1)
歷史的定義和價值
歷史是怎樣一種學問?究竟有什么用處?從前的人,常說歷史是“前車之鑒”,以為“不知來,視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為戒。這話粗聽似乎有理,細想卻就不然。世界是進化的,后來的事情,決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樣。病情已變而仍服陳方,豈惟無效,更恐不免加重。我們初和西洋人接觸,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敗的。
又有人說:歷史是“據事直書”,使人知所“歆懼”的。因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壞,就不免“遺臭萬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顧惜名譽。強悍的人,就索性連名譽也不顧。況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難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眾所共知的就不過是其表面;其內幕是永不能與人以共見的。又且事情愈大,則觀察愈難。斷沒有一個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說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據以直書,那就非愚則誣了,又有一種議論:以為歷史是講褒貶、寓勸懲,以維持社會的正義的。其失亦與此同。
凡講學問必須知道學和術的區別。學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術則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舊話說起來,就是“明體”和“達用”。歷史是求明白社會的真相的。什么是社會的真相呢?原來不論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為什么成為這樣的一個我?這決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樣的家庭中?受過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這都與我有關系。合這各方面的總和,才陶鑄成這樣的一個我。個人如此,國家社會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風俗;各種人有各種人的氣質;中國人的性質,既不同于歐洲;歐洲人的性質,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決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須追溯到既往;現在是決不能解釋現在的。而所謂既往,就是歷史。
所以從前的人說:“史也者,記事者也。”這話自然不錯。然而細想起來,卻又有毛病。因為事情多著呢!一天的新聞紙,已經看不勝看了。然而所記的,不過是社會上所有的事的千萬分之一。現在的歷史,又不過是新聞紙的千萬分之一。然則歷史能記著什么事情呢?須知道:社會上的事情,固然記不勝記,卻也不必盡記。我所以成其為我,自然和從前的事情,是有關系的;從前和我有關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為我的。我何嘗都記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為我。然則社會已往的事情,亦用不著盡記;只須記得“使社會成為現在的社會的事情”,就夠了。然則從前的歷史,所記的事,能否盡合這個標準呢?
怕不能罷?因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況社會的全體?然則從前歷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說:其病,是由于不知社會的重要。惟不知社會的重要,所以專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專描寫英雄、記述政治和戰役之類。殊不知特殊的事情,總是發生在普通社會上的。有怎樣的社會,才發生怎樣的事情;而這事情既發生之后,又要影響到社會,而使之改變。特殊的人物和社會的關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論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會,察其對于社會的結果。否則一切都成空中樓閣了。
從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會,這也無怪其然。因為社會的變遷,是無跡象可見的。正和太陽影子的移動,無一息之停,人卻永遠不會覺得一樣。于是尋常的人就發生一種誤解。以為古今許多大人物,所做的事業不同,而其所根據的社會則一。像演劇一般,劇情屢變,演員屢換,而舞臺則總是相同。于是以為現在艱難的時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來,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執陳方以藥新病。殊不知道舞臺是死的,社會是活物。
所以現在的研究歷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現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為社會正是在這里頭變遷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風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風化,當然不會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風化,則山崩只是當然的結果。
一切可以說明社會變遷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來說明社會的變遷。社會的變遷,就是進化。所以:“歷史者,所以說明社會進化的過程者也。”
歷史的定義既明,歷史的價值,亦即在此。
我國民族的形成
民族和種族不同。種族論膚色,論骨骼,其同異一望可知,然歷時稍久,就可以漸趨混合;民族則論語言,論信仰,論風俗,雖然無形可見,然而其為力甚大。同者雖分而必求合,異者雖合而必求分。所以一個偉大的民族,其形成甚難;而民族的大小和民族性的堅強與否,可以決定國家的盛衰。
一國的民族,不宜過于單純,亦不宜過于復雜。過于復雜,則統治為難。過于單純,則停滯不進。我們中國,過去之中,曾吸合許多異族。因為時時和異族接觸,所以能互相淬礪,采人之長,以補我之短;開化雖早,而光景常新。又因固有的文化極其優越,所以其同化力甚大。雖屢經改變,而仍不失其本來。經過極長久的時間,養成極堅強的民族性,而形成極偉大的民族。
各民族的起源發達,以及互相接觸、漸次同化,自然要待后文才能詳論。現在且先作一個鳥瞰。
中華最初建國的主人翁,自然是漢族。漢族是從什么地方遷徙到中國來的呢?現在還不甚明白。既入中國以后,則是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粵江流域漸次發展的。古代的三苗國,所君臨的是九黎之族,而其國君則是姜姓。這大約是漢族開拓長江流域最早的。到春秋時代的楚,而益形進化。同時,沿海一帶,有一種斷發文身的人,古人稱之為越。吳、越的先世,都和此族人雜居。后來秦開廣東、廣西、福建為郡縣,所取的亦是此族人之地。西南一帶有濮族。西北一帶有氐、羌。西南的開拓,從戰國時的楚起,至漢開西南夷而告成。西北一帶的開拓,是秦國的功勞。戰國時,秦西并羌戎,南取巴、蜀,而現今的甘肅和四川,都大略開辟。
在黃河流域,仍有山戎和嚴狁,和漢族雜居。嚴狁,亦稱為胡,就是后世的匈奴。山戎,大約是東胡之祖。戰國時代,黃河流域,和熱、察、綏之地,都已開辟。此兩族在塞外的,西為匈奴,東為東胡。東胡為匈奴所破,又分為烏桓和鮮卑。胡、羯、鮮卑、氐、羌,漢時有一部分人居中國。短時間不能同化,遂釀成五胡之亂。經過兩晉南北朝,才泯然無跡。
隋唐以后,北方新興的民族為突厥。回紇,現在通稱為回族。西南方新興的民族為吐蕃,現在通稱為藏族。東北則滿族肇興,金、元、清三代,都是滿族的分支。于是現在的蒙古高原,本為回族所據者,變為蒙古人的根據地,回族則轉入新疆。西南一帶,苗、越、濮諸族的地方,亦日益開辟。
總而言之:中華的立國,是以漢族為中心。或以政治的力量,統治他族;或以文化的力量,感化他族。即或有時,漢族的政治勢力不競,暫為他族所征服,而以其文化程度之高,異族亦必遵從其治法。經過若干時間,即仍與漢族相同化。現在滿、蒙、回、藏和西南諸族,雖未能和漢族完全同化,而亦不相沖突。雖然各族都有其語文,而在政治上、社交上通用最廣的,自然是漢語和漢文。宗教則佛教盛行于蒙、藏,回教盛行于回族。滿族和西南諸族,亦各有其固有的信仰。漢族則最尊崇孔子。孔子之教,注重于人倫日用之間,以至于治國平天下的方略,不具迷信的色彩。所以數千年來,各種宗教在中國雜然并行,而從沒有爭教之禍。我國民族的能團結,確不是偶然的。
中國疆域的沿革
普通人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為歷史上所謂東洋,系指亞洲而言;西洋系指歐洲而言。其實河川、湖泊,本不足為地理上的界線。烏拉山雖長而甚低,高加索山雖峻而甚短,亦不能限制人類的交通。所以歷史上東西洋的界限,是亞洲中央的蔥嶺,而不是歐、亞兩洲的界線。蔥嶺以東的國家和蔥嶺以西的國家,在歷史上儼然成為兩個集團;而中國則是歷史上東洋的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