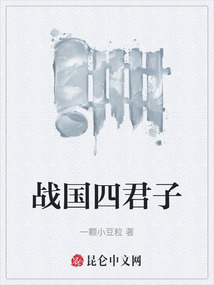
戰國四君子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前言
公元前260年的冬天,長平古道上的雪下得格外烈。
四十萬趙卒的尸骨在雪中半露半藏,像被凍僵的白棘,密密麻麻鋪向天際。秦兵的馬蹄踏過雪層,碾碎了尚未凍透的血肉,留下暗紅的印記,很快又被新雪覆蓋。消息像一群失了魂的鳥,撲棱棱掠過太行山,掠過黃河,掠過中原大地上星羅棋布的城郭——邯鄲城頭的守將攥碎了手中的符節,大梁夷門的看門人對著北方嘆了口氣,薛邑的城門在暮色中緩緩關閉,楚都壽春的朝堂上,使者們的爭論聲被風雪吞得只剩半截。
那時候,他們還不是后來被史書釘在“戰國四君子”匾額上的符號。
魏無忌在大梁的府邸里燒著竹簡,火苗舔舐著那些關于秦趙戰事的密報,他睫毛上凝著霜,像個怕被兄長發現秘密的孩子。趙勝在邯鄲的相府咳得撕心裂肺,血濺在案頭的地圖上,暈染開的紅跡正好蓋住上黨郡的位置,仿佛這樣就能抹去那個讓他悔恨終生的決定。田文站在薛邑的城樓上,看著遠處秦軍的營火,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腰間的佩劍,那劍曾劈開過秦國的關隘,此刻卻只想護住腳下這方小小的封地。黃歇剛從秦國的章臺宮回來,楚頃襄王賞賜的玉璧在袖中發燙,他望著北方的雪線,忽然想起在秦廷上,范雎笑著說“天下英雄,不過是時勢手里的棋子”。
他們是那個時代最耀眼的貴族,卻也是最矛盾的“士”。
信陵君魏無忌,魏國宗室里最不該有“平民心”的公子,偏要和看門人侯嬴分飲一壺濁酒,聽屠夫朱亥講市井里的道理。他的“禮賢下士”不是裝出來的姿態,是真的信“士為知己者死”,可這份天真最終要了他的命——或者說,成就了他的名。
平原君趙勝,趙國朝堂上最像“君子”的相邦,府里養著三千門客,卻因為小妾嘲笑跛子差點丟了人心。他不是不懂得“尊重”,只是貴族的傲慢像一層薄冰,裹在骨頭外面,平時看著晶瑩剔透,踩碎了才知道底下全是泥。
孟嘗君田文,齊國宗室里最不像“君子”的異類,母親是卑賤的侍妾,從小被父親扔在一邊,靠著“雞鳴狗盜”之徒才活下來。他養士從來不是為了“禮”,是為了“用”,就像農夫囤糧,旱澇保收。可當他真的成了“薛邑之王”,卻在某個深夜對著馮諼的空座發愣——那個彈著劍要魚要車的門客,到底圖他什么?
春申君黃歇,四君子里唯一不是宗室的“異類”,靠著一張嘴從秦國的刀下救回了楚國太子,卻在晚年把懷孕的姬妾送進王宮。他最懂“向上爬”的滋味,也最懂“站不穩”的恐懼,就像踩著高蹺走在刀尖上,風光是真的,疼也是真的。
后人說他們“養士三千,輔國安邦”,可翻開那些泛黃的竹簡,看到的卻是一群在亂世里掙扎的人。他們有私心,有怯懦,有算錯棋的時候,也有被權力迷了眼的瞬間。信陵君竊符救趙,是大義,也是對兄長的背叛;平原君受上黨之地,是為趙國拓土,也是為自己博名;孟嘗君聯秦伐齊,是自保,也是忘恩;春申君“移花接木”,是貪婪,也是對“非宗室”身份的焦慮。
他們不是完美的君子,只是在“禮崩樂壞”的時代里,努力想給“士”和“君”找個位置的人。
長平之戰像一道分水嶺,把他們的人生劈成了兩半。戰前,他們是各國的“新星”,忙著在權力的棋盤上落子;戰后,他們成了“舊人”,看著秦國的鐵騎踏碎了一個又一個國家,才明白自己守的不是一座城、一個國,是那個即將逝去的“貴族時代”。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總在想:如果能穿越回去,在大梁的酒肆里遇到那個微服的信陵君,在邯鄲的雪夜里撞見咳血的平原君,在薛邑的城樓上碰到望著秦營的孟嘗君,在壽春的宮道上追上那個揣著玉璧的春申君,該對他們說些什么?
或許什么都不必說。他們的故事,本就是對那個時代最好的注解。
戰國的風,吹了兩千年,還在吹。那些關于理想與現實、道義與利益、個體與時代的掙扎,從來沒有停過。就像長平古道上的雪,下了又化,化了又下,蓋住了尸骨,卻蓋不住那些在風雪里站過的人。
翻開這本書,你會看到他們的榮耀,也會看到他們的狼狽;看到他們的堅守,也會看到他們的妥協。他們是信陵君、平原君、孟嘗君、春申君,也是每一個在時代里努力活過的人。
風起于青萍之末,而他們,就是那個時代最烈的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