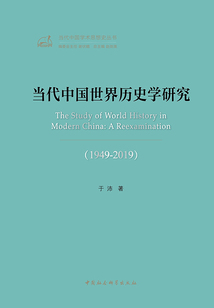
當代中國世界歷史學研究1949—2019(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叢書)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代序 國世界史學者的社會責任[1]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世界歷史研究最深刻的變化,是在其發展歷程中,實現了從翻譯、編譯,以及一般性地介紹向深入、系統、獨立研究的轉變,“世界歷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完全具備了任何一門科學學科所具有的科學形態,以及不可或缺的理論和方法。世界史研究是中國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研究隊伍的成長、壯大,以及一系列標志性的成果問世,其地位和影響日漸擴大。當然,這是就世界歷史整體學科的狀況而言的。今天中國的世界歷史研究,無論在通史、斷代史、地區史、國別史,還是在專門史、歷史人物、歷史文獻的研究上,都可謂碩果累累;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均“前無古人”,“史無前例”。黨的十七大報告論述“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時提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推進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鼓勵哲學社會科學界為黨和人民事業發揮思想庫作用,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和優秀人才走向世界”[2]。這使廣大世界史工作者不僅深受鼓舞,更深感責任重大。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如何使世界史研究順應時代發展要求,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我們應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做出明確的回答。
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是重視對外國歷史的研究。司馬遷《史記》,分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五類,計130卷。有關外國的介紹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列傳”中,如《大宛傳》《匈奴傳》等,包括朝鮮、越南、印度,以及大宛、烏孫、康居、燕蔡、大月氏、安息等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3],是司馬遷歷史思想的核心。而要達此目的,也需要對中國以外地區的了解。只不過當時的某些“外國”,現在早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在當時并沒有在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史記》以下的二十五史,除了《陳書》《北齊書》之外,其他二十三種史書中,都涉及了對外國的介紹和研究,各代官修紀傳體史書中都有“外國傳記”,包括東南亞、中亞、西南亞、歐洲和西非許多重要的地區和國家。
近代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的萌生,始于19世紀中葉,這和中國“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聯系在一起。中國先進分子為拯救民族危機“睜眼看世界”,林則徐編譯《四洲志》、魏源編纂《海國圖志》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甲午戰爭、辛亥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影響下,中國世界史研究從“萌生”開始逐漸發展,力圖通過外國“亡國史”“革命史”“建國史”的研究,尋找中國獨立、自由、解放的道路。辛亥革命期間,美國《獨立宣言》(當時譯為《美國獨立檄文》或《美利堅民主國獨立文》)曾五次在《國民報》《民國報》等報刊全文發表,絕非偶然。20世紀初,唯物史觀傳入中國,對中國史學,特別是對中國的世界歷史研究,產生了革命性的深遠影響。1920年,李大釗在《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理愷爾的歷史哲學》一文中,深入淺出地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他強調“欲單從上層上說明社會的變革即歷史而不顧基址,那樣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歷史。上層的變革,全靠經濟基礎的變動,故歷史非從經濟關系上說明不可”。“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4]除李大釗外,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蔡和森、李達、瞿秋白、惲代英等,也開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在唯物史觀理論的指導下,人們對“改造世界”的理性認識,有了新的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抽象的“學術”。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的特點是與時代的脈搏同時跳動,它研究方向的主流,從不曾脫離時代的主題。中國世界史研究萌生時期即表現出的特點。在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繼續發揚光大,并不斷賦予其新的社會意義和時代內容。
1980年,中國的社會發展已經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的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也迎來了自己的春天,進入迅速發展時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全面恢復;北京大學等高校歷史系開始設立世界歷史專業;高校和研究機構開始招收世界史專業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國家級的《世界歷史》雜志創刊,在國內外公開發行;10余個全國性的世界史研究會(國別史和專門史)相續成立;國家社科基金設立世界史組,開始接受世界歷史科研項目的申報和評審;等等。然而,這一切令人鼓舞的事實,并沒有解決一個更為迫切、更為直接的現實問題,即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繼承發揚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優秀傳統,自覺堅持世界史研究的正確方向問題。“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造成的嚴重思想混亂,要真正做到“撥亂反正”尚需要時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不等于這條路線就可以一帆風順地貫徹落實了。改革開放初期,西方學術思潮,包括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魚目混珠,大量介紹到國內來,一時不少奇談怪論充斥其間,有人甚至公開鼓吹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出路,是“國際化”,是“價值中立”,是“全盤西化”等,所有這些都使得“方向”問題越發重要。
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世界歷史研究如何體現出它的社會責任尤其重要。為名利而研究,還是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研究,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基本立場問題。世界史或其他學科研究的主、客體有其特定的內容和規范,但這與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針并不相悖。世界歷史研究的社會責任,從根本上要落實在“二為”方針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世界歷史研究的成果令世人矚目,但毋庸諱言,在前進的道路上仍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少數人仰承洋人的鼻息,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史學理論,生吞活剝,盲目崇拜,甚至主張放棄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話語系統,去與西方“接軌”,使我們的學術研究受制于人,喪失起碼的學術尊嚴和民族自信心。這與我們所說的有選擇地汲取外國史學的優秀成果為我所用,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當前,社會上的浮躁風氣和商業上的投機心理侵蝕著學術,世界歷史研究也不是在真空之中,如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復、粗制濫造、假冒偽劣、抄襲剽竊;熱衷炒作、拉拉扯扯,無原則地吹捧;等等,而信仰、理想、使命等,卻被拋到九霄云外。凡此種種,都是沒有起碼的社會責任感的具體表現。學術研究是一項嚴肅、艱苦而又崇高的工作,研究人員要自覺地承擔起社會責任。我國的世界歷史研究要發展,有許多事情要做,但首先要加強研究人員的社會責任感,要牢記學術研究的目的,不為名利所惑。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水平,體現著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狀態和文明素質。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國家文化力量的重要標志和體現,是國家重要的戰略性資源。充分認識廣大世界史工作者的社會責任,在今天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聯系到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的現實,筆者以為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加強世界史工作者的社會責任。
其一,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統領世界史研究,重視對世界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在充分實現世界史研究的科學認識功能和社會功能的同時,服務大局,自覺地堅持“二為”方向。關于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問題的研究,這既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理論問題,也是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理論問題。吳于廑、齊世榮在編纂《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和《世界通史》時,曾探討過這個問題,目前,世界史學界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正不斷深化。
吳于廑認為,人類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經歷了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的漫長過程。縱向發展,“是指人類物質生產史上不同生產方式的演變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會形態的更迭”。而橫向發展,“是指歷史由各地區間的相互閉塞到逐步開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聯系密切,終于發展成為整體的世界歷史這一客觀過程而言的”。“研究世界歷史就必須以世界為一全局,考察它怎樣由相互閉塞發展為密切聯系,由分散演變為整體的全部歷程,這個全部歷程就是世界歷史。”[5]吳于廑關于世界史研究理論體系的立論基礎,是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中,馬克思首次提出了世界歷史概念并逐漸形成了自成系統的世界歷史理論。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與交往的發展,“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6]。馬克思強調:“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7]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唯物史觀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今天我們理解“全球史觀”的理論基礎。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相繼出版了齊世榮總主編的4卷本《世界史》。這部著作的《前言》寫道:“馬克思主義根據人類社會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質,把人類歷史發展的諸階段區分為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和共產主義制幾種生產方式和與之相應的幾種社會形態。它們構成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的縱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國家的歷史都一無例外地按照這個序列向前發展。有的沒有經歷過某一階段,有的長期停頓在某一階段。總的說來,人類歷史由低級社會形態向高級社會形態的更迭發展,盡管先后不一,形式各異,但這個縱向發展的總過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規律性的意義。”[8]當前,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問題的討論不斷深化的主要標志,是將理論上的探析,同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人類學筆記》的研究結合起來,使人們不僅從理論上,而且通過人類歷史矛盾運動的實際過程,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的真諦。
其二,理論聯系實際,在世界歷史研究中,努力做到深刻的理論探究與高度地關注現實的辯證統一。中國世界史研究歷史感與現實感并重的優秀傳統,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加重視弘揚歷史研究的時代精神,將歷史認識建立在對當代世界和中國現實的深刻理解上。對現實理解的深度,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歷史認識的深度,成為越來越多的世界史學者的共識。“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局勢發生新的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繼續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各種矛盾錯綜復雜,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沒有改變,我們仍面臨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我國改革發展處在關鍵時期,社會利益關系更為復雜,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9]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只有清醒地認識到機遇和挑戰并存的國際國內現實,我國的世界史研究才能有根有魂,廣大世界史學者才能自覺地肩負起社會責任。例如,彭樹智主編的《中東國家通史》13卷,包括《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拉克卷》《土耳其卷》《巴勒斯坦卷》《伊朗卷》《埃及卷》《阿富汗卷》《敘利亞和黎巴嫩卷》《也門卷》《海灣五國卷》《約旦卷》《塞浦路斯卷》。這是我國第一部多卷本《中東國家通史》著作,由商務印書館自2000年陸續出版,這既是一部學術精品,對世界歷史學科建設有積極意義,同時也是對世界歷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論”的有力批判。
又如,美國歷史學家魏特夫在《東方專制主義》中提出“治水社會”的理論,杜撰出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概念,他不僅攻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歪曲古代中國、希臘、印度和埃及的歷史,而且污蔑社會主義國家是“東方專制主義的變種”。為揭露這部“學術著作”的欺騙性和反動性,1995年,《史學理論研究》雜志開辟專欄,組織世界史學者撰寫論文,從東方社會的特點和性質、東西方專制制度比較、水利在東方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概念的歷史考察”等方面,系統地揭露了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在理論上史實上的謬誤,以及政治上的反動政治意圖。
包括世界史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有一個不可回避的社會責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要旗幟鮮明,不能失語。不久前病逝的吳冠中先生曾說:“走上藝術的路,就是要殉道,還需要痛苦,而我的心永遠被痛苦纏繞著。”[10]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同樣需要殉道者的精神,要時刻牢記自己平凡而又崇高的使命。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一定要充分認識自身肩負的歷史使命,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去努力工作,在科研工作中開拓創新、錘煉自我,爭取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績。
注釋
[1]《中國世界史學者的社會責任》,曾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第32卷,第3期,收入本書為《代序》時,作了一些修改。
[2]《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頁。
[3]《漢書》卷62《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35頁。
[4]李大釗:《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理愷爾的歷史哲學》,見李大釗《史學要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344頁。
[5]《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5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頁。
[8]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當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9]《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見《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頁。
[10]韓小蕙:《文藝·人生·時代——從吳冠中現象看文藝家與時代的辯證關系》,《光明日報》2010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