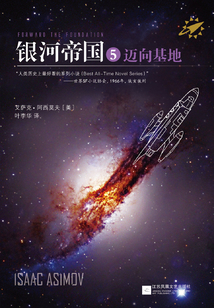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4評論第1章 伊圖·丹莫刺爾(1)
伊圖·丹莫刺爾:……雖然在克里昂大帝一世在位的大半時期,伊圖·丹莫刺爾無疑是政府中真正的掌權者,歷史學家對他的統治方式卻眾說紛紜。根據傳統的詮釋,他是銀河帝國分裂前最后一個世紀間,那些一個接一個、強勢而無情的壓迫者之一。但如今已經浮現一些修正主義觀點,堅持他即使是獨裁者,也屬于開明專制派。根據此一觀點,他與哈里·謝頓的關系被人大做文章(不過真相永遠無法確定),尤其是在拉斯金·久瑞南事件那段非常時期。后者的曇花一現……
——《銀河百科全書》
01
“我再講一遍,哈里,”雨果·阿馬瑞爾說,“你的朋友丹莫刺爾麻煩大了。”他非常輕微地強調了“朋友”二字,而且帶著如假包換的嫌惡神態。
哈里·謝頓察覺到話里的酸味,卻未加理會,他從三用電腦前抬起頭來。“我再講一遍,雨果,這毫無意義。”然后,他帶著一點厭煩——一點而已,補充道:“你為什么要堅持這件事,無端浪費我的時間?”
“因為我認為它很重要。”雨果以挑戰的架式坐下,這種姿態代表他不會輕易動搖。他人在這里,而且要留在這里。
八年前,他只是達爾區的一個熱閭工,社會階級低得不能再低。是謝頓將他從那個階級拉拔出來,使他成為一名數學家與知識分子——非但如此,還成為一名心理史學家。
他無時無刻不記得過去與現在的分際,以及這個轉變是拜何人之賜。這就意味著,假如為了謝頓好,他必須對謝頓疾言厲色,那么即使他對這位老大哥萬分敬愛,即使他顧及自己的前途,也都無法阻止他這樣做。他虧欠謝頓太多太多,這份疾言厲色只是其中之一。
“聽我說,哈里,”他一面說,一面用左手虛劈一記,“由于某種我無法理解的原因,你對這個丹莫刺爾評價頗高,但我可不然。除你之外,那些值得我尊重他們意見的人,對他都沒有什么好感。我不在乎他這個人發生什么事,哈里,可是只要我想到你在乎,我就沒有選擇余地,不得不向你報告這件事。”
謝頓微微一笑,一半是針對此人的熱忱,另一半是認為他的關心毫無用處。他很喜歡雨果·阿馬瑞爾,甚至不只是‘喜歡’兩字所能形容。他一生中曾有一段短暫時期,在川陀這顆行星表面四處逃亡,雨果便是他當時結識的四個人之一。另外三人是伊圖·丹莫刺爾、鐸絲·凡納比里以及芮奇。后來,他再也沒有結識類似的患難之交。
這四個人,以四種不同的特殊方式,成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就雨果·阿馬瑞爾而言,是因為他對心理史學原理的敏捷領悟力,以及對新領域充滿想象的洞察力。謝頓感到相當安慰,因為他知道,倘若在這個領域的數學尚未發展完善之際(它的進展多么緩慢,過程多么困難重重),自己就有什么三長兩短,至少還有一個優秀的頭腦會繼續這項研究。
他說:“很抱歉,雨果,我不是有意對你不耐煩,或是對你急著要我了解的事不屑一顧。只是我手頭的工作,身為系主任……”
這回輪到雨果露出笑容,他趕緊壓下一聲輕笑。“很抱歉,哈里,我不該發笑,但你沒有擔任那個職位的天分。”
“我十分了解,但我必須學習。我必須好像是在做些無害的事,而再也沒有——再也沒有——比在斯璀璘大學數學系當系主任更無害的事。我可以讓瑣事占滿我整天的作息,這樣一來,就沒有人需要知道或問及我們的心理史學研究進展。可是問題在于,我的確讓瑣事占滿我整天的作息,我沒有足夠的時間……”他環顧一下這間研究室,對儲存在電腦中的材料瞥了一眼。這些電腦資料只有他與雨果能夠開啟,而且刻意以自家發明的符號記述,即使外人誤打誤撞闖了進去,也無法理解那些符號的意義。
雨果說:“一旦在這個職位上進入狀況,你就能把工作分派下去,然后便會有較多的時間。”
“但愿如此。”謝頓透著懷疑說,“別管了,告訴我,哪件和伊圖·丹莫刺爾有關的事那么重要?”
“只不過是伊圖·丹莫刺爾,浩哉吾皇的首相,正忙著制造一場叛變。”
謝頓皺起眉頭。“他為什么要那樣做?”
“我不是說他要,但是他正在那樣做——不論他知不知道,而他的一些政敵還幫了很大的忙。你也了解,我可無所謂。我甚至認為,在理想情況下,將他趕出皇宮,逐出川陀……甚至逼他遠離帝國會是件好事。可是正如我剛才所說,你對他評價頗高,所以我才來警告你,因為我覺得你對最近的政治趨勢關心得還不夠。”
“還有許多更重要的事要做。”謝頓溫和地說。
“比如說心理史學,我同意。可是如果我們對政治始終無知,心理史學的發展怎么會有成功的希望?我是指當今的政治。此時,此刻,才是現在轉變成未來的時刻。我們不能光研究過去,因為我們知道過去發生過什么。我們能用來檢驗研究成果的,是現在和不久的將來。”
“在我的感覺中,”謝頓說,“我以前好像聽過這番論述。”
“以后你還會聽到。向你解釋這點,似乎對我并沒有什么好處。”
謝頓嘆了一口氣,將身子靠向椅背,帶著微笑凝視著雨果。這個小老弟也許滿身是刺,可是他對心理史學極其認真,而這就勝于一切。
雨果仍有當年熱閭工的本色。他擁有寬闊的肩膀,以及慣于重度體力勞動的魁梧體格。他沒有讓身體松軟下來,這倒是件好事,因為它對謝頓是個激勵,幫助他抗拒把每一分鐘都花在書桌前的沖動。謝頓并沒有雨果那般的體力,但他仍舊保有一名角力士的技能——雖說他今年已經四十歲,絕不可能永遠保有,不過目前還沒有衰退的跡象。拜每日勤練之賜,他的腰身仍然苗條,雙腿與雙臂也結實依舊。
他說:“你對丹莫刺爾如此關切,不可能純粹由于他是我的朋友,你一定還有別的動機。”
“這點毫無疑問。只要你是丹莫刺爾的朋友,你在這所大學的職位便有保障,你就能繼續從事心理史學的研究。”
“這就對了。所以我的確有與他為友的理由,這絕不是你無法理解的。”
“你有必要去巴結他,這點我能理解。但至于友誼嘛,這,就是我無法理解的。然而,假如丹莫刺爾喪失權力,姑且不論對你的職位可能造成什么影響,到時候克里昂會親自掌理帝國,這就會加速它的衰落。在我們發展出心理史學所有的枝節,使它成為拯救全體人類的科學之前,無政府狀態便可能來臨。”
“我懂了。但是,你可知道,我實在認為我們無法及時發展出心理史學,借以阻止帝國的衰亡。”
“即使無法阻止,我們至少能緩沖這個效應,對不對?”
“或許吧。”
“那么,這就對了。我們在安定中工作的時間越長,我們能阻止衰亡或至少減輕沖擊的機會就越大。既然情況如此,那么倒推回來,拯救丹莫刺爾也許就有必要,不論我們——或至少我自己——喜不喜歡這樣做。”
“但你剛才還說,希望見到他被趕出皇宮,逐出川陀,甚至遠離帝國。”
“沒錯,我是說在理想情況下。但我們并不是處于理想的情況,所以我們需要我們的首相,即使他是個壓迫和專制的工具。”
“我懂了。可是你為什么認為帝國已接近崩潰的邊緣,失去一位首相就會引爆呢?”
“心理史學。”
“你用它作預測嗎?我們甚至連骨架都沒搭好,你能作些什么預測?”
“別忘了還有直覺這回事,哈里。”
“直覺自古就有,但我們要的不只是這個,對不對?我們要的是個數學方法,它能夠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告訴我們某些特定發展的幾率。假使直覺足以引導我們,我們就根本不需要心理史學。”
“這未必是個無法并存的情況,哈里。我是在說兼容并蓄:二者的結合。這也許好過在兩者中作出選擇——至少在心理史學盡善盡美之前。”
“倘若真能完成的話。”謝頓說,“別管了,告訴我,丹莫刺爾的危機是打哪兒來的?有可能傷害他或推翻他的是什么東西?我們是不是在討論丹莫刺爾可能被推翻?”
“是的。”雨果繃起臉來。
“那么可憐可憐我的無知,告訴我吧。”
雨果面紅耳赤。“你太謙虛了,哈里。不用說,你一定聽說過九九·久瑞南。”
“當然,他是個群眾煽動家——慢著,他是從哪兒來的?尼沙亞,是嗎?一個微不足道的世界,我猜,居民以牧羊為生,生產高品質的乳酪。”
“對了。然而,他不只是群眾煽動家。他統率一個強大的黨派,而且它一天比一天強大。他說,他的目標是爭取社會公平,擴大人民的參政權。”
“沒錯,”謝頓說,“這些我都聽說過。他的口號是‘政府屬于人民’。”
“不完全對,哈里。他說的是‘政府即人民’。”
謝頓點了點頭。“嗯,你可知道,我相當認同這個想法。”
“我也是,久瑞南若是真心的,我全心全意贊成。但其實不然,他只是拿它當踏腳石。那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要把丹莫刺爾趕下臺,接下來,控制克里昂一世就會很簡單。然后久瑞南自己會坐上皇位,那時他就成了人民。是你自己告訴我的,在帝國歷史上,這種事例比比皆是。而且如今帝國已大不如前,變得衰弱且不穩定。過去僅會令它搖晃的沖擊,現在卻可能將它撞得粉碎。帝國將陷于內戰,永遠無法自拔,我們卻沒有心理史學指導我們該怎么做。”
“對,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想要除掉丹莫刺爾,也絕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不清楚久瑞南的勢力變得多強了。”
“他變得多強并不重要。”謝頓眉宇間似乎掠過一個念頭,“我不懂他父母為何替他取名九九,這名字聽來有些幼稚。”
“他的父母和這件事無關。他的真名叫拉斯金,那是尼沙亞上一個很普通的名字。九九是他自己取的,想必是源自他的姓氏第一個字。”
“那他更傻了,你不覺得嗎?”
“不,我可不覺得。他的追隨者總是喊著:‘九……九……九……九……’一遍又一遍,頗有催眠作用。”
“好吧,”謝頓再度俯身面對他的三用電腦,開始調整它所產生的多維模擬,“我們靜觀其變。”
“你怎能那么不當一回事?我是在告訴你危險迫在眉睫。”
“不,不會的。”謝頓答道,他的雙眼如鋼鐵般冷酷,他的聲音突然強硬起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不知道什么?”
“我們改天再來討論這個問題,雨果。現在,繼續做你的研究吧,讓我來擔心丹莫刺爾和帝國的局勢。”
雨果緊抿著嘴,不過他對謝頓的服從早已根深蒂固。“好的,哈里。”
但也不是強到壓倒一切。他在門口轉過頭來,說道:“你在鑄成一個錯誤,哈里。”
謝頓輕輕一笑。“我可不這么想,反正我聽到你的警告了,我不會忘記的。話說回來,一切都會平安無事。”
雨果離去后,謝頓的笑容隨即斂去。真的一切都會平安無事嗎?
02
可是,謝頓雖然沒有忘記雨果的警告,卻也未曾特別用心想過。他的四十歲生日倏來倏去,照例又帶給他一次心理打擊。
四十歲!他已不再年輕。生命不再像一片浩瀚的未知領域,地平線不再隱沒在遙遠的盡頭。他來到川陀已有八年,時間過得真快。再過八年,他就將近五十歲,老年歲月即將來臨。
而在心理史學的研究上,他甚至還沒有一個好的開始。雨果·阿馬瑞爾總是興致勃勃地談論一些定律,并且根據直覺提出大膽的假設,再根據假設導出他的方程式。但是怎么有可能測試那些假設呢?心理史學還不是一門實驗性科學;心理史學的完整研究所需的實驗,將牽涉到許多世界的民眾、數個世紀的時間,還要完全不顧任何道德責任。
這是個不可能解決的難題,而系務工作所花的每一分鐘都令他心痛,所以這天傍晚,他是懷著憂郁的心情走回家去。
通常他只要在校園里走一趟,總是能令精神振奮起來。斯璀璘大學的穹頂很高,整個校園都讓人有置身露天的感覺,卻不必忍受像他上次(也是唯一一次)造訪皇宮時遇到的那種天氣。這兒有許多樹木、草坪、人行步道,他仿佛回到了當年母星赫利肯的那個學院。
今日的天氣設定成陰天的幻象,其中陽光(當然沒有太陽,有的只是陽光)以不規則的間隔忽隱忽現。氣溫有點涼,只有一點而已。
在謝頓的感覺中,天涼的日子似乎較過去頻繁了些。是川陀在節約能源嗎?或是越來越缺乏效率?還是他年紀漸漸大了(想到這里,他在心中皺了一下眉頭),體內的血液逐漸稀薄?他將雙手放進外套口袋里,還縮了縮脖子。
通常他都不必依靠意識引導自己前進。從他的研究室到他的電腦房,再從那里到他的寓所,或是相反的方向,他的身體都十分熟悉這些路程。在一般情況下,他總是一邊走一邊想別的事。但是今天,一個聲音貫穿他的意識,一個沒有意義的聲音。
“九……九……九……九……”
那個聲音相當輕柔而且遙遠,但是它喚起了一段記憶。沒錯,雨果的警告,那個群眾煽動家。他正在校園內嗎?
謝頓未曾刻意作出決定,他的雙腿便突然轉向,帶他爬過了小丘,向大學運動場前進。那里是學生做柔軟體操和各項運動,以及大放厥詞的場所。
在運動場中央,聚集著不多不少的一群學生,正在狂熱地齊聲吶喊。而某個演講臺上,站著一個他不認識的人,那人聲音洪亮,并且帶著搖擺的節奏。
然而,他并不是那個久瑞南。謝頓曾在全息電視上看過久瑞南幾次,自從聽到雨果的警告,謝頓便特別留意。久瑞南身材高大,微笑時帶著一種邪惡的革命情感。他有著濃密的沙色頭發,以及一對淺藍色眼睛。
這個演講者則是小個子——瘦弱、寬嘴、黑頭發、大嗓門。謝頓并未注意聽那些話,不過還是聽到一句“權力由一人之手轉移至眾人”,接著便有許多人高聲附和。
很好,謝頓心想,可是他打算怎么實現呢?還有,他是認真的嗎?
現在他來到了人群的外圍,正在四下尋找熟人。他發現了芬南格羅斯,數學系大學部的一個學生。他是個不錯的年輕人,有著黝黑的皮膚與卷卷的頭發。
“芬南格羅斯。”他喊道。
“謝頓教授。”芬南格羅斯望了一會兒才應聲,仿佛認不出手邊沒有鍵盤的謝頓。他快步走過來。“您來聽這家伙演講嗎?”
“我來這兒只是要找出喧囂的來源,此外沒有任何目的。他是誰?”
“教授,他叫納馬提,他在替九九發表演說。”
“我聽到了。”謝頓答道,此時那些齊聲吶喊再度響起。顯然,每當演講者提出一個強而有力的論點,聽眾就會開始吶喊。“但這個納馬提到底是誰?我沒聽過這個名字。他是哪個系的?”
“他不是這所大學的成員,教授,他是九九的人。”
“如果他不是這所大學的成員,那么除非有許可證,否則他就無權在此演講。你認為他有許可證嗎?”
“教授,我可不知道。”
“好吧,那我們來弄清楚。”
謝頓正要走入人群,芬南格羅斯卻一把拉住他的袖子。“別輕舉妄動,教授,他帶著幾名打手。”
演講者身后站著六個年輕人,彼此間有一段距離。他們雙腿張開,兩臂交抱,臉色陰沉。
“打手?”
“武斗用的,以防有人想做什么傻事。”
“那么他絕不是這所大學的成員,即使他有一張許可證,也不能帶著你所謂的‘打手’。芬南格羅斯,給大學安全警衛發訊號。就算沒有人發訊號,他們現在也該來了。”
“我想他們不愿惹麻煩。”芬南格羅斯喃喃道,“拜托,教授,別出頭。如果您要我去找安全警衛,我這就去,但請您等他們來了再說。”
“也許警衛還沒來,我就能把他們驅散。”
他開始往里面擠。這并不太難,在場有些人認識他,其他人也看得到他的教授肩章。他走到演講臺前,雙手搭在上面,輕哼一聲,縱身跳上三尺高的臺子。他懊惱地暗自想道,十年前,他用一只手就能辦到,而且不會哼這一聲。
他在演講臺上站直身子。那演講者早已住口,正以機警而冰冷的目光望著他。
謝頓平靜地說:“先生,請出示對學生演講的許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