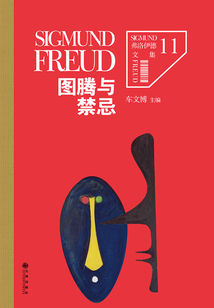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圖騰與禁忌--蒙昧人與神經癥患者在心理生活中的某些相同之處(1)
按語
本書是弗洛伊德應用精神分析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社會心理學的首次嘗試。也是弗洛伊德第一次集中闡述自己關于宗教和道德起源的一部重要著作。全書由四篇論文組成,通過蒙昧人與強迫神經癥患者的比較,推斷了圖騰崇拜的本原意義。認為圖騰禁忌反映了人類對亂倫的恐懼;塔布禁忌則是矛盾情感的產物。它構成了蒙昧人的原始道德觀;蒙昧人的法術思維品質--思維萬能,構成了他們泛靈論原始思維模式。在這一思維模式作用下,他們用支配心靈生活的法則來支配實在之物,漸漸形成了自己的神靈觀念,并因此為宗教的形成鋪平了道路。還斷定圖騰崇拜中的圖騰動物乃是“原父”的替代物;圖騰崇拜的來源即在于那些被父親驅逐的兒子們聯合在一起,殺害并吞食了自己的父親以后產生的罪惡感、悔恨和懷念,故所有的神都是依據父親的形象的構成物。而宗教的發展正是來自于對弒父罪惡感的“集體意識”,人們把這種心理過程以潛意識的形式一代又一代地積淀。這種唯心理論(psychologism)的觀點固然并非科學,但對我們研究宗教和道德起源的認識根源也不無參考價值。
序言
這里的四篇論文最初以本書副標題為題目,發表于《意象》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上。《意象》是一種在我指導下出版的期刊。這幾篇論文是我在將精神分析學的觀點和研究成果應用于社會心理學(V lkerpsychologie)中某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方面所做的最初嘗試。因此,它們與馮特(Wilhelm Wundt)所做的廣泛詳盡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形成對照。因為,在這些研究中,所有的假設和非分析的心理學研究方法,都是圍繞上述相同的目的而展開的。另外,它們還可以與精神分析蘇黎世學派的一些研究文獻形成對照。這一學派致力于運用社會心理學來解決個體心理學的問題。(參見榮格,1912和1913)應該承認,正是依據這兩種來源,我獲得了撰寫這些論文的最初動力。
我深知我的這幾項研究難免掛一漏萬。對于一項開拓性研究的一些必然特征,我不必贅言。不過,其他方面還需闡述一下。雖然本書所收集的四篇論文旨在引起廣大有識之士的興趣,但是除了對于精神分析學的精髓有所掌握的很少一部分人士以外,這些論文事實上很難被人們所理解和賞識。我力求使它們成為社會人類學、語言學、民俗學諸學科的學子與精神分析學家之間的溝通橋梁。然而,它無法給任何一方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既不會給前者足夠的有關心理學新方法的啟示,也不會使后者更充分地掌握研究材料。能引起雙方的注意,并促使他們相信彼此間的不斷合作一定會有益于該學科的研究,我便感到滿足了。
讀者會發現,圖騰與塔布(這本小冊子正是以此為標題的)這兩大主題并沒有得到同等的研究。有關塔布的分析頗為詳盡,在力圖解決這一問題方面也有足夠的把握。有關圖騰的研究我們只能說“在闡明圖騰這一問題方面,精神分析學目前所能貢獻的只有這些”。這一差異源于圖騰仍然存在于我們之中這一事實。盡管圖騰是以一種消極形式表現出來,并指向另一種主題內容,但是就其心理本質而言,它與康德的“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相差無幾。“絕對命令”以一種強迫的方式運作并拒絕任何有意識的動機。與之相反,圖騰崇拜是一種異于我們感情的東西--一種被作為現實性而久已丟棄并由更新的形式所取代的宗教-社會習俗。它在當今各文明民族的宗教、風俗和習慣中僅殘留些微小的痕跡。即使在那些至今仍受其支配的民族中,圖騰也早已經受了廣泛的改變。人類歷史中的社會和技術進步對塔布所產生的影響,遠不如對圖騰的影響。
本書試圖通過圖騰崇拜的“童年時代”的殘跡(即通過它復現于孩子們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跡象),來推論它的本原意義。圖騰與塔布的密切聯系使得我們在通往本書所提出的假設方面,又往前跨出了一步。縱然最終這一假設顯露出不可能之外象,那也沒有任何理由拒絕這樣的可能性,即這一假設多多少少地在接近那極難重構的現實。
1913年9月于羅馬
希伯來文版序言
本書[希伯來文版]的讀者中絕不會有人感到,將自己置身于這樣一位作者的情感狀態之中是件容易的事。因為,這位作者對圣書的語言已全然無知;對其祖先的(以及所有其他的)宗教已完全生疏;在民族主義理想中也未能貢獻一份力量。可是,他卻從未遺棄自己的人民,他感到自己在本質上仍是一位猶太人,而且也不希望改變這一本質。如果有人問他:“既然你已放棄了祖國同胞所擁有的那些一般特征,那你還有什么可藉以為猶太人呢?”他會回答說:“還有很多很多,甚至可能是其精髓。”他現在也許無法用言辭將那精髓表達出來,但是,毫無疑問,對一位科學家來說,總有一天這是能辦到的。
因此,對于這樣一位作者來說,他的一部研究宗教和道德起源的著作,雖然并未采用猶太人的觀點,也沒有偏愛猶太族的例外,卻被譯成了希伯來語并放到了這些讀者手中,在他們看來書中的那些古老言語都是他們須臾不能離的母語,這確是一次十分特別的經歷。而且,這位作者希望他和讀者都能一致堅信,新生的猶太民族的精神絕不會永遠將公正的科學視同陌路。
1930年于維也納
(第一篇)對亂倫的恐懼
通過史前人遺留下來的那些毫無生氣的石碑器具,通過我們直接或憑借各種傳奇、神話、仙幻故事間接獲得的,對史前人的藝術、宗教和人生態度的認識,通過依舊殘存于現代風俗習慣中的、史前人的思維模式,我們對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史前人已有所了解。不過,進一步而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史前人仍然是我們同時代人。正如我們所認為的那樣,當今仍有些人異于我們而更接近于初民,我們因此將他們視為初民的直系后裔或繼承人。我們就是這樣來看待那些被我們稱為蒙昧或半開化的民族的;如果我們有理由從初民的心靈生活中,洞察到一幅保存完好的、有關我們自己的早期發展的畫面,那么這樣的心靈生活尤其能引起我們濃厚的興趣。
如果這一見解正確的話,那么經由社會人類學所獲知的原始民族心理和精神分析學所揭示的神經癥患者心理間的兩相比較,一定能展示眾多的共同之處,并使我們對這兩門學科中的一些熟識的事實產生新的認識。
出于內在,更出于外在的原因,我選擇那些被人類學家描述為最落后、最可憐的蒙昧人--澳洲這一最年輕大陸上的土著人,作為部落比較的基礎。我們還可以觀察到,這里的動物群也是最古老的,在其他地方早已不復存在了。
澳洲土著是一獨特的種族,無論在體格還是在語言上,都與其最相近的鄰居--美拉尼西亞人、波利尼西亞人和馬來人毫無關聯。他們從不建造房屋或永久性棚屋,從不耕田種地;除了狗以外,他們從不飼養任何家畜;他們甚至沒聽說過陶器制作技藝。他們的生活完全有賴于他們獵獲的各種獸肉和挖掘的各種根莖。他們不知君王或酋長為何物;一切公共事務都由長老會決定。很難說他們有任何以神明崇拜為形式的宗教。與沿海部落相比,那些處在大陸腹地、因水源奇缺而在最艱難的生存條件下掙扎的部落,在各個方面都顯得更為原始。
我們當然不會期望,這些赤身裸體、可憐巴巴的食人野民的性生活,會具有我們所說的道德意義。我們也不期望,他們的性沖動會受到嚴格的規范。然而我們卻發現,為了避免亂倫的關系,他們一絲不茍,處處留心,嚴厲得近乎痛苦。確切地說,他們的整個社會組織似乎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或者說是圍繞這個目標而設立的。
澳洲土著人沒有宗教的和社會的機構體系,凡此種種均由“圖騰崇拜”體系所取代。澳洲的部落又劃分為更小的分支或氏族(clans),每個都以其圖騰命名。什么是圖騰?圖騰通常是一種動物(或是可食無害的,或是危險可怕的)。偶爾也會是一種植物或一種自然現象(如雨或水),它與整個氏族有著某種奇特的關系。圖騰首先是氏族的共同祖先,同時也是向他們發布神諭并提供幫助的監護神。雖說對外族而言圖騰很危險,但是它能識別并寬容自己的子民。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族人都有一項神圣的義務:不宰殺不損毀圖騰,不吃圖騰的肉,也不用其他方式以此謀利。圖騰的品質是天生的,并非只存在于某一只動物或一種東西之中,而是存在于某一類的全體個體之中。在時常舉行的喜慶活動上,族人在禮儀舞蹈中表現或模仿著圖騰的動作和特性。
圖騰是通過母系或父系傳承的。也有可能原初盛行母系傳承,只是后來才為父系傳承所取代。個人與圖騰間的關系是澳洲土著人一切社會義務的基礎,因為它遠勝于這個人在部落中的成員關系以及血緣關系。
圖騰并非依附于某一特定的地方。一個氏族內的成員往往散居各地,并與其他圖騰氏族的成員們和睦相處。
至此,我們終于觸及圖騰體系中能引起精神分析學家重視的特征了。在所有有圖騰的地方,我們都可以發現一條定規:擁有相同圖騰的人們,不可在彼此間發生性關系,因而不可通婚。這樣就有了“族外婚”(exogamy)--一種與圖騰崇拜(totemism)相關的習俗。
這一嚴格實施的禁忌(prohibition)是十分奇特的。我無法用上面所提到的圖騰的概念或某些特征來預見它。我們很難理解,它是如何涉入圖騰體系的。因而有些研究者事實上認為,族外婚原初(意指起源或本意)與圖騰并無關系,只是在婚姻限制(marriage restrictions)成為必然的某一時期添附上去的(沒有絲毫的深層聯系)。對于這樣的看法,我們并不感到意外。不管怎么說,圖騰崇拜和族外婚之間存在著聯結,而且顯然是非常牢固的。
進一步的探討可以使得這一禁忌的意義更加明了:
a.違犯這一禁忌不會像違犯其他圖騰禁忌(如不可宰殺圖騰動物)那樣,僅僅是受到報應而已。全族成員都將全力以赴地進行報復,猶如在對付一件危及全族的大難或罪惡即將臨頭的大事一樣。下面是從弗雷澤(1910,第1卷,第54頁)的書中引用的一小段文字。它們表明,那些用我們的標準來衡量的毫無道德的蒙昧人,是多么嚴厲地對待這些不端行為的:
“在澳洲,對與禁族(forbidden clan)成員進行性交的一般處置是處死,無論這個女人與其同屬一個本地群體(local group),還是打仗時從另外一個部落擄獲的。氏族內的男子以這樣的外族女子為妻的話,會受到本族成員的獵殺,那個女人也不能赦免。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他們能夠成功地逃避追殺并躲上一段時間的話,也許能獲得赦免。在新南威爾士的塔塔苔(Ta-ta-thi)族,雖然鮮有但確曾發生過這樣的事:男的被殺死,女的則遭痛打或矛刺,或兩者齊上,直至她瀕臨死亡。不立即殺死她的原因是,她可能是被迫的。即使是對于偶爾偷情,氏族禁忌也絕不網開一面。對于這些禁忌的任何違犯都被視為極度可惡而處以極刑。”[摘自卡麥容(Cameron,1885,第351頁)]
b.既然這一嚴厲的懲罰也同樣適用于沒生孩子的、短暫的婚外戀,所以形成這一禁忌的各種原因不太可能具有實際性。
c.既然圖騰世代相傳不因婚姻而改變,禁忌的后果是不難看到的。例如,在母系傳承中,如果一個屬袋鼠圖騰的男子,娶了一個屬鴯鹋圖騰的女子為妻,所生孩子無論男女都歸鴯鹋氏族。圖騰規則因而保證在這一婚姻中出生的男孩,不可能和與其同屬鴯鹋氏族的母親或姐妹發生亂倫關系。
d.但是,稍加深入思考便可發現,與圖騰相關聯的族外婚的作用是很大的(因此目的也很大),遠非僅僅防止一個男人與母親或姐妹亂倫。它通過將氏族內所有的包括許多非血親(blood-relatives)的女人,視為一個男子的血親,從而使得這個人不可能與這些女人性交。由于這種波及面甚廣的限制在已開化的民族中不具可比性,因而要一眼看出它在心理學上的合理性并非易事。不過,從中我們還可以獲知,圖騰被當作祖先乃是一件十分認真的事。來自同一圖騰的人都是血親,他們組成一個大家庭(family),在這里即使是最遙遠的親緣關系(kinship)也被當作性結合的絕對障礙。
我們因此知道,這些未開化的人對于亂倫抱有非同尋常的恐懼,甚至對這一話題也極其敏感。同時我們還感到,他們將亂倫與某種我們尚不可知的、以圖騰家庭關系取代真正的血親關系這一奇特的現象結合在一起。但是,后者的矛盾現象不可過分夸大。我們務必記住,圖騰禁忌也包括以特例方式對真正亂倫的懲處。
在圖騰的本質得到解釋之前,圖騰氏族何以能夠取代真正的家庭也許只能是個謎。同時可以看到,如果婚外性結合具有一定自由度的話,血親接著便是亂倫防范,就會變得很不確定,因而禁忌的范圍必須擴大。有必要指出,澳洲人的風俗使得男子對一名女子在婚姻上的獨占權受到侵犯的現象,在某些社交場合或喜慶活動中得以發生。
這些澳洲部落的語言習慣的奇特性與此無疑是有關聯的。因為他們用來表達不同等親家族關系(degrees of kinship)的術語,并沒有表示兩個個體之間的關系,而是表示了某個個體與一群體間的關系。這就是摩爾根(L.H.Morgan,1877)所說的關系的“類別”體系。所以一個人不止稱他的生父為“父親”,凡是原先依據族規可以娶他母親而可能生下他的人,都是父親;同樣,他也不止稱他的生母為“母親”,凡是不違反族規而可能生下他的人,都是母親;“兄弟”和“姐妹”也不止用來稱呼他生身父母的兒女們,而是泛指所有類別意義上的父母的兒女們;等等。所以,澳洲人彼此間的親屬稱謂并不總是像我們一樣表達血緣關系(consanguinity),它們表達了社會關系而非生理關系。在我們也存在這種類似類別體系的現象。例如,我們也教孩子稱呼父母的朋友為“叔叔(Uncle)”或“阿姨(Aunt)”,我們有時還在隱喻的意義上使用“阿波羅神廟的兄弟們”或“教堂的姐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