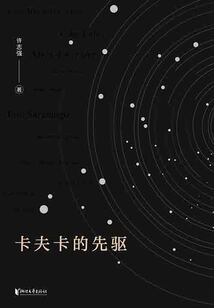
卡夫卡的先驅(qū)
最新章節(jié)
- 第14章 后記
- 第13章 附錄·《木心遺稿》與“后制品”寫作
- 第12章 附錄·《20世紀(jì)歐美經(jīng)典小說》:獻(xiàn)給普通讀者的禮物
- 第11章 卡夫卡的先驅(qū)
- 第10章 反向介入——米歇爾·萊里斯的自傳寫作
- 第9章 詩人 野性與超驗(yàn)主義——讀《梭羅傳》
第1章 代序 無家可歸的講述
庫切的自傳體小說《夏日》(文敏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講述了這樣一個(gè)故事:
庫切死后,有人想要搜集材料為他寫一部傳記;這位傳記作者與庫切素昧平生,他從死者遺留的筆記中找到若干線索,開始一系列采訪,從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金斯頓到南非的西薩默塞特,從巴西圣保羅到英國謝菲爾德和法國巴黎,采訪死者的情人、表姐和同事,試圖構(gòu)建20世紀(jì)70年代初庫切在南非的一段經(jīng)歷。
生前友好提供的證詞,逐漸形成了庫切早年的一幅肖像,那是一個(gè)幽靈般的存在,邋遢孤單、局促不安而且自我封閉,是一個(gè)不知如何與情人相處的書呆子,似乎隨時(shí)要透過肖像的邊框逃逸出去,抱臂獨(dú)坐在灰暗的角落。
《夏日》帶來的這幅陰郁而略帶滑稽感的肖像,便是庫切想象自己死后如何進(jìn)入別人講述的一種描繪,也可以說,是從死亡的暗房里沖洗出來的一卷水淋淋的膠片;只不過捏著底片的還是活人的手,其實(shí)是庫切自己彎曲的手指尖。這幅看似容易滑落的肖像——庫切寫庫切死后關(guān)于庫切的傳記,未嘗不是一種機(jī)智的筆墨游戲。此種構(gòu)想也許很多人的頭腦里都曾出現(xiàn)過,但從我們有限的閱讀來看,真正形諸文字的還是庫切這部新作。
《夏日》于2009年問世后,大西洋兩岸的英語評(píng)論界即刻給予高度關(guān)注。《時(shí)代》文學(xué)副刊稱其為“過去十年里庫切的最佳作品”。《紐約客》的文章認(rèn)為“自《恥》之后他還從未寫得如此峻切而富于情感”。人們稱贊這部自傳體小說寫法“聰明”“機(jī)巧”,“打破了回憶錄的體裁界限”,是“對(duì)生活、真實(shí)和藝術(shù)的嬉戲沉思”,也是“對(duì)何謂虛構(gòu)小說的一種重新定義”。若干有影響的書評(píng),幾乎通篇都在談?wù)撨@部作品的構(gòu)建,它的敘事形式和視角,也就是它作為自傳類作品的“非常規(guī)寫作方式”所產(chǎn)生的效應(yīng)。從《夏日》別出心裁的文本構(gòu)造來看,讀者的這種關(guān)注也是很自然的。
該書副標(biāo)題是“外省生活場(chǎng)景”,與作者另外兩部自傳體小說《男孩》和《青春》的副標(biāo)題相同。讀過《男孩》和《青春》,再來看《夏日》,這三部作品在時(shí)間上大致構(gòu)成一個(gè)系列,從孩提時(shí)代的南非小城伍斯特到青春時(shí)光的開普敦和倫敦,現(xiàn)在又回到開普敦,主人公三十來歲,如標(biāo)題“夏日”所喻指的,正是歲月成熟的季節(jié)。《青春》中漂泊異鄉(xiāng)、迷茫孤獨(dú)的文學(xué)青年,終于在開普敦出版了第一部小說,圓了他的作家夢(mèng)。按照“自傳三部曲”的傳統(tǒng)看,新作提供的是續(xù)篇也是終篇;這個(gè)系列的寫作似乎可以結(jié)束了。至少,《青春》內(nèi)在的懸念已經(jīng)部分得到解決。試圖成為一個(gè)作家或最終如何成為一個(gè)作家,這是銜接前后兩部作品的懸念。
《夏日》所要做的無非是延續(xù)這個(gè)內(nèi)在的敘事動(dòng)機(jī),給予實(shí)質(zhì)性的描繪和交代。我們看到,這一回主人公已經(jīng)不是那個(gè)叫約翰的男孩和青年,而是“當(dāng)代著名作家約翰·庫切”;第三人稱隱約其詞的交代,這個(gè)模式已經(jīng)放棄,代之以明確的自我指涉,不少地方甚至出現(xiàn)了蓋棺論定的調(diào)子。它表達(dá)的是一個(gè)成熟的作家的世界觀,像是給仰慕他的讀者提供必要的提示和解答,包括他對(duì)政治和社會(huì)的看法,對(duì)生活和命運(yùn)的審視,對(duì)自己的作品及創(chuàng)作個(gè)性的評(píng)價(jià)。
作家得以公開談?wù)撟晕遥瑥钠涔P尖收回遠(yuǎn)距離的觀察,使得往事不再像迷霧中的暗流那樣難以真正觸及,而是像一面“重現(xiàn)的鏡子”,在同一時(shí)間匯聚并試圖展現(xiàn)它的全貌。
《夏日》敘述的重點(diǎn)落在1972年至1977年庫切在南非的一段生活。為什么單單選擇這個(gè)時(shí)期來寫?
按照書中那位傳記作者的說法,因?yàn)椤斑@是他生活中一個(gè)重要時(shí)期,重要,卻被人忽視,他在這段時(shí)間里覺得自己能夠成為一個(gè)作家”。此外,20世紀(jì)70年代正是南非種族隔離最嚴(yán)酷的時(shí)期,從社會(huì)歷史的角度看,選擇這個(gè)時(shí)期來講述自己的故事,應(yīng)該有更多的內(nèi)容可以談。既然寫的是一部自傳體小說,那么傳記提供事實(shí)往往要比提供觀點(diǎn)更吸引人。
庫切是那種通常被認(rèn)為缺乏生活的學(xué)院派作家,亦即所謂的知識(shí)分子作家。這類作家會(huì)對(duì)馬爾羅、索爾仁尼琴之類的人物倍感興趣。《夏日》開篇提到的南非詩人布萊頓巴赫,便是一個(gè)頗為有趣的人物;他拿南非總理沃斯特的床笫之事寫作諷刺詩,被關(guān)了七年監(jiān)牢,游走于南非和巴黎之間,在私生活、寫作和社會(huì)活動(dòng)中都異常活躍。如果說詩人布萊頓巴赫還不能算是庫切崇拜的偶像,至少也應(yīng)該是后者所羨慕和思量的對(duì)象。某種意義上講必定如此。
而庫切的《青春》讓我們領(lǐng)略到,他游離于這個(gè)世界的邊緣,所提供的事實(shí)既不夠雄辯,也較為有限;書中講述的生平事跡,以類似于雕刻刀的減法構(gòu)成客觀性的某種見證。其言下之意是,只要作家的審視是誠實(shí)的,則其陳述的事實(shí)哪怕有限,也仍不失其可貴的力度和價(jià)值。
身為作家,庫切對(duì)此一向抱有信心。他的每一個(gè)篇幅不長的作品也都在證實(shí)這一點(diǎn)。但是,作為一個(gè)人,在特定環(huán)境中生存的人,他又如何面對(duì)自己?如他與女人的相處并不成功,在親友中遭到奚落,而且顯然還難以超脫生存的壓力和恐懼,過著貧困知識(shí)分子的生活,這個(gè)形象自然是無法給人提供慰藉的。那么,選擇這個(gè)形象作為傳記的中心人物,究竟是出于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的需要,還是僅僅緣于一種誠實(shí)的自我寫照?
閱讀《夏日》,會(huì)讓人產(chǎn)生類似的思考。這也關(guān)系到此書別具一格的文體和視角。真實(shí)的庫切和書中的庫切,兩者的關(guān)系多少有些微妙。針對(duì)自傳體小說這種較為混雜的文類,庫切的寫作總是突顯其人工制品的性質(zhì)。較之《男孩》和《青春》,新作《夏日》在這個(gè)方面無疑做得更為露骨,或許,也做得更為審慎。
“他在事實(shí)的面紗之下悄悄放進(jìn)虛構(gòu)。”一位英國書評(píng)家如是說,“他把自己的姓名、歷史面貌、國籍和職業(yè)生涯都給了他筆下的主人公,但是有些關(guān)鍵的細(xì)節(jié)并不準(zhǔn)確。例如,小說中極為重要的一點(diǎn)是主角沒有結(jié)婚,一個(gè)不合群的近乎性冷淡的人,而事實(shí)上在此書描寫的1972年至1977年那個(gè)時(shí)期,他有婚姻并且育有一子一女。”庫切的前妻和孩子在這本書中消失得無影無蹤。讀者自然要問:“虛構(gòu)背后應(yīng)在何種程度上關(guān)乎真實(shí)?虛構(gòu)應(yīng)在何種程度上照亮真實(shí)同時(shí)又隱藏真實(shí)?”
顯而易見,我們讀到的《夏日》是一部“小說化的自傳”(fictionalized memoir),或者說是一部偽自傳。作者對(duì)此絲毫未加掩飾。此書的主體部分由五篇訪談組成,沒有一篇是真實(shí)的;這些訪談?dòng)涗洠由蟽善⒚魅掌诩拔醋⒚魅掌诘牧闵⒐P記,都是未經(jīng)編輯的所謂原始材料,還聲稱其中有兩篇是從其他語種(葡萄牙語和阿非利堪語)翻譯過來的,構(gòu)成《夏日》的敘事。
作者試圖以虛構(gòu)事實(shí)的方式觸及真實(shí),借助他者的主觀性追溯歷史,在自我陳述和客觀性面具之間保持平衡。此種話語方式的機(jī)巧,把小說家的虛構(gòu)及其對(duì)敘事的操控暴露無遺;所謂的自傳便成為含有自傳性的虛構(gòu)作品,而“重現(xiàn)的鏡子”則是一面破裂的鏡子,通過碎片拼湊影像。書中那位傳記作者解釋說:
我們都是虛構(gòu)者。我不否認(rèn)這一點(diǎn)。可是你覺得哪種情況更好些:由一個(gè)一個(gè)獨(dú)立的視角出發(fā)來建構(gòu)一組獨(dú)立的敘事,使你能借以分析得出總體的印象;還是僅由他本人提供大量的、單一的、自我保護(hù)的材料來建構(gòu)一種敘事更好呢?
庫切寫作自傳的觀點(diǎn),令人想起約翰·伯格關(guān)于小說創(chuàng)作的名言:“單獨(dú)一個(gè)故事再也不會(huì)像是唯一的故事那樣來講述了。”
小說的寫作是如此,生平故事的寫作也是如此。
《夏日》將自傳故事納入小說文本的建構(gòu),包含作者對(duì)于敘事真實(shí)的一種審慎處理;反映的是現(xiàn)代小說的寫作觀念,與傳統(tǒng)史詩敘事相對(duì),源自福樓拜、喬伊斯、紀(jì)德等人所倡導(dǎo)的現(xiàn)代小說意識(shí)。
本雅明在《小說的危機(jī)》一文中指出:“小說的誕生地乃是離群索居之人,這個(gè)孤獨(dú)之人已不再會(huì)用模范的方式說出他的休戚,他沒有忠告,也從不提忠告。所謂寫小說,就意味著在表征人類存在時(shí)把不可測(cè)度的一面推向極端。”本雅明還引用盧卡奇的說法,認(rèn)為現(xiàn)代小說代表的是一種“先驗(yàn)的無家可歸的形式”,而這正是現(xiàn)代小說的本質(zhì)屬性。
那么,將小說家的自傳與虛構(gòu)混合起來,難道只是出于一種玩弄形式的考慮嗎?并不是。庫切在《夏日》中把自己塑造成離群索居、無家可歸的人,從其真實(shí)的履歷表上減去婚姻這一項(xiàng),通過適度的虛構(gòu)加工,從而將人物的孤獨(dú)與其存在中難以測(cè)度的那一面更為清晰地聯(lián)系起來,這么做也是頗為耐人尋味的。
作家表述其孤獨(dú)的存在,有別于常規(guī)的處理,而且也打破了讀者的預(yù)期。是的,《夏日》的主旨是講述作家成長的故事,對(duì)于如何成為一個(gè)作家卻講得不多。開篇描述南非種族隔離的悲劇,寥寥幾筆,傳達(dá)出那個(gè)時(shí)期近乎凝固的政治氣氛,但書中對(duì)種族隔離的描寫未做主題式展開。此書的主題是指向作家隱秘的私生活,也就是中心人物體內(nèi)的“性”,確切地說,是他體內(nèi)的中性、去性或無性。
通過《朱莉亞》《瑪戈特》《阿德里亞娜》這三個(gè)故事,我們讀到的正是這樣一個(gè)多少有些尷尬的主題,而在其他作家的自傳或傳記類作品中,還從未出現(xiàn)過類似的描寫和提示。例如,君特·格拉斯的《剝洋蔥》,阿摩絲·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其性欲的描繪多半是自我充盈的。相比之下,《夏日》的主角更像是一個(gè)處在更年期的鰥夫。這倒不是說此人的性取向有什么問題,有某種古怪的癖好,或是一個(gè)天生的厭女癥患者。這些都不是。他做過鄰居朱莉亞的情人,追求過舞蹈教師阿德里亞娜,與同事索菲也是戀人關(guān)系。像任何一位年輕男子,他有愛與被愛的需要,樂于扮演想象中的唐璜角色。人物的古怪并非出于反常,一定程度上也是緣于某個(gè)評(píng)價(jià)框架;而在那個(gè)反復(fù)出現(xiàn)、類似于社會(huì)評(píng)估的框架中,他的存在令人失望,成了女性眼中的“中性人”,似乎難以激發(fā)她們的熱情和性趣;總之,他孑然孤立的形象帶有幾分灰暗和滑稽。
朱莉亞、瑪戈特或阿德里亞娜,她們都是這么看待他的。在和朱莉亞的情事中,庫切更像是一個(gè)無聲的影子伴侶;而在荒野中度過的一夜,使瑪戈特對(duì)這位渾身沒有一絲熱氣的表弟隱隱產(chǎn)生憐憫;對(duì)于舞蹈教師阿德里亞娜來說,她感到被這樣一個(gè)書呆子追求簡(jiǎn)直莫名其妙。這個(gè)總是不忘記詩歌、舒伯特和柏拉圖理念的單身漢,他對(duì)女性的努力追求,有時(shí)也讓人有些哭笑不得。隨著故事的展開,我們品嘗到這些故事所蘊(yùn)含的一種特色:古希臘英雄那種駕馭生活(其實(shí)也是駕馭女性)的傳統(tǒng)在庫切的這本書中徹底流失;故事的主角(英雄)來回穿梭,出現(xiàn)在不同女性的講述之中,事實(shí)上他已經(jīng)由主角變成了配角,而且,這種被動(dòng)的性質(zhì)多少顯得有點(diǎn)兒幽默。
傳記的主人公變成了傳記的配角;故事的講述與庫切相關(guān)也經(jīng)常偏離視線;這篇專注于自我的敘事便逐漸成為積累不同側(cè)面的小說。朱莉亞的中產(chǎn)階級(jí)隱私,瑪戈特的家族農(nóng)莊,阿德里亞娜的底層移民背景,還有“馬丁”和“索菲”這兩個(gè)章節(jié)中的學(xué)院小景,串聯(lián)起20世紀(jì)70年代南非社會(huì)的一幅圖景。庫切作品中的不少人物和母題,也重新匯入《夏日》的敘事。
開篇“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筆記”,描述暴力的氣氛和遺世獨(dú)立的選擇,包含《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shí)代》的主題;《瑪戈特》的女主角對(duì)這片土地的認(rèn)同,也是《恥》中出現(xiàn)的主題;還有《內(nèi)陸深處》《青春》《男孩》等篇,縈繞于“外省生活場(chǎng)景”的插曲,讓人記憶猶新。《男孩》對(duì)百鳥噴泉農(nóng)莊的描寫,像夏日清澄的空氣折射美麗的光芒。還有《男孩》中的那個(gè)父親,因挪用委托保管基金借給失信商人,被褫奪律師資格,干脆躺在家里逃避責(zé)任;床底下的尿壺里還浸泡著發(fā)黃的煙蒂。這個(gè)父親出現(xiàn)在《夏日》中,和兒子住在一起;在追求阿德里亞娜的野餐會(huì)上,父子倆在樹下躲雨,野餐會(huì)泡了湯,他倆一副倒霉的模樣,正好讓彼此成為注腳。
如果說,此類描寫讓人覺得有趣,甚至發(fā)笑,那也是一種滲透了尖酸苦味的幽默。書中那些不無莊重的細(xì)節(jié),例如,庫切報(bào)名參加阿德里亞娜的舞蹈班,他在頹圮的鄉(xiāng)村做著詩人夢(mèng)(“噢,炎熱的大地。噢,荒蕪的峭壁”),還有他要求朱莉亞配合舒伯特的音樂與他做愛,等等,都透出一股酸澀可笑的味道。
這種尖酸滑稽的幽默,讓人想起貝克特的作品。事實(shí)上,庫切的創(chuàng)作(其格調(diào)和形象)一直浸潤于貝克特的靈感中。考察庫切藝術(shù)的來源和所受的影響,貝克特始終居于首位。這并不是什么秘密。
納博科夫談到貝克特的小說時(shí)這樣描述:
他的作品有一幕非同尋常:他用一根拐杖支撐著自己走過森林,身上穿著三件大衣,腋下夾著報(bào)紙,還忙著從一個(gè)口袋往另一個(gè)口袋轉(zhuǎn)移那些鵝卵石。一切顯得那么灰色,那么不舒服,就像老人做的夢(mèng)。這種狼狽相有點(diǎn)類似卡夫卡的人物,外表叫人不舒服,惡心。貝克特的作品就是這種不舒服的東西有趣。
這種不舒服的灰色液體也流淌在庫切的作品中,使得自我定義所要求的同一性、生命中各種行為的總和所描繪的同一性,在有待描繪之前便已破裂,沉入生命冰涼的殘?jiān)烨袔е@種感覺去描寫事物,講述他的故事,體味他那種孤獨(dú)的命運(yùn),恰恰因?yàn)檫@個(gè)就是他的命運(yùn)——去尋找他破裂的生活中值得一寫的東西。
他用質(zhì)樸細(xì)膩的語言敘述,平穩(wěn)的筆觸帶著層級(jí)遞進(jìn)的效果,而其尖銳的敘述有時(shí)誠實(shí)得讓人心里打戰(zhàn)。那個(gè)像是在從事秘密勾當(dāng)?shù)淖骷遥ā队陌抵亍返淖髡撸掖亿s往旅館幽會(huì);周旋于封閉的自我與孤獨(dú)的性事之間,他的人生真實(shí)嗎?
他好像在跟腦子里關(guān)于女人的某種想象交合,半閉空洞的眼瞼,缺乏真實(shí)的個(gè)性;也許,他從未真正擁有過一個(gè)女性的身體?他那些情人講述的不就是這樣一副面目?
此人既非騙子亦非消極墮落者;稱得上是一位有道德原則的紳士。可他的體內(nèi)卻包藏著一團(tuán)冷氣,像發(fā)酸的老人,或是像患有自閉癥的兒童,活在某個(gè)不透明的模式中;而在老人和孩童之間,他那種男性的特質(zhì)被抽空,剩下的是身體里的中性、去性或無性。
萊昂內(nèi)爾·特里林在評(píng)論詩人濟(jì)慈時(shí)提出“成熟的陽剛之氣”的說法。在其《對(duì)抗的自我》一書中,他將這個(gè)概念定義為:
與外部現(xiàn)實(shí)世界的一種直接的聯(lián)系,通過工作,它試圖去理解外部現(xiàn)實(shí)世界,或掌握它,或欣然安于它;它暗示著勇氣、對(duì)自己責(zé)任和命運(yùn)的負(fù)責(zé),暗示著意愿以及對(duì)自己個(gè)人價(jià)值和榮譽(yù)的堅(jiān)持。
真正的作家,其個(gè)性的精華是某種脆弱的幻想,能夠從其存在的另一面,呼應(yīng)這個(gè)定義所包含的類似于祈禱或驅(qū)魔的意義。馬爾羅、索爾仁尼琴或布萊頓巴赫,他們?cè)谝欢ǔ潭壬夏転檫@個(gè)定義提供注腳;他們都是“成熟的陽剛之氣”的代表。
而書名“夏日”(Summertime)一詞作為隱喻,指向恒定的云朵和空曠的麥田,似乎也在解釋特里林的觀念。作者像是在祈禱——把自己交付給世界吧,像果實(shí)吐出它的內(nèi)核,如同卡夫卡日記中反復(fù)幻想的那樣。
撇開進(jìn)化或變態(tài)的法則不談,僅就藝術(shù)對(duì)個(gè)性的需求而言,這個(gè)過程的困難似乎在于,詩人的自我的不可通約(也就是本雅明所謂的“不可測(cè)度”)的那一面,總是有意無意地要對(duì)此加以抗拒。
特里林所謂的“成熟的陽剛之氣”,延續(xù)托馬斯·卡萊爾的觀念,倡導(dǎo)英雄主義的“道德活力”,或許未能顧及藝術(shù)創(chuàng)造所需的危險(xiǎn)和脆弱。特里林所謂的責(zé)任和藝術(shù)家擔(dān)負(fù)的責(zé)任不一定能夠協(xié)調(diào),倒是有可能概括得較為簡(jiǎn)單。在此意義上講,《夏日》的主題并不是專注于情愛或性征,而是突顯主角的獨(dú)特的面目,其存在的緊張感及現(xiàn)實(shí)喜劇性,或者說是詩人那種較為古怪的命運(yùn)。
讀過《男孩》和《青春》,我們對(duì)這個(gè)形象不會(huì)覺得太陌生。而在《夏日》中,庫切將主角的形象變得更為醒目,并且勾畫出這個(gè)角色獨(dú)特的現(xiàn)實(shí)喜劇性。他的描寫有時(shí)讓人發(fā)笑,也難免讓人驚異。這幅多少有些陰郁的肖像,帶有庫切自身個(gè)性的印記,亦可視為詩人的一種表征。
由于文本作者隱蔽的介入,作者與敘事人的同謀關(guān)系有時(shí)也會(huì)讓敘述失之過火(例如“阿德里亞娜”的章節(jié))。但從總體上看,這個(gè)形象的再現(xiàn)能夠喚起隱秘的激情,猶如冰塊與火焰的結(jié)合。
庫切塑造的形象,他的低調(diào)、深思的寫作,涉及道德倫理層面,從不滿足于輕易獲得的答案;他的創(chuàng)作展示一個(gè)自我拆解的過程,蘊(yùn)含著對(duì)立意圖的責(zé)難與反詰;正如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授獎(jiǎng)詞所言,“他以眾多作品呈示了一個(gè)反復(fù)建構(gòu)的模式:盤旋下降的命運(yùn)是其人物拯救靈魂之必要途徑”。自傳三部曲的寫作遵循的便是這一模式,將自我陳述處理得像是追蹤地下生活的報(bào)告。
對(duì)于庫切的創(chuàng)作來說,仿佛只有在那幽暗冷漠的國度,它們才會(huì)見證時(shí)代的隔離和荒蕪靈魂的悲喜劇;而在這顯然是低于生活的地方,詩人的超越性的存在未免顯得古怪,有點(diǎn)過于孤立,與群體意識(shí)對(duì)立,但也能夠表達(dá)類似于祭獻(xiàn)的幽秘的激情。
庫切于20世紀(jì)70年代初從美國回到南非,在開普敦大學(xué)英文系教書,其間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幽暗之地》,開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生涯。他為什么要回到南非工作,而若干年后又離開南非,再也沒有回去,這一點(diǎn)從其履歷表上不容易得到解釋。《夏日》講述他這段時(shí)期的經(jīng)歷,正好可以提供線索。
事實(shí)上,他是因?yàn)閰⒓臃丛綉?zhàn)游行而被美國當(dāng)局驅(qū)逐出境,丟掉了那邊的工作。《青春》中發(fā)誓不再回南非的他,只好回到祖國謀生。由于“他斷絕了與自己的國家、家族和父母的關(guān)系”,他的回歸未免有些無奈和尷尬。“瑪戈特”的章節(jié)對(duì)此作了一番描述,其他章節(jié)中也斷斷續(xù)續(xù)談到。
總之,他對(duì)自己的國家抱著難以化解的抵觸態(tài)度。《夏日》的結(jié)尾敘述兒子與父親的和解,也透露了情感上的某種抑制;他那種懺悔的愿望即便已經(jīng)非常誠懇,但最后一筆交代說他還是要走的,像是有一股力量拽著他離開,留下醫(yī)院里治病的老父親。
一個(gè)始終像在獨(dú)自告別的人,在朱莉亞的臥房和清晨的睡夢(mèng)里,在家族聚會(huì)的餐桌旁,弓起緊張的身體。他年紀(jì)輕輕,卻像一個(gè)落寞的鰥夫。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死去。人們談?wù)摰氖且粋€(gè)死去的著名作家,談?wù)撍^去生活中的模樣。無論是同情也罷,隔膜也罷,總不外乎指向他那種讓人困惑的特殊性。他們是談得太多,還是談得遠(yuǎn)遠(yuǎn)不夠?
也可以這樣來問:對(duì)一位著名作家的關(guān)注真的應(yīng)該比對(duì)“阿德里亞娜的丈夫”的關(guān)注更多一些嗎?后者是巴西難民,在開普敦當(dāng)保安,被人用斧頭砍在臉上,最后死在了醫(yī)院里。這類無名者的生活故事,豈不是有著和詩人故事一樣多的情感空間?
《夏日》有三處寫到醫(yī)院,也都是跟底層的流離失所的命運(yùn)相關(guān)。主人公趨于冷感的身體,他可悲的“去性化”狀態(tài),未必能夠在他人的故事中得到解釋,卻和這些臟污、凄涼的圖景一樣,讓人看到生活如此殘缺,缺乏慰藉。
在《兇年紀(jì)事》中,庫切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他說,他為伊凡的選擇落淚。作為一個(gè)徹底的懷疑論者,伊凡不給他的信仰留出一絲余地;他選擇退出,向那位全能的造物主提出“退票”。某種意義上,我們亦可借助這個(gè)細(xì)節(jié)來看待《夏日》的主人公,他于20世紀(jì)70年代初回到南非的經(jīng)歷,他經(jīng)歷中包含的尖酸苦澀,他那種對(duì)抗性的意識(shí)形態(tài)立場(chǎng)。
對(duì)庫切來說,成為一名移民身份的作家,亦即意味著三重意義上的錯(cuò)位或放逐:他是拒絕鄉(xiāng)土專制的世界主義者,他是出生在南非的白人后裔,他是用英語寫作的殖民地知識(shí)分子。《夏日》正如庫切的其他作品,也是在這三重意義上講述自我和他者的故事,書寫著他的像是永遠(yuǎn)不會(huì)完結(jié)的主題(或心結(jié))。
庫切的三重身份,既是緣于一種“歷史的宿命”,也包含自我抉擇。讀者在《夏日》中不無驚訝地看到,作家的成長竟然是沒有被青春和祖國的機(jī)體所吸收,而是被吐落在外面,輾轉(zhuǎn)于這個(gè)世界的別處。他最終選擇退出,不愿茍同任何一種現(xiàn)實(shí)政治;不尋求妥協(xié),也得不到慰藉;像卡拉馬佐夫家的伊凡,糾結(jié)于他的清醒和分裂,他的懷疑論的痛苦,他的詩性和枯竭,還有他無家可歸的荒涼和夢(mèng)魘。
(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