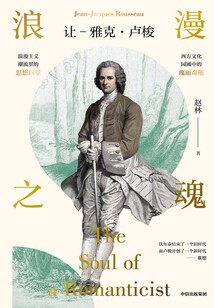
浪漫之魂:讓—雅克·盧梭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導言
20世紀美國著名哲學家和史學家威爾·杜蘭特在其巨著《世界文明史》第10卷《盧梭與大革命》的開篇處這樣寫道:“一位出身寒微,在呱呱墜地之際即失去母親,不久復遭父親遺棄,而身染一種痛苦的、不可告人的疾病,在陌生城市和敵對的信仰中,流浪達12年,而為社會和文明所排斥;以反對伏爾泰、狄德羅百科全書派和理性時代為己志,而被視作危險的反叛分子,被看成精神失常,被疑為圖謀不軌,為人驅逐,流離失所,而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幾個月里,方能親眼見到最反對他的人,對他所表示的崇敬——如何在他死后,竟然能遠勝伏爾泰,使宗教復活,使教育改變形態,使法國民氣提高,從而激發了浪漫主義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進而影響到康德、叔本華的哲學,席勒的戲劇,歌德的小說,華茲華斯、拜倫和雪萊的詩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以及托爾斯泰的倫理學——諸如此類影響,使他在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18世紀作家和思想家中,成為對后代貢獻最大的一位。”[1]這位偉大的時代叛逆者和后世一切具有浪漫情懷的人們心中不朽的精神偶像,就是讓—雅克·盧梭。
在這本關于盧梭的人生和思想的小冊子里,讀者們將會認識到一位在歷史上頗有爭議的思想巨擘。他在理性最具有權威性的時代里公然以樸實無華的天然情感來反對矯揉造作的理性,在功利主義甚囂塵上的社會里大聲疾呼一種天國情調的道德良心,在傳統宗教遭受滅頂之災的氛圍中義無反顧地承擔起拯救信仰的崇高使命。他的一生充滿了苦難,他的行為也有著許多不光彩的瑕疵,而且,長期離群索居的孤獨生活和顛沛流離的坎坷經歷,使他難免在心理情緒上有些譫妄變態,在言談舉止上有些乖戾瘋狂,但是他的那種自我批判和社會批判的勇氣與真誠卻是無人能出其右的。雖然無論是在理論的系統性方面還是在實踐的道德性方面,盧梭都無法與后來的康德相比,然而恰恰是那位令后世人們肅然起敬的思想道德圣賢康德,卻對盧梭這位在歷史上毀譽參半的人物懷著深深的敬仰之心,在他那簡樸的寓所里,唯一的一幅裝飾品就是盧梭的畫像。有一次海德格爾在談到黑格爾的時候說:“我們的時代之所以不理解黑格爾,只是因為黑格爾太深刻,而我們的時代太淺薄。”同樣,如果今天的人們不懂得盧梭,問題并不在于盧梭,而在于我們自己。
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物質主義瘋狂膨脹的時代,迅猛發展的現代科技在使我們的生活環境變得越來越舒適的同時,也使我們的靈魂變得越來越冷漠和麻木。信息社會不僅杜絕了肉體流浪的可能性,而且也正在日益消除精神叛逆的可能性,人們都像大棚里的蔬菜一樣茁壯成長,也像動物園里的獅子一樣變得溫柔馴服。物質的進步要求精神必須做出某種犧牲,在陽光普照的文明大地上,我們再也不需要盧梭這樣躁動不安的精神流浪者了。
然而,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那偶爾失眠的心靈難道就不會泛起一絲一毫的惆悵和焦慮嗎?
也許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會想起讓—雅克·盧梭……
注釋
[1]威爾·杜蘭特:《世界文明史》第10卷《盧梭與大革命》上冊,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