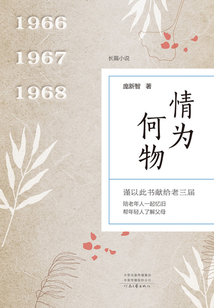
情為何物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我要給紅姐寫信,盡管我已經有了她的更便捷的聯系方式,是她丈夫紅巖的手機號碼,但是對于紅姐,我還是要采用這種最古老的溝通方式。我覺得,書信這種方式,不僅能使人“見字如面”,而且比之于打電話、發短信,更讓對方覺得你鄭重認真;很多時候,文字表達比口頭表達似乎更有味道,當著面我可能無話可說或者不知說啥才好,寫信我卻能洋洋灑灑有說不完的話。
其實我這封信的實際內容極其簡單。核心是:我已把租房子的事情辦妥,和老伴兒一起入住了,感覺很好。還有你們臨走時安排的事,也有了眉目。當地的領導和學校都很支持,領著我們兩口在山下的小學轉了一圈,教學條件再好沒有。和一些小孩及家長也有接觸,他們都表現出濃厚興趣,前景應該非常理想。而且,你還記得小時候跟媽上課時,咱們一起記的筆記嗎?我一本不少地保存著,全都拿來了。這就是現成的教材,至少可以作為參照,略加修改即可。可以說是萬事俱備,只候大駕光臨。不知你們那邊情況如何,何時過來,望告。
接著又不由自主地寫了些家長里短的閑話和進山隱居這幾天的愉快心境,以及問候之意。
寫完,叫老伴兒來看。老伴兒很快就看完了,一邊笑一邊微微地搖頭,說:“你們倆呀,真是的……挺好,寄出去吧。”
我不知道她說的“挺好”,是說信寫得挺好呢,還是說我倆的事挺好,還是我們幾個義務教學挺好,不管是什么,反正是批準通過了。
我拿過信封,在收信人處寫上“曲紅旗姐姐收”。似覺不妥,又拿過一個信封,想了想改成“郝紅巖賢弟、曲紅旗姐姐收”。看了看仍覺不妥。再拿過一個信封,改成“曲紅旗姐姐、郝紅巖賢弟收”。想想可以了,才把信封好,貼上郵票。老伴兒在一旁看著只是笑,最后說了句“你呀”,笑著走開了。
第二天八點半,我就拿著信去鄉郵所,不遠,在村頭的公路邊,下個坡就到了。我來到柜臺前,把信交給里邊坐著的穿工作服的姑娘。她看了我一眼,熟練地蓋上郵戳,沒等她往柜臺下邊放,我就說:“給我吧。”她似乎覺得奇怪,但還是把信給了我。
我站在門口等候,沒過幾分鐘,就聽到了縣里郵遞員的摩托車聲。他總在這個時候來的,我觀察過。
他走進郵所和姑娘交接了郵件,走出來時,我把蓋好郵戳的信交給他。他看了郵戳就塞進車后的綠色郵袋里,跨上車座,一只腳使勁一蹬,車子“突突突”響起來,帶著一溜煙塵飛快跑了。
我一直看著他騎車遠去,轉過了遠處的山口。
郵遞員帶著我的信走了,摩托車的聲音早已消失在夏日藍色的天幕里。我仍然不知所以地站著,望向遠方,我喜歡這樣。
遠方,青山仍在沉思;腳下,小溪仍在奔忙。
一
自從那天遇到紅姐,我就開始覺得“天意”這個東西,或許真的是存在的。
那是在半個月前,我和老伴兒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的是濟源太行山周莊村,有個在外地經商的周老板,回村看到年輕人紛紛進了城,老家幾近十室九空,除了少數留守老人和孩子,好多院落已經無人居住,原有的舊房因年久失修早已破敗不堪,院里更成蓬蒿樂園,其荒涼景象正應了那句古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除了溝底的水地尚有人耕種,更多的山上的梯田都撂了荒。周老板覺得可惜,感嘆之余便有了主意。他想,此處山清水秀,環境優美,正是個休閑養老的最佳境地。于是召集鄉親們共同商量,利用這些廢棄的土地和院落,因地賦形,建起一批農家窯洞小院。同時還弄出個名叫農家樂的酒店,又下功夫組織起一套非常完善的管理服務隊伍,果然就吸引來一批想要落葉歸根、歸隱田園的退休老人入住。這些老人過得舒適,就有人寫出文章發在網上。其中有一篇類似“新桃花源記”,全文如下:
周莊公社記
余退休歸里,偶遇故友,曰:濟源有汝同窗好友周希真者,昔時宦海苦行,小有所成,每見紅塵熙熙攘攘,時感有違本心之痛,遂辭官歸里,逍遙謀生。未幾便略有積蓄。一日,召集同窗故友曰:三千年讀史,無外功名利祿;九萬里尋道,終歸詩酒田園。人之在世,當心靜如水,自由自在,豈可因斗米而心為形役、惆悵獨悲。迷途未遠,來者可追。吾欲歸故園修建農莊,與諸君同食同住同作同息,植樹種菜,自給自足,抱團養老,返璞歸真。諸君以為如何。眾人皆曰:善。于是周君歸里,盡傾囊中所積,依山就勢,因地賦形,建起農家小院。眾皆應招而至,閉山鎖聽,偏處一隅,不知山外四時,今夕何年,實乃古桃花源之今在也,汝可相隨前往一觀。余欣然應諾。
驅車而行,周莊至矣。俯瞰四方形勝,北依王屋主峰天壇山,古帝祭天之所也,彩云繚繞,連高天之祥瑞;南臨小浪底水庫腹地,華夏母親之河也,碧波萬頃,接地脈之柔陰;西靠大峪鎮狩獵場,蓬蒿茂而鳥獸集,生機勃發,古樸自然;東望乃百余里懷川,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又溝底有清溪如帶,名硯瓦河,纏繞農舍而過;山間有飛瀑灑珠,曰天上水,挾青山薄霧輕飄。入農莊訪俗,所見多鶴發童顏,儀態溫潤,平靜謙和,君子之風也。
每有雄雞司晨,霞光下或起舞于場上,晨霧中或徜徉于溪邊。聽鳥語婉轉,空谷清響也;看舟分荷塘,漁家收網矣。出工鐘聲響起,眾荷鎬鍬南崗植樹,沿小路魚貫而上,笑語陣陣,溝壑同歡。昔時荒坡今已成林矣,常年桃李花開不謝,四時松柏長綠怡顏;山果熟時,喜邀農家采摘,其樂融融,親如家人。午時收工,集體用餐,山村小吃,健康天然,笑品故鄉滋味,樂享口舌之福。餐罷各歸午憩,靜室酣然夢足。起而自由活動,因趣各取所需。有扶杖隨處游覽,盡得山水之樂;有展卷各代經典,略知古今異同;有聚而練書描畫,全無名人達士驕矯之氣,貴在發自內心之稚拙本色;有散而小院打理,皆存草木百姓平和心態,妙在紫藤紅花只求有緣。而或皓月當空,清風徐來,或相約于高臺之上,或圍坐于小院之中。一壺釅茶,洗卻俗腸;幾杯村酒,暢抒胸臆;娓娓盡肺腑之言,殷殷皆兄弟之情。及至興起,亦歌亦舞,亦戲亦鬧,盡歡而散。及歸,正東墻蟲吟,西塘蛙喧,極靜境界,無夢而眠也。
一路看來,唏噓不已。友笑問如何,余答曰:真世外桃源,吾所愿也。友嘆曰:此境雖佳,然其名不貼也,汝試命之。余沉吟良久,對曰: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如周學弟諸君能跳出三界,識破紅塵,舍繁華而就簡樸,遠名利而求本真,排眾議而持獨行,棄俗欲而親自然者,實不易且難得也。此處既有個人空間,更重群體享受,各取所樂,各盡其能,人人關愛,關愛人人,和睦相處,堪比至親,植一片森林于當世,傳一段佳話于后人,足見志趣高遠矣。其意與儒家之天下公平,與道家之清靜無為,與佛家之空靈自在,甚而與今人追求之大公理想,均有相通之處,莫如命名曰周莊公社,敢問可貼否?友大笑曰:善,何不秉筆以記之。余頷首應諾。
既歸,展紙疾書,題曰:周莊公社記。
我和老伴兒讀完文章,也對這個地方有了興趣,就決定前去實地看看,權當老兩口出去旅了趟游。
那天和老伴兒一起來到周莊,游人還真不少。村里村外轉了一圈,感覺確實不錯。路過一座小橋時,和一群人擦肩而過。在這群人的前面,有個十來歲的男孩跑得飛快,那群人里就有人高喊:“慢點兒,別跑太快,注意安全!”
好熟悉的聲音!好熟悉的話語!我不禁停住了腳步,回頭尋找那喊話的人。小橋那邊喊話的人也正回過頭來張望,是個老太太。我倆就這么看著,突然我的心要跳出來了,天哪,這不是紅姐嗎?老太太頓時也明白過來,顫聲問:“你……你是紅星吧?”
我急答:“是,我是紅星,你是紅姐!你……你讓我找得好苦啊!”
事情來得如此突然,猶如做夢一般。
我倆都快步走上小橋,就在拱形小橋的中央,四目相對,對望了很久,還是她先開口,說:“我們都老了。”
我說:“是,我們都老了。”
其他人都圍過來,紅姐拉過一個老漢,給我介紹說:“這是老郝,你姐夫,叫紅巖,其實比你小,小兩個月,你吃虧了。”又給紅巖介紹:“這就是紅星,你知道的。”
紅巖大方地和我握手,我也很熱情地握住他的手,上下打量。第一印象敦實健壯。留個板寸頭,雖然頭發有些稀疏且夾雜些許白發,但仍然不失干練。特別是那張典型的國字臉,很有大將風度。
他緊緊握著我的手說:“說了你幾十年,今天總算見到真人了,哈哈哈,怎么頭發全白了?白了就顯老,不過白了有風度。我猜你是個文人,靠腦子吃飯,不像我這工人,出力不費腦,自然身板兒好,你說是不是?哈哈哈。”一邊說一邊用另一只手拍我的肩膀,感覺很有力量,相伴著的又是一陣笑聲,甕聲甕氣,爽朗極了。
我也指著老伴兒給他們介紹:“這是我老伴兒,高國慶,初中的同學。”
老伴兒就和紅姐很有風度地握手:“老同學,還認識我嗎?初中我在四班,姐和紅星在二班,姐早就是我們的偶像,忘了你是全縣初中會考的女狀元?長得又漂亮,還洋氣,才貌雙全,咱們那一茬女同學誰不崇拜你呀!后來的事我也知道,紅星跟我說過的。”
“咋能不認識呢?你比那時候更漂亮。”紅姐抿著嘴笑,用一種神秘的眼神盯著老伴兒看,又朝我瞟一眼說:“你倆還一塊兒演過戲呢!”
老伴兒就哧哧笑起來,在我肩上使勁拍了一下,臉也紅了。
紅巖就搶上來和我老伴兒握手:“弟妹很漂亮嘛!想當年一定是朵校花。”說著扭頭又看紅姐,說:“俺家紅旗也很漂亮,年輕時你倆有一比。”
老伴兒也不讓他,笑著“批判”他:“謝姐夫夸獎。人老嘴不老,說出話來照樣甜,可想當年是咋騙紅旗姐的。這輩子占了紅旗姐的便宜,還不滿足呀?”
紅巖仰天大笑一陣,回敬道:“弟妹你說這話可不對,當年可是她死活要追我的,非我不嫁!不信你問她。”
他們倆說著話,紅姐拉過那個小男孩,給我們介紹:“這是我孫子,名叫希望,今年十一歲。”又指指我和老伴兒對孩子說:“這是閃爺爺,這是高奶奶。”孩子很有禮貌地大聲叫著“爺爺好,奶奶好”,給我倆各深深鞠了一躬。
老伴兒高興得很,說:“希望這個名起得好,又通俗又有味兒,大俗大雅。大到國家,小到個人,只要有了希望,就有了精氣神,一切也都有了意思。”說著話,就從兜里掏出錢來,兩張一百元,親切地說:“真是好孫子,這是爺爺的,這是奶奶的。”一張一張遞給孩子。
紅旗、紅巖急忙阻攔,推來讓去。老伴兒有點急了,對他們說:“你倆都別管,這也是俺的孫子,頭次見面,俺咋能不懂禮數?”
他們兩口這才不再阻攔,孩子說聲“謝謝爺爺奶奶”,接過錢又遞給紅姐。我在心里直夸老伴兒腦子快,我還真沒想到這老禮數呢!
大家結伴而行,我這才發現紅巖腿腳不大利索,走路有點跛。我看了老伴兒一眼,老伴兒向我使了個眼色,我知道不便多問,倒是紅巖樂呵呵的,問我老伴兒:“弟妹長得這么漂亮,咋起了個男孩名字呢?”
老伴兒說:“好多人都問過我,其實我也曾經覺得別扭,我是四九年生,陽歷十月份,剛過了開國大典,舉國同慶,我家又姓高,爺爺就和父母商量,起了‘高國慶’這個名,說是喜上加喜。后來我想改個女性化的名,爺爺說托了共產黨、新中國的福,有紀念意義,就沒人再提改名的事,也就這么叫過來了。其實名字就是個符號,叫順了也覺得挺好。全國不知有多少人叫國慶,說明大家都認為這名字好,你說是不是?”
紅姐聽著瞪大了眼,似乎很吃驚;紅巖聽了又是一陣哈哈大笑,說:“這真是巧了,不瞞弟妹說,我也是開國大典后生的,原本也叫國慶的,加上我家姓郝,你念念,好國慶,比你那高國慶還直接。后來那本很有名的小說《紅巖》出來了,我伯父就是渣滓洞牢房里的烈士,為了紀念伯父,也因為我特別喜歡《紅巖》這本書,才改成‘郝紅巖’這個名字了。”
我和老伴兒都“噢”了一聲。
我正陷入深思,老伴兒已經找到了新話題,對紅巖說:“姐夫要是這么說,那咱倆可得排個大小。我是陽歷十月五號,你是幾號?”
紅巖撲哧笑了,只不說話。老伴兒覺得有戲,逼他快說。紅巖只好有些泄氣地說:“算你能,比我早一天,我是陽歷六號。”
老伴兒得意起來:“想著你就比我小,怎么樣?以后不能吃虧,不叫你姐夫了,你改叫我姐,聽見了嗎?”老伴兒開始擺起譜來。
紅巖不同意,反駁她:“要這么說,咱這兩家不就亂了嗎?”
老伴兒寸步不讓:“咋亂了?咱們各叫各的,紅旗姐是紅旗姐,你該叫我姐就叫我姐,聽起來更親切。紅旗姐你說是不是?”
紅姐連答“是是”,抿著嘴笑。
我們就這樣一路說笑著,在山里邊走邊看,兩家真的親如一家。最后老伴兒提議今天住下不走了,兩家的故事相互說了幾十年,上天安排今日得見,怎么能不好好說說話呢?
紅巖隨即表態贊成:“對對對!我正想說呢,弟妹先替我說了,哈哈哈。”
老伴兒推他一把,瞪眼瞅著他。
紅巖不解,也瞪眼瞅著老伴兒:“咋了咋了?”
老伴兒笑著問:“你剛才叫我啥?”
紅巖愣了一下,忽然明白過來:“噢噢,不能叫弟妹,該叫國慶姐!我這輩子正缺個姐疼我呢,老了老了,天上掉下個姐姐來,哈哈,大喜大喜。”說著話停下腳步,雙手扳過老伴兒的肩膀,一副鄭重其事的架勢說:“咱可得說好,我叫你姐可以,姐也得有姐的樣子不是?你可得好好疼我。”
“疼你歸疼你,”老伴兒笑起來,“你可得乖一點兒,不然姐打你。”
紅巖也笑了:“要說我有點虧,你只大我一天,對了,以后我就叫你小姐,對,叫你小姐,哈哈哈!”
老伴兒隨即在他背上捶了一拳:“胡說,是老姐!”
紅巖說:“是小姐。”
老伴兒說:“是老姐。”
于是他倆小姐、老姐,老姐、小姐地鬧起來,結果連他倆自己也說亂了,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
紅姐瞟了紅巖一眼,小聲問他:“照你說的,我這輩子就沒疼你了?”
紅巖恍然大悟,用手拍著嘴說:“打嘴打嘴,我可沒有這個意思,這輩子要不是你疼我,我咋能有這么好的身板?”又面對我們認真地說:“你們紅姐是真疼我,可是我知道,她心里可是還一直疼著紅星哩。”又面向老伴兒說:“小姐——老姐你不會吃醋吧?”
老伴兒撇著嘴笑看紅巖一眼說:“你也太小看你老姐了,有人背地里疼俺家紅星,說明啥?說明俺優秀,說明俺有艷福唄。”
紅姐仍然只是抿著嘴笑,嘴角的兩個酒窩讓嘴變成了向上彎曲的彎彎的月牙。
我看著紅姐,突然,她的這副神態,一下子把我帶回到了六十年前……
二
我和紅姐的認識,純屬天意。
那是建國初期的1956年夏天,我七歲。當時國家還很窮,農村和山區更不用說。我家住在豫西的淺山區,應該說家里啥都缺,但最缺的還是零花錢。吃的也不寬余,但你總還能去地里刨,可有些東西是必須要花錢的,你總得吃鹽吧,總得點燈吧,諸如這些花銷,通常也就靠采點山果、攢點雞蛋,拿到山下換錢,或者偶爾有貨郎擔到村里來時拿出來直接交換。
我父親小時候讀過一年半私塾,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也確實比別人有些見識。頭一年農閑時,父親去山下的鎮上軋花——現在的人已經不知道軋花這個詞了,那時候人們穿衣,全是自家織的土布,也叫粗布。要織布就得先種棉花,新摘的棉花里是帶著籽的,叫籽花,需要送到軋花作坊“脫籽”,這就叫軋花。然后再送到彈花作坊去彈花,讓棉花蓬松。然后回家利用高粱芯搓成尺把長的細條,才能在紡車上紡線。然后再經過幾道工序,才能織成土布。最后再買染料染上顏色,才能一針一線做成衣服。所以,那個時代人們穿的衣服很單調,原因就在于此了。
在軋花坊里軋花,是不花錢的,只把棉籽留下就行了。人家把棉籽賣給榨油的油坊,一轉手就有了收入。父親在軋花坊里坐著,進來了一位同樣是來軋花的瓜農。兩人坐著沒事,也就閑聊起來,聊著聊著,就成了朋友。
既然是朋友,人家就給指了一條路:你回去跟社里說說——當時已經從初級社轉成高級社,大村一個村算一個社,小村幾個村合成一個社,下邊分幾個小隊,土地、牲口、大型農具當然都已經歸公。
那位瓜農對父親說:“你跟社里說說,不如少種點西瓜,也沒有賣不掉的壓力。山上旱地瓜甜,成熟也早,利用這時間差弄到城里,人都愛吃個新鮮,價格也好,不圖掙大錢,解決個日常花銷是不是?”
父親覺得很有道理,就跟人家學了種瓜技術,回來跟社里商量,選了一塊墑情好的土地試種。收完麥,頭茬瓜就熟了。父親摘了瓜,裝在獨輪車上,次日趕早推到了縣城去賣。我家離縣城三十多里,全是最原始的鄉間土路。父親讓我跟著去,路上也好幫著拉拉坡,更重要的是想讓我開開眼界、長長見識,我可是還從未出過山呢,當然也興奮得不行。
我們雞叫頭遍就出發了,到了縣城,大約才九點多鐘。父親推著獨輪車在街上走,要選個熱鬧的地方。我卻兩眼忙不過來看新鮮:乖乖!這就是縣城呀!房子這么好,賣東西的這么多,人來來往往不斷頭兒,天天都有廟會呀!
這次進城,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其實那時的縣城,也不過是個大農村。后來每每想起,我都會告訴自己,人是很容易滿足的,起點不同而已。
父親選了個街口的地方,將瓜切開,一牙一牙擺好——那時賣西瓜,可不是現在這樣整個賣的。
生意不錯,城里人就愛嘗個鮮。過了晌午,來了一個“客人”——只要是買瓜的,父親都稱他們“客人”。這人三十來歲的樣子,長得細高,清清瘦瘦,白白凈凈,留著小分頭,大概是個子有點高,背就有點彎。看到我們的瓜攤停下來看,嘴里說:“西瓜可下來了,您是哪兒的?”
父親熱情地招呼他,告訴他:“俺是西山的,旱地瓜熟得早,客人不嘗個鮮?”
這人連說“嘗嘗、嘗嘗”,就讓父親給稱了兩牙。
他拿起一牙咬了一大口,連說:“不賴,不賴。”
父親就和他閑聊起來——來縣城的路上父親就教我,做買賣就得嘴甜,會跟客人聊天,三聊兩聊就親近了,買賣就好做了。
父親試著問他:“客人一定是國家干部吧?”
他邊吃瓜邊回答:“也算吧,在初中教書。”
父親問他:“貴姓?”
他說:“免貴姓高。”
父親笑了,說:“這就對了。”
那人有點不解,仰起頭看著父親。
父親仍然笑著,說:“你姓高,個子也長得高,職位也高,當了國家干部,學問也高,就能來城里教書了。”
那人顯然覺得意外,“撲哧”一聲把嘴里的西瓜噴了出來,哈哈大笑起來,說:“我還當你說啥哩,你說的和我姓高沒啥關系,老鄉你真會說話啊!”說著笑著站起來,從制服口袋里掏出一塊疊得很方正的洋布手巾擦嘴。
父親也很高興,說:“不說不笑不熱鬧,大家高興就好。”
高老師應著“是是”,又坐下繼續把瓜吃完,付了錢笑著走了。
看著客人走遠,父親對我說:“看見了吧,這就是買賣人。嘴要甜,會說話,讓人家掏了錢,心里還高高興興的。”
瓜攤前暫時沒人,父親就讓我把地上的瓜皮收拾干凈。我彎腰撿瓜皮時,突然發現地上有一塊錢,疊了兩折,紅色的,混在瓜皮里很不顯眼。我拿給父親看,父親說肯定是高老師掉下的。我說是,高老師掏手巾時,我就覺得有啥掉下來了。父親離開瓜攤走到街道中間,朝高老師走的方向望了望,知道人已走遠了,轉回來對我說:“你把錢拿好,興許高老師過一會兒會回來找,一定要還給人家。”
我很認真地點點頭,把一塊錢緊緊地攥在手里。
高老師一直沒有回來。到了下半晌,就只剩下一個瓜了。父親想了半天說:“這個瓜不敢切開了,萬一賣不了,咱又得趕著回家,不就可惜了?”
父親決定再等等看,實在沒有機會就推回去。然而等來等去,雖然有人來買,但父親堅決賣整不賣零。眼看時間不早,我們正準備收拾回家,突然來了一個騎自行車的人,三十多歲,戴著眼鏡,車子后面帶著一捆書。他看見我們就跳下車,問瓜咋不切開,父親說賣整不賣零。那人覺得奇怪,父親就說了原因。那人“哦”了一聲,問我們是哪村的,然后就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問我們:“三十多里呢,回到家還不半夜了?”說著開始打量我,問我幾歲了。
我小聲回答七歲。他點點頭說:“也該上學了。”
父親打量著他,試探著問:“客人高就?”
那人大約覺得父親文縐縐說話好笑,說:“啥高就不高就,在初中教書。”
父親一聽大喜,忙說:“這就好了,我向您打聽個人,高老師您可認識?”就把剛才拾錢的事講了一遍,我也伸開手讓他看已經被汗浸濕的一塊錢。
也許是被我滿懷期望的眼神所打動,他看了我半天,很認真地問:“地上拾來的錢,不就是自己的嗎?”
我也很認真地回答:“拾的是別人的錢,不是自己的。”
他不住地點著頭,微笑著夸獎我:“這孩子不簡單。”又轉臉對父親說:“你教育得好啊!”接著說到剛才的高老師,他說這個高老師不僅認識,而且就在一個學校,然后說:“這樣吧,這個瓜我買了,只是沒法拿,你幫我送到家,就在前面不遠,可以嗎?”
父親連說“中、中”,趕忙收拾東西。
那人住在一個很深的院子里,我向四周瞅瞅,是好幾家合住在一起的。父親把瓜搬起來,那人卻并不去接,只是對屋里叫了一聲:“小秋,來客人了。”
隨著門上竹簾掀起,一個女人應聲而出,也戴著眼鏡,身條細細的,下巴尖尖的,說話弱弱的:“屋里坐吧。”
父親推讓再三,還是搬著瓜跟進屋里。
那人開始自我介紹,說他姓曲,叫曲忠義,是縣里初中的教師,女的是他的愛人,叫鐘望秋,桌子旁坐著看書的是女兒,叫紅旗。解放了,紅旗插遍全中國,就起了這個名字。
他們大人說話,我就站到紅旗旁邊,想看看她讀的什么書,剛伸出手,她就一把將放在一邊沒讀的書拉到自己面前,微微抬著頭,拿眼睛瞪著我。我急忙收回手,只覺得她的一雙眼睛好大。
一旁的大人都看到了這一幕。曲老師叫了一聲“紅旗”制止她,她的媽媽卻轉身過來,拍拍紅旗的肩膀弱弱地說:“人家是客人,你們是小朋友,我們家紅旗當然是懂禮貌的。”于是大人的話題,就轉到了我們兩個孩子身上。
曲老師問我的情況,父親回答:“七歲了,屬牛,解放那年七月七生的,是農歷,孩子落地時天上的雨剛好停了。”曲老師有點吃驚:“這就巧了,我們家紅旗也是那年生的,農歷七月七,乞巧節嘛,深夜兩點半出生,是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你們家孩子是幾點?”
父親也覺得巧了,說:“農村不論鐘點,就是后半夜吧,過一個多時辰天就亮。”
曲老師仰頭算了算,說:“這么說我們紅旗比這個孩子大一個時辰。”
曲老師就拿眼睛打量著我,問:“你喜歡讀書嗎?”
我點了點頭。
又問:“讀過什么書?”
我低下了頭。
父親替我回答:“沒有讀啥書,只是跟我學過《三字經》啥的,會背。”
曲老師就讓我背一下聽聽,我就很流利地背起來。沒背多少他又讓我停下來,說:“那我問你,知道‘昔孟母,擇鄰處’是啥意思?”
我答:“就是不要和不好的人在一起,要和好人在一起。”
曲老師高興起來,大聲說:“孺子可教。”又回頭看了看鐘老師,鐘老師會心地微笑著點了點頭,扭身在紅旗肩上輕輕拍了一下,問:“怎么樣?”
紅旗又用大眼翻著我,說:“還可以吧。”
氣氛已經很熱烈了。曲老師就招呼鐘老師上飯。父親不肯,曲老師也不讓,說還有幾十里路呢,家門都進了,咋能讓您空著肚子回。父親見辭不掉,就一起吃飯。飯后,鐘老師從抽屜里拿出一塊錢交給曲老師,曲老師塞到父親手上,說是買瓜錢。父親哪里肯收,說是飯都吃了,還沒付飯錢呢。
推來讓去,曲老師說:“也罷,過些天還會見面的,今天就算認了一門親戚。”父親這才千恩萬謝地告了別。
出縣城不遠,天就黑了。一路上父親感慨萬分,不知說了多少個“好人哪,一家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