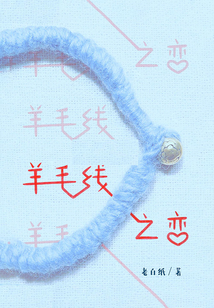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雨田
童年不是為了長大成人而存在的,它是為了童年本身、為了體會做孩子時才能體驗的事物而存在的。童年時五分鐘的經歷,勝過大人一整年的經歷。精神創傷也是在這時期形成。
——宮崎駿
在一個夕陽時分,跳入一片暖洋洋的金色海面,從此在安靜美麗的海底生活,這是我從8歲就向往的。
這個向往驅使我在23歲的時候,動用存了多年的旅費,暫停二十幾年懵懵糟糟的生活,喘一口氣。
我選擇了便宜而神秘的南美,而且那里的熱烈、風情萬種,正是我身上缺失的部分,因此,類似這樣的國度,從小就吸引著我。
先在陸地上閑逛一兩天,南美真是購物天堂,手工的、現代的、設計師的、紡織品的、古著的、香艷的、暗舊的、植物的、驚人的想像力和耐心,配色更是美得讓人眼淚都要流下來了。拉美人把熱力給了最低微的泥巴啊,玻璃啊,鏡面啊,碎布條廢紙片啊,塑料什么的,做成人人都負擔得起的、又便宜又動人的東西,他們簡直是生活家、藝術家。
我像貪戀花粉的小蜜蜂每天去各種店鋪探險,跟著Google map走啊走,已忘乎所以。買陶土的小杯盞、木雕面具、手工染色的床單以及種種讓我愛不釋手的零零碎碎,最后,即將離開的時候,還在一個角落里的小攤位上,發現一位老先生在賣手搓的羊毛線,那個染色簡直美得不像話,我哪一種顏色都舍不得放下,索性每種都買一團,真的不便宜呢。
心滿意足,接著,我登上卡雷拉斯號貨輪,準備開始八天的漂流。對,沒錯,這是一艘只有一層甲板的哥倫比亞貨輪,并不是擁有十幾層甲板的豪華游輪——出航時攜帶一定數量的游客,是許多貨輪運貨之外賺外快的方式。而像我這樣,既沒有足夠的錢,又喜歡自然而不是奢華的游客,就很適合這樣的貨船旅行。
船上的游客不算少,幾乎全是臉孔深邃的族類,除了我。作為一個神秘的東方人,我的外表做了最好的詮釋:頭發厚而細軟,像套了一頂烏黑的氈帽在頭上。我穿長到膝蓋、兩邊開衩的棉布長衫,配寬大的棉布褲子和各種平底鞋,這么穿讓我感到很自在。棉布的東西便宜而且環保、舒服透氣,也不用小心打理,總之,穿上它們就有種包裹全身的安心感,很適合漂流的旅途。這樣的棉布褲子和長衫,我在上海街角的小裁縫店做了好幾套,每天可以按照顏色做不同的搭配,沉浸在這種與美有關的事里面,讓我覺得陽光都更燦爛些。
我這么個穿衣法,配上風都吹不動的黑色毛氈長發,順利的變成各國甲板客中最怪異的一位。這種怪異有時候也有福利,可以得到一種孤獨的清凈。
這是貨輪航行的第三天,今天穿墨綠色底子灑著淺藍碎花的長衫,舊粉色的褲子在下面露出膝蓋那么長的一截。我住在貨輪上靠近馬達的一個小房間,便宜,缺點是比較吵,所以天氣不錯時,我通常去甲板上躲避噪音,看看海,吹吹風,發發呆,釋放一下成長過程中的憂傷和自食其力后的疲倦。
甲板上起風了,順手抄起我最依賴的、已經起球的、軟和的暗紅色毛線披肩,戴上自己編織的黑色水手帽,走向甲板。耳垂上,我用珠石串的長耳環,正隨著走路搖曳多姿。
天氣不錯,大概全體游客都跑到甲板上來了,交織著各種陌生的語言和面孔。在熱熱鬧鬧中待了一會兒,我繞到后面一個人少的太陽地,坐在一個無人的白色陽傘下,繼續制作我的護身符。
我從小就不是愿意對親人展示甜蜜的孩子,喜歡找機會離開他們總是憤怒的視線,安靜地在角落看一本不知道讀了多少遍的書,或者偷一點家里的布頭線腦,再加上他們不要的破襪子,給自己縫一個布娃娃,再給她做些小衣服。10歲左右的時候,我已經開始用家里的舊秋褲為自己改制內褲,或者為難看的手套縫一個手織的蝴蝶結、繡一些彩色的波點,讓它漂亮起來,我整天就在琢磨這些。
可以說,在很小的時候,獨處對我來說就已經是一種享樂,我一點都不覺得孤單,反而總是充滿欣喜,我仿佛為耽于獨處而生,我不歌頌孤獨,也不向隨和諂媚。通過不被傷害的獨處,我的眼睛過濾掉某些晦暗,只剩下閃亮的世界。或者也許不管怎樣,孩童總是處于一種嗑藥的狀態,一切都像水晶燈一樣發亮,像糖果鋪一樣香甜,世界隨時隨地是讓人欣喜、驚訝的,不然為什么小孩子會經常呈現出,同時張大眼睛和嘴巴、要喊出“哇哦”的樣子。
我的父母,據說是一對靈秀的人,他們都是家中排行最小的孩子,童貞多、怨氣少,離世俗遠。輪流養我的親人,提到他們總是皺眉搖頭沒有好臉色,從鄰居的閃爍其詞里,我慢慢拼湊了他們簡短潦草,但對我來說,至情至性的一生。他們的戀愛因為世俗的原因被兩邊父母拆散,媽媽未婚有了我,東躲西藏地勇敢生下來,卻被有傷風化的評判壓垮了,郁郁恍惚間,被大卡車撞倒,再也沒有機會去過她本想沖破世俗、跟相愛的人一起的余生。第三天,爸爸就燒炭追隨她而去。
小時候,我的小腦袋瓜留了很多位置給他們。我想象他們的故事,感受與他們神秘的連接,我知道他們就在某個地方,他們仍在相愛,他們手牽手,每時每刻都在溫柔地看著我。我經常跟看不見的爸爸媽媽撒個嬌、說說話,他們讓我在獨處的時候,離他們更近、離美好更近、離寵愛更近。長大后,越來越接近媽媽當時的年齡時,我會猜想媽媽的心思,比如她給了我星星這個名字,我想著純美的她,溫和有靈、不染雜塵,她一定希望我像星星一樣,做一個不奪人光芒,柔和晶瑩、自足自得的女孩。
在姑父不那么暴躁,又或是嬸嬸停止指桑罵槐的時候,我也有機會在平靜的氛圍中,從電視里看一段世界名著改編的電影,或者講述宇宙的科普片。有一次,我一邊在黑暗里把電視的聲音調到幾乎聽不見,一邊忍受旁邊已經睡了的姑姑每隔幾分鐘的粗暴呵斥,讓我別再看了,但是那次我實在不能順從,電視里正在演一個叫瑪格麗特的女攝影師,她特立獨行的一生,她的藝術格調、她的愛情……我青春的心在黑暗里萬馬奔騰,我無聲地吶喊,眼淚隨時要迸發出來。
那時候,免費的市立圖書館是我躲清靜的最好去處,我總是帶著摘抄本子上,畫下的那些星圖,畫下天文望遠鏡的光學圖,畫下經典音樂的五線譜,抄寫關于藝術,關于嫁接,關于文學,關于永不言悔的一切。那些在閉鎖時光里,屬于童年、少年的無法填滿的、忠貞的求知欲,閃著爍爍星芒的、永遠孤獨卻從未停止的求索。就是那些獨特的人或是浩瀚的宇宙,滋養著我,給了我很多向往,這么長大的小孩,難免被遠方吸引。
日復一日被并不信服的人無理訓誡,讓我早早在日記里寫道,要自己教育自己,就這樣,在整個青春期,漸漸把天生軟弱膽小的性子,矯正為一種暗潮洶涌的叛逆,表面不做無謂的反抗,但什么都自己拿主意,什么主意都敢拿,我就這樣長成了一個善良敏感、不管到了哪里,首先得找個昏黃的角落待著的倔強少女。
18歲那一年,終于拿到我要求自己的最低教育程度——高中畢業。盡管成績很好,但我沒有參加高考,這讓親人們如釋重負。看上去像一棵豆芽菜一樣柔弱乖順的我,以又一次不加掩飾地厭棄為契機,不顧一切地逃離,循著包吃包住的大型超市廣告,坐了30個小時的慢火車,跑去上海,那里足夠遠,那里人與人之間足夠疏離,正應和了我的羞怯和自由主義,我品嘗到無人關注的自在。
那段超市歲月非常溫暖,收銀的大姐、倉庫的小哥、推銷的小妹,都隱身在一座大城的影子里,無聲但自尊自強。每個人都很努力,為了遠方的家人,也為了有夢想有尊嚴的自己。一年之后,我的主管孫姐鼓勵我,不要窩在這里,學習一個可以立世的技藝,走出去——這和我初中時的日記不謀而合,那時候的小女孩寫道:要有一個可以養活自己的技能——孫姐幫我報名了平面設計的培訓課,我永遠不會忘記,她對當年那個小女孩的善意和殷切,她認真盯著我的眼睛說:“朱星,我覺得你有這份天賦!”。我無限信賴地接受她的鼓勵和安排,這是第一次,我不用自己做決定,而是可以依賴一個溫柔而堅定的人。
孫姐的這份關愛,讓我每天下班之后,倒兩次地鐵、再坐一次公交車去培訓班。學習的時候,鉚足了勁兒,再辛苦都覺得很幸福。我進步很快,從連電腦和鼠標都沒怎么碰過,到可以熟練使用三種Adobe軟件,對顏色和像素大小的敏感,也讓老師流露贊許。我那時還不懂得,是孫姐的愛,帶給我如此的力量。
到上海的三年之后,我終于跳了第一次槽,而且還上了孫姐為我墊付的培訓費,還用每月三分之一的工資,在鬧市租下了一間10m2的亭子間,廁所和廚房都在樓下,跟其他冷漠的本地鄰居共用。我讓房東把占據大半個房間的雙人床換成1米寬的窄床,把其中一整面墻做成了置物架,安置好雜七雜八的工具和材料之后,還有空間把一張小桌子放在唯一的小窗前,窗子正對著我最愛的思南路。筆記本電腦占用一半的桌面,另一半用來做手工。除了在一間步行可達的中國香港公司做設計民工,或周末偶爾參加市集,販賣一點手工的小玩意兒,我沒有任何娛樂,都宅在家里,天馬行空、變著花樣做手工,樓下孩童的吵鬧聲和鄰居的人間煙火讓人安心,與世隔絕在這個甜蜜的小空間里,心卻有無限的自由,常常做手工做到靈魂出竅。
周末早晨的賴床,是我寵愛自己的最好方式:睡到自然醒之后,在窄窄的小床上躺著玩一會兒手,自言自語或是傻笑一氣兒,手舞足蹈一陣后再發一會兒呆。終于有了自己的空間,雖然很小很破舊,但足夠我品嘗前所未有的自由,不論做什么,我再也不用擔心耳邊隨時會響起的斥責聲、無孔不入地控制或是極致地冷漠和忽略,這些都已遠離我的生活。那時候,我有一點學會了像貓咪一樣放松,身體不再像從前那樣,總是冷硬和僵緊。
我不怪親戚們,長大后我明白,要疲憊的大人們,去愛一對離經叛道的男女所生的孩子,的確太難了,他們把我喂養大,給我讀書讀到高中,已盡全力,再多的索要就是奢求。
獨居后最重要的是,我終于可以隨心所欲的創作和“禍害”(他們口中的)東西了,不用再偷偷摸摸了。也不必再與十幾個女孩分享一個小小的房間,想做手工的時候,要跑去公園的石桌上。這讓我在獨處時,微笑時不時就自己溢出來,經常對著空氣傻傻笑出來,事到如今,我滿足和感恩到不行。
最近幾個月迷上做護身符,為此還買了一本關于護身符的英文電子書,這次上船之前,在亭子間挑了幾樣基本的工具和材料,剩下的打算在旅途中汲取靈感并就地取材、任意發揮,我選中了便宜而風情濃烈的南美,心想在那一定會得到許多關于手工的靈感。
說回在白色陽傘下做護身符的事。我用閃閃的銀線,在黔東南侗族手染的亮布上,施展我的刺繡本事,繡上一些煉金術神秘學符號,再縫成打火機大小的布包,把之前在陸地上拜神廟時偷拿的,做儀式留下的木渣草灰的,塞進去,塞到鼓起來像個小枕頭為止,正小心翼翼塞的時候,右肩與右頸的這個90°夾角的空間里,探進一個腦袋在說英文,聲音渾厚、發音純正:“嘿!需要幫忙嗎,你看起來還真需要幫助”。
皺了皺眉,做手工的節骨眼兒上被打擾,我有點緊張。
“對不起,我在忙。”我低著頭擺出一張不客氣的成年人的臉,我扎實的高中英語一路以來已經練習得相當順滑。
“哦,是嗎,那我不得不請你移步到另一個地方去忙了,這把躺椅是我每天小睡一會兒的地方——怎么連這么偏的地方都被你找著了?”
我斜著眼睛,由下到上掃視來人,他很壯實,雙腿像彈簧一樣隨時準備彈來彈去。黝黑的臉上棱角分明,白眼球跟牙齒一樣醒目,不得不說,他笑起來整個世界都亮了。
我站起來,直視他的單眼皮小眼睛,那里面正閃著一層神秘莫測的光芒,一瞬間,想起夕陽下金色的海面。“對不起啊”,我有點慌亂,“我不知道這是你的地方”。一樣接著一樣撿起我啰里啰嗦攤在跟陽傘連在一起的桌子上的各種零碎,正準備塞進我用布條編的小筐里走人時,他坐下來,一手撐著下巴,一手按住小筐,仰著頭,眼睛里明明蓄滿亮晶晶的好意,卻給人玩世不恭的感覺:“我仔細想了想,是我打擾你了才對,你繼續吧,但是我能知道你在干什么嗎?你的這個小東西好像挺復雜的……哎,我來幫你怎么樣?”
雖然我抗拒一切不是自然發生的事,包括搭訕,但是這個留著小平頭、又黑又壯、像個壞人的家伙卻真誠得讓我無法拒絕。我還真想看看,他究竟怎樣用他粗得像老虎鉗一樣的手指,把干葉子的碎渣或者一小撮草灰什么的,塞進我留下的一公分寬的小洞里。
我把縫成方形的護身符遞給他,指指小洞的位置,再把裝了神秘碎渣的布袋遞給他,等著看笑話。
他拿起護身符,瞪大眼睛輪流看了看小洞和碎渣,再抬頭不可思議地看看我,露出想哭的表情,我憋著不笑,“請你幫幫我吧,真的很頭疼呢。”
他鎖住眉毛,嘴角向下,停了一會兒,就得意地搖了搖右手食指,接著從他的破爛牛仔褲的屁股口袋里,掏出一個已經做成了弧形的干癟香煙盒,從里面抽出包煙卷的箔紙,卷成一個錐形的細長小漏斗,插進小洞,小心翼翼把碎渣從大的一端倒進護身符,直到我喊“夠了夠了!”
隨著一聲戲謔的口哨,他把已經鼓鼓囊囊的護身符遞給我,單手插著褲袋,得意洋洋地晃著頭壞笑,我趕快穿針引線把小洞縫起來,又彈了彈這個小枕頭,好讓里面的內容分布得均勻一些,再把這個看起來足夠神秘的小枕頭護身符,掛在脖子上,拍了拍,抬頭瞅了瞅這個人,他一臉燦爛的大笑容,就像一個孩子遇到了讓他感到新鮮、好玩兒的事,所呈現出來的那種清澈的欣喜。“你戴上它棒極了!”他由衷地說。
但他剛才得意的樣子把我給氣著了,“那么,你是韓國人嗎?”我瞅著他的單眼皮挑釁地問。
“什么啊,我是中國人,你明明也是東亞人,怎么會分不清中國人和韓國人?那你又是哪的人啊,我看不出哪個國家會穿得這么奇怪,每天在甲板上的一堆人里,一眼就能看見你那個孤單的蓬蓬頭小身影。”
“我也是中國人啊”,我激動得把英文切換成中文,一路以來,天天英文說得舌頭都硬了,終于碰到自己人,連不合群的我,臉上也堆起熱絡親切的笑容,“奇了怪了,好幾天了,船上的游客基本都混了個臉熟,怎么還沒見有一個中國的你?”
他也激動起來,笑瞇瞇地說:“我不是游客啊,我在船上干活呢,就在下面的貨倉。”他用手指了指下面。
“我叫雨田”,他伸出大大的手掌,我把我的手放進去,有點害怕似的輕輕捏了捏他飽滿的手指肚,沖他點點頭說,“我叫朱星”。
這是我第一次碰觸異性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