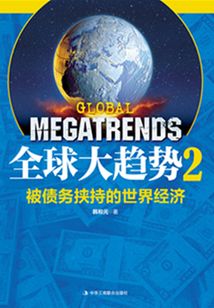
全球大趨勢2:被債務挾持的世界經濟
最新章節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引言亂世降臨(1)
我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預測都是徹底錯誤的。但問題是,種種跡象表明,我的預測是千真萬確的。
——史蒂芬·李柏
雖然米塞斯早就警告過“財政和貨幣把戲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時之效,從長遠看它肯定會讓國家陷入更深重的災難”。但掌權者顯然沒有將這樣的忠告聽進耳朵里去。相反,隨著2007年經濟泡沫的破滅,那些善于道聽途說的掌權者,從凱恩斯那里獲取了他當年的瘋狂之念——通過貨幣和財政予以大力刺激。他們試圖用刺激政策復蘇經濟。從因果關系來看,今天世界經濟的麻煩實拜2008年的刺激所賜。更為緊要的是,世界人口老齡化問題只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得更為嚴重,越來越多老人需要贍養,能創造財富的勞動力日益減少。世界性的債務問題猶如雪球,只會越滾越大。在這個民粹主義當道的世界政治格局下,我們可以預見的是,政府只能開動印鈔機,為其龐大的支出進行貨幣“融資”。而其結果又只能是創造更大的通脹和更大的債務,整個世界也因此進入一個惡性循環的亂世之中。
瘋狂之念
世界經濟再次探底的陰影終于在2011年8月橫掃全球資本市場,各地股市呈現一片拋售景象,在短短兩周之內,數以6萬億美元計的財富瞬間蒸發了。這種恐慌性拋售,透照出之前市場對于正常周期性復蘇的預期是錯誤的。
而引發這次恐慌的肇因,卻是再度出現的類似于2008年秋季的違約危機。只不過,上次的麻煩制造者是那些金融機構,而這一次則是政府。然而,2008年的危機應對之策恰好是當前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對于這種風險,事實上早于2007年,我就曾予以警告:
美國目前的問題,本身就是因為過去格林斯潘所采取的低利率政策而產生的過度消費所造成。這個時候予以降息,只是將問題往后拖延了而已。
我認為美國,甚至包括緊步美國后塵的全球各經濟體,應該做的是將問題解決在當時而不是留給以后。我當時這樣寫道:
目前美國和全球經濟的安危,主要系于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一人身上。他需要做的僅僅只是徹底切斷與“格林斯潘”式政策思路的任何聯系。然而這需要更多的智慧、勇氣及挑戰精神了。
很不幸,在美國,無論是布什、奧巴馬還是伯南克,他們非但沒有與“格林斯潘”式的政策思路予以切割。事后來看,他們的手段與格林斯潘的政策相比,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這一切得“感謝”他們從若干年前的“拙劣”的學者那里獲取的瘋狂之念。
對于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很多觀點,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去予以懷疑、反對甚至駁斥,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有時候傻瓜也能夠說出智者的語言。
經濟學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確與否,都比通常所認為的力量更大。事實上,世界是由少數思想統治的……善于道聽途說的瘋狂掌權者,從若干年前的拙劣的學者那里獲取瘋狂之念。
這句經常被人們引用的名言,是凱恩斯勛爵在75年前寫就的,用它來描述當前的世界政治經濟,特別是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與凱恩斯主義之間的這一曖昧關系,無疑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2006年春末,美國房市的虛弱無力變得明顯起來。房價開始下跌,起初比較慢,后來越來越快。根據廣為使用的“凱斯-希勒房價指數”,2007年第二季度,房價只從一年之前的頂點下降了約3%,而其后的一年時間里房價下跌了15%以上。在佛羅里達州沿海地帶等泡沫嚴重的地區,房價降幅遠大于此。2007年9月,美聯儲開始大手筆降息,企圖以此來刺激消費、避免經濟衰退。
但縱是如此,正如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論述的那樣,美國經濟還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崩潰的邊緣。對于這一境況,一些添油加醋者這樣描述:“在2007~2008年,當全球經濟被次貸危機百般蹂躪時,整個人類世界如墜深淵。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經濟活動雪崩的景象唯有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或可比擬”。
2008年12月16日,美聯儲終于將利息降到了地板價——0~0.25%的利息降無可降。在這一常規貨幣工具“彈盡糧絕”的時候,美聯儲于2009年3月18日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緊接著又于3月23日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就是進一步促進流動性,使貨幣政策的重心向“量化寬松”政策傾斜。
這些政策背后所隱含的是,掌權者們固執地把貨幣當成了經濟體的潤滑劑。在他們看來如果貨幣太少,交易成本就會增大,這必然會造成通貨緊縮,壓抑經濟的增長,甚至導致經濟的衰退。所以伯南克們一再地吹噓說,他們采取這項行動是因為他們已經從美聯儲在20世紀30年代所犯下的錯誤中汲取了足夠的教訓。他們認為當時的大蕭條完全是因為美聯儲沒能在危機期間向銀行提供足夠的準備金。世界各國的伯南克們堅持認為,正是由于他們以超常規的市場干預手段,才挽狂瀾于既倒,避免了金融體系的崩潰,從而避免了“大蕭條”的重演。
當他們在做上述表述的時候,卻沒有將另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明白地告訴大家。那就是,2008年的危機事實上已經將之前由龐大泡沫所掩蓋的結構性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福利方面做了過度的開支、發展中國家對出口過度依賴、國際貨幣體系先天不足導致債務和國際貿易嚴重失衡——暴露出來,而他們——各國政府與中央銀行,并沒有著手去解決結構性問題,而是采用了一種“眼下先顧增長,問題留待日后”的策略,試圖用刺激政策復蘇經濟。
假性繁榮
無可否認,正是在美國兩輪的“量化寬松”和中國的“4萬億”這兩劑強心針的積極刺激下,全球經濟才又開始“生龍活虎”了。
2011年的第一個季度,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認為始于2007年12月的美國經濟衰退于2009年6月結束,歷經18個月。從2009年6月至2010年12月,美國經濟繼續呈復蘇態勢,GDP呈現6個季度的連續增長。
但正如我于2009年10月出具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正步入正面Q時期——未來一年世界宏觀經濟前景展望》的報告里所強調的:
過去美國政府長期以來正是有意無意地利用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和全球經濟結構的先天性不足——世界貿易的不斷發展,客觀上推動了美國發行更多的國際結算貨幣:美元,來充當世界商品交換的媒介。這一要求的必然結果是,默許了美國人為壓低利率、主動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實現他們擴大貸款的需求,支持其增加商品及資源的進口,刺激其經濟的增長。過去的布什政府如此,當前的奧巴馬政府顯然也不例外。
然而,大量的經濟學家和掌權者們沾沾自喜,自認為他們讓世界經濟成功地避開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這一悲劇的重演。他們認為最糟糕的情況已經過去,并堅信整個世界已在他們的治理下邁向了所謂的“后危機時代”。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這一切僅僅只能是一個短期現象,全球經濟正面臨更大的風險。
風險在哪里呢?風險就在“我們當前復蘇的形式,只是源于傳統的流動性驅動的復蘇,而不是源于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新經濟的驅動,這種復蘇是不可持續的、是脆弱的”。
事實上,早在2007年3月,我就對當時即將出臺的刺激政策發出了嚴重的警告,當時我所基于的理由是:
美國是個典型的資產推動型的經濟體,現在出現7年來的第二度過剩局面。繼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目前美國經濟問題表現為房地產的泡沫正在破裂。這已經把美國推向衰退邊緣,而危機的根源就在于錯誤的利率政策。
……美聯儲人為地在壓低利率造成信貸的擴張,誤導著美國的消費者,使他們熱衷于消費很多在正常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消費的項目(美國的房地產業危機就是一個明證),由此當然能夠形成一時間的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