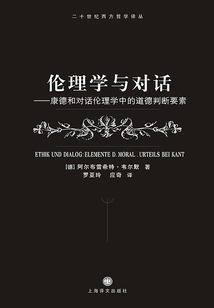
倫理學(xué)與對話
最新章節(jié)
- 第17章 注釋
- 第16章 譯后記
- 第15章 附錄二 交往與解放:批判理論中的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之反思[165]
- 第14章 附錄一 理性 解放和烏托邦
- 第13章 調(diào)停于康德和對話倫理學(xué)之間(3)
- 第12章 調(diào)停于康德和對話倫理學(xué)之間(2)
第1章 導(dǎo)論
道德哲學(xué)的懷疑主義和革命的人道主義是啟蒙的天然產(chǎn)物。在某種程度上,這一點在古代希臘的啟蒙時期就已經(jīng)是真實的了,而對于近現(xiàn)代歐洲的啟蒙運動來說就更加明顯了。在兩種情形中,啟蒙運動都意味著這樣一種發(fā)現(xiàn):除了人類的意志,恰當(dāng)生活的表面上可靠的規(guī)范并無可理解的基礎(chǔ),而在此之前,人們是通過事物的秩序、上帝的意志或傳統(tǒng)的權(quán)威為這種規(guī)范辯護(hù)的。我猜測,這種發(fā)現(xiàn)必定在首次發(fā)現(xiàn)這一點的人那里引起了一種五味雜陳的眩暈感。他們必定感到,他們的生存根基發(fā)生了動搖。他們必定隱隱約約地感到了一種自由,這種自由不是令人戰(zhàn)栗的,就是令人興奮的。換句話說,他們可能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秩序是以強制、壓迫和幻想為基礎(chǔ)的。而從那些受到這種啟蒙意識影響的人的視角或社會立場來看,這些因素中必定有一個或另一個已經(jīng)處于支配地位。哲學(xué)的懷疑主義、保守的犬儒主義和革命的人道主義都很有可能是對這種啟蒙運動的發(fā)現(xiàn)的反應(yīng)。
犬儒主義(懷疑主義的“憂郁的”版本)是一個心理學(xué)的和道德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認(rèn)識論的問題,因此我不打算在此對其展開詳細(xì)論述。[1]另一方面,從一種認(rèn)識論的觀點看,懷疑主義和革命的(或者至少是普遍主義的)人道主義是對啟蒙之發(fā)現(xiàn)的另一種反應(yīng)。懷疑主義質(zhì)疑道德之新基礎(chǔ)的可能性,而革命的人道主義則在理性存在者的統(tǒng)一意志中看到了這種可能性。我現(xiàn)在暫不討論這種區(qū)分,也不對道德哲學(xué)的懷疑主義作更進(jìn)一步的論述;這是后話。我首先感興趣的是革命人道主義的命運,我指的是它的哲學(xué)命運。當(dāng)然,我并不打算重新敘述整個故事,而只想考察它的兩種最先進(jìn)的形式,目的是為了得出關(guān)于它的可能的(哲學(xué))命運的結(jié)論。我所謂“先進(jìn)”是相對于它們的時代而言的。而修飾詞“革命的”則是為了表明我們這里正在討論的人道主義與近代革命之間的哲學(xué)聯(lián)系;而不涉及探究的主題本身。我們討論的并不是革命理論,而是(普遍主義的)倫理學(xué)。
我想探討的兩種立場分別是康德形式倫理學(xué)的立場和哈貝馬斯與阿佩爾所發(fā)展的對話倫理學(xué)立場。這兩種形式都是普遍主義的理性倫理學(xué),或者,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是“認(rèn)知主義的”倫理學(xué)。這兩種立場的特色在于,它們都在一種形式原則中尋求倫理學(xué)的基礎(chǔ),形式原則的形式性表明它同時也是一種普遍主義原則。道德有效性在這里奠基于一種合理的程序,因為這種程序一方面刻畫出理性存在者普遍共享的合理性內(nèi)核,另一方面與(根本上)自由平等的所有理性存在者相關(guān)。普遍有效性與道德原則本身的普遍主義特征相互交叉:在這一基本點上,哈貝馬斯和阿佩爾都同意康德的觀點,而且,至少就法的“合法性”概念而言,他們也同意革命的自然法學(xué)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討論的作者都屬于啟蒙的人道主義陣營。
下面我并不打算詳盡地說明康德、阿佩爾或哈貝馬斯采納的道德哲學(xué)立場。我的分析和解釋的目標(biāo)更為有限。我更多是出于啟發(fā)式的原因關(guān)注康德的倫理學(xué)。我認(rèn)為康德的選擇性解釋是為了表明其倫理學(xué)的長處和弱點,從而說明“交往”或“對話”倫理學(xué)的發(fā)展動機(jī),也是為了澄清這種理論需要論證的那些觀點。我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康德的倫理學(xué)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得到辯護(hù),而這就是我特別要揭示它的長處的原因。有些讀者可能會指責(zé)我有時像個斷章取義之人,專挑那些對自己特別有用的段落。但是另一方面,在探討對話倫理學(xué)時,我極為嚴(yán)厲地對待它發(fā)展這樣一種體系的要求,這種體系借助普遍語用學(xué)或先驗語用學(xué)來解決康德的問題,從而把康德的倫理普遍主義形式“揚棄”在對話的普遍主義形式中。我并不相信對話倫理學(xué)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這個抱負(fù),這就是為什么與對待康德的倫理學(xué)相比,我對它采取了一種更為嚴(yán)厲的態(tài)度。我把后者當(dāng)作一種尺度,盡管它本身可能已經(jīng)變得是可疑的,但用來判斷聲稱要“揚棄”康德倫理學(xué)的理論之解決問題的潛能,它仍然能夠發(fā)揮有益的作用。
在對康德的批判中,對話倫理學(xué)把焦點集中在康德倫理學(xué)的三個弱點上。首先是康德的道德原則形式上的獨白性,與康德自己的看法相反,它認(rèn)為康德沒有回答主體間有效的道德判斷的可能性問題。其次是康德倫理學(xué)的嚴(yán)格主義,這種倫理學(xué)基于一種對法則概念的獨特的形式主義的實體化。第三,它批評康德在哲學(xué)上為他的道德原則進(jìn)行辯護(hù)或奠基的嘗試。對話倫理學(xué)試圖通過把康德的獨白形式的普遍主義“揚棄”在一種對話形式的普遍主義之內(nèi),從而克服這里所指出的康德倫理學(xué)的三個弱點:首先,關(guān)于道德上有效的準(zhǔn)則,對話倫理學(xué)所重新表述的道德原則并不要求我,而是要求我們能夠愿意它們成為普遍法則。其次,按照這種表述,可以把正當(dāng)行動的問題理解成有需要的、脆弱的存在者之間的合理交往問題,這樣就排除了倫理學(xué)嚴(yán)格主義的諸種僵化態(tài)度。第三也是最后一點,對話倫理學(xué)對道德原則的重新表述,有可能實現(xiàn)一種新形式的終極奠基(Letztbegründung):阿佩爾和哈貝馬斯試圖表明道德原則是奠基在論證的普遍結(jié)構(gòu)之上的。而我對迄今為止的對話倫理學(xué)的異議,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它一方面依然是過于康德式的,另一方面又不夠康德式。與康德靠得太近的批評指向?qū)υ拏惱韺W(xué)的共識論前提,以及終極奠基的綱領(lǐng)。當(dāng)然,表面上看,對話倫理學(xué)的這兩個方面與康德沒有什么聯(lián)系。但是正如我將要嘗試表明的,共識理論的理想形式的概念構(gòu)造,以及不訴諸道德意識歷史的中介而直接從理性的普遍結(jié)構(gòu)中推出一種普遍主義倫理學(xué)的嘗試,都是康德式的,并且是有問題的。當(dāng)然,我并不是說我們今天仍有可能返回從康德到黑格爾的道路。盡管黑格爾是第一個最清楚地表明康德的道德哲學(xué)是如何走入死胡同的人,在不忽視黑格爾的諸種批評的情況下,任何避免這些死胡同的努力,都得繞開黑格爾的體系。我用可錯論的解釋取代對普遍主義對話倫理學(xué)的共識論的解釋(這種解釋是康德的“目的王國”概念的回聲),我用一種多維的、弱的辯護(hù)要求取代一種單維的、強的辯護(hù)要求。一旦道德意識已經(jīng)成為普遍主義的,它就確實不需要期待一種調(diào)和狀態(tài)(不管如何從形式上描述這種狀態(tài)),也不需要依靠最終的哲學(xué)基礎(chǔ)的保障。我毋寧相信,只要普遍主義的倫理學(xué)堅持這兩個絕對的觀點,那么,相對于黑格爾的批評,它不但容易遭到批評,它還容易遭到懷疑論的批評。因此,當(dāng)我說對話倫理學(xué)與康德依然靠得太近時,我是根據(jù)以下的假設(shè)這樣說的:倫理學(xué)必須走出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虛假的非此即彼的處境,這就是說,道德和理性不會隨著最終一致或終極奠基的絕對主義一道沉浮。
當(dāng)我說對話倫理學(xué)迄今為止的形式不夠康德式時,我指的是它未能作出在康德那里已經(jīng)很清楚的區(qū)分。我尤其指的是道德問題與法律問題之間的區(qū)分。毫無疑問,康德是想把道德與法律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是至少從分析的角度說(在我看來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他把規(guī)范的合法性的問題與道德上正當(dāng)行動的問題區(qū)分了開來。我關(guān)心的并不是康德構(gòu)造法律與道德之間的聯(lián)系的細(xì)節(jié)(這方面當(dāng)然有很多問題),而是他通過表述道德原則,把道德上正當(dāng)行動的問題與規(guī)范的正義性問題區(qū)分開來的方式。在這方面,對話倫理學(xué)再沒達(dá)到康德在這方面已經(jīng)達(dá)到的區(qū)分程度,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它的共識論諸前提。因此可以說,對話倫理學(xué)靠康德太近以及它與康德相比缺乏上述區(qū)分,這兩者都是與真理共識論的可疑假設(shè)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對話倫理學(xué)的基本直覺——這是我想捍衛(wèi)的——也與它對康德的立場有關(guān)。我認(rèn)為,對康德倫理學(xué)的形式主義的——獨白的嚴(yán)格主義的批評,以及通過倫理學(xué)的一種對話的擴(kuò)展超越這種僵硬的形式主義的嘗試都完全是言之有據(jù)的。最根本的是,我與阿佩爾和哈貝馬斯一樣,抓住了從形式主義倫理學(xué)到對話倫理學(xué)的過渡和從意識哲學(xué)到語言哲學(xué)的過渡之間的聯(lián)系。的確,我相信,我們需要重新確定康德倫理學(xué)中那些可以作為一種按對話模式理解的倫理普遍主義之出發(fā)點的觀點。這是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為自己提出的任務(wù)。第二部分是對對話倫理學(xué)及其共識論前提的一個批評。在第三部分中,我希望表明,對話倫理學(xué)的基本直覺怎樣根據(jù)第一部分中提出的“準(zhǔn)康德式的”觀點得到重新表述。
在這個導(dǎo)論的最后,我還要就道德哲學(xué)中的懷疑主義問題發(fā)表一點看法。我相信,認(rèn)真對待它和不認(rèn)真對待它都是有正當(dāng)理由的。作為一種道德態(tài)度,它用不著認(rèn)真對待,但是作為一種質(zhì)疑理性主義的和基礎(chǔ)主義的認(rèn)知要求的方式,它應(yīng)當(dāng)?shù)玫秸J(rèn)真對待。我的意思是,我相信理性主義必須吸收懷疑主義并把它轉(zhuǎn)化為啟蒙過程的催化劑。一種受懷疑主義啟發(fā)的理性主義既不是理性主義的,也不是懷疑主義的,它也許可以說是通情達(dá)理的。因此我相信,延續(xù)啟蒙運動傳統(tǒng)和革命人道主義傳統(tǒng)的最佳前景就是與某些理性的理想告別。這并不意味著與理性本身告別;毋寧說它意味著與理性關(guān)于自身的一種虛假構(gòu)想告別。
本文第二部分對阿佩爾和哈貝馬斯的批評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對作者過去的觀點的自我批評,盡管我并沒有費心去表明何處是這樣。然而,讀者將很清楚,雖然我在具體的問題上批評阿佩爾和哈貝馬斯,我仍然對他們對于我自己的思想的一種決定性的和持久的影響心存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