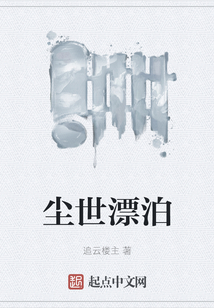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32章 少年子弟江湖老,長嘆空隨一陣風
- 第31章 聞噩耗拜山掃墓,居鄉下教字授文
- 第30章 內戰平學校獻公,俞瑨兒上山下鄉
- 第29章 啟遺物資辦教育,棄紅塵英雄出家
- 第28章 慶壽誕表親驚至,憶往昔軍戎歲月
- 第27章 聽光復歡天喜地,歸故鄉物是人非
第1章 社稷傾禍斷商路,積善家終有后繼
清朝末年,內憂外患,社稷將傾。雖有忠志之士想要力挽狂瀾,但歷史的車輪滾滾,是誰也擋不住的。這一年道光皇帝駕崩,咸豐皇帝繼承大統。看上去新的皇帝并沒有給人們帶來新的希望曙光,不久之后,洪秀全便造了反。或許這小小的反叛對比西方列強來說,咸豐帝并不上心,但戰亂一起,人們難免會漂泊天涯,四海為家。
或許有一個人的經歷更能道盡滄桑,因為他飽受漂泊之苦。如果您想聽,容我慢慢講。
話說江西九江,有一戶俞姓人家,世代為商,販賣茶葉。因為信譽良好,價格公道,茶葉生意做的風生水起,雖不是大富大貴之家,但家中的錢糧也是不少。
每年的清明時節,浙江杭州的龍井茶枝嫩葉美,正是摘采之時,老掌柜便會囑咐他的兒子俞恒看好家中生意,自己和商隊一齊出發去杭州。他們按照往例會從九江走旱路去杭州,從杭州的茶農們手中收購新茶,聘請炒茶師傅,經過制作,裝貨成箱,走水路將茶運回九江,這一年當然也不例外,老掌柜和商隊一齊去了杭州……
不久之后的一天傍晚,天色將暗未暗,路上行人已寥寥無幾了,俞恒在茶鋪清算賬目。管家行色匆匆地來到茶鋪,找到俞恒說:
“少爺,老爺回來了。”
俞恒一手拿著筆,一手打著算盤,依舊忙碌,嘴里回道:
“好,我算完這一筆帳就回。”
說罷便將手中的筆放下了,喝了口小伙計沏的茶,回頭對小伙計說:
“帳算完了,你收拾收拾,打烊罷。”
小伙計應聲道:“哎,少東家,慢走。”
俞恒起身往家走,管家更在后面說:
“少爺,老爺死了,剛剛把人運回了。”
說罷管家便抽咽起來,俞恒先是一愣,只覺得有一個雷在自己腦中嗡嗡的響起來,然后便趕緊往家的方向跑去。
俞恒的母親早在俞恒年幼時就身染重疾去世了,老掌柜卻從未有續弦的念想,獨自將俞恒撫養成人,教他生意之事,父子之情至深。
等到俞恒跑到家中,門口已掛起了白布,只見一口黑漆棺木停在庭院之中,他便撲倒在棺木旁,此時哪里還有聲音,哭都已經沒有了聲音。管家緊跟著也跑進來了,站在少爺身后,揮揮手,叫來兩個家中的小伙計,說道:
“開棺,讓少爺再見老爺一面。”
小伙計打開棺木便退到一旁。俞恒往棺中觀瞧,見父親的身上俱是刀痕,便不解地問:
“身上怎么都是……?”
管家在身后小聲回道:
“送老爺回來的人說老爺在去杭州的路上遇到了長毛賊。”
“這條商路,我們家少說也跑了二十年了,雖然遇到過強盜,但也是花點買路錢,怎么就……”俞恒對管家說道:“合棺罷,明日起大辦白事,高搭靈棚,請來高僧誦念經文。”
事出突然,但管家心中已有打算,他總是能有條不紊地辦起事來,這一點大家都是知道的。
翌日,訃告發出,各界親友前來吊唁自不用說,鐵佛寺的住持智通禪師帶領者寺中的十幾位僧侶來念誦經文,卻分文不取,只因鐵佛寺中所用之茶歷來是由俞家所獻。只可惜俞恒舞象之年便已失了雙親,也可惜這條茶商之路從此就沒人敢走了。俞家茶鋪的生意也因此漸漸暗淡下去,幸好老主顧們的暗暗支持,茶鋪雖然不怎么掙錢,但也不至于開不下去。
時光就像九江城外的江水般一直在流淌。一眨眼,殺死老掌柜的長毛賊成了太平軍,洪秀全成了太平天國的“天王”了,九江也在其領域之內。林啟榮奉命鎮守九江城,整頓城防,修繕城墻,新建炮臺,看上去固若金湯。人們或許應該短暫的高興一下,享受一下戰亂之中難得而又稍縱即逝的安寧。似乎俞恒清楚這一點,于是,他娶了親。娶的是城東頭楊家的小姐,名叫楊惠鳳。楊家小姐向來是溫柔賢惠,但是她的弟弟楊惠虎卻是一個十足的賭徒,一份家業揮霍殆盡。
好景不長,曾國藩領導湘軍攻打太平天國,一路勢如破竹,但林啟榮鎮守的九江城卻似鐵桶一般,久攻不下。雖然九江城的東門、南門的城墻被炸塌了,但林啟榮馬上拆除城中的房屋填充缺口。楊家的房子靠近城東墻,自然被拆了。惠鳳的雙親不忍眼睜睜地看著家中房子被拆,想要攔住軍士,就這樣白白的送了命。
不幸中的萬幸,惠鳳出嫁了,惠虎出門賭錢了,不然也勢必要成刀下之魂。等到惠虎回家之時,才發現房子被拆了,雙親被殺了。惠虎無處投奔,找到姐姐惠鳳,以不再賭錢為條件,隨姐姐留在了俞家。惠虎天天又是早出晚歸的賭錢,只是騙姐姐說是找了事由,要天天出去干活。
不久之后,曾國藩就滅了太平天國,但戰亂已經給九江城中的人們帶了巨大的傷害,許多人流離失所,人們腹中饑餓的所發出的聲音很快地占領了九江。俞家雖然生意暗淡下來了,但家中尚有銀錢,日子似乎沒有受到什么影響。
一天晚飯后,惠鳳對俞恒說:
“老爺,再過幾天就是九月十九了,此乃觀音菩薩悟道出家之日。今城內外戰亂已定,我有心去鐵佛寺降香,不知可往否?”
俞恒回道:“我與夫人同往。”說罷,便叫來管家,讓他準備一切應用之物,九月十九清早去鐵佛寺中降香。
待到降香之日,早有兩頂轎子在門外等候。俞恒、惠鳳紛紛上轎,管家和幾位轎夫步行就往寺中而去。到了廬山腳下,惠鳳喊停了轎,要步行上山。眾人不解,惠鳳言說:
“坐轎上山,對佛不敬,你們山下等候罷,管家帶上東西,我們跟著老爺走上去。”
俞恒本想坐轎上山,被惠鳳一言,也只好下了轎子,一齊走上山去。
業已深秋,漫山黃遍,叢林深處偶有鳥鳴,蕭瑟之感頓生心中。待到寺中,卻又另外一般,香煙彌漫籠罩,僧侶念誦經文,梵音不絕于耳,實在熱鬧。寺中迎客之僧見有香客,便欣然相迎,俞家三人跟著迎客之僧進了大雄寶殿,三人皆跪倒在大佛面前,口中默念保佑之言,扣頭三拜。起身之時,見寺中住持智通禪師立于身旁,慈眉善目地看著三人。三人施禮,智通禪師雙手合十道:
“阿彌陀佛,俞家三位施主,隨貧僧來禪房待茶。”
三人跟隨著智通來到禪房,剛剛坐下,便有一位小徒弟捧著茶盤而進,盤中四碗茶,一人一碗,小徒弟雙手遞上,便立于智通身旁。智通將手中佛珠往手腕處一推,拿起茶碗,將茶蓋一掀,說道:
“施主請。”
隨即,細飲一口,放下茶碗。俞家三位也各自品了一口。智通將茶碗一放,微笑著說道:
“多蒙俞家施主心善,多年來施舍敝寺茶葉,寺中所飲之茶,皆為俞家施舍的好茶,香味沁人,全寺無一不愛。”
俞恒回道:“家中無好物,惟有此爛葉枯枝,幸蒙眾高僧不棄,聊表寸心,以結善緣。”
“哪里,哪里,施主輕賤此茶了。”智通微微一笑道,隨即又飲了一口茶。
一番噓寒問暖之后,智通終于把話頭挑了出來:
“貧僧乃野寺山人,進來卻聽說九江城中之人飽受饑餒之苦,不知可有此事?”
俞恒嘆了一口氣道:
“有此事。今城內外戰亂已定,只是苦了眾百姓。流離之人滿街,言饑之語塞路。”
智通聽完閉上了眼,雙手合十道:
“阿彌陀佛,現在還是秋季,到了冬日,不知餓凍至死之骨有幾何啊。”
念佛之人心中都是向善的,惠鳳也不例外。這時候,她便暗暗地向俞恒說道:
“老爺家大業大,施舍一點錢米,幫助窮苦之人罷。”
俞恒心中自然是明白的,點了點頭對惠鳳說道:
“早有此心,但此事卻不知如何出力。”
智通此時又言道:
“佛家慈悲為懷,貧僧欲在此寺中搭上席棚,每月初一,施舍錢米,直至來年春暖,渡眾人身脫冷餓之苦,不知寺中還有多少銀錢?覺了,去問問你監寺師叔。”
智通身旁的小和尚,答應了一聲,就要出去,卻被俞恒叫住了:
“覺了小師傅,慢。”
覺了站住了,看了看他的師父智通,智通擺擺手叫他回來,于是他又站到智通身旁。
俞恒便接著說道:
“大師果然是得道高僧。不瞞大師,我也有心施舍,但家中瑣事纏身,未能力行,故錢米之事大師不必費心,每月月底我打發家人送來錢米,麻煩寺中眾高僧施予窮苦之人,只是每月一日,怕不足其所用,大師可添一日否?”
大師點了點頭道:
“都說善財難舍,可見施主是至善之人啊,每月初一、十五,本寺施舍粥米之事,全仰施主了。”
俞恒自是應承。
從此之后,鐵佛寺中每月初一、十五施粥送米,俞家每月月底送錢米上山,僧侶們出力,俞家出錢米,寺中主持特意在棚席之上寫“俞家施粥”,自從,九江城中饑苦之人皆有粥米可用。雖然俞家家中之財半數被其所用,但九江城中之人無論窮富,提起俞家,都不覺地豎起大拇指,提到俞恒,都稱其善人。俞家茶鋪的生意也因此漸漸好轉起來。
轉眼到了冬月月底,臘月將至。俞家管家不知為何,前幾日害了風寒,雖然病好的差不多了,但俞恒卻不忍心讓他帶病奔走。因此這次上鐵佛寺送錢米,自己帶著幾個伙計去了。一路行去,至寺中,智通迎道:
“施主親自來了,有失遠迎。”
俞恒回道:
“大師客氣了,下月所用錢米,我給您送來了。下個月就是臘月了,佳節將至,我臘月十五清晨送來銀錢,多予銀錢,權作正月之用,共度佳節,正月就不必施粥了,不知大師意下如何?”
智通點了點頭說道: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施主想的周到,全依施主。”
智通本想讓俞恒寺中歇息一會再下山,奈何他家中事務繁忙,也不強留。俞恒便就此下山回到家中。
待到臘月十四夜,俞恒便叫管家清算好明日施舍的銀錢,裝在車上,待明日好親自將銀錢送上山。
耳聽得九江城中譙樓之上鼓響五更,俞恒與管家帶著伙計們就往鐵佛寺中而行。冬日的天總是亮的比較晚,走在前面的伙計手中還提著兩盞燈籠。俞恒看了看天空,天上毫無星亮,云中隱著月亮,一陣寒風呼嘯而過,俞恒身上不禁一陣顫抖,攏了攏身上的披風,實指望身上的披風能擋住一點寒氣,卻也是徒勞。眾人都不言語,仿佛開口就會有寒氣進入身體中一般,只是腳下快了起來。一路馬不停蹄的來到寺中,將銀錢卸下車來,碼的整整齊齊,吩咐伙計們等會施粥之時,分予窮苦之人,供其佳節之用。
不多時便是施粥之時,來人雖多,卻也不亂。俞恒和伙計們一起分放銀錢,一人一份,有條不紊。
不知為何,人群中似有爭斗之聲。俞恒往人群中望去,見一個年輕人與家中的三位伙計扭打在一塊,年輕人雖然被按在地上,這三人卻也似乎按不住他,仿佛一較勁就能站起來。
俞恒過去分開眾人,問自己家伙計:
“何事如此?”
伙計回道:
“每人都領一份銀錢,他卻要領兩份銀錢,我們不給,他就上來搶,我們就想按住他,拿回銀錢,卻按他不住。”
俞恒看了看這位年輕人,施了禮道:
“看你年青力長,不似掙不到銀錢之人,為何要領雙份銀錢?其中必有原因,你能否說我聽聽?”
這年輕人整了整身上的衣服,也還了一禮說道:
“小人叫趙武,本來是在碼頭上當個勞力,為人家卸貨為生,雖然日子不富裕,但是能勉勉強強養活家中老母。可近來老母害了病了,大夫看了說要用好藥,可是家里銀錢不多,抓上兩次就用的所剩無幾了,我本來想接著去碼頭卸貨,可是家中就我們母子相依為命,她的病不好,我不敢出去干活。聽聞老爺在此施舍,所以我就上山來領錢米,是我多領了一份,可我也是沒有辦法了。望老爺行行方便。”
俞恒點了點頭說道:
“倒是孝子。不應該為難你,這樣罷。管家,給他五份銀錢。”
管家又拿了三份銀錢遞到趙武手中,趙武卻“撲通”地跪下了。俞恒上去攙了起來接著說道:
“病來如山倒,快拿回家,多買點補品補補。”
趙武點了點頭,又跪下磕了個頭,這才匆匆下山。俞恒見人人也都領了銀錢,就讓管家清點了一下銀錢,將錢裝上車,向智通告了辭,一行人也往家中走去。或許俞恒并沒有將趙武的事情記得很久,但是趙武卻記到了骨子里,到后來為此還少殺一個人……
春暖花開,俞家終于不再施舍粥米了,大家的日子也漸漸好了起來,俞家的家財卻用了十之八九。
樹木的年輪在一圈一圈的增加,鬢邊的黑發也一根一根的在變白,可是俞恒卻始終沒有孩子。惠鳳讓俞恒再娶一房,俞恒卻不同意,只是年年朝山拜廟,歲歲補路修橋,祈求老天爺早降麟兒。
俞恒過了四十大壽,惠鳳也終于懷孕了,老來得子終歸是一件好事。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俞恒請了三位有名的穩婆來接生,應用之物備好,但那個年代的生產總是困難的,惠鳳在床上疼的死去活來,俞恒在門外焦急走來走去。孩子的啼哭響起,惠鳳卻吃力的昏睡過去了。穩婆們急忙向俞恒道喜:
“恭喜老爺,是位少爺,母子平安。”
俞恒竟然一時恍惚了,只是口中暗暗地說道:
“我有兒子了,我有兒子了……”
穩婆們領了賞各自開心,結伴歸去了。俞恒把孩子抱了過來,癡癡地看著在襁褓中啼哭的兒子,心中難以言說的歡喜。管家在旁邊對著俞恒說道:
“老爺,起個名字吧。”
俞恒點點頭,又看了看孩子,說道:
“叫他望卿怎么樣?俞望卿,俞望卿。”
大家都附和說好,只有惠虎在一旁看了看說道:
“你們就知道望卿,望卿,就沒人望望我姐嗎?”
俞恒笑了笑說道:
“你姐睡著了,有人伺候著,不要擔心。”
一眨眼,望卿便滿月了,俞家大擺筵席,來人不少,鐵佛寺中智通和他的徒弟覺了也來了。大宴已畢,大家都要看看望卿,惠鳳抱了出來,都道恭喜,恭喜之后,就各自散去了,智通和覺了卻沒走。
智通施了一禮道:
“施主,老衲年事已高,今天色已晚,山路難行,恐要叨擾一宿。”
俞恒自然是歡迎的,說道:
“大師稍坐,我叫人打掃潔凈房間。”
智通看了看惠鳳懷里的望卿,笑了笑。惠鳳卻問智通:
“大師,你看此子命運如何。”
智通回道:
“生此亂世,難免如浮萍漂泊于江湖。”
說罷,又看了看望卿,又笑了笑。或許智通說對了,生逢亂世,怎能安生?但是他為什么總是笑,亂世之中,笑從何來?或許,他看到的不僅僅是惠鳳懷中的望卿。
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智通參禪悟道真的是太久了,久到大概已經忘記了時間。時間可真是公平且無情,年小的出生了,年長的便老了,昔日的貧僧現在已經是老衲了。或許智通也是這么想的,所以他在年老之時,來看一看新生的孩子,他想看一看時間到底是怎么流逝的,我想他應該看到了,但是看到了又能怎么樣呢?時間,它總歸是在流逝的。時間,他總歸是參看不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