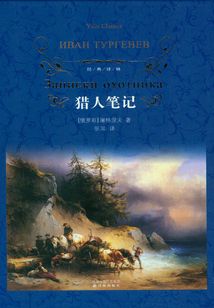
獵人筆記(經典譯林)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譯序(1)
伊·謝·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是十九世紀俄國杰出作家。他一生四十余年的筆耕生涯中,創(chuàng)作了被譽為“藝術編年史”的六部長篇小說,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說、特寫、戲劇、抒情詩、敘事詩、散文詩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并撰寫了相當數(shù)量的文學評論、回憶錄、文學書簡等等,他的創(chuàng)作極大地豐富了俄國文學的寶庫,為俄國文學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的作品也深受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如今已成了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
《獵人筆記》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部現(xiàn)實主義力作,在他的整個文學創(chuàng)作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獵人筆記》是一部形式獨特的特寫集。其第一篇特寫《霍里和卡利內奇》最初發(fā)表于俄國《現(xiàn)代人》雜志一八四七年第一期。后面的絕大部分篇章也都是陸續(xù)發(fā)表于同一雜志。直至一八五二年,作者將先后刊出的二十一篇特寫匯編在一起,外加一篇未曾發(fā)表的新作《兩地主》,以《獵人筆記》為書名,出版了單行本。至一八八〇年,作者又加進了后來創(chuàng)作的三篇:《切爾托普哈諾夫的末路》(一八七二)、《車轱轆響》(一八七四)、《枯萎了的女人》(一八七四),共計二十五篇,這便成了作者生前最后的定本。今天我們所據以譯出的就是這樣的定本。
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fā)展,俄國農村中農奴制的存在已成了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嚴重障礙,因此,農奴制的改革問題便被提上了日程,成了當時社會最關注的迫切問題。
屠格涅夫出身于奧廖爾省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母親就是一位殘暴的農奴主。他自幼目睹地主階級的兇殘專橫,早就產生了對農民悲慘處境的深切同情。上大學后,又受到了進步思想的熏陶,下定決心要與農奴制度作不倦的斗爭。一八四三年他結識了著名批評家別林斯基,在別林斯基的思想影響下,他更堅定了與農奴制作斗爭的決心。
《獵人筆記》就是他以反農奴制為中心思想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在這里他以敏銳的觀察力提供了自己的新題材,發(fā)出了自己的吶喊。所以《獵人筆記》一出版,便引起舉世矚目,其影響所至遠遠超過了文藝界而擴及于整個社會。不同階級的人們對它作出了不同的反應。它的思想內容立刻激起沙皇政府及統(tǒng)治階級的驚恐和憤怒。當時沙皇政府中那位頗具政治嗅覺的教育大臣很快便嗅出了書中的反農奴制氣息,他向尼古拉一世報告說:此書的大部分篇章都“帶有侮辱地主的絕對傾向”,說書中的地主“不是被表現(xiàn)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極不體面而有損于他們名譽的樣子。”隨后不久,屠格涅夫便受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被遣返故里監(jiān)管一年。而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此書則受到普遍的歡迎。作家有一次在一個小車站上遇到兩位不相識的青年農民,當他們得知他就是《獵人筆記》的作者時,便脫帽向他致敬。其中一位還以“俄羅斯大眾的名義”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謝”。進步的文藝界人士更給予此書以很高的評價。尤其是別林斯基,當此書的第一篇特寫《霍里和卡利內奇》剛發(fā)表時,便立即給了作者以極大的鼓勵。別林斯基寫信對作家說:你大概還不清楚自己的作品具有何等的價值,你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創(chuàng)作形式,你走上了出色的道路,你的前程遠大。著名作家赫爾岑也稱贊此書是一部“反農奴制的控訴書”。
這部作品反農奴制的思想傾向明顯地表現(xiàn)在對作為農奴制社會基礎的地主階級的揭露和批判上,表現(xiàn)在對農民命運的深切同情上,表現(xiàn)在對農民的才能和精神世界的熱情贊美上。
在揭露和批判地主階級方面,俄國“自然派”文學奠基者、杰出作家果戈理已率先作出了出色的貢獻,他在《死魂靈》中已成功地刻畫了從瑪尼洛夫到普柳什金等系列的典型的地主形象。屠格涅夫繼承并發(fā)展了果戈理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在《獵人筆記》中以不同于前者的風格,向讀者展示了一系列新舊地主的畫像。
沙皇政府中那位教育大臣所說的這部作品把地主不是表現(xiàn)得“滑稽可笑”,就是被弄得“極不體面”。從表面粗粗看來,所寫的似乎就是如此而已。當你細細地品味書中的內容時,你就可發(fā)現(xiàn),書中所寫的地主不僅僅是“滑稽可笑”,他們的行為也遠不止是“極不體面”。在農奴制的舊俄國,地主與農民的關系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系。在這樣的關系中,地主必然會表現(xiàn)出諸如殘暴、狠毒、貪婪以及虛偽、愚蠢、空虛、無恥等等卑劣的性格和行為。這些正是作家要揭露和批判的對象。不過,作家在這本書中一般沒有直接描寫地主們兇殘猙獰的面孔,沒有直接描寫他們殘酷迫害農民的張牙舞爪的舉動,沒有直接描寫他們最丑惡的表現(xiàn)。在不得不寫的地方,也顯得特別的小心,主要是通過間接的暗示和啟發(fā),讓讀者通過聯(lián)想去認識他們卑劣的行為和品性。這固然是為了使作品易于通過書刊審查,更主要的是這位作家對自己的作品持有特殊的審美要求。
地主佩諾奇金是書中刻畫得最出色的典型形象。此人受過“良好”教育,頗有“文明”風度。他儀表堂堂,衣著時髦、舉止文雅,“為人正派”、“通情達理”。他家里收拾得既干凈又舒適,他又飲食講究,待客熱情。但即使這樣,客人還是不樂意登門,原因是他家里總是彌漫著可怕的氣氛,令人窒息。他對奴仆雖然說話和氣,貌似仁慈,但實際上非常冷酷無情,奴仆們偶有伺候不周之處(如侍仆菲多爾忘了把他的酒燙熱),便會受到嚴厲懲罰。即便在這種場合,這位老爺仍然顯得文質彬彬,既沒有表現(xiàn)出怒氣沖沖,也沒有厲聲呵斥,更不用親自動手打人,他只是坦然地、低聲地吩咐旁邊的奴仆“去處理一下”就行了。
佩諾奇金還善于利用總管、村長之類爪牙去經管各處的田莊。索夫龍就是他手下一名很得寵的總管,佩諾奇金得意地夸贊這位總管有“治國安邦”之才。索夫龍主管下的什比洛夫村就是老爺?shù)奶锴f的樣板。當老爺光臨該村時,村長(總管的兒子)早就在村口迎候。老爺?shù)能囎舆M入村子時,幾個坐著大車、一面唱著歌從打谷場上歸來的莊稼人一見到老爺前來,馬上就閉口不唱了,都摘下了帽子,低下了頭。老爺?shù)牡絹砹⒖淌谷濉罢痼@”了。不僅嚇得娃娃哭著朝家里跑,連雞也嚇得直往大門底下鉆。要說索夫龍的“管理”才能,確實有兩下子:在他的治下,莊稼人都乖乖地按期向東家繳佃租。凡繳不起租的,索夫龍可給代繳,但這莊稼人就得給索夫龍當牛作馬,凡欠了一些租的,就得給索夫龍當長工。凡是頂撞過索夫龍的(如安季普),就會被他折騰得家破人亡:幾個兒子全被送去當兵,最后連母牛也被牽走,婆娘還挨一頓毒打。若還敢向東家告狀(安季普真的告了狀),就得徹底完蛋。所以在莊稼人眼里,索夫龍不是人,而是“一條惡狗”。作家無疑是想通過這些情節(jié)向社會啟示:一個“文明”、“有教養(yǎng)的”地主的統(tǒng)治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地主的統(tǒng)治了。
《兩地主》也是一篇諷刺性很強的特寫,講的是兩個性格各異的地主。一個姓赫瓦倫斯基,是個退伍軍官,好像沒有打過仗。此人“心地善良”,但有一些“奇怪的見解和習慣”。他瞧不起無錢無勢的貴族,對他們“決不平等相待”,至于對那些地位卑微的人,更是“連看也不看”,要是需要同這些人說句話,他的聲音便變得“像鵪鶉叫”。他還沒有娶妻,很好色,在路上一看見漂亮的女人,便窮追不舍。他喜歡打牌,但只愿同身份低的人打,這樣他可以隨意呵斥。等到同省長或其他高官打牌時,他那態(tài)度便發(fā)生驚人的變化:滿臉堆笑,整個人變得像蜜一樣甜。他還喜歡拋頭露面,在各種莊嚴的公共場合上表現(xiàn)不凡。他很吝嗇,所以竟不愿意接受貴族長這樣的榮譽頭銜,他大概怕開銷大,不合算。
另一個地主是斯捷古諾夫。他自稱是“老實人”,辦事“照老規(guī)矩”,生活中的一切都保持古風。可有時也會趕新潮:為了顯示自己不落后于時代,十年前便從莫斯科買來一臺打谷機,可是一直把它鎖在棚子里不用,心里便很滿足。他待客十分熱情,顯得是個“好心腸的人”,然而對附近的莊稼人卻很不客氣:例如近鄰的農家有幾只雞跑進了他的花園,他便大喊大叫,不僅把雞沒收,還要抓住那個進來趕雞回去的小姑娘鞭打一頓。他對奴仆也很殘酷無情:他吩咐人鞭撻奴仆,自己坐在涼臺上一邊喝茶,一邊隨著鞭打聲的節(jié)奏喊:“吧噠!吧噠!吧噠!”他對那些不夠聽話的莊稼人就更狠心了:“把他們送去當兵,把他們打散,這里一個,那里一個”,即使這樣,他仍感到不解氣,因為這樣“還是不能讓他們絕根”。他還總結出一套理論:“老爺總歸是老爺,莊稼人總歸是莊稼人”;“如果老子是賊,兒子一定是賊”。
在其他一些篇章中還描寫了各種類型的地主,如蠻橫地搶占他人土地的地主(“獵人”的祖父);精神空虛、變著法子折磨莊稼人和家仆的科莫夫;穿著像馬車夫,表面上對農民客客氣氣,可又使他們心里害怕的柳菲沃諾夫;設立莊園“辦事處”,通過一批爪牙進行管理的女地主洛斯尼亞科娃等等。通過對這些地主乖僻行為和習性的描寫,自然使讀者聯(lián)想到,在他們主宰下的黑暗王國里,廣大的農民會有什么樣的命運。
揭示農民的悲慘命運,也是《獵人筆記》的基本主題之一。在屠格涅夫之前,利戈羅維奇的《鄉(xiāng)村》和《苦命人安東》對此已作過一定程度的反映。在《獵人筆記》中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因農奴制的長期壓迫而變得極其可憐委瑣的舊式俄羅斯農民。例如《莓泉》中那個斯焦布什卡,他原先曾是地主的家仆,后來被主人完全拋棄了,結果落到“不被當人看”的地步,在人口調查簿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連一份“口糧”也沒有。他為了糊口,整天“像螞蟻似的”到處覓食充饑。《利戈夫村》中綽號“小樹枝”(即蘇喬克)的庫濟馬,也是個家仆,在眾多的地主手里被轉來轉去,被主人當一件東西似的任意擺布,先后充當過幾個地主家的廚子、車夫、鞋匠、戲子、漁夫等角色,他被扭曲成一個毫無個性、膽小如鼠的可憐蟲,以至于在那次涉水過河面臨滅頂之災時,竟不敢伸出手去抓住走在前面的“老爺”的衣襟。還有《兩地主》中那個管餐室的仆役瓦夏,受了鞭打之后仍認為主子是個好人,是自己罪有應得,說主子是“不會無緣無故打人的”。書中的這類描寫,顯然是對農奴制的嚴厲控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