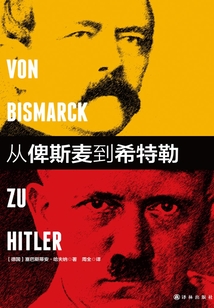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3評論第1章 導(dǎo)言
假設(shè)我們通過望遠(yuǎn)鏡來回顧德意志國的歷史,馬上可以發(fā)現(xiàn)三個(gè)奇特之處。
首先是這個(gè)國家的短暫壽命。它只在前后共計(jì)七十四年的時(shí)間內(nèi),成為一個(gè)具有行為能力的整體:從1871年到1945年。即便有人寬宏大量,將其前身的“北德意志邦聯(lián)”[1]一并列入,同時(shí)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四大戰(zhàn)勝國還愿意將德國視為一個(gè)整體來管轄的短暫時(shí)期,所得出的總和也只有八十或八十一年(1867年至1948年),僅僅相當(dāng)于一個(gè)人一生的歲數(shù)。就一個(gè)國家存在的期限而言,這個(gè)時(shí)間未免短得可怕。我?guī)缀醪粫缘眠€有任何別的國家會(huì)如此國祚短促。
其次引人注目的是,德意志國在此非常短暫的生命期限內(nèi),至少有兩度(1918年和1933年)——但實(shí)際上是三次(還包括更早的1890年)——徹底更改了自己的內(nèi)在性格與外交政策路線。這八十年的時(shí)間內(nèi)于是出現(xiàn)過四個(gè)涇渭分明的階段,而且我們甚至可以如此表示:德國在其中的每一個(gè)階段都變成了另外一個(gè)德國。
第三個(gè)奇特之處則在于,這段如此短暫的歷史是以三場戰(zhàn)爭作為序幕,然后以兩場駭人聽聞的世界大戰(zhàn)收尾,而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或多或少脫胎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由此看來,德意志國的歷史簡直就像是一部戰(zhàn)爭史,而且難免會(huì)有人設(shè)法把德意志國稱作“戰(zhàn)爭之國”。
人們自然會(huì)想問個(gè)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德國人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加好戰(zhàn)嗎?我倒并不這么認(rèn)為。若將德國人的歷史看成一個(gè)整體,亦即著眼于一千年出頭的時(shí)光,便可發(fā)現(xiàn)德國人在俾斯麥的時(shí)代以前很少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而且?guī)缀鯖]有發(fā)動(dòng)過侵略戰(zhàn)爭。德國自從近代初期以來就位于歐洲的中央,成為一個(gè)巨大而呈現(xiàn)出多元面貌的緩沖地帶,不但時(shí)而有外力介入干預(yù),德境內(nèi)部也爆發(fā)過大規(guī)模的軍事沖突:諸如“施馬爾卡爾登戰(zhàn)爭”“三十年戰(zhàn)爭”“七年戰(zhàn)爭”[2]等等。但是這些內(nèi)部紛擾并未演變成對外侵略的行動(dòng),不像德意志國在20世紀(jì)的時(shí)候有兩次那么做了,并且隨之走上末路。
德意志國究竟為何覆亡?它為什么會(huì)偏離其創(chuàng)建者俾斯麥的初衷,變成了一個(gè)向外擴(kuò)張、侵略成性的國家?對此出現(xiàn)過各種不同的理論,但我認(rèn)為它們都不怎么具有說服力。
其中有一種論點(diǎn)把全部責(zé)任都推給普魯士——德意志國畢竟是通過普魯士才建立起來的。德意志國完全被看成是某種形式的“大普魯士國”(至少其建國者如此認(rèn)為),普魯士在德境享有主導(dǎo)地位。在此過程中同時(shí)出現(xiàn)了德國的第一次分裂:奧地利被排除在德國之外。這么說來,一切都該歸咎于普魯士了?假如當(dāng)初法蘭克福“保羅教堂”內(nèi)召開的國民議會(huì),在1848年革命時(shí)就能夠?qū)⒌聡⒃诿裰鞯幕A(chǔ)上,一切豈不可以發(fā)展得比較理想?
但說來奇怪的是,情況并非如此。即便有許多人這么認(rèn)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huì)的外交政策可一點(diǎn)也不和平。“保羅教堂”事實(shí)上甚至將許多場戰(zhàn)爭一并納入考慮——“左派”的國民議會(huì)成員巴不得跟俄國大打一仗來解放波蘭;中間派及“右派”的議員則為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3]的緣故,不惜與丹麥開戰(zhàn),而且普魯士果真在1848年把那場“代理戰(zhàn)爭”進(jìn)行了好一陣子,然后才半途收兵。除此之外,“保羅教堂”內(nèi)許多身為自由民主派人士的政界顯要還大咧咧地公開宣示:我們的當(dāng)務(wù)之急,就是要為德國爭取權(quán)力。“德意志民族已對原則與教條、字面上的‘偉大’和理論上的‘存在’深感厭煩。它所要求的,就是權(quán)力、權(quán)力、權(quán)力!能夠給它權(quán)力的人,就可以從它那邊得到榮耀,而且所能得到的榮耀將超出其人自己的想象。”以上是尤利烏斯·福祿貝爾的用語;此人今日早已遭到遺忘,然而當(dāng)時(shí)他是“保羅教堂”大德意志派政治人物中的翹楚。
在整個(gè)“保羅教堂”里面都有非常強(qiáng)烈的愿望,就是要擺脫德國人數(shù)百年來在歐洲中央所處的被動(dòng)狀態(tài)。他們希望能夠仿效歐洲外圍列強(qiáng)已經(jīng)行之有年的做法,也來推動(dòng)權(quán)力政治與擴(kuò)張政策。此類愿望在俾斯麥身上卻淡薄許多,而且他在1871年后不斷強(qiáng)調(diào),德意志國是一個(gè)已經(jīng)飽足的國家。但比較正確的講法其實(shí)是:普魯士在這個(gè)國家的內(nèi)部已經(jīng)飽足,而且過于飽足。或許普魯士向南德的進(jìn)展,甚至已略微超出自身勢力范圍的天然界限。不過,一直要等到俾斯麥下臺(tái)以后,才可發(fā)現(xiàn)德國其實(shí)完全未曾饜足——而且隨著普魯士的色彩日益減少,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成分不斷增多,那個(gè)現(xiàn)象也就愈益顯著。因此我們無法用普魯士的罪過來解釋德意志國的罪過(假如我們硬要使用“罪過”一詞的話)。反之:當(dāng)普魯士依然在德意志國境內(nèi)享有支配權(quán)的時(shí)候,它實(shí)際上扮演了剎車而非發(fā)動(dòng)機(jī)的角色。
此外還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被拿來解釋德意志國走上擴(kuò)張與覆亡的理由。例如有一派理論將工業(yè)化視為主要原因,因?yàn)樗俪傻乱庵緡跇O短時(shí)間內(nèi)躍升為歐陸首屈一指的經(jīng)濟(jì)強(qiáng)權(quán):這種快速工業(yè)化釋放出強(qiáng)大的社會(huì)動(dòng)能,最后爆炸開來。
這種論點(diǎn)可以用一個(gè)事實(shí)來加以反駁:工業(yè)化并非德國特有的發(fā)展。工業(yè)革命在19世紀(jì)的時(shí)候分成幾個(gè)階段逐步傳遍了歐洲大陸。它傳到法國的時(shí)間稍早于德國,以及荷蘭和比利時(shí)等較小型的西歐強(qiáng)國。奧地利開始工業(yè)化的時(shí)候又比德國晚一點(diǎn),而俄國開始的時(shí)間更晚。那是一個(gè)全歐洲性的發(fā)展過程。德國固然將工業(yè)化進(jìn)行得特別徹底和特別成功,但整體而言仍大致與歐洲其余各國同步邁進(jìn)。假如德意志國的駭人動(dòng)能與擴(kuò)張主義是工業(yè)化所導(dǎo)致的結(jié)果,那么自然而然就會(huì)衍生出另外一個(gè)問題:為何偏偏只有德國如此?莫非一個(gè)目前正走紅的史學(xué)流派在此發(fā)揮了作用,有意以言過其實(shí)的方式將經(jīng)濟(jì)與政治緊密地結(jié)合到一起?
其他若干解釋模式則讓人注意到,它們涉及了特定政治立場的意識(shí)形態(tài),而且實(shí)際上是被刻意構(gòu)思出來的,以便為相關(guān)政治立場做出證明。比方說吧,如果有誰的看法與列寧一致,也認(rèn)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的話,那么免不了就會(huì)怪罪于資本主義,認(rèn)為是它害得德意志國走上帝國主義,并且為此而土崩瓦解。
或許因?yàn)槲也皇邱R克思主義者的緣故,那種論點(diǎn)向來無法令我折服。但即便試著設(shè)身處地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思考,我也無法不注意到,有許多奉行資本主義的國家從未走上帝國主義之路——例如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瑞士。那些國家為何沒有走向帝國主義呢?該問題導(dǎo)引出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解釋模式,而且我認(rèn)為這種解釋更加合情合理。
瑞士是一個(gè)小國,而小國與大國在外交上的生存法則迥然不同。小國必須選邊站或者維持中立,向來無法試圖通過自己的強(qiáng)權(quán)政治來改善命運(yùn)。各大強(qiáng)國卻很容易就會(huì)出此下策。它們只要在任何地點(diǎn)發(fā)現(xiàn)了空隙,便傾向于朝著那里擴(kuò)張過去,借以鞏固和擴(kuò)大自己的權(quán)力,而權(quán)力正是其賴以立國的基礎(chǔ)。德意志國是一個(gè)強(qiáng)權(quán),這是它有異于德境昔日國家形態(tài)的地方,也是其真正的新奇之處。然而德意志國找不到什么有機(jī)可乘的空隙,難以趁虛而入進(jìn)行擴(kuò)張。
一位青壯派的美國歷史學(xué)家,戴維·卡里歐,曾經(jīng)表示:“德意志國誕生于包圍之中。”這么講就正確多了,因?yàn)榇驈囊婚_始就有許多強(qiáng)權(quán)環(huán)伺在德意志國的周圍。德意志國在西方面對法國和英國,在南方和東南方與奧匈帝國接壤(當(dāng)時(shí)奧地利仍為列強(qiáng)之一),在東方則毗鄰巨大的俄羅斯帝國。
德意志國的地理位置可謂相當(dāng)不利。它缺乏可供開拓的自由空間,既無法像英國、法國,甚或比利時(shí)、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那般經(jīng)由海路進(jìn)行擴(kuò)張,也無法和俄國一樣?xùn)|向深入亞洲腹地。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德意志國已然成為強(qiáng)權(quán),于是也具備了強(qiáng)權(quán)的本能,打算讓自己變得更大。這種本能可說是一開始就被放入了它的“大國搖籃”。
此外,還存在著第二項(xiàng)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國處于不大不小的尷尬地位。早在建國戰(zhàn)爭時(shí)期就已經(jīng)顯示出來,它在一對一的時(shí)候或許強(qiáng)過任何單獨(dú)的歐洲大國。但它當(dāng)然敵不過列強(qiáng)的同盟,更遑論是由圍繞在外的全體強(qiáng)權(quán)一起組成的同盟。正因?yàn)檫@個(gè)緣故,德意志國始終對此類的同盟心生畏懼。列強(qiáng)當(dāng)中的法國、奧地利、意大利甚至俄國卻都感覺自己不如德意志國強(qiáng)大,于是傾向于爭取與他國締結(jié)同盟。德意志國又因?yàn)樗鼈兊拇朔N傾向,不斷設(shè)法阻止形成這樣的同盟,必要時(shí)更不惜訴諸武力,通過戰(zhàn)爭來加以破除。我們可別忘了:對當(dāng)時(shí)所有的強(qiáng)權(quán)來說,戰(zhàn)爭仍然是“最后的理性”,亦即最終與最嚴(yán)峻的政治手段。這種情況所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德國人在違背帝國創(chuàng)建者原意的情況下(我在此重復(fù)這一點(diǎn),并且將在后面更詳細(xì)地加以闡述),往往會(huì)認(rèn)為建立德意志國的工作仍不完全——它非但不是民族歷史的極致,反而是一個(gè)跳板,通往從未明確定義出來的擴(kuò)張行動(dòng)。
人們?yōu)楹螌?871年在凡爾賽宮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稱作“德意志國”(Deutsches Reich),而不直截了當(dāng)?shù)胤Q之為“德國”(Deutschland)?主要的理由在于:它從一開始就大于——但同時(shí)也小于——“德國”這個(gè)民族國家。“小于”,那是因?yàn)樗鼘⒃S多德國人排除在外的緣故:它是“小德意志”國。它只在普魯士力有所逮的范圍內(nèi)被建立成一個(gè)民族國家,而且必須與普魯士的霸主地位協(xié)調(diào)一致。因此它稱得上是“普魯士的德意志國”。
但是“德意志國”這個(gè)名目不僅涵蓋了此一“較小”的層面,同時(shí)也隱喻著“較大”的一面:此即中世紀(jì)“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羅馬帝國”在歐洲跨越民族界限的普世要求。
“德意志國”既可以是“普魯士在最大范圍內(nèi)所能支配的德國”,或者也可以是“德國在最大范圍內(nèi)所能支配的歐洲或世界”。前者是俾斯麥的見解;后者則是希特勒的詮釋。從俾斯麥通往希特勒之路不僅是德意志國的歷史,同時(shí)亦為德意志國敗亡的歷史。
這部歷史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于,德意志國看起來簡直是從一開始就把自己推向毀滅。其權(quán)力擴(kuò)張的規(guī)模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捉摸,以致德意志國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一個(gè)由敵人所構(gòu)成的世界,最后被那個(gè)敵對的世界擊破,并且在敵國之間遭到瓜分。隨著德意志國的分裂,那些敵國卻仿佛受到魔棒點(diǎn)擊一般,突然都不再是敵人。自1949年起接替俾斯麥帝國的兩個(gè)德意志國家——“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打從一開始就分別在西方和東方?jīng)]有了敵國。時(shí)至今日我們所生活的時(shí)代,東方對“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以及西方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繼續(xù)存在,似乎也都逐漸有辦法以正面的態(tài)度來看待。兩個(gè)德意志國家已經(jīng)對峙了幾近四十年,而且此種局勢還看不見有結(jié)束的一日。這正好讓我們有辦法以從前不可能的方式,仿佛從遠(yuǎn)方通過望遠(yuǎn)鏡一般地來回顧“德意志國”的時(sh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