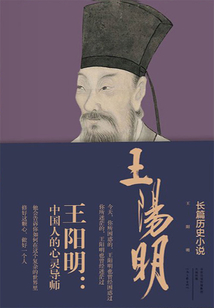
王陽明(全集)
最新章節
書友吧 30評論第1章 序幕:余姚風水 詩書傳家
在中國智慧的發展史上,大明王朝的成化八年(1472),農歷壬辰年,龍年,因為一個后來被稱為王陽明的嬰兒出生時的一聲啼哭,一下子多了些哲學意義。
天地在壬辰,王家的二兒媳鄭氏在妊娠,已經足月,馬上就要生產了。
王家老先生叫王倫,三個兒子,大兒子王榮,二兒子王華,小兒子王袞,家住浙江余姚縣城。
現在,農歷九月三十的傍晚,龍泉山山腳北邊的王家小院,女人們在后宅,來往穿梭,手忙腳亂,有端盆的,有提水的,激動著,緊張著,她們準備迎接呱呱墜地的新生命;男人們在庭院,高凳端坐,全身放松,有布道的,有聽講的,靜著心,他們在延續著一個舊傳統。
懷孕生孩子是女人的事。至少今晚上王家小院里的男人們是這樣認為的。生孩子是火上房的急事,萬一攤上個倒生、難產什么的,男人們總不能不搭把手吧?這幾個不知道輕重緩急的老爺兒們在干什么?
今晚是余姚“舜象讀書會”的例行活動,每月十六和三十(或者二十九),準時會讀一次,按輪轉排序,今日正好輪到在讀書會成員王華家舉辦。核心成員有陸恒、黃珣、王華、謝遷等。今晚特邀嘉賓有王倫、舉人諸讓,諸讓是黃珣的朋友,王袞屬列席人員,又兼添水倒茶的身份。地點選在王家袖珍型修竹園內一座四面以竹為墻、三面開窗的小軒內。
竹軒北面竹墻靠上方位置,掛著一塊木匾,上書兩個王右軍行書體墨色大字“靜學(靜學)”,木匾下方斜掛著一把帶鞘長劍,東向的劍柄上垂下一束墨綠色的流蘇。王倫頭戴儒士巾,身穿玄色道袍,面南背北端坐,淡定的目光暫時灑在胸前古琴的琴弦上,他在靜坐養神;座下許多人是生員打扮,頭戴儒巾,身著一襲圓領青衣;諸讓有舉人功名,頭戴遮陽帽,以帽子區別于幾位秀才。會員中陸恒年齡最長,是會長,在左邊首位坐,挨肩是黃珣;諸讓是客人,與陸恒坐對面,然后依次是謝遷、王華與王袞。
會長陸恒起立發言。陸恒已過而立之年,個子不高,在余姚城東縣衙北街辦有“拙庵龍門學館”。
陸恒說:“今天例會,我們請到了竹軒翁。”被稱作“竹軒翁”的王倫,聽到自己新取的號被稱呼到,想到這號的內涵——像竹子一樣的氣節,心中的笑意不經意間飄到純凈的臉上,于是他長而不削的臉上,在泰然的靜氣中,活潑著一絲絲的笑意。他扭臉對著諸舉人,睜開細長的眼睛,微微頷首,接著掃了一眼在座的晚輩,清和中透著嚴肅,高高隆起的眉骨,凝聚著一股清貴之氣。
陸恒接著說:“我們還請到了諸讓諸孝廉,養和先生。”
孝廉是舉人的雅稱,秀才是府學和縣學學生的雅稱。
諸讓國字臉上,一臉英氣,座中他功名最高,別人都敬他三分,他也不免會流露出些矜持。聽到點名,諸讓馬上起身,開言道:“不方便行大禮,請竹軒翁見諒。”說著,向后撤身,斜對著竹軒翁,一鞠躬。王倫隨即起身,說道:“地方窄狹,諸孝廉不必客氣。”說著話,還要拱手。諸讓眼明手快,雙手握住王倫的兩手,輕輕按扶他坐下,然后拱著手對大家說:“幸會!幸會!”陸恒示意諸讓坐下,說:“今天還有德章。德章,給大家端茶倒水,你辛苦了。”坐在下首的王袞慌忙起身,嘴里說著:“應該的!應該的!”因為起身猛,身下的長條凳離桌子太近,身子站不直,一下子急得滿臉通紅。同坐一條凳子的王華見父親威嚴地瞪向弟弟,抬眼發現弟弟的窘態,不動聲色地欠起身,把長條凳往后輕輕移了移,讓弟弟站穩。
陸恒繼續說:“今天的主題有三個,第一,請竹軒翁介紹一些讀書體會;第二,請養和給我們講講他應舉的感受;第三,常規內容,會講一下上次例會的讀書內容,商定下次的會讀內容。今天有學壇前輩、老同學、新朋友,我們先互相認識一下,我介紹一下竹軒翁的情況,一會兒大家再自我介紹。”
陸恒說:“竹軒翁詩書傳家,高祖諱性常,才兼文武,受終南山道士贈書,精通術數,受到了誠意伯劉伯溫先生的景仰和薦舉,為國死難嶺南;曾祖號秘湖漁隱,隱居終生,人稱孝子;祖父遁石翁,精研易經,學問養身,高風亮節,隱遁深山;父親槐里先生繼承我們余姚的傳統,專修一門《禮記》,是南京國子監太學生;竹軒翁幾十年主修《禮記》,在江浙各地處館講學,提攜后進,培養英才。我們一會兒請竹軒翁講學。現在互相認識一下,今天不便作揖打躬,點頭為禮,心到禮到。按年齡排序,養和先開始。”
諸讓揚了揚矜持的下巴,爽朗地說:“我叫諸讓,字養和,今年三十三歲,主修《禮記》,三年前僥幸中舉。”說到僥幸,他好像有些賣弄的意味,聲調不由自主地有些上揚,有些輕狂。這時他猛然想到父親的告誡。諸老先生老早就發現這個兒子英氣逼人,他在自家兄弟之間爭強好勝,又身材高大,特意給他起名“讓”,意在損其有余,補其不足;年輕氣盛,自然不免有些心浮氣躁,在“讓”的基礎上,啟蒙老師又給他取字“養和”。師長希望以名字來時時提醒他修身養性。諸讓語調一轉,謙和地說:“請竹軒翁不吝指教,也請各位學友做我的諍友,知無不言,矯枉糾偏,百尺竿……”諸讓因為要表現謙虛,不好再往下說,就打住話頭,望著陸恒。
陸恒接口道:“自然是再進一步,遮陽帽換成進士冠。人往高處走,天經地義。正好輪到我介紹:我叫陸恒,字有常,自號‘拙庵’,今年三十四歲,比養和癡長一歲,才卻短養和不止兩寸吧!”諸讓自知陸恒才氣不比自己差,甚至比自己還要好,發現大家都盯著自己,于是特意稍低一下頭,免得下巴上揚,擺著手,真誠地說:“僥幸中舉,僥幸!確實是僥幸!”黃珣、謝遷、王華和王袞,羨慕地笑著,心里渴望著這種僥幸。陸恒接著說:“我名字中有‘恒’有‘常’,其實沒有持之以恒,北上進京的路走不順,我退守余姚,教教小孩子,給大家做鋪路石吧。下面廷璽。”
廷璽是黃珣的字。他說:“鄙人黃珣,字廷璽,三十四歲,二十多年寒窗,很慚愧!愧對高堂!唉!”黃珣說著,嘆了一口氣。王倫精于道家術數,盯住黃珣的臉,開導道:“廷璽賢侄,安心勿躁,修學養德,迎接富貴。”
王華七尺男兒,繼承了父親王倫的臉型骨架,長方形臉龐,眉骨棱起,眼神清澈,一副貴相,比父親不同的是,他臉頰隆起圓潤,所以臉就有些圓滿,這給貴氣中增添了很多的福相。王華面色純凈,臉上和頭頂洋溢著一層純粹的純陽之氣。他示意弟弟,條凳后移,靜靜地起身,聲音清純,說:“末學王華,字德輝,二十六歲,今天面對家君大人,有諸孝廉在場,王華不孝,愧對家君大人!我一定繼續努力,德學并進,光耀門庭。”
王倫對兒子的態度一直是滿意的,不準備給兒子壓力,就笑看著諸讓。諸讓會意地一笑,對王華說:“德輝賢弟,小小的舉人功名,何足掛齒。他日折桂金鑾殿,舍老弟這等大才,還能有誰!”
該謝遷了。浙東謝家,從東晉開始,多少年都是名門望族,這就給謝家后人一些志在國家的聯想,想到先人的位尊權重和垂世功勛,經常會激發他們奮發向上的志氣和勇氣;看看眼下自己身居草野,遠離廟堂,距離先祖好像有十萬八千里,不免又會黯然神傷,他們就在這種矛盾心情中掙扎著、打拼著。雖然遠,畢竟有路,那就是科舉,這就是努力的方向和目標。謝遷平和大氣地說:“晚輩謝遷,字于喬,二十四歲。請前輩多指教。”說著,從容起身,扭身向王倫躬了躬身,然后向大家拱手,劃了個半弧。
最后是王袞。王袞身子骨有些單薄,繼承了他父親的長方形臉架,但是臉頰比他父親還要瘦。他急忙站起身,學著他哥說:“末學王袞,字德章,二十三歲,我也愧對家君大人,我一定向各位先生好好學習。”
大家介紹完畢,陸恒說:“以前我們的會讀,是兄弟會,圍繞一個主題,大家自由發揮。今天竹軒翁是主講,諸孝廉是副講,給我們講學。現在我們開始禮請主講。”于是,六個人紛紛起身,到桌子南面,站成兩排,陸恒、諸讓、黃珣站在前排。陸恒唱禮:“講學,就是講道。講臺之上,講師,就是道的代表,我們尊師就是尊道。現在,大家整理衣冠,清凈身心。好,讓我們開始,我們以至誠之心,祈請竹軒翁,一鞠躬,興;再鞠躬,興;三鞠躬,興。”聽著陸恒清越又抑揚頓挫的長音,看著晚輩們虔誠地行禮,竹軒翁正了正身子,捋了一下花白的山羊胡子,神色更加端莊、莊嚴。他的目光在諸讓高大的身軀上停了一下,意識到他的舉人身份,下意識地欠了欠身子,準備表示一下禮遇,也只是一轉念,他再次確認了自己的身份,現在自己是講師,就像陸恒說的,是道的代表,也許自己本身只有小道末術,與大德大賢比起來不足掛齒,但是,現在他就是大道的代表,身臨師位,代道講學。此念一生,竹軒翁一下子覺得自己像一棵高聳修長的翠竹,內里的一節節關節上下貫通,身心空靈,知覺中竟然找不到身軀,沒有了頭腦,這個空靈輻射到無限的夜空,只剩下一個“知道”,知道什么呢?卻什么也不知道,眼前這幾個人影,是誰呀?……竹軒翁馬上收攏心神,一定神,意識到要講學。
成禮后,六位入座。
竹軒翁上身因脊柱挺直顯得稍微后仰,臉部被帶動自然上揚,顯得更加大氣。他開講道:“今晚蒙幾位學友不棄,我們有了這個交流機會。俗話說,有學不在年高,在學問上,上年紀人也不能倚老賣老。胡子長,表示經歷多,經驗多,知識多,但是呢,學問與智慧關系最為密切。大家抬頭看看這個。”竹軒翁說著話,左手食指向上一挺,“看到什么了?”“竹軒翁的食指。”黃珣隨口答道。這樣的小兒科問題,諸讓舉人功名,保持著身份的矜持,不能搶著回答,其實是不屑于回答,于是故意笑了一下。陸恒是余姚名校的精英人物,提問別人是他的特權,已經沒了回答問題的習慣,此時此刻心里還揣著自己余姚名師的身份,心有所想,身有所現,不由自主地端起了名師的架子,忘了聽講者的身份,幾乎成了督教的校長,要監督鑒定講師的學問。謝遷娘胎里帶來的聰明,腦子銳利,他想,這要是問手指頭,老先生還不至于這么迂腐,于是上翻眼珠,盯住竹軒翁所指向的木匾上的兩個字“靜學(靜學)”,但是他不好開口,這位未來的大政治家,心里頭想的是不會輕易出口的。王華呢,老實人一個,他只看著手指頭,不去多想,何必急呢?就像老婆生孩子一樣,總會出來答案的。王袞呢,聽他父親說“上年紀人也不能倚老賣老”,正在琢磨,老先生今天說話與平常在家對自己的態度咋這么大區別呢?一愣神,脫口而出:“手指頭!”
王倫聽到兒子的回答,想到了先賢們開發智慧的公案,就是那個有名的《指月錄》,明明指向的是明月,他們卻只看手指頭。王倫痛心地給小兒子下了個“難成大器”的鑒定,也懶得賣關子,接著說道:“這‘靜學(靜學)’兩個字,從左念也通,自右讀也成。”王倫多年游走于江浙大地各處私塾學堂,靠滿腹才學糊口養家,見慣了各色學生,今晚,不看大家的眼神,憑他清凈的心神也覺察到了在座中的躁氣,于是他說道:“靜學,靜中學;學靜,學心靜。我來操琴,學友們靜靜心。”
王倫兩手撫琴,眼簾微垂,他先冥想一下,醞釀一下思路。此時,窗外的竹林在夜風的慫恿下,造起了波浪運動,沙沙沙沙作響。窗外竹林有規律的風鬧聲,襯托得竹軒內更加幽靜。秀才舉人們不再聽講,身心放松下來,他們重新調整身體,坐得更輕松,神情顯得更自然。這時,王倫的心中生起了一輪明月,月光下,他的指尖下流淌出了一首歌《學做圣賢》,他手指輕撫琴弦,琴弦上迸發出了錚錚鏘鏘的音流,隨著深邃悠遠的琴聲,王倫隨口吟唱起來:
今夕是何夕?
孟秋月晦夜。
繁星點點煩惱多,
明月一輪智慧開。
明月何處尋?
不必中秋夜。
人人心頭藏明月,
念念清凈照乾坤。
竹林青竹竿,
個個好青年。
心虛才能節節高,
修直向上美名傳。
學貴有師友,
舜象互借鑒。
心悟身行是渡船,
智慧仁勇最圓滿。
王倫靈巧的手指下飄出悠遠、深邃、清幽的琴聲和口中徐徐流溢出的歌聲,像一劑融化劑,消磨了諸讓心中的矜持,抽空了陸恒身心中一直端著不放的精英架子,消融了謝遷頭腦中的智巧,洗刷了黃珣和王華心中的思索,這幾位心中的點點繁星都被皎潔似的月光吞噬了。只有王袞,仍在一心多用:一會兒,哎呀,竹林里的風變小了一些,老父親唱歌,渴不渴呀,是不是給他續些熱水?唉,這找師友,怎么會“舜象互借鑒”,難道要借鑒象這個壞家伙嗎?直到最后,琴聲歌聲戛然而止,王袞心頭的念緒也一下子跟著停止了,和其他幾位一樣,他靜靜地、愣愣地坐著。
王倫察覺到竹軒內一派沉靜之氣,幾位年輕人臉上和眼神已純凈多了,于是他示意呆愣著的王袞撤下古琴,自己悄無聲息地啜飲了幾小口茶,隨機開講:“學,就需要我們現在這個心境,就是靜。學什么呢?我們分析一下這個‘學(學)’字,上頭像一雙手捧著一個‘爻’字,大家都知道《易經》,有常是‘《易經》’專家。”王倫說著,看了一眼陸恒。陸恒已經忘掉了剛才的精英架子,對著“爻”字,他下意識地點了點頭,但是意識到《易經》深邃,沒有窮盡,馬上又搖了搖頭。王倫繼續說道:“這個爻呢,無須我多說,一長橫‘—’代表陽,兩短橫‘--’代表陰,一陰一陽謂之道。學,就是要學這個道。一陰一陽,一長橫,兩短橫,互相組合,揭示了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等自然現象的變化規律。了解運用規律,小則修身養性,大則安邦定國。掌握規律,要靠智慧,有了智慧,先把身心安置好,至于學技術,就容易多了。科舉就是個技術活。”科舉是大家迫切關心的事,幾雙眼睛一下子盯住了王倫。王倫注意到了大家的關注,接著說道:“科舉就是幾篇文章,知識非常必要,經驗固然重要,關鍵還是智慧,知識要靠智慧來組合。這智慧哪里來?就從心靜中來。”
王倫停了停,發現大家沉浸在“靜”中,在體味和琢磨這個“靜”,幾個人拘束得不敢動,就啟發道:“今天你們這個讀書會的名字,提醒了我,舜象讀書會,舜和象好像一好一壞,好像各是各,嗯,想不到你們年輕人這么有智慧,首先說向老師學習,不見得老師都要比我們強,見賢者思齊,見不賢者退而自省,這樣一來,像象這個一時的落后分子,也可以成為我們的一面鏡子,也是我們的老師;另外我們自身呢,大多數時間,是好思想、好念頭,不少時候,也有不少不好的念頭,好的時候就是舜,不好的時候就是象。你們看,一個好人身上還有舜象。我們學習呢,就是擴充好念頭,融化不好的念頭。同樣道理,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不能一說到靜,就連動也不敢,靜是心境,一個激烈運動著的人可能心很靜,一個坐下不動的人,也可能心動得很厲害。”
聽了這話,幾位秀才舉人活躍起來,黃珣晃了晃因長時間靜坐而顯得有些僵化的雙肩和腰身,問道:“先生說這些,有些像大海,其實我們只需要一瓢水就夠了,就需要一個單刀直入的方法。”
王倫意味深長地看了一眼黃珣,說道:“不見得人人都擠一條道。要學,就大學,《大學》說得最清楚,第一段……”
這時,內宅二樓的產房內傳出一聲清亮的啼哭聲,“哇啊、哇啊、哇啊……”一個將被稱呼為王陽明的嬰兒來到了人間。
竹軒內,王倫正在侃侃而談,他的話頭突然被一個女聲打斷。一個小媳婦一路小跑過來,笑著匯報道:“爹、爹,生了!生了!是個小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