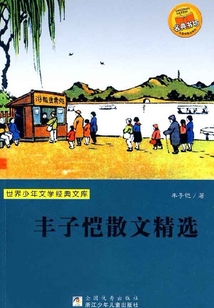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9評(píng)論第1章 前言
小讀者們,相信你們對(duì)豐子愷的漫畫都不會(huì)陌生吧。他的漫畫往往用簡(jiǎn)單的線條勾勒出生動(dòng)傳神的人物形象,而且內(nèi)涵豐富的意蘊(yùn),讓人在會(huì)心一笑之余又忍不住思緒萬千。在中國(guó)二十世紀(jì)的畫壇上獨(dú)樹一幟。《豐子愷畫集代自序》中作家自己曾寫道:“最喜小中能見大,還求弦外有余音。”這可以說是豐子愷一以貫之的創(chuàng)作理想,不僅體現(xiàn)在其漫畫創(chuàng)作上,在他的文學(xué)實(shí)踐上,也是如此。
豐子愷(1898—1975),原名豐潤(rùn),浙江桐鄉(xiāng)人,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著名的漫畫家和散文家。1914年起就讀于著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xué)校,期間,成為李叔同(弘一法師)的入室弟子,迷上了美術(shù)和音樂。1921年東渡日本,繼續(xù)學(xué)習(xí)繪畫和音樂。他學(xué)畫師從恩師李叔同,出版過《護(hù)生畫集》、《子愷漫畫》等畫冊(cè)。成為中國(guó)現(xiàn)代漫畫的創(chuàng)始人。
在散文方面,豐子愷從二十世紀(jì)二十年代中期即開始從事散文創(chuàng)作,直到晚年從未間斷,歷經(jīng)半個(gè)多世紀(jì),收獲甚豐。曾先后出版了《緣緣堂隨筆》、《子愷小品集》、《豐子愷創(chuàng)作選》、《緣緣堂再筆》等十多種散文集,其中又以《緣緣堂隨筆》、《緣緣堂再筆》等最為著名。本書以這兩本文集為藍(lán)本,選編豐子愷在各個(gè)時(shí)期創(chuàng)作的內(nèi)容適合青少年閱讀的作品,并以創(chuàng)作時(shí)間的先后編排順序,再配以作家的同題材漫畫作品,以便小讀者對(duì)豐子愷的文與畫有一個(gè)比較鮮明客觀的認(rèn)識(shí)和了解。
“緣緣堂”最初是作家在上海寓所的名字,其名稱的由來還有一段故事:當(dāng)時(shí)弘一法師正云游上海,豐子愷請(qǐng)他為自己的寓所命名。弘一法師就讓他在紙上寫了一些自己喜歡且可以隨意搭配的字,團(tuán)成球撒在釋迦牟尼畫像前的供桌上抓鬮,結(jié)果作家兩次均抓到了“緣”字,遂命名為“緣緣堂”。豐字愷很喜歡這個(gè)名字,后來他在家鄉(xiāng)建造的居所亦從之而稱,并以此名其散文集。
豐子愷的散文除去一些藝術(shù)評(píng)論以外,大都是敘述他親身經(jīng)歷的生活和日常接觸的人事,表現(xiàn)出濃厚的生活情趣,如《山中避雨》、《廬山游記》、《上天都》、《食肉》、《癩六伯》、《吃酒》等。他善于從身邊的日常生活描寫中表現(xiàn)對(duì)人生、社會(huì)的哲理性思考。《山中避雨》里先寫游西湖遇雨,接著很自然地去茶鋪避雨,而鋪?zhàn)永锏牟璨┦康睦僖嗍潜藭r(shí)彼境最貼切不過的場(chǎng)景。因了同去小女孩的掃興,作家自自然然地走過去借了茶博士的胡琴拉了起來,這時(shí)候,一縷溫馨的情愫隨琴聲悠然響起。琴聲歌聲將避雨的人們匯集在一起,“愿人們同聲齊唱,愿人間十分溫暖”的人生社會(huì)理想,被作家融化到這瑣碎的事件描寫中,一切皆如行云流水般自然。
當(dāng)然,豐子愷的作品中,以他那“小燕子似的一群兒女”為主角的文章總是最吸引人的,在充滿著趣味的字里行間深蘊(yùn)著作家的人生理念。子女們的一舉手一投足,在他眼里都是那么鮮活,且內(nèi)涵至潔的人類本性。以兒童為審美對(duì)象,是豐子愷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一大主題,在漫畫或散文中皆是如此。這類的散文作品較多,如《華瞻的日記》、《給我的孩子們》、《憶兒時(shí)》、《兒女》、《作父親》、《送阿寶出黃金時(shí)代》、《王囡囡》等。
豐子愷熱愛孩子,珍視童心,并以此來反照成人世界的虛偽和做作,是他兒童類題材作品的主題。隨筆《華瞻的日記》,作家干脆用兒子華瞻的口吻,來寫他的所為所思,直接表現(xiàn)孩子特有的“荒誕不懂事”的思維,而這正是作家主張呵護(hù)的“童心。”童心的表現(xiàn),主要有三個(gè)方面:
一是興趣本位。由于天真幼稚,孩子們往往不循常規(guī),一味憑著自己的興趣喜好率性而為。華瞻憑著趣味,非常投入地與鄭德菱玩騎竹馬游戲,到了吃飯的時(shí)間而不愿意吃飯。在大人看來,該吃飯時(shí)自然應(yīng)首先吃飯,這是生活常識(shí)。孩子們卻全然不管。
當(dāng)然,孩子們也要吃東西,而且還會(huì)吃得非常投入。散文《兒女》就寫了夏夜和四個(gè)孩子一同吃西瓜的情景。面對(duì)美味的西瓜,每個(gè)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表現(xiàn)。在作家看來,孩子們的“作品”,三歲的阿韋的音樂表現(xiàn)最為深刻而完全,最能直接地表現(xiàn)出他的歡喜的感情。五歲的瞻瞻的詩,已打了個(gè)折扣,但猶流露著活躍的生命力。至于軟軟和阿寶的散文的、數(shù)學(xué)的、概念的表現(xiàn),比較起來就更膚淺一層,然而,孩子們?cè)诔晕鞴蠒r(shí)全身心地投入,其明慧的心,比大人們所見的已完全、純粹得多。表達(dá)了作家對(duì)孩子的欣賞與靠近。
二是自我中心。兒童尚不知自我約束,更不會(huì)偽飾自己的要求。《送阿寶出黃金時(shí)代》就回憶了幼時(shí)的阿寶是一個(gè)以自我為中心的“搗亂分子”。而當(dāng)作家看到阿寶居然主動(dòng)把珍貴的巧克力拿出來分給弟妹們時(shí),明白“成長(zhǎng)”已不可遏制地來臨了。此時(shí)的作家既欣慰又若有所失,心態(tài)頗為復(fù)雜。
三是對(duì)世間萬物充滿情誼。孩子們分不清人與物,往往把世間的一切當(dāng)成是與自己一樣有靈性的動(dòng)物。在豐子愷看來,凡是能保持兒童這種天性的人,就有了一顆藝術(shù)家的心。他在散文中常常驚喜地向讀者描述孩子們的這份天性:外婆普陀去燒香買回來的泥人,華瞻何等鞠躬盡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自己失手打破了,號(hào)哭得比誰都傷心。阿寶認(rèn)真地給凳子穿上自己和軟軟的襪子,得意地叫:“阿寶兩只腳,凳子四只腳!”童話《有情世界》寫了兒童阿因的夢(mèng)。在夢(mèng)中,月亮姐姐、白云伯伯、蒲公英、松樹、杜鵑花、溪澗妹妹,都成了與阿因一同玩樂的伙伴,童趣盎然。
豐子愷憧憬超越功利的童真世界,將兒童世界與成人世界兩者相對(duì)立看待。《給我的孩子們》就明確地表達(dá)了作者的這一思想。但是,孩子的黃金時(shí)代有限,現(xiàn)實(shí)的丑惡終于要暴露在他們面前。豐子愷眼看兒時(shí)的伴侶中的英雄、好漢,一個(gè)個(gè)退縮、順從、妥協(xié)、屈服起來,到像綿羊的地步,不禁為孩子們的將來深感憂慮。老大長(zhǎng)成了懂事的少女,豐子愷在《送阿寶出黃金時(shí)代》中表達(dá)了自己悲喜交集的心情:“然而舊日天真爛漫的阿寶,從此永遠(yuǎn)不得再見了!”
成人世界與兒童世界時(shí)時(shí)會(huì)有沖突。美好的兒童世界是脆弱的,經(jīng)不起丑陋的成人世界的沖擊。作家想要呵護(hù)童心,有時(shí)也不免陷入尷尬的境地。散文《作父親》就寫了一個(gè)尷尬的小故事。賣小雞的販子見孩子們對(duì)小雞喜愛之極,咬定高價(jià),不肯松口。小雞沒有買成,作父親的要怎么辦呢?豐子愷自然不忍心將成人世界可惡的“游戲規(guī)則”教給孩子們,但孩子們遲早要融入社會(huì),也遲早會(huì)接受這一切。這是最最無可奈何的。
豐子愷的散文習(xí)慣用一種看似平淡且相對(duì)閑適的文字與意境來表達(dá)真情實(shí)感,即使是針砭時(shí)弊的批判也還是用比較溫和幽默的調(diào)子,與同時(shí)代的主流作家們那種唇槍舌劍似的鋒芒相去甚遠(yuǎn)。因此,他的文章在現(xiàn)當(dāng)代文壇自成一格:率真,樸素,富有詩趣,亦不乏理趣。
《車廂社會(huì)》是豐子愷描寫世間眾相,諷刺社會(huì)不平的代表作。作家通篇用了比喻的手法,將車廂社會(huì)比作人類社會(huì)的縮影,對(duì)種種的眾生相作了細(xì)致的觀察和描寫,溫和地嘲笑了人事的紛擾和世態(tài)的滑稽,不平于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勢(shì)力和不平等。立意鮮明,主題尖銳,但文風(fēng)并不鋒芒逼人,這是作家這一類型作品的特點(diǎn)。
當(dāng)然,作為一位進(jìn)步的愛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溫和的豐子愷在面對(duì)民族大憂患時(shí),同樣表現(xiàn)出了自己堅(jiān)定的信念和抗日必勝的信心。1938年,抗戰(zhàn)的硝煙彌漫了作家的家鄉(xiāng),豐子愷扶老攜幼舉家逃難,這一遭遇被寫入了《還我緣緣堂》、《愛護(hù)同胞》等一系列作品中。文章夾敘夾議,逃難途中的艱辛,民眾生活的顛沛流離,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反感,對(duì)故鄉(xiāng)的懷念,以及對(duì)和平生活的渴望和戰(zhàn)勝困難的信念都被如實(shí)記錄下來。組成一幅戰(zhàn)時(shí)生活的眾生相,而這眾生相中卻使人讀到了希望。
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一直講究文如其人,散文尤其如此。豐子愷就是一個(gè)最好的例子,他為人真率一如一個(gè)大孩子,他的散文更是“文品如人品”:滿腹情愫,一掬而出,不帶一絲虛假造作。在他的作品里,幾乎一切都敞開著,不存在隱秘的角落,沒有灰暗的蛛網(wǎng)。年輕的讀者們,面對(duì)這樣的人這樣的作品,請(qǐng)拿起這本書來,認(rèn)真地讀一讀吧。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