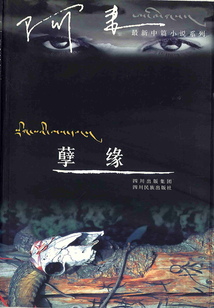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7評論第1章 孽緣(1)
這是第三次回家了,還是沒有見到舅舅。從嘎洛死后,我年年回鄉,卻始終沒有見到過他。
我問母親,她一言不發,卻扯起衣角擦拭眼睛。我轉過臉去。我十分熟悉母親哭泣的樣子。剛回家時,母親突然把頭埋進我的懷里,而離鄉多年,已經成人的我卻像是在大庭廣眾之下,讓一個情人扎進了胸懷。我窘迫地后退一步。母親嚶嚶嗡嗡的聲音立即止住了。她背過臉去,又扯起了衣角。后來母親靜靜地聽我談在外面的種種經歷,說:“可憐你吃了多少苦啊。”她說著就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輕輕摩挲。我又一次把手抽走了。母親突然怨憤地說:“阿來,你就跟你父親一模一樣。”
我知道,這是指我冷漠的脾性。
我知道我從小跟父母就不是十分親密。
我知道我傷了我可憐媽媽的心。心頭掠過了那些深刻在媽媽心房上的痛楚。阿媽啦,阿媽。作為補救,我掏出妻子和兒子的彩色照片。母親把照片移到眼前,又遠遠地送到陽光底下。她的嘴唇輕輕地哆嗦起來,可是她沒有流淚,而是輕輕地笑了。她把照片放在膝蓋上,用粗糙的手掌撫摸,手上的繭疤在光潔的照片上留下了清晰的劃痕。母親喃喃地說:“我的孫兒。”
她的孫兒在夏天的充滿花香的陽臺上緊貼他媽媽的臉腮,好像知道他父親未有過像他那么幸福的童年,一生下來就知道充分享受父愛母愛,領略生活的所有芬芳與甘甜。
這時藏歷新年剛過不久。地里麥苗還未出土,已經分群筑巢的野鴿在遠處成雙成對地戲弄陽光。輕風來自東南方向,飽含著水的氣息,春天已經來了。
母親說:“給我生了孫兒的人就是我的女兒。”
“是這樣,阿媽。”
“你要早點帶他們回家。”
“是,阿媽,我帶他們回來。”
“現在不像以前了,我要給他們做衣服,做好吃的東西。”
“他們也要給阿媽捎來你喜歡的東西。”
“我只要看到他們,我的女兒,我的孫兒。阿來。”母親掠了掠落在耳輪上的頭發,“你要對自己的女人好,脾氣不要像你阿爸那樣。”
我看母親的眼圈又在泛紅了,就趕緊岔開話題,問:“舅舅斯丹巴怎么不在村里?”
“你去找他了?”
“找了。”我告訴母親自己怎樣在村里轉悠,我去了梭磨河邊的新色爾古村沒有找到舅舅的新居,又去了瑪崗覺卡邊狹窄山溝里的老色爾古村,看到舅舅那座遠遠吊在村邊的孤獨的老房子,看到它和老色爾古村大多數已經廢棄的房子一樣,屋頂早塌陷了,墻頭上搖曳著隔年的枯草,墻縫里已經爬滿了苔蘚。我只是沒有告訴她還在一所破敗的房子里看到炊煙,然后,在《舊年的血跡》一書中著力描繪過的市場上,我遇見一個固執的老人。這將成為我的一篇小說的內容。我的一本書又有了一個新的章節。
“舅舅……是不是又病了?”
“不”,媽媽說,“他又回到廟里做和尚去了”。
“哪個廟子?”
“垠口廟子。”
“他的私娃子在外面做生意。你曉得吧,你舅舅當生產隊長時跟莫多家的阿朵有過一個娃娃。哦,你不曉得,那陣你已經走了,那娃娃已快二十了吧。他的名字也是你舅舅取的,叫柯亞。”
我們坐在門前的臺階上,母親回屋取來了奶茶,還把一碟新鮮奶酪放在我面前。她把孫兒和媳婦的照片鑲了起來,然后一直用手擦拭鏡框的玻璃,不太干凈的手在鏡面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痕跡。
母親說要捎信叫舅舅回來。
母親不知道我假期將滿,已悄悄打點行裝準備回城了。新年已過,新年時用麥面涂在大門和屋內飾墻以及櫥柜上的吉祥圖案已沒有先前那樣潔白光鮮了。
母親說,舅舅回來會看到我,看到我可愛妻兒的照片。
“你要等你舅舅回來。”她以不容置辯的口吻說。
這種口吻使我感到一個兒子所能體會到的母愛的全部溫暖。
舅舅和母親是同母異父的兄妹。母親一個遠嫁的姐姐和他們好像也是同母異父。我沒有見到過外婆的模樣,她沒有留下照片。家里只有一幀舊得發黃的兩寸照片。一個女孩子對著鏡頭吃吃暗笑,那是十幾歲時的母親。挨著母親的是一個小和尚,表情癡呆麻木,正在努力扯起袈裟,遮住袒裸的赤膊和胸前小小的男孩子的乳頭。小和尚就是丹巴舅舅。
丹巴舅舅6歲就被他在廟子里修習醫術的伯父領去廟里學藏文。他伯父一直阻止他接觸整本經文,只摘出各種經書中的佛本生故事和喇嘛教各代宗師故事作為教學課本。和許多在廟里認字讀書的孩子一樣,舅舅早上出去放馬,晚上到井泉邊取水,實際上當了寺廟的雜役。
外婆帶著任何時候似乎都在吃吃暗笑的母親到寺廟進香時,看見丹巴舅舅因放下手中活路去偷聽活佛講經正受到鞭打。他跪在草原暴毒的太陽底下,背上的血跡結成了紫痂。
外婆看看四周無人,趕緊取下一片帶水的大黃葉子遮到兒子的光頭上,那是她們趕路時采來頂在頭上遮避陽光的。舅舅一歪身子,大黃葉子“叭”一聲落到地上,他又在烈日下挺直了鞭痕深重的脊梁,就像鞭打他的鐵棒喇嘛那樣滿臉強硬的神情。和尚們誦經和聽人講經時,那鐵棒喇嘛就威嚴地在陰森的經堂中逡巡,懲治不守規矩的和尚和違例進人神圣禁地的閑雜人等。
外婆哭了。
尚未充分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更對我的生命一無所知的母親提起拖地的衣裙,光著腳在寺廟院子里四處走動。她輕輕悄悄地走動,腳踩院中碧綠的茸茸青草。丹巴舅舅定睛看著她光潔的赤腳碰掉草葉上的露水和蒲公英細長的黃色花瓣。
妹妹說:“阿哥啦,他們都在念經,你快快起來。”
哥哥立即感到頭頂和背脊上毒烈的陽光變得沁涼,好似感受到輕柔的湖水在蕩漾。
他搖搖油汗淋漓的和尚腦殼。
一只牛虻落在了禿頭上。
“牛蠅咬你了,阿哥丹巴。”
丹巴舅舅說了一句自己也不懂的艱深梵語。他不肯舉起雙手,只抖動眉毛。頭頂相應的部位也顫動起來,牛蠅抖抖透明的美麗翅膀避開那塊地方,一夾雙翅,又在另一個地方扎下了尖利的吸管。小和尚又抖動耳朵,這次,牛繩根本就不在頭皮跳動的那塊地方。
妹妹笑了起來,笑聲明麗清脆,猶如此時使草原使寺廟的金頂變得明亮輝煌的陽光。
而做母親的哭聲像牛蠅在快樂地嚶嚶歌唱,這種嚶嚶聲也是蜜蜂歌唱的聲音,是那些看不出流向的河水穿過平坦無垠的草原與深厚陽光屏幕的聲音。
哭聲與笑聲交織在一起。
哭聲是孤獨的,是一個個男人先后離開,而把一部分生命棄置在她腳前的女人的哭聲;笑聲出自一個天真未鑿的混沌女子。哭聲與笑聲同樣飽含深刻的啟悟。據說當時丹巴舅舅眼前開始飛舞金光,一些不連貫的從未修習過的經文從口中吐了出來。他看見奪目金光中經堂厚重的木門慢慢洞開了。
舅舅被太陽曬昏了。他母親的哭聲穿過心房。
經堂的木門果然洞開了。
許多臉膛紅潤的、皺紋深刻的、快樂的、憂戚的、似有感悟的、麻木不仁的和尚臉重重疊疊地出現在陽光下。眾多的眼睛都被強光刺激得瞇縫起來。等那些眼睛睜開,就看到了一個蓬頭的婦人和一個赤腳的少女,看到活佛托起小和尚的頭,有人遞給他一瓢涼水,活佛把涼水含進了他的金口,“噗”一聲噴到小和尚的臉上。
小和尚呻吟一聲,說:“水。”
喝完水,丹巴舅舅突然對活佛說他看見了佛本生故事里所說的鹿群,它們在湖邊飲水,它們踩在湖底倒映的白云上邊,頸上掛著銀鈴鐺,腳踝是少女的腳踩。
他說這是黎明時分。
他說聽到了漸漸黯淡的月亮像流水一樣哭泣。
活佛吩咐舅舅的伯父澤尕爾甲過來,給丹巴身上的鞭痕涂滿一種黑色無味的藥膏。
這時只有陽光靜靜傾瀉。
活佛問趴在地上的小和尚聽到了什么。
他說聽到風從很遠的地方過來。
“像火苗一樣抖動嗎?”
“像。”
“像水一樣回旋嗎?”
“像。”
“起來。”
舅舅起來了。
“我將收你為我的親授弟子。”
舅舅又跪了下來。
和尚們祝頌活佛新收下的弟子的智慧,像潔凈晶瑩的井水,清澤圓潤的玉石,飽滿如秋天的漿果和溢蜜的蜂巢,幽深如月夜的笛音,光耀如同太陽和月亮。
我的外婆也跪下了。她感激涕零的嚶嚶哭泣又和母親銀鈴般的笑聲交織在一起。
只有小和尚的伯父心事重重地坐在遠處,坐在中心的邊緣,處于事件之外。按照佛學觀點,他的存在可以當作一種影子而忽略,或者干脆取消,但他依然自在地坐在那里,手撫包著各種藥材的包楸,心事重重,他不喜歡不能直接療治人身疾苦的和尚。
活佛過來問他這樣能從空中望見什么。
澤尕爾甲說:“我老了,我看不見藍空中出現潔白的蓮花。我不想看了。”
“那你還看見什么?”
“我看見天快變了。”
果然,遠處的水面上有一陣旋風卷起了高高的一柱水花,被太陽照耀得五彩斑斕。
“那是1950年7月間的事情。”舅舅在色爾古村后的草坡上對我說。
這是1968年春天。舅舅的哮喘病犯了,我在學校請了假,幫他上山攔羊。初春時節,黑色的灌木叢上掛著綿羊一綹綹的絨毛,天氣就要變暖,剪羊毛的季節就要到了。《羊毛剪子嚓嚓響》,這首澳大利亞民歌在我們那里流傳得很廣。
吃了一冬的沒有養分的枯草,新草遲遲不肯露頭,每過幾天就有一只瘦弱的羊子躺倒在山坡上,閉上灰色的眼睛。灰色是羊眼在任何季節任何時候的顏色,羊子們就是用那樣的眼睛看著我們。
羊子把舅舅看得一臉青灰。
舅舅說那天活佛剛剛確立他為親傳弟子,人群還沒有散開,遠遠的草灘上就出現了一匹紅色的快馬,帶來解放軍離這里只有幾十里了的消息。
不久,活佛就去內地參觀。
臨行時活佛說:“這樣也好,你就先練練打坐吧。先根除俗念,回來我就授課與你。”
等丹巴舅舅再次見到活佛時,活佛已經當了政協主席,按照政府的意思得裁減寺廟人員。于是舅舅回到農村發展生產。活佛為舅舅摩了頂,說:“你必得多多行善,孝敬父母。其實所有因明學問,天地奧秘也深藏于人世之間。你去了吧。”活佛把一摞銀洋擱在他手中,“你去了吧,不要回頭。”其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世事變遷,使活佛大徹大悟,揮金如土。據說為戰爭募捐時,他獻給政府的金條足夠買下半架飛機。后來,舅舅看見電影里或我的連環畫上,在空中化為碎片的飛機時忍不住扼腕嘆息。
舅舅躺在草坡上喚我:“阿來。”
“嗯?”
“活佛對我講了那番道理,才給銀洋。他給其他和尚都是紙票子。”
“阿來。”
“嗯。”
“你聽清了嗎?”
“聽清了。”
丹巴舅舅說:“我怕你還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的,我明白。”
他這才愜意地嘆息了一聲,像一個臨死的人一樣,心滿意足地合上了眼皮。那些日子我確實以為他就要死了。陽光與風驅散了山間的蒙蒙霧氣,群山與草原邊緣的城鎮出現在遠處。刷經寺鎮上除了城鎮所有的一切外,還有一座陸軍醫院、一座軍營和一座漂亮的烈士陵園。我父親曾在那所醫院里治過傷,那座陵園里有他的戰友。
“你父親恨我。”
我說我不知道。
“你母親對我說過他恨我。我有病,還有我那時沒有把他打死。”
我靈感突來,說:“也許就是恨你當時沒有把他打死。”
這句出自八歲小孩之口的話立即產生了強烈效果。舅舅翻身坐起,說:“阿來,阿來,你這話不是當真吧?這話像是我當年發了昏說我看見經書中寫過的鹿,是那樣嗎?”
“是的,阿古丹巴。”、
忽然,我們身后一股厲風卷過,回頭時,剛好看到一只鷹沖到地面,伸出了黑色的尖利爪子,看到爪子刺進了早上才脫離母體的羊羔的兩肋,看到了血。鷹轉瞬間騰空而起,向遠處的樹林飛去,剩下羔羊無助的細弱叫聲在空中飄蕩。羊群騷動一陣又安詳地吃起草來。溫順的羊子們一副老成持重,對死亡毫無感觸的模樣。
就在這天早上,草上的霜針還沒有被陽光融化。那只臨產的母羊叫聲凄厲。舅舅叫我轉過臉去。母羊的叫聲變了,低沉而又深長。群羊在早上料峭的寒風中和我一起輕輕顫抖。待我轉過臉時,看見母羊正在替剛剛落地的羊羔舔凈身上的血污。舅舅正掰碎了晌午的饃饃撒在母羊跟前,我便防止其它羊子前來爭搶。
中午,我們給母羊送去了鹽和熬過的茶葉。
現在,那只母羊靜默著,趴在地上一動不動。產后的血在兩只后腿上結成了硬塊。我不知道,它對在遠處樹林中在鷹的利爪下化為碎片的小生命有無感覺。
人不知道羊子的事情。
后來,我才明白人也不太知道人的事情。這一點,舅舅和父親都深有同感。
那只鷹又出現了。它不再四處盤旋,它直沖云端,在高空中平展了翅膀,懸浮在那里。陽光把它放大的影子投射到地上。
“風是它的酒。”舅舅說,他的眼睛又像群羊的眼睛一樣沒有了神采。
“你阿爸恨我。”舅舅又說。
我聽見他喉間呼嚕呼嚕的聲響。
“阿來,那天我們八個人伏在柳樹叢中,和他們只隔一條小河。他們的大部隊在后面。他們四個人是前哨。你父親就在他們里面。他們下了馬,叫馬飲水。馬聞到了生人的味道不肯飲水。馬是很聰明的。世界上就是人死到了跟前也不知道。”
我父親下了馬,馬卻繃緊了韁繩要離開河岸。父親起了疑心。對岸那片柳樹林過于安靜了,連鳥鳴的聲音也稀少。他暗暗推開了槍上的保險。他感到了卡賓槍上飽滿的彈匣的分量。父親是老兵了,只要槍支在手,彈藥豐富,就不會感到驚慌。
父親向后面的大部隊發出了安全信號。
遠處大隊騎兵奔馳的聲音使他安下心來,也使有預感的戰馬安下心來。四個騎兵在河邊一字排開,解開衣扣。馬頭伸向河水時平靜的水面蕩起了層層漣漪,對岸樹叢中暗伏的槍口對準了他們的胸膛。那些槍口隨著槍手的呼吸輕輕晃動。
“阿來。你不知道被槍貓住的感覺。被貓準的地方就像有一溜螞蟻叮咬一樣,癢癢的,還有點點刺痛。你阿爸是最后一個踏上河岸的。我槍法好。槍法好的一個對一個。槍法差的三個對一個。我瞄準時才認出了他——色爾古村頭人的兒子。擊發時,我動了動托槍的拇指,結果只打飛了他的帽子。你父親立即跳到一匹死馬背后。我救了他。”
舅舅沙啞著嗓子嘿嘿地笑了。
“他們大部隊趕到時,機槍子彈落在我們后面很遠的地方。”
舅舅不提他們餓急了停下來,輕而易舉就成了俘虜。
先是機槍子彈把他們壓在地上。然后,碉堡里傳來喊聲,叫他們把槍支放下。
“向東!向東,三分鐘內!”
東邊有一隊解放軍等著押解放下武器的俘虜。一些人爬到他們的槍口下,舉起雙手。舅舅舉起雙手時,發現自己正好站在父親面前。這時,碉堡里的機槍壓低了,發出得意的咯咯歡笑。拒不投降的土匪有的被打得往空中彈跳起來;有的發出了驚詫的叫喊。
舅舅叫父親:“雍宗,你放了我。”
父親搖搖頭。
“在河邊我只打掉了你的帽子。”
父親眼中突然生起了一股可怕的綠光。那次河邊三個尖兵四匹戰馬一齊倒下,只有父親死里逃生。那天,和父親一起出來的一個同村戰友又拖槍逃跑,父親便受到懷疑。父親的預備黨員資格被取消了,雖然提升他做了戰斗班副班長。父親惡狠狠地把鋒利的馬刀抵在舅舅腰上,說:“你再說話!”
“我不說了。”
“說吧,說吧。你這個土匪。”
“不說了。解放軍寬大俘虜。”
“土匪!”
父親還把槍機弄出了嘩嘩的聲響。
舅舅又說:“解放軍寬大俘虜,同志寬大俘虜,我是受苦人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