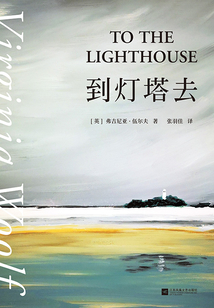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窗(一)
“嗯,當然可以,如果明天天晴,就讓你去。”拉姆塞夫人說。“但你必須早起。”她補充道。
對她兒子來說,這些話傳遞了無與倫比的喜悅,就好像這趟遠足必能成行,一切都已成定局,似乎他年復(fù)一年所期待的奇跡,在漆黑的一夜和一日的航行之后就觸手可及。雖然詹姆斯·拉姆塞年僅六歲,由于他已屬于那個偉大的族群——他們無法區(qū)分自己的情感,一定要讓自己對未來喜憂參半的期許給眼前的一切籠上陰霾——對于這類人來說,即使在童年最早的時期,任何情感之輪的轉(zhuǎn)動都有力量讓承載著陰暗或是光輝的瞬間結(jié)晶并凝固下來。媽媽說話的時候,他正席地而坐,滿心歡喜地剪著陸海軍商店帶插圖的商品目錄,一張冰箱的圖片就讓他感到無比快樂。空氣中彌漫著喜悅。手推車、割草機、白楊樹的聲響、雨前泛白的葉片、白嘴鴉呱呱亂叫、掃帚敲打著地板、連衣裙沙沙作響——所有這一切在他腦中都是如此的色彩斑斕、清晰可辨,他甚至早已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密碼,他的秘密語言,雖然那高聳的前額、凜冽的藍眼睛和孤傲的坦率純真,在外表上給人以刻板嚴肅的感覺,但看到人類弱點時,他會輕皺眉頭,因此,母親看著他利落地用剪刀勾勒著冰箱的形狀,想象著他身穿紅袍、披著白貂皮坐在法官席上;或是在某個重要企業(yè)遭遇公關(guān)危機的時候,指點它渡過難關(guān)。
“但,”他的父親在客廳窗前停下腳步說,“天氣不會好的。”
倘若詹姆斯的手邊有把斧頭、火鉗或是任何一種武器,能在他父親胸口戳個洞讓對方當場斃命,此時此刻,他會毫不遲疑地抓起武器。這就是拉姆塞先生,只需露個面就能在自己小孩心中激起如此極端的情緒。現(xiàn)在他站在那兒,身體瘦削如一把匕首,單薄得像片刀刃,一臉挖苦地咧嘴笑著,他不僅從打擊兒子、嘲笑妻子(當然在詹姆斯眼中,拉姆塞夫人要比他好成千上萬倍)的行為中得到了巨大滿足,還悄悄地為自己判斷精準而沾沾自喜。他所說的是實話,一向如此。他沒有撒謊的能力,從不歪曲事實真相,從不會為了滿足或是討好他人,把難聽的話說得委婉一點,為他的孩子們就更不可能,他們是他的子嗣,應(yīng)該從孩童時期就意識到生活的艱辛,事實是不容妥協(xié)的,而想要前往那片傳說中的土地(拉姆塞先生直起了腰板,瞇著藍色的小眼睛向地平線望去)——那片碾碎我們最耀眼的希望的土地、那片在黑暗中擊沉我們?nèi)醪唤L小船的土地,我們最需要的是勇氣、真相以及忍耐力。
“但天氣也有可能好起來——我希望如此。”拉姆塞夫人不耐煩地說,手里拿著棕紅色襪子繼續(xù)織了幾針。如果她今晚能織完,如果燈塔之旅最后真的能成行,這襪子要送給燈塔看守人的小兒子,他飽受髖骨結(jié)核病的折磨;她還準備帶上一疊舊雜志和一些煙草,是的,只要是她能找到的平常四散在房間里沒什么用、只給房間添亂的東西,都一起送給那些窮苦的人們,給他們解解悶。他們肯定無聊死了,除了擦擦油燈、剪剪燈芯、在一點點大的花園里東耙耙西耙耙,只能整日無所事事地呆坐在那兒。她會這么問,要是你,你愿意每次與外界斷絕一個月聯(lián)系,被困在一塊只有網(wǎng)球場大小的巖石上?如果遇上暴雨季,時間可能還要更長些。而且還沒有信件、沒有報紙,也見不到任何人。如果你已經(jīng)結(jié)婚了,見不到你的妻子,不知道你小孩的近況——他們是生病了,還是跌倒摔斷了手腳;如果周復(fù)一周眼前所見都是一成不變的浪花飛濺,可怕的暴風雨襲來,浪花敲打著窗戶,海鳥直沖向塔燈,礁石搖晃不止,而你根本不敢打開門探出頭去,只怕被卷入海浪之中。你心里是什么感覺?她特意說給女兒們聽,所以說,她用截然不同的語氣說道,我們必須盡可能地給他們帶去安慰。
“風向朝西,”無神論者坦斯利張開瘦骨嶙峋的手指,讓風從指縫穿流而過。他此時正和拉姆塞先生一同作晚間的散步,在露臺上走來走去。這也就是說,要想登陸燈塔,現(xiàn)在的風向是最糟糕的。的確,他總說些令人不悅的話,拉姆塞夫人承認,在這種時候火上澆油,實在是太可惡了,而這也讓詹姆斯更失望了。但同時,她不允許別人嘲笑他。“那個無神論者”,他們管他叫“那個小無神論者”。羅絲取笑他,普魯取笑他,安德魯、賈斯伯、羅杰也取笑他,就連嘴巴里一顆牙都沒剩的老狗巴杰也咬過他。大家這么對他,是因為(按照南希所說),他是第一百一十個大老遠追趕著他們來到赫布里底群島[1]的年輕人,而大家更希望能清清靜靜地待著。
“胡說。”拉姆塞夫人極其嚴厲地說。孩子們夸大事實的習(xí)慣遺傳自她,他們暗示她邀請了過多的人來住(這倒也是事實),有時不得不安排一些人到鎮(zhèn)上去住。拋開這兩點不說,她無法容忍客人們遭到無禮對待,尤其是對那些青年男子,他們一貧如洗,她丈夫說他們“才華橫溢”,是他的仰慕者,是來這里度假的。的確,她把整個異性群體都納入羽翼之下,至于原因,她也解釋不了,或許是因為他們的騎士精神和勇氣;或許是因為他們商定條約、統(tǒng)治印度、控制財經(jīng)這些事實;但最終還是因為他們對她的態(tài)度,那種信任、像孩子般的崇敬,沒有一個女性會感受不到或不會因此而感到愉悅。這種來自青年男子的敬慕之情,作為一位上了年紀的女性可以坦然接受,不會有失尊嚴,而這要是發(fā)生在年輕女子身上可就大難臨頭了——上天保佑這不會發(fā)生在她任何一個女兒身上!——她們不會刻骨銘心地感受到它的價值和深意。
她嚴厲地對南希說,并不是坦斯利先生追著他們來到這里,他是受邀而來。
她們必須找條出路逃離這一切。或許有更簡單、不那么費勁的方式,她嘆了口氣。當她望向鏡子,看到自己灰白的發(fā)絲和塌陷的雙頰,已經(jīng)五十歲了,她想,或許自己本可以把事情打理得更好一些——她的丈夫、金錢、他的書。可就她個人來說,她從來沒有為自己的決定后悔過一分一秒,也從來不曾逃避困難或是怠慢自己的職責。在她嚴厲地說了關(guān)于查爾斯·坦斯利的那些話后,她的女兒普魯、南希和羅絲把目光從盤子上移開,抬頭看著她,她此時看上去有點令人生畏。只有在沉默之中,幾個女孩才能玩味起那些驚世駭俗的想法,她們腦中醞釀著與母親截然不同的生活;或許是在巴黎;一種更狂野的生活方式;并不需要總是照顧某個男人或者其他人;因為在她們幾個人的腦海中,對于順從和騎士精神、對于英國銀行和印度帝國、對于套上婚戒的手指和婚紗都有一種無聲的質(zhì)疑。盡管對她們來說,在這一切中存在著美的本質(zhì),呼喚出她們少女心中的男子氣概,并讓她們在母親的注視下坐在桌邊,對那種異常嚴厲和極其恭謙有禮的態(tài)度感到肅然起敬,母親為了那個可憐的、跟著他們——或者更準確地說,受邀來斯凱島做客的無神論者而如此嚴厲地訓(xùn)誡她們時,就像是一位從泥濘之中站起身的女王,去為乞丐清洗骯臟的腳丫。
“明天肯定沒法上燈塔。”查爾斯·坦斯利正和她丈夫站在窗前,拍著手說道。的確,他已經(jīng)說得夠多了。她希望這兩個人能繼續(xù)聊天,別再來煩詹姆斯和她。她看著坦斯利。孩子們說,他真是一個可憐的家伙,弓背駝腰、瘦骨嶙峋的;他連板球都不會打,他隨便亂揮、躲躲閃閃。安德魯說,他是個愛挖苦人的冷酷家伙。他們知道他最喜歡干什么——就是走來走去,和拉姆塞先生一起不停地來回踱步,聊著誰贏了這個、誰又贏了那個;誰是“第一流”的拉丁文詩人;誰“很聰明可是根本不可靠”;誰毫無疑問是“貝利爾學(xué)院[2]”里最有才能的人;誰暫且屈就于布利斯托爾或貝德福德,可當他將關(guān)于數(shù)學(xué)或哲學(xué)某些分支的緒論公之于世時,必然會聲名大噪,而坦斯利先生擁有的這些緒論的前幾頁手稿就是證據(jù),如果拉姆塞先生愿意的話可以看看。他們談?wù)摰木褪沁@些。
有時候她會情不自禁地笑起來。前些天,她說了一句類似“驚濤駭浪”的話。“是的,”查爾斯·坦斯利說,“浪的確有點大。”“你不是渾身濕透了嗎?”她說。坦斯利先生擰了擰衣服、摸了摸襪子后回答道:“是潮濕,沒有濕透。”
但是孩子們說,他們介意的倒不是這些,并不是他的外表,也不是他的言談舉止,而是他本身——他的觀點。他們對查爾斯·坦斯利不滿之處在于,每當大家探討一些有趣的事,比如說人啦、音樂啦、歷史啦……任何事,哪怕只是說句“今晚天氣很好,何不到屋外坐坐”,他都會轉(zhuǎn)移話題,只有等他開始凸顯自己、貶低他人的時候,才會感到滿意。他們說他去畫廊的時候,還會問別人是否喜歡他的領(lǐng)帶。羅絲說,天曉得,人家才不喜歡呢。
一吃完飯,拉姆塞夫婦的八個兒女就像雄鹿般,悄然從餐桌上敏捷地溜走,回到他們的臥室。在這座房子任何角落都不可能擁有隱私,只有那里才是他們的堡壘,在那里可以盡情談?wù)撊魏问虑椋禾顾估念I(lǐng)帶、修正法案的通過、海鳥和蝴蝶、各式各樣的人物……孩子們的房間在閣樓上,每個房間只隔著一塊木板,每一個腳步聲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就連瑞士女孩因為父親身患癌癥而啜泣的聲音也聽得見,她父親現(xiàn)在住在格勞賓登山谷,已經(jīng)時日不多了。在孩子們暢談之時,陽光傾灑在閣樓之中,照亮了房間里的球拍、球衣、草帽、墨水瓶、顏料罐、甲殼蟲,還有小鳥的頭骨……釘在墻上那些皺巴巴的長海藻在陽光的照射下散發(fā)出咸咸的藻味兒,在海里游泳后使用過的毛巾沾滿了沙子,也有同樣的味道。
爭吵、分裂、意見不同、深植于心的偏見,唉,拉姆塞夫人哀嘆道,孩子們怎么那么小就開始爭執(zhí)不休。她的孩子們太喜歡品頭論足了,他們說的話簡直荒唐透頂。她拉著詹姆斯的手,走出餐廳,只有他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離開。在她看來,制造分歧簡直是荒謬可笑,說句實話,就算不這么做,人們的差別已經(jīng)夠大了。她站在客廳的窗邊想著,真正的分歧已經(jīng)夠多了,非常多了。此刻她想到的是貧富懸殊、出身貴賤;對于偉大的出身,雖然不太情愿,但她還是懷有一些敬意,因為她血管里不正流淌著意大利名門望族那高貴又略帶神話色彩的血液嗎?意大利的名門閨秀,在十九世紀分散到英國各個家庭的客廳中,她們略帶口音的英語是如此迷人,她們脾氣火爆,而她的智慧、她的儀態(tài)、她的品性都傳承自她們,而不是遲鈍的英國人,或是冷漠的蘇格蘭人;然而更引起她深思的是另一個貧富懸殊的問題,以及她每日每周在這里或是倫敦親眼所見的那些事情——她手上挽著提包,親自去探望某位寡婦或者某位艱苦謀生的妻子,用筆記本和鉛筆仔細地一欄一欄記下每家每戶的收支情況和就業(yè)失業(yè)情況。她希望自己不再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女人,不希望自己做善事只是為了安撫內(nèi)心的憤怒,或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雖然沒有受過正規(guī)訓(xùn)練,但她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直以來非常敬佩的社會調(diào)查者,去研究社會問題。
她站在那里,拉著詹姆斯的手,覺得這些問題對自己來說似乎是無解的。那個被大家嘲笑的年輕人跟著她來到了客廳,站在桌子邊搗鼓著什么,尷尬窘迫、無所適從的樣子,她不用看就知道。他們都離開了——孩子們,明塔·道爾和保羅·瑞雷,奧古斯都·卡邁克爾,她的丈夫——他們都離開了。于是她轉(zhuǎn)過身來,嘆了口氣說道:“坦斯利先生,如果你不嫌麻煩,陪我出去一趟好嗎?”
她要進城去辦點瑣事,她有一兩封信要寫,她大概需要十來分鐘,她要戴上自己的帽子。十分鐘后,她又拿著籃子和陽傘出現(xiàn)了,一副做好準備、要去遠足的樣子。不過經(jīng)過網(wǎng)球場的時候,他們必須停一下,問問卡邁克爾先生是否需要些什么,他正在曬太陽,那雙貓眼似的黃色眼睛微張著,也像貓眼一樣,能夠反射出晃動的樹枝和天邊飄過的云朵,但卻不會透露出任何內(nèi)心的思緒或者情感。
他們要去遠征,她笑著說。他們準備進城。“郵票、信紙、煙草?”她停在卡邁克爾先生身旁的時候,試探地問了問。可是,不,他什么也不要。他的雙手緊扣在自己的大肚腩上,眨了眨眼睛,仿佛想要友好地回應(yīng)她的一片殷勤(她的確有魅力,可有點神經(jīng)質(zhì)),但他做不到,他身陷于一種灰綠色的睡意之中,無須言語,所有一切都籠罩在一種寬大仁慈的、充滿祝福的慵懶狀態(tài)之中;整棟房子、整個世界、所有人都沉浸其中,因為他在午餐時往杯子里偷偷放了幾滴東西,孩子們認為,那解釋了為什么他原本乳白色的胡須上有一道明顯的淡黃色痕跡。不,什么都不需要,他嘟囔著。
他們往漁村走的時候,拉姆塞夫人說,要不是卡邁克爾先生有過一段不幸的婚姻,他本該成為一位偉大的哲學(xué)家。她把黑色陽傘撐得筆直,臉上帶著一種難以描述的期待神情,她繼續(xù)往前走,好像要去轉(zhuǎn)角處見什么人。她講述了卡邁克爾先生的經(jīng)歷:在牛津時與一位姑娘墜入情網(wǎng);很早就結(jié)了婚;一貧如洗;去過印度;翻譯了一點詩歌,“我相信他譯得非常優(yōu)美”,愿意教男孩們波斯語或是梵文,但那又有什么用處呢?——然后就是像我們剛看到的那樣,躺在草坪上。
查爾斯·坦斯利受寵若驚。一直以來他都備受冷落,但拉姆塞夫人的這些話撫慰了他的內(nèi)心。他又打起精神。她剛才的那番話暗示著,即便在男性潦倒之時,她也能欣賞他們的才華;還暗示著所有妻子都應(yīng)該順從地支持丈夫的事業(yè)——并不是說她責怪那個女孩,她認為他們的婚姻也是很幸福的。她讓坦斯利自我感覺前所未有的好,如果他們乘坐出租車,他是樂意付車費的。至于她的小手提包,需要幫她拿嗎?不,不,她說向來都是自己拿著那個包的。的確如此。是的,他從她身上能感受到這一點。他感受到許多東西,有一樣讓他特別激動、興奮又心煩意亂,可至于是什么原因,他也說不上來。他希望她能夠看到自己穿上博士袍、戴上博士帽,走在畢業(yè)生列隊之中。成為一名研究員或是一名教授,他覺得自己無所不能,還看到自己——但她在看什么?她在看著一個男人貼海報。那幅在風中啪啪作響的巨型海報慢慢被貼平了,工人的刷子每揮動一下,就露出幾條新的大腿、一些鐵圈、馬匹,還有耀眼奪目的紅色、藍色……海報完美平整地鋪展開,直到馬戲團的廣告蓋滿了半個墻面——一百位馴馬師,二十頭參加表演的海豹、獅子和老虎……因為視力不好,拉姆塞夫人伸長脖子,念出聲來:“即將訪問本市。”她驚呼起來,對只有一條胳膊的人來說——他的左手兩年前被收割機切斷了——像那樣站在梯子頂端也太危險了。
“大家一起去!”她大喊一聲,繼續(xù)往前走,好像那些騎手和馬兒讓她充滿了孩子般的狂喜,讓她忘掉了之前對廣告工人的同情。
“我們?nèi)グ伞!彼舌舌俺鲞@幾個字,重復(fù)了她的話。不過他說話時的那種扭捏令她畏縮。“大家一起去看馬戲。”不,他說的不對。他沒有那種感覺。但是為什么呢?她覺得奇怪。他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她這會兒真的挺喜歡他的。她問道,難道小時候沒人帶你們?nèi)タ催^馬戲表演嗎?從來沒有,他回答,好像她剛好問了一個他盼望已久的問題,就像這些天他都在等待著傾訴自己小時候為什么沒能去看馬戲表演。他來自一個大家庭,九個兄弟姐妹,就靠父親一人工作。“拉姆塞夫人,我父親是藥劑師,開了一間雜貨店。”自打十三歲起,他就靠自己謀生。他經(jīng)常一整個冬天都沒有一件大衣。在大學(xué)時他從來也無法“回報別人的熱情款待”(這是他又干又硬的原話)。他必須讓自己的東西比其他人的耐用一倍;他抽最廉價的煙草、煙絲,就是碼頭上的老頭們抽的那一種。他拼命工作——一天工作七個小時。他現(xiàn)在研究的課題是某種事物對某人的影響——他們邊說邊往前走,拉姆塞夫人沒太聽懂他的意思,只是斷斷續(xù)續(xù)地聽到一些單詞——論文……研究員職位……高級講師職位……講師職位。她聽不懂那些他脫口而出、令人生厭的學(xué)術(shù)術(shù)語,但她暗自思忖,現(xiàn)在終于明白了,為什么去看馬戲表演這件事會讓他感到如此挫敗,可憐的小伙子,她也明白了為什么他立刻把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情況和盤托出。她會確保那些孩子們不再取笑他,她要把這個告訴普魯。在她看來,他更愿意跟外人說起的是自己如何與拉姆塞一家人去看易卜生的戲劇,而不是馬戲。他真是一個自命不凡的討厭鬼——噢,是的,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討厭鬼。現(xiàn)在他們雖然已經(jīng)到了城里,走在大街上,身旁駛過的馬車碾壓著路上的鵝卵石,但他仍然說個不停——關(guān)于將來的職業(yè)、教師、工人、幫助我們的階層,還有那些講座……直到她意識到他已經(jīng)完全找回了自信,已經(jīng)完全從馬戲團的打擊中恢復(fù)了,正準備(現(xiàn)在她又挺喜歡他了)告訴她——但是,此時,道路兩旁的房子已被遠遠拋在身后,他們已經(jīng)來到碼頭上,整片海灣展現(xiàn)在他們面前,拉姆塞夫人忍不住驚呼:“噢,實在是太美了!”她眼前是一望無垠的藍色大海,遠處是灰白色燈塔,遺世獨立于海水中央。而在右手邊,目光所及之處,那些綠色的沙丘身上披戴著游弋的野生水草,在海浪的沖洗之下,慢慢消失,坍塌成軟軟的、低低的小皺褶,看上去像是要逃離到某個無人居住的月亮國度。
她停下來說,丈夫愛的就是這里的風景,她那灰色眼珠的顏色變得更深了。
她安靜了片刻。但是這會兒,她說,藝術(shù)家已經(jīng)來過這里了。的確,在那邊,幾步之外就站著一個藝術(shù)家,戴著巴拿馬草帽,穿著黃靴子,神態(tài)嚴肅、柔和又專注。盡管有十個小男孩在旁圍觀,他圓圓的紅臉蛋上還是流露出無比滿足的神情,他凝視著眼前的景色,等看完后,就用畫筆筆尖蘸一下柔和的綠色或粉色顏料。自從三年前龐斯福特先生來這里后,所有的畫都長那樣,她說,綠色和灰色混在一起,點綴著一些檸檬黃色的帆船和海灘上的粉色女士。
他們經(jīng)過畫家的時候,她偷偷瞥了幾眼說,她祖母的朋友們最辛苦了,首先他們要自己混顏料,然后磨碎,之后為了讓顏料保持濕潤的狀態(tài),要用濕布把它們蓋起來。
所以坦斯利先生猜想,她是想讓他看看那個男人的畫太平淡了,人們是這么說的嗎?顏色不夠豐滿?人們是這么說的嗎?自從他在花園里想要幫她拿包后,就逐漸萌生出這樣一種感情;在他們進城之后,他想要向她坦白關(guān)于自己的一切之時,這股感情逐漸增強,隨著一起散步,這一路下來,感情不斷發(fā)展,在這股強烈感情的影響下,他越發(fā)能看清自己,而以前所了解的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這實在太奇怪了。
他站在這個狹窄的小房子的客廳里等著她,是她帶他來的,現(xiàn)在她需要一點時間到樓上去見一個女人。他聽到樓上傳來她快速的腳步聲,聽到她愉快的聲音,然后對話聲低了下來。他看著那些地毯、茶葉罐還有玻璃罩,等得有點不耐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回家,下定決心要在回家的路上替她拿包。然后他聽到她出來了,關(guān)上門,對房間里的人說,必須要把窗戶開著、把門關(guān)上,然后對著房子問,他們是否需要什么東西(她肯定是在和一個孩子說話)。突然之間,她走了過來,安靜地站了一會兒(就好像她剛才在樓上的表現(xiàn)都是假裝的,而現(xiàn)在需要一點時間讓自己恢復(fù)正常),她一動不動地站在維多利亞女王的畫前,畫中的女王佩戴著嘉德勛章的藍色緞帶,他突然之間意識到那種不可名狀的感情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她是他見過的最美麗的人。
她眼中閃爍著星辰,頭上披戴著面紗,還有櫻花草和野紫羅蘭——他在胡思亂想些什么?她至少有五十歲了,她生過八個小孩。她穿過鮮花綻放的田野,懷抱著凋零的花蕾和迷失的羊羔;她眼里閃著星光,微風拂過她的發(fā)絲——他拿起了她的包。
“再見了,艾爾西。”她說,然后他們走到街上,她把陽傘舉得筆直,走路的樣子像是會在街角遇到熟人,而對查爾斯·坦斯利來說,他有生之年第一次感到無比驕傲;一個正在挖排水溝的男人停下來看著她,任憑自己垂著胳臂,就這樣看著她;查爾斯·坦斯利有生之年第一次感到無比驕傲,因為他正和一位美麗的女性一同散步,感受到了迎面吹來的風,還有櫻花草和野紫羅蘭。他替她拿著手提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