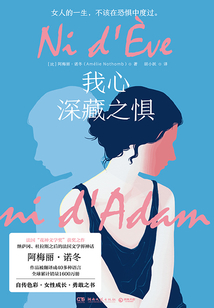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譯者序
阿梅麗·諾冬(Amélie Nothomb)是比利時法語作家,也是當今法語文壇最活躍、最受矚目的作家之一。自一九九二年出版處女作《殺手保健》以來,她一年出一本書,年年轟動,本本暢銷,成了歐洲文學界的“神話”。她的作品已被譯成四十多種語言,其中不少已被拍成電影或改編成戲劇,在歐美舞臺上上演。她的作品獲獎無數,包括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等。她的作品片段已被收進法國、加拿大和比利時的教科書,她的名字也被收入法國著名的《小羅貝爾詞典》,她的頭像還曾被印在比利時的郵票上。現在不少國家都出現了研究其作品的論文,研究她的專著也越來越多,這標志著她已進入當代一流作家的行列。二〇一五年,她被選為比利時法語語言與文學皇家學院成員,以表彰她“作品的重要性、她的獨創性和邏輯性,以及她在國際上的影響”。
阿梅麗·諾冬原名法比安娜·克萊爾·諾冬,一九六七年生于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郊區小鎮埃特貝克的一個外交官家庭。諾冬家族是當地的望族,歷史上出過許多政治與文化名人。阿梅麗幼年時就隨父母輾轉于亞洲多個國家,先后在日本、中國、老撾、孟加拉國、緬甸等國生活與居住,直到十七歲才回歐洲繼續上學。讀完文科預科,她進入著名的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學法律,但她不喜歡,僅讀了一年,就轉學哲學與文學,因為她迷上了尼采和法國作家喬治·貝爾納諾斯[1]。
大學畢業后,她的父親又被任命為比利時駐日本大使,她也再次回到小時候生活了好多年的日本,進入一家日本企業工作,當譯員。她原先把自己當作半個日本人,認為日本是自己的半個祖國,卻不料東西方文化的沖突使她無所適從,讓她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她仿佛成了一個邊緣人和“無國界人士”。這段經歷使她日后寫出了一部杰作——《誠惶誠恐》。
諾冬喜歡寫作,每天必須寫四小時以上,每年都寫三四本書,至今仍是如此。一九九二年,二十五歲的她從抽屜里選了一部自己比較滿意的書稿——《殺手保健》,寄到了她所崇敬的法國伽利瑪出版社,卻不料被該社權威的審讀員菲利普·索萊爾斯直接拒絕了,那位“文壇教父”認為這個小女子對老作家大為不敬,竟敢如此調侃和嘲笑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作家。諾冬只好另找門路,她的一個朋友替她把稿子送到了法國另一家大出版社——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該社的審讀班子讀了書稿以后一致叫好,老板馬上拍板錄用,并一口氣跟她簽了四本書的合同。諾冬并不心慌,她抽屜里有的是書稿。
《殺手保健》出版之后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成了當年的暢銷書之一,還在第二年、第三年連續獲獎。法國的媒體驚呼“文壇上出了一個天才”,諾冬一下子就出名了。一九九三年,諾冬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說《愛情與破壞》,并獲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燃料》是諾冬迄今為止所創作的唯一的劇本,大概是在《殺手保健》中沒有過夠對話癮。該劇本寫的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天,三個垂死者把自己關在公寓里,盡自己的最后力量閱讀和選擇圖書,把他們認為不好的書扔進火中。他們還能活多久?他們之間有些什么秘密?他們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讀書、焚書?種種疑團籠罩著全書。《午后四點》是諾冬的第三部小說,出版于一九九五年,寫的是一對老年夫婦為安度晚年而隱居在一個偏僻的鄉下,卻天天被一個自稱醫生的鄰居騷擾。讀者能感受到,面對空虛和失望時,文明和禮貌是多么軟弱無力。該書曾被法國《讀書》雜志評為當年二十本最佳圖書之首,不少人把它當作諾冬的代表作,認為其可與《殺手保健》媲美。
諾冬雖然每年都寫幾本書,但每年只出版一本,永遠是在同一家出版社,永遠是在同一個季節。從一九九二年出道至今,她已出版了二十八本書。縱觀她的全部作品,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自傳性小說,主要寫自己的經歷與身世,如《愛情與破壞》《誠惶誠恐》《管子的玄思》《饑餓傳》《我心深藏之懼》等。這類小說以基本事實為依據,主人公有時甚至與她自己同名,她偶爾也會悄悄地加上一些虛構的東西。她在這些書中表達了對自己所生活過的地方的愛與恨、懷念與追憶、諷刺與批評,并不惜自嘲,但更多的還是在尋找自己的身份與歸屬感。作者常常用調侃的語言、幽默的語氣和近乎荒誕的情節,通過自己的故事,來探尋活著的意義和生存的矛盾。
另一類是純虛構的小說,靈感來自多方面,可以是哲理名言和歷史故事,也可以是音樂或童話,有時也受現實生活的啟發。《某種活法》的背景是伊拉克戰爭,《硫酸》反映的是電視直播和大眾傳媒。在這類作品中,主人公大多是一個年輕的知識女性,智慧、機敏、勇敢,思辨能力強,口齒伶俐,如《殺手保健》中的女記者尼娜,《老人·少女·孤島》中的女護士弗朗索瓦絲,《藍胡子》中的薩圖尼娜。其對手往往是年老丑陋的男性,或富有,或權威,但虛偽、霸道、粗野、強大,不過最后都敗在這位美麗智慧的年輕女性手里。有時,主人公也可能是一個天真、善良、乖巧、誠實的女孩,而她的對手是與她年齡相仿的女孩或稍大的女性,或是同學,或是伙伴,或是老師,但性格和品德與她完全相反,如《反克里斯塔》中的“我”和克里斯塔、《硫酸》中的帕諾尼克和澤娜、《敲打你的心》中的狄安娜和奧麗維婭。
諾冬的小說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情節,也沒有宏大的背景,人物不多,不涉及重大題材,書中探討的往往是生活中常見的命題:友誼與背叛、美與丑、善與惡、道德與虛偽、正義與非正義。愛情、死亡和哲理構成了諾冬大部分小說的支點,而把它們連接起來的,是敏銳的觀察、犀利的語言、巧妙的思辨和無處不在的黑色幽默。這就使她的小說殘酷而不殘忍,灰色而不灰暗,深刻而不晦澀,愛情始終在某處招手,驅使著人們去冒險、去搏擊、去不擇手段、去鋌而走險。
在《殺手保健》中,老作家殺的是他深愛的表妹,理由是,他太愛她了,不想讓她受到玷污。在《老人·少女·孤島》中,少女阿彩被囚禁在一個孤島上,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一個粗魯的老船長,她以為自己奇丑無比,其實美若天仙。老船長為了把她牢牢地抓在手里,才騙她說她被毀了容。在《公害》中,一個奇丑的男人為社會所不齒,到處受排擠,沒有人愿意與他為伴。他受盡折磨、奚落和嘲笑,后來卻成了國際法庭的大法官和選美評委會的評委,這使他得以對社會的公正和美做出新的解釋,而愛神也隨之降臨在他的身上。在《刺客》中,主人公埃皮法尼也是一個丑得不能再丑的人物,綽號叫“卡西莫多”,他暗戀上了一個漂亮的女演員愛泰爾。愛泰爾喜歡他,卻不愿意嫁給他,因為他太丑。埃皮法尼這才明白,自從有了人類之愛,丑人就沒有過位置。為了報復,更多是為了占有美,他用愛泰爾扮演斗牛時用的道具牛角刺死了他心愛的人,為王爾德的一句名言做了注解:“每個人都會殺死自己的所愛。”《反克里斯塔》寫的是一個壞女孩的故事,她壞得可以用各種貶義詞來形容,作者在書中揭示了惡的可氣可恨之處,展現了它的破壞力和欺騙性,并告訴讀者,要戰勝惡,不光需要勇氣和力量,更需要智慧。《冬之旅》中的主人公佐伊勒在愛情中找到了美,但這種美不愿放棄丑,也就是說,在得到美的同時也必須接受丑。面對這種艱難的抉擇,他很彷徨、痛苦、猶豫,但最終決定寧愿毀滅美也絕不與丑同流合污,由此踏上了一條不歸路。美與丑、善與惡在《硫酸》中也一直在進行斗爭,只是這一次斗爭的方式有些奇特。女獄卒澤娜無疑是丑惡的化身,但惡并不是不能被改造的,小說的最后,澤娜在帕諾尼克的說服、感化和影響下,終于洗心革面,做出了壯舉。而《午后四點》是在埃米爾和貝爾納丹的斗智斗勇中展開的,兩人像是在玩推手,一推一擋,你來我往,較量了許多個回合。諾冬是學哲學出身的,不滿足于在書中講故事、玩小聰明,而是更喜歡在書中展示自己的學識,引經據典,把歷史、宗教、神話、哲學和文學等方面的內容穿插在字里行間。故事講述到一半,她開始探討起禮貌、虛空、善惡等問題來,妙語奇思也隨之而來。
語言是諾冬的小說中最讓人享受的東西之一,尤其是人物對話,她的許多小說幾乎全以對話組成,如《殺手保健》《敵人的美容術》《藍胡子》《歷史影片》等。作者用對話編織了一個個巧妙、曲折而神秘的故事,光是對話本身就足以吸引讀者。作品中正方反方高手過招,唇槍舌劍,妙語連珠。諾冬的語言是智慧的,也是辛辣的;諷刺是無情的,又充滿了幽默。《午后四點》中的貝爾納丹太太睡覺時會發出巨大的呼嚕聲,自己卻睡得很沉,“如果她自己發出的響聲都不能吵醒她,那就沒有什么東西能吵醒她了”;貝爾納丹家里臭氣熏天,偏偏又不開窗,“他們的窗戶總是關著的,好像怕浪費他們寶貴的臭味”。《冬之旅》中,劫機這種瘋狂而恐怖的行為,在諾冬的筆下,竟有種滑稽的感覺,對從安檢搜身、廁所清潔到等待登機的寫作,都讓人覺得這場死亡之旅并不是去制造災難,而是去演出一場喜劇。對往昔的回憶、對動機的探討、對結果的想象,使一本驚險小說慢慢地變成了哲理小品和愛情詩篇。
諾冬的小說篇幅都不長,結構相對簡單,線索也不復雜,情節卻一波三折,使讀者看了一半也猜不到故事的結局,甚至與當初想象的完全相反。《殺手保健》中的前四個記者都被博學善辯的塔施反駁得落荒而逃,就在讀者以為塔施必勝無疑時,小說出現了反轉,第五個記者——一個柔弱的女子上場了,她抓住了塔施的要害,逼其就范,揭露出驚天秘密:那個大名鼎鼎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竟然是個殺人犯。誰也想不到,《某種活法》中那個自稱在伊拉克前線作戰、喜歡讀諾冬小說的美國大兵,完全是一個躲在鄉下大吃大喝、消沉懶惰、胖得出不了門的冒牌軍人。
諾冬的小說結局雖然難猜,但大多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殺人。無論是多么溫情的故事,有多么溫和的人物,小說最后都會出現命案。誰也沒想到,《敲打你的心》這本與謀殺、戰爭相距甚遠的“情感小說”,最后也出現了命案,只是死法有些特殊,奧麗維婭這位心臟病專家的胸口被扎了二十多刀。《羅貝爾專名詞典》的主人公是一個名叫普萊克特魯德的小女孩,從小沒有父母,母親生下她后殺死了丈夫,然后自殺身亡。《午后四點》中的貝爾納丹好不容易鼓足勇氣自殺,卻被埃米爾救下,但為了成全他,埃米爾最后只得自己充當兇手。在這里,殺人再次成了助人的善舉,就像《殺手保健》中的那個女記者和《敵人的美容術》中的杰洛姆。《藍胡子》也一樣,死是免不了的,惡必須根除。這些小說充滿了神秘氣氛和冷幽默,貫穿著歷史與宗教知識,也不乏戲言,懸念很足,引人入勝。《刺客》中當然也要死人,當埃皮法尼遭到愛泰爾的拒絕,并且真相被揭穿時,他便動手行刺了,從而成全了諾冬的又一部以溫柔開場、殺人結束,全文貫穿著幽默、自嘲、諷刺和哲理思辨的小說。
怪異奇特的書名、人名也是諾冬小說的一個特點。她的書名里有很多是不可譯的,硬譯過來也會讓人不知所云、莫名其妙,如《老人·少女·孤島》法語書名為Mercure(水銀,信使,墨丘利神),《午后四點》的法語原名為Les Catilinaires(敵意的語言或尖銳的諷刺),《誠惶誠恐》的法語原名為Stupeur et Tremblements(驚愕與顫抖),《我心深藏之懼》的法語原名是Ni d'Eˋve ni d'Adam(既非夏娃,也非亞當)。她小說中的人名也是如此,往往很長,很罕見。《羅貝爾專名詞典》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名叫普萊克特魯德的小女孩,《藍胡子》中的男主人公叫堂·艾雷米里奧,《殺手保健》中的文豪叫普雷泰克斯塔·塔施,還有《敵人的美容術》中的泰克托爾·泰克塞爾……這些名字看似與主題無關,其實并非如此,只是要花心思去琢磨,如同她在書中引用和提及的那些句子或故事,雖有炫耀之嫌,但不懂一點哲學、歷史、宗教、文學,還真會被蒙在鼓里。她的書名好像信手拈來,其實也并不盡然,它們可能源于某一哲學理論、某個神話、某種傳說或某個典故。據《法語詞源詞典》的作者瓦爾特·馮·瓦特堡考證,“Ni d'ˋEve ni d'Adam”這個句子源于一七五二年的一個法國俗語,意思是“不認識,不知道,從來沒有聽說過,哪怕是追溯到亞當夏娃的時代”。“Les Catilinaires”則源自古羅馬的一段歷史:羅馬貴族喀提林(Catiline)多次策劃陰謀,但屢屢被西塞羅挫敗。西塞羅訓斥喀提林的演說非常著名,后來“斥喀提林”便成了一個名詞。諾冬選用這個詞做書名,不排除有戲謔的成分,但也不能說它與小說完全無關,小說中的埃米爾不是曾學西塞羅滔滔不絕、高談闊論,試圖以另一種方式戰勝貝爾納丹嗎?讀諾冬的小說是愉快的,她幽默的語言、奇妙的構思和獨特的敘述方式常常讓人手不釋卷——當然,這是小聰明,不是大智慧,是小作品,不是大手筆。但她的小說輕松而不膚淺,輕快而不乏犀利,篇幅不長但可以反復咀嚼和品味,她做的是家庭小炒,但她會把小菜做得漂漂亮亮。諾冬的小說似乎好懂,翻譯起來卻很不容易,很多地方原先以為讀懂了,細細再讀,才發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的文字中潛伏著太多的言外之意,正如她在情節中設置了太多的陷阱一樣。讀她的書,翻譯她的書,都是一種智力游戲,稍有不慎,就會上當,她則像書中的女主人公那樣,壞壞地躲在一旁偷笑。譯者有幸多次見到作者本人,尤其是二〇〇六年,譯者在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實習數月,諾冬在那兒有一個辦公室,她每天上午來拆看和回復讀者來信,譯者得以不時與她交談,向她請教翻譯中的問題,和她一起喝咖啡,談她小時候在北京的故事。生活中的諾冬真誠、爽直,并不像書中的“她”那樣難以捉摸。
胡小躍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