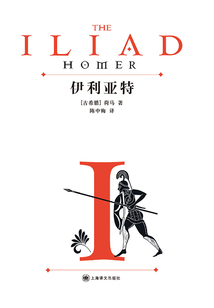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
陳中梅
荷馬的身世向來撲朔迷離。有西方學者甚至懷疑歷史上是否確有荷馬其人。英國詩人兼文論家馬修·阿諾德曾用不多的詞匯概括過荷馬的文風,其中之一便是“簡明”(simplicity)。然而,這位文風莊重、快捷和簡樸的希臘史詩詩人卻有著不簡明的身世,給后人留下了許多不解其“廬山真面目”的疑團。首先是他的名字。Homeros不是個普通的希臘人名。至少在希臘化時期以前,史料中沒有出現過第二個以此為名的人物。Homeros被認為是homera(中性復數形式)的同根詞,可作“人質”解。Homeros亦可拆解作ho me(h)oron,意為“看不見(事物)的人”,亦即“盲人”。這一解析同樣顯得勉強,也許是根據《奧德賽》里的盲詩人德摩道科斯所作的類推,把荷馬想當然地同比為古代歌手中不乏其人的瞽者。細讀史詩,我們會發現荷馬有著極為敏銳的觀察力,對色彩的分辨尤為細膩。荷馬的名字還被解作短詩的合成者。有學者試圖從Homeridai(荷馬的兒子們,荷馬的后代們)倒推homeros的成因,所作的努力值得嘉許。然而,此類研究也可能走得過遠。比如,歷史上曾有某位英國學者,此君突發奇想,竟將Homeros倒讀為Soremo,而后者是Soromon的另一種叫法,由此將荷馬史詩歸屬到了一位希伯來國王的名下。應該指出的是,從字面推導含義是西方學者慣用的符合語文學(philology)常規的做法,即便嘗試倒讀人名,也算不得十分荒唐,只是由此得出的結論可能與事實不符乃至南轅北轍,這是我們應該予以注意的。
即便承認荷馬確有其人,他的生活年代也充滿變數,讓人難以準確定位。學者們所能做的,只是提出并滿足于自以為能夠自圓其說的設想(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延伸評估)。從特洛伊戰爭時期(一般認為,戰爭的開打時段在公元前十三世紀至公元前十一世紀之間)到戰爭結束以后不久,從伊俄尼亞人的大遷徙到公元前九世紀中葉或特洛伊戰爭之后五百年(一說一六八年),都被古人設想為荷馬生活和從藝的年代。史學家希羅多德認為,荷馬的在世時間“距今不超過四百年”,換言之,大約在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歷史》2.53);而他的同行修昔底德則傾向于前推荷馬的創作時間,將其定位于特洛伊戰爭之后,“其間不會有太遠的年隙”(《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3)。荷馬到底是哪個“朝代”的人氏?我們所能找到的“外部”文獻資料似乎不能確切回答這個問題。另一個辦法是從荷馬史詩,即從“內部”尋找解題的答案。大量文本事實表明,荷馬不生活在邁錫尼時期,因此不可能是戰爭的同時代人。從史詩中眾多失真以及充斥著臆想和猜測的表述來看,荷馬也不像是一位生活在戰爭結束之后不久的“追述者”。由此可見,希羅多德的意見或許可資參考。但是,考古發現和對文本的細讀表明,希羅多德的推測或許也有追求“古舊”之虞。《伊利亞特》6.302—303所描述的塑像坐姿似乎暗示相關詩行的創編年代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八世紀;11.19以下關于阿伽門農盾牌的細述,似乎表明這是一種公元前七世紀以后的兵器;而13.131以下的講述更給人“后期”的感覺,因為以大規模齊整編隊持槍陣戰的打法有可能盛行于公元前七世紀末以后。著名學者沃爾特·布爾克特(Walter Burkert)將《伊利亞特》的成詩年代推遲到公元前六六〇年的做法[1],似乎沒有得到學界的廣泛贊同。荷馬史詩自有他的得之于歷史和文學傳統的古樸性,零星出現的后世資證和著名學者的“靠后”評論,都不能輕易改變這一點。綜觀“全局”,我們認為,把荷馬史詩的成篇年代定設在公元前八世紀中葉或稍后比較適宜,其中《奧德賽》的成詩或許稍遲一些,可能在公元前八世紀末或前七世紀初。事實上,這也是許多當代學者所持的共識。大致確定了荷馬史詩的成詩時期,也就等于大致確定了荷馬的生活和活動年代。如果古希臘確實出現過一位名叫荷馬的史詩奇才,那么他的在世時間當在公元前八世紀——這一時段定位或許比別的推測更接近于合理,更少一些由于年代的久遠和可信史料的匱缺(以及誤讀史料)所造成的很難完全避免的草率。
荷馬的出生地在哪兒?這個問題同樣不好準確回答。《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均沒有提供現成的答案,公元前八世紀至前七世紀也沒有在這方面給我們留下任何可以作為信史引證的第一手資料。據說為了確知荷馬的出生地和父母是誰,羅馬皇帝哈德里安還專門求咨過德爾菲的神諭[2]。在古代,至少有七個城鎮競相宣稱為荷馬的出生地,并且似乎都有各自的理由。它們是斯慕耳納(現名伊茲米爾)、羅德斯、科羅豐、(塞浦路斯的)薩拉彌斯、基俄斯、阿耳戈斯和雅典。能夠成為荷馬的鄉親,自然是個莫大的榮譽,尤其是在公元前六世紀以后,詩人的名望鼎盛,如日中天。但是,荷馬的出生地畢竟不可能多達七處,否則我們將很難把他當做一介凡人(只有神才可能有那樣的“分身術”)。希臘文化的傳統傾向于把荷馬的故鄉劃定在小亞細亞西部沿海的伊俄尼亞希臘人的移民區。任何傳統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荷馬對伯羅奔尼撒的多里斯人所知甚少,表明他不是從小在那個地域土生土長的。此外,《伊利亞特》中的某些行段(比如9.4—5,11.305—308)暗示他的構詩位置可能“面向”希臘大陸(或本土),即以小亞細亞沿海為“基點”。荷馬所用的明顯帶有埃俄利亞方言色彩的伊俄尼亞希臘語,也從一個側面佐證著他的出生地不在希臘本土或羅德斯等地。再者,作為一個生長在小亞細亞的希臘人,荷馬或許會比生活在希臘本土的同胞們更多一些“國際主義”精神,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敘事的中性程度以及不時流露出來的對敵人(即特洛伊人)的同情心里看出來。上述原因會有助于人們把搜尋的目光聚集到小亞細亞沿海的斯慕耳納和基俄斯,與傳統的認識相吻合。我們知道,阿耳戈斯曾是個強盛的城邦,而公元前六世紀以后,雅典逐漸成為希臘的文化中心和書籍發散地(阿里斯塔耳科斯就認為荷馬是雅典人),但歷史和文本研究都不特別看好這兩個地方,所以即使在古代,它們的競爭力也不甚強勁,無法與基俄斯等地相抗衡。基俄斯的西蒙尼德斯設想基俄斯是荷馬的出生地(片斷29;他稱荷馬是一個“基俄斯人”〈Chios aner〉);事實上,那兒也被古代文論家認為是“荷馬后代們”(Homeridai)發跡并長期誦詩從業的地方。在古代,荷馬被認為是史詩作者(或詩人)的代名詞,所有的“系列史詩”(如《庫普里亞》、《埃塞俄丕亞》和《小伊利亞特》等)以及眾多的頌神詩(如《阿波羅頌》和《赫耳墨斯頌》等)都被認為出自荷馬的憑借神助的天分。基俄斯詩人庫奈索斯創作了《阿波羅頌》,但卻并不熱衷于擁享作品的署名權。不僅如此,他似乎還有意充分利用人們對荷馬的感情,憑借人們對荷馬的印象,宣稱該詩的作者是一位“來自山石嶙峋的基俄斯的盲(詩)人”(tuphlos aner,《阿波羅頌》172)。庫奈索斯的做法當然可以理解,因為他不僅是基俄斯人,而且還是當地“荷馬后代們”的首領,率先(公元前五〇四年)向遠方輸出荷馬的作品,在蘇拉庫賽(即敘拉古)吟誦“老祖宗”的史詩。哲學家阿那克西美尼相信荷馬的家鄉在基俄斯,但史學家歐伽蒙和學者斯忒新勃羅托斯則沿用了公元前五世紀同樣流行的荷馬為斯慕耳納人的傳聞。抒情詩人品達的“視野”似乎更顯開闊,既認為荷馬是斯慕耳納人(片斷279),也愿意“折中”,即接受荷馬同時擁有基俄斯和斯慕耳納雙重“國籍”的提法。有人認為荷馬出生在斯慕耳納,但在基俄斯完成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創作。相傳荷馬卒于小島伊俄斯,該地每年一次,在一個以荷馬名字命名的月份,即Homereon里用一只山羊祭奠詩人的亡靈。
荷馬的名字絕少見于公元前七世紀的作品史料。學問家鮑桑尼阿斯(生活在公元二世紀)在談到史詩《塞貝德》時寫道:“卡萊諾斯曾提及這部史詩,并認為此乃荷馬所作。”(ephesen Homeron ton poiesanta einai,《描述希臘》9.9.5)一般認為,卡萊諾斯即為厄菲索斯詩人卡利諾斯,其活動年代在公元前七世紀上半葉,以擅作對句格詩歌著稱。如果卡萊諾斯即為卡利諾斯的推測不錯,那么鮑桑尼阿斯的引文或提及很可能是現存惟一的一則比較可信的可資論證一位公元前七世紀詩人提及(原作當然早已佚失)荷馬名字的珍貴史料。需要指出的是,卡利諾斯不太可能稱荷馬創編了《塞貝德》,因為這部史詩的成文年代很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紀。卡利諾斯的意思或許是,他知曉發生在塞貝的戰事,而荷馬作為一位史詩詩人,編述過關于那場戰爭的故事[3]。一位生活年代不遲于公元三世紀的拜占庭評論家曾提及阿耳基洛科斯的觀點(片斷304W.),稱這位詩人相信《馬耳吉忒斯》乃荷馬的作品。阿耳基洛科斯同樣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紀,但考證表明《馬耳吉忒斯》的創作年代當在公元前六世紀初以后,所以拜占庭評論家的論述顯然有誤,與事實不符。阿耳基洛科斯或許知曉荷馬,但他的詩作已基本佚失,使我們無法就此進行準確的辨析。有趣的是,“傻瓜史詩”《馬耳吉忒斯》長期被古代文家們認定為荷馬的作品。我們知道,遲至公元前四世紀,像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大文論家依然對此深信不疑,將《馬耳吉忒斯》看作是喜劇的“前身”(參閱《詩學》4.1448b38—1449a2,另參考《尼各馬可斯倫理學》6.7.1141a14)。同樣偽托公元前七世紀詩人提及荷馬的還有另一見例。著述家菲洛科洛斯(出生在公元前三四〇年以前)引用過據說是出自赫西俄德的三行詩句(片斷〈dub〉357M.—W.),其中包括“我與荷馬在德洛斯高歌”,“唱頌萊托之子、持金劍的福伊波斯·阿波羅”等詞語。菲洛科洛斯肯定是憑借道聽途說編敘的,他的離奇說法在古代就沒有什么信奉者,當代學者更不會把它當作嚴肅的史料加以引用。赫西俄德確曾參加過詩歌比賽并且獲獎,但地點是在卡爾基斯,不是在德洛斯,而他的對手應該也不是荷馬,否則很難相信他會在對那次歌賽的記述中放過這一宣揚自己的絕佳素材,不予提及(參閱《工作與時日》654—659)。盡管如此,在公元前七世紀,荷馬不是默默無聞的。據說詩人忒耳龐德耳曾在斯巴達吟誦荷馬的詩作,圖耳泰俄斯、阿爾克曼和阿耳基洛科斯等詩人也都吟誦過《伊利亞特》或《奧德賽》里的詩行。也就在同一時期,《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里的某些內容已見諸瓶畫。應該指出的是,上述詩人的引詩有可能出自公元前八世紀以前即已成詩流行的短詩,而這些詩段也是荷馬用以加工并構組長篇史詩的原材料。同樣,瓶畫藝術家們也可能取材于荷馬史詩以外內容近似的故事,進行高度的藝術概括后,使其成為可視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景觀形象。
荷馬的得之于傳統的歷史真實性在公元前七世紀沒有受到懷疑。盡管如此,荷馬的名字在那個時期成文的作品中非常罕見,這或許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文人們的疑慮,也可能與存世作品的稀少不無關系。公元前六世紀初以后,這種情況發生了質的改變,荷馬名字的出現率大幅度提升,仿佛人們突然意識到荷馬的重要,覺得既然可以隨意復誦或吟誦他的詩行,就不必忌諱提及他的名字,不必再對荷馬的歷史真實性存有戒心。或許,“荷馬后代們”的活動逐漸開始發揮作用,不斷擴大著荷馬的影響,最終會同其他因素,使荷馬的名字進入千家萬戶,成功塑造了一位“詩祖”的形象。在公元前六世紀下半葉,荷馬是否確有其人已經不是問題。人們熱衷于關注的是荷馬的功績(以及功績有多大),此外便是他的過錯。人們開始評論荷馬。有趣的是,得以傳世至今的對荷馬及其詩歌最早的評論,不是熱切的贊頌,而是無情的批評。科洛豐詩人哲學家塞諾法奈斯抨擊荷馬和赫西俄德的神學觀,指責他們所塑造的神明是不真實、有害和不道德的(片斷11、14、15)。大約三四十年之后,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以更嚴厲的措詞狠批荷馬,認為荷馬應該接受鞭打,被逐出賽詩的場所(agones,片斷42)。據傳畢達哥拉斯曾在地府里目睹過荷馬遭受酷刑的情景。故事的編制者顯然意在告訴世人:荷馬為自己對神祇的不體面描述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此類傳聞荒誕不經,自然不可信靠,這里略作提及,或許可從一個側面說明后世某些哲人對荷馬以及由他所代表的詩歌文化的憎恨程度。公元前六世紀,新興的邏各斯(logos)及其所代表的理性思想開始在希臘學界精英們集聚的城邦里傳播,哲人們顯然已不滿于荷馬史詩對世界和神人關系的解釋,迫切想用能夠更多反映理性精神的新觀點取代荷馬的在他們看來趨于陳舊的“秘索思”(mythos,“詩歌”、“故事”)。在新舊思想碰撞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哲學對詩歌的批評,自然會把攻擊的矛頭對準荷馬,這一點不足為怪。當然,哲人們本來或許可以把語氣放得溫和一點,這樣既可以顯示風度,又能給從來無意攻擊哲學的詩歌保留一點面子,還能為自己日后向詩歌的回歸(至少是靠攏,如或許指望用自己的詩性哲學取代荷馬的傳統詩教的柏拉圖所做的那樣)提前準備一條退路。
真正有意將荷馬掃地出門的哲學家只是極少數。荷馬對希臘哲人的潛在和“現實”影響是巨大的。我們不敢斷定希臘哲學之父泰勒斯在提出水乃萬物之源觀點之前是否受過荷馬關于大洋河俄開阿諾斯是眾神之源的見解(《伊利亞特》14.246)的啟示,但后世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某些成員熱衷于引用荷馬的詩行以論證自己觀點的做法,卻是古典學界廣為人知的事實。蘇格拉底的老師阿那克薩戈拉斯對荷馬史詩的喻指功能興趣頗濃,而他的再傳弟子亞里士多德對荷馬的敬重和贊揚更是有目共睹。我們知道亞里士多德曾賦詩贊美過老師柏拉圖,但比之他在《詩學》里熱情謳歌荷馬及其史詩的話語,他對柏拉圖的贊揚不僅顯得零碎,而且肯定不夠具體。就連有意把荷馬史詩逐出理想國的柏拉圖本人,也對荷馬懷有深深的景仰之情,并且會在行文中情不自禁地信手摘引他的詩句,以佐證自己的觀點。柏拉圖對荷馬史詩的喜愛一點也不亞于奧古斯丁對維吉爾作品的喜愛,只是二者都出于維護各自政治和宗教理念的需要,不得不努力遏制自己的“情感”,服從“理性”的支配,轉而攻擊或批判自己原本喜愛的詩人。
就在少數哲人批貶荷馬的同時,詩人們卻繼續著傳統的做法,就整體而言保持并增加著對荷馬的信賴和崇仰。西蒙尼德斯贊慕荷馬的成就,認為由于荷馬的精彩描述方使古代達奈英雄們的業績得到了彪炳后世的傳揚。在說到英雄墨勒阿格羅斯在一次投槍比賽中獲勝的事例時,他提到了荷馬的名字,用以增強敘事的權威性:“荷馬和斯忒西科羅斯便是這樣對人唱誦的。”(參閱《對句格詩》11.15—18,19.1—2,20.13—15)埃斯庫羅斯謙稱自己的悲劇為“荷馬盛宴中的小菜”(阿塞那伊俄斯《學問之餐》8.347E)。我們了解埃斯庫羅斯對悲劇藝術的卓越貢獻,認可他的作品所取得的高度的藝術成就。他之所以這么說,固然是考慮到荷馬史詩的規模和數量(在當時,荷馬被普遍認為不僅僅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但同時可能也是出于他對荷馬的敬重和嘆服。他不認為自己的成就可以與荷馬相提并論,故用了“小菜”(或“肴屑”)一詞。當然,從埃斯庫羅斯的形象比喻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納入荷馬的“系統”(柏拉圖稱荷馬為第一位悲劇詩人),以能夠成為荷馬傳統的一部分而感到光榮。事實上,無論是從思想感情還是氣質或(行文)“品格”來評判,埃斯庫羅斯都秉承了荷馬的遺風,是最具荷馬風范的悲劇詩人。喜劇大師阿里斯托芬同樣崇仰荷馬。他贊賞荷馬的博學,不懷疑他在希臘民族中所處的當之無愧的教師地位,譽之為“神圣的荷馬”(theios Homeros,《蛙》1034)。抒情詩人品達摘引荷馬,贊同當時流行的荷馬是史詩《庫普里亞》作者的觀點(從現存的史料來看,希羅多德是把《庫普里亞》刪出荷馬作品的第一人,《歷史》2.117),并稱荷馬把這部史詩作為陪嫁,將女兒嫁給了庫普里亞(即塞浦路斯)人斯塔西諾斯。品達對荷馬并非沒有微詞,但是,他的批評是含蓄而合乎情理的,有別于同樣多次提及荷馬的赫拉克利特對他的惡毒攻擊(當然,在崇尚言論自由的古希臘,這么做是允許的)。品達認為,荷馬拔高了古代英雄們的形象,以他典雅和瑰美的詩句使奧德修斯受到了過多的贊揚(《奈彌亞頌》7.20—21)[4]。
希羅多德引用荷馬史詩十一個行次。此外,作為書名,《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最早見諸他的著述(《歷史》5.67)。修昔底德引《伊利亞特》僅一個行次,但引《阿波羅頌》的詩行卻高達十三例。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是把《阿波羅頌》當作荷馬史詩加以引用的。這表明他也像許多前輩文人一樣,將包括《阿波羅頌》在內的我們今天稱之為《荷馬詩頌》的眾多頌神詩都看作是荷馬的作品。這種情況在公元前四世紀發生了改變。亞里士多德似乎已不認為《阿波羅頌》是荷馬的詩作,盡管他仍然把《馬耳吉忒斯》歸入荷馬的名下。當柏拉圖和塞諾芬提及荷馬史詩時,他們的指對一般均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所引詩行似乎也都出自這兩部史詩。從現存的古文獻來看,雷吉昂學者塞阿格奈斯(Theagenes,活動年代在公元前五二五年前后)是希臘歷史上著述研究荷馬史詩的第一人,所著《論荷馬》以討論荷馬史詩的“喻指”功能為主,在公元前三世紀以前即已失傳。他提出的荷馬史詩里的神祇皆可喻指自然界里的物質或現象的觀點,對后世學者解讀荷馬的影響甚深,斯忒新勃羅托斯(據說他能揭示作品中藏而不露的意思〈tas huponoias〉),格勞孔和阿那克薩戈拉斯等人都曾沿襲他的思路,著述或研討過當時(即公元前五世紀)的學者們所關注的某些問題。柏拉圖對荷馬史詩頗有研究,但囿于自己的學觀取向,他的研究往往多少帶有偏見,無助于人們正確和客觀公正地解讀荷馬。亞里士多德寫過《論詩人》、《修辭學》、《論音樂》、《詩論》等著作,其中應該包括研析荷馬史詩的內容。《荷馬問題》是一部探討荷馬史詩里的“問題”和如何解析這些問題的專著,可惜也像上述文論一樣早已失傳。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是他的論詩專著中碩果僅存的一部(當然,他的《修辭學》也間接談到詩論問題)。在《詩學》里,亞里士多德高度評價了荷馬史詩的藝術成就,贊揚他“不知是得力于技巧還是憑借天賦”,幾乎在有關構詩的所有問題上都有自己高人一籌的真知灼見(《詩學》8.1451a22—24)。羅馬文論家賀拉斯很可能沒有直接讀過《詩學》,但有理由相信他會從亞里士多德的學生塞俄弗拉斯托斯和其他亞里士多德學派的成員(如薩圖羅斯和尼俄普托勒摩斯等)的著述中了解到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觀,包括對荷馬以及他的史詩的評價。包括西塞羅在內的羅馬文人,大概也會通過上述途徑接觸到亞里士多德學派的詩藝觀,從而加強自己的理論素養,加深對荷馬的印象。
伴隨著吟游詩人們(rhapsoidoi)的誦詩活動,荷馬史詩從公元前八世紀末或前七世紀初即開始從小亞細亞的發源地向外“擴張”,逐漸滲入希臘本土和意大利南部地區。據說魯庫耳戈斯于旅行途中偶遇吟游詩人,由此把荷馬詩作引入了斯巴達(參考普魯塔克《魯庫耳戈斯》4)。但普魯塔克所述的真實性頗值得懷疑。據希羅多德記載,魯庫耳戈斯的活動年代在公元前九百年左右;即使依據古代的保守估計,此君的盛年從政時期也應在公元前七七五年以前,因此除非前推荷馬創作史詩的時間,我們很難估測魯庫耳戈斯有可能在公元前九世紀或前八世紀初引入荷馬史詩,讓斯巴達人有那等耳福。然而,魯庫耳戈斯的“引進”或許不實,但吟游詩人和“荷馬后代們”的誦詩活動至遲在公元前六世紀下半葉已形成“氣候”,大概不是聳人聽聞的虛假之談。吟游業的發展勢必會導致所誦詩作(或故事)在枝節乃至重要內容上出現不可避免的變異。在沒有“定本”的情況下,吟游詩人們會各逞所能,即興增刪誦詩的內容,加大異變荷馬史詩的勢頭。據說面對這樣的情況,梭倫曾發布政令,要求吟游詩人們嚴格按照傳統的“版本”誦詩,不得擅作改動。據傳公元前五三五年前后,雅典執政裴西斯特拉托斯組織了一個以俄諾馬克里托斯為首的詩人委員會,負責收集各種詩段并以傳統成詩為標準,基本“定型”了荷馬史詩的受誦樣本。公元前五二〇年左右,裴西斯特拉托斯或他的兒子希帕科斯下令,將吟誦荷馬史詩定為泛希臘慶祭節上的保留項目,由參賽的詩人們依次接續,當眾吟誦。裴西斯特拉托斯(或其子)的努力,對規范吟游詩人們的誦詩和增強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對荷馬史詩的校勘工作卻遠沒有因此而中止。柏拉圖的同時代人、史詩《塞貝德》的作者安提馬科斯校編過荷馬史詩。此外,古時還盛傳亞里士多德曾專門為他的學生、馬其頓王子亞歷山大校訂了一部日后伴隨他南征北戰的《伊利亞特》。
公元前四世紀末,托勒密家族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利用雄厚的財富資源大力推動并弘揚科學文化事業,鼓勵學人重視對古希臘重要文獻文本的搜集和整理,在亞歷山大創建了規模宏大的圖書館。至菲拉德爾福斯統治時期(公元前二八五至前二四七年),圖書館收藏的各種抄本已達四十萬卷(相當于當今八開本的圖書四萬冊)。圖書館擁有從馬耳賽勒斯、阿耳戈斯、基俄斯、塞浦路斯、克里特和黑海城市西諾佩等地搜集到的荷馬史詩抄本,其中的大多數或許均成文于對上述雅典(即在裴西斯特拉托斯或其子希帕科斯督導下形成的)校勘本的(有變異的)轉抄。荷馬史詩研究由此成為顯學。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是菲勒塔斯的學生、厄菲索斯人澤諾多托斯(大概出生在公元前三二五年)。他校勘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并首次將這兩部史詩分別節分為二十四卷。在此之前,學者們習慣于以內容定名或稱呼其中的部分,所指不甚精確,也難以形成規范。澤諾多托斯著有《荷馬詞解》(Glossai)。和他的校勘一樣,此舉雖然功不可沒,但明顯帶有嚴重的個人主觀取向,對詞義的解析常顯不夠精細,且過于武斷。繼厄拉托塞奈斯之后,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生卒約為公元前二五七至前一八〇年)接任亞歷山大圖書館館長職務,繼續著由澤諾多托斯在那個時代開創的以詮解詞義為中心的研究工作。阿里斯托芬是個博學的人,精通文學、語言學、語文學,擅長文本的考證研究,首創重音符和音長標記,在澤諾多托斯和瑞諾斯(Rhianos)校本的基礎上較大幅度地改進和完善了校勘的質量。
真正具備嚴格的學術意識并且能夠代表亞歷山大學者治學(即荷馬史詩研究)水平的,是阿里斯托芬的學生、來自愛琴海北部島嶼薩摩斯拉凱的阿里斯塔耳科斯(生卒約為公元前二一七至前一四五年)。阿波羅尼俄斯卸任后,阿里斯塔耳科斯接受了亞歷山大圖書館館長的榮譽,也挑起了這一重要職位所賦予的責任。他以更加嚴肅的態度治學,兩次校訂荷馬史詩(換言之,完成了兩套校訂本),并在頁邊寫下了大量的評語,其中的許多行句經后世學者引用而得以傳世,受到現當代荷馬史詩研究者的高度重視。作為當時的頂尖學者(ho grammatikotatos〈阿塞那伊俄斯《學問之餐》15.671〉),阿里斯塔耳科斯一生寫過八百余篇短文,大都與荷馬及其史詩(或相關論題)的研究有關。與有時或許會夸大比喻的作用,傾向于過度開發喻指的潛力以佐證斯多葛學派觀點的裴耳伽蒙學者克拉忒斯不同[5],阿里斯塔耳科斯強調并提倡例證的收集以及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類推(anology)的研究方法,重視文本內部提供的信息資料,避免無依據的立論,不作缺乏語法和可靠語義支持的哲學或哲理引申。阿里斯塔耳科斯建立了自己的學派,他的直接影響力一直延續至羅馬的帝國時代,學生中不乏后世成為著名學人的佼佼者,包括修辭學家阿波羅道羅斯和語法學家狄俄尼索斯·斯拉克斯。盡管如此,阿里斯塔耳科斯及其前輩們的工作仍難免帶有時代賦予的局限性。他們接過了荷馬乃包括《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在內的眾多古代史詩的作者的傳統,接過了荷馬的受到包括亞里士多德在內的眾多學者文人頌揚,因此需要予以維護的名聲。他們同樣折服于荷馬的詩才和傳統形成的權威,遇到問題時總是傾向于往“好”的方面去設想。所以,盡管阿里斯塔耳科斯的研究方法經常是分析的,他的治學立場卻是“統一”的,亦即立足于維護荷馬的威望以及他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不可分割的統一(或“單一”)作者的傳統觀點。立場決定具體的校勘行為。此外,大學問家的固執和時代賦予的局限也都會導致他誤用自信,在釋解史詩用語時牽強附會。
無論是阿里斯托芬還是阿里斯塔耳科斯,都沒有把荷馬的著述范圍擴大到希羅多德或亞里士多德愿意接受的范圍,而他們的前輩澤諾多托斯則似乎更趨“肯定”和“現代”,將荷馬史詩的所指限定于《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三位學者都不懷疑荷馬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盡管亞歷山大學者中有人對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反傳統的觀點。公元前三世紀,學者克塞諾斯和赫拉尼科斯先后對《奧德賽》的作者歸屬提出異議,認為它與《伊利亞特》很不相同,因此不可能由創編《伊利亞特》的詩人所作。一般認為,克塞諾斯和赫拉尼科斯是最早的“分辨派”學者(chorizontes),他們的態度和觀點或許在阿里斯塔耳科斯等正統派學者看來不很嚴肅,卻有著不可忽視的歷史意義。畢竟,他們率先就荷馬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鐵定作者的觀點提出了挑戰,使人們聽到了另一種聲音。或許是因為受到了權威學者的有力反駁,或許是因為論證的方法不夠學術,他們的觀點未能得到后世有影響的學者的重視和積極響應。毫無疑問,史料因嚴重佚失而造成的匱缺,會“阻礙”我們的視野,“干擾”我們對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們的見解沒有成為近代分析派學者立論的依據,沒有對后者的思考產生過質的影響。
公元三世紀,亞歷山大已不再是古典學術和文化的研究中心。隨著中世紀的到來,曾是一門顯學的荷馬史詩研究(包括文學批評)經歷了長達一千多年的沉寂。但丁應該讀過荷馬史詩(他尊稱荷馬為“詩人之王”),但肯定不太熟悉歷史上作為一門學問的荷馬(史詩)評論。及至莎士比亞寫作戲劇的時代,人們對荷馬及其史詩的了解程度有了較大的改觀。莎翁寫過一出取材于有關特洛伊戰爭傳聞的悲喜劇《特羅伊洛斯與克瑞西達》,頗得好評,可見當時的倫敦觀眾已或多或少地具備了接受此類劇作的文學素養和審美情趣。與此同時,荷馬研究也在歐洲大陸悄然興起,開始成為學者們談論的話題。十七世紀九十年代,發生在英、法兩國的“書戰”(The Battle of the Books)起到了某種激勵的作用,會同其他因素,把歐洲學人的目光引向對《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內容孰“新”孰“舊”問題的關注,由此啟動了新一輪的以荷馬史詩為對象的“歷史批評”。熱奈·拉賓和威廉·坦布爾坦言他們更愿意相信裴西斯特拉托斯執政時期定型的荷馬史詩抄本。一六八四年,學者佩里卓尼俄斯提請人們重視書寫在文學創作中所起的作用;一七一三年,理查德·本特利發現并指出了輔音F(作W音讀)在荷馬史詩里已經消失的“隱性”存在,提出荷馬創編的很可能是一批內容上可以獨立成篇的短詩(他們大概均以為荷馬生活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數百年后才由后世歌手或吟游詩人組合成長篇史詩的觀點。《新科學》的作者、那不勒斯的維科語出驚人,認為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荷馬其人,“荷馬”只是個代表并統指古代歌手的“集體”名稱。羅伯特·伍德于一七六九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論荷馬的原創天才與寫作——兼論特羅阿得的古貌與現狀》的文章,認為荷馬“既不能閱讀,也不會書寫”。這一見解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息,亦即荷馬史詩之所以在古代得以流傳,靠的不是實際上不存在的規范文本,而是建立在博聞強記基礎上的詩人的口誦。
在這一領域做出劃時代和集大成貢獻的,是德國學者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一七九五年,沃爾夫發表了專著《荷馬史詩緒論》,大致奠定了近代荷馬學的理論基礎。除了羅伯特·伍德的上述和相關見解,促使沃爾夫寫作《荷馬史詩緒論》的另一個因素,是法國學者維洛伊森(Villoison)于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所發現并隨之予以整理發表的Venetus A。此乃《伊利亞特》現存最早的抄本,在當時是個轟動的事件。在沃爾夫看來,既然Venetus A的成文不早于公元一世紀(他誤以為此抄本的母本是當時已受到質疑的阿里斯塔耳科斯的校勘本,盡管校勘本本身早已失佚),但卻是既有最早的抄本,因此它毫無疑問地不是古代權威抄本的“真傳”。他由此推斷荷馬史詩肯定以口誦的方式長期存在于成文抄本的出現之前,口頭唱誦是荷馬史詩流傳的本源。伍德沒有提及而沃爾夫依據上述認識引申得出的另一個觀點是,考慮到人的記憶力的有限,詩人不太可能完整地把長篇史詩默記在心。因此,《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必定只能由短詩串聯和組合而成,而這些短詩所涉內容有所差異,故事的風格也不盡相同。“荷馬”要么是第一個構組取材于特洛伊戰爭的詩人,要么是一個以編誦此類故事為業的口誦詩人群體,亦即此類詩人的總稱。以精深和廣博的語言學知識以及大量取自文本的例證,加之使用了科學的、合乎學術規范的論證(包括發現并解析問題的)方式,沃爾夫集思廣益,博采前人和同時代文人學者的洞見與智慧,建立了一個至今仍不顯整體過時、仍在產生影響的理論體系。
在整個十九世紀,分析派(也被叫做分辨派或區分派)的學說在西方荷馬研究領域強勢占有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在沃爾夫的《荷馬史詩緒論》以及眾多響應者的著述面前,統一派的見解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個別統一派學者的抗爭頂不住基于文本事實的批駁,顯得捉襟見肘,他們維護荷馬“一統”權威的良好意愿也常常顯得過于感情用事,經不起學術規則的檢驗。直到十九世紀末以前,西方學界既沒有推出一部高質量的維護統一派立場的專著,也沒有出現過一篇學術含量高得足以與分析派觀點相抗衡的論文。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英國學者逐漸加入到分析派的行列,但總的說來,分析派是一個德國現象,持分析(即分辨)立場的頂尖學者集中在德國的一些高校里,從事著書立說和傳授弟子的工作。
分析派不是鐵板一塊。從這個“陣營”里很快分裂出兩個派別,一派完全秉承沃爾夫的學說,強調荷馬史詩的合成(liedertheorie),而不刻意區分合成成分的主次。這派學者以卡爾·拉赫曼(1793—1851)為代表,主要成員包括赫爾德和藤薩爾等。另一派學者以高特弗雷德·赫爾曼為先鋒人物。在一八三二年發表的《論荷馬史詩里的竄改》一書里,赫爾曼指出,荷馬史詩不同于《卡萊瓦拉》和奧西恩詩歌,不由等量部分的依次排列平鋪直敘地組合而成。荷馬史詩有一個核心(kernel),屬于它的原創成分,由荷馬所作,而其他部分則為后世詩人的添續,或緊或松地圍繞核心展開敘事。《伊利亞特》的核心是阿基琉斯的憤怒,其他內容來自有關特洛伊戰爭的眾多短詩,由后世詩人(如某些Homeridai)匯編到既有的核心情節之中,形成一個規模龐大的故事組合。《伊利亞特》形成于一個不斷增補、不斷改動、調整和彌合的匯編過程。譬如,在赫爾曼看來,《伊利亞特》1.1—347是詩作的原初內容,而1.430—492、348—429則(原本)分屬于別的故事,是后世被組合到《伊利亞特》里的內容。赫爾曼及其追隨者們的主張逐漸壓倒合成派學者的觀點,獲得了包括菲克(Fick)、貝特(Bethe)、維拉莫維茲(Wilamowitz)、格羅特(Grote,此君力主今本《伊利亞特》由原詩和《阿基里德》組成)、默雷(Murray)、里夫(Leaf)和克羅賽(Croisset)等一批德、法、英國學者程度不等的贊同。上述學者在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不管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一個群體,荷馬生活在開啟了一個口頭史詩傳統的源頭時代;(他們中的一些人傾向于認為)荷馬的原作是最好的,而后世詩人的增補(包括改動)和串合則常常顯得唐突、蕪雜和笨拙,造成了許多用詞和敘事上前后難以呼應或不一致的矛盾,破壞了史詩原有的明晰、直樸和自成一體的詩歌品位。不難看出,這里既有深刻的洞見,有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品味的明智論斷,也有我們應予仔細分辨和甄別的眾說紛紜,或許還有我們無法茍同并且應該予以修正的不翔實的表述。
分辨的負面作用很快開始顯現出來。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核心,并且無例外地全都以為自己的主張有理。此外,如何限定《伊利亞特》里作為核心的阿基琉斯的憤怒的所涉范圍,也是個不好確定并容易引起爭執的問題。學力的互相抵消和學派主要成員間的內訌,嚴重削弱了分析派和核心論的影響力,直接促成了統一派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東山再起,與在當時已呈分崩離析之狀的分析派相抗衡。新時代的統一派學者們也“裝備”了當時最高水平的語言學知識,學會了充分利用考古成果(包括海因里希·施里曼在特洛伊和邁錫尼卓有成效的發掘)佐證和強化理論分析的本領,從而得以進入長期以來為分析派學者所壟斷占據的領域,借助同樣的方法和同類型的資料實施反擊,與對手展開周旋。安德魯·蘭教授脫穎而出,先后發表了專著《荷馬和史詩》(1893年)、《荷馬與他的時代》(1906年)以及《荷馬的世界》(1910年),成為統一派的領軍人物。分析派學者曾把某些詞匯不同的詞尾變化看作是確定成詩年代遲早的論據。統一派學者其時依據對同類資料的研析,認為此類詞尾的變異表明荷馬史詩從一開始就具備了充滿活力的兼容性,兼采了來自不同地域的方言。特洛伊出土的文物中武器均為銅制,分析派學者曾據此將荷馬史詩中出現鐵制兵器的段落全部劃為后人的續貂。統一派學者其時對這一結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荷馬史詩的兼采性和對社會文化現象的兼容性解答了分辨派學者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所不能妥善回答的問題。持荷馬史詩乃由同一位詩人所作觀點的學者隊伍持續壯大,先后吸引了羅塞(Rothe)、德瑞魯普(Drerup)、斯各特(Scott)、愛倫(Allen)、伍德豪斯(Woodhouse)和C·M·鮑拉等一批飽學之士的加盟。
考古發現表明,公元前八世紀并不一定是個全社會均為文盲的時代。二十世紀中葉,統一派學者注意到了一只新近出土的成品于公元前八世紀的阿提卡瓶罐上有刻寫的文字,這一事實表明當時有人或許掌握某種形式的書寫技巧。當然,瓶罐的產地是阿提卡,因此還不能直接證明荷馬生活的小亞細亞沿岸地區也有人能夠熟練程度不等地書寫。盡管如此,這一發現還是對在此之前流行的(新的)希臘字母產生于公元前六世紀的傳統認識形成了沖擊。荷馬史詩本身也提供了不利于分辨派的信息。人們把其中提到的鐵制兵器和腓尼基人的貿易活動聯系起來,斷言史詩內部存在著某種以往可能被忽略的深層次上的關聯。眾多跡象表明《奧德賽》的作者對《伊利亞特》有著至深的了解,延續了《伊利亞特》已經定下的調子,有鋪墊地發展著奧德修斯的個性以及他與雅典娜之間的關系。諸如此類的例證不僅使得公元前八世紀成為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成詩時期,而且也使得作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單一作者的荷馬呼之欲出,使之看來像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荷馬作為一個史詩詩人的“地位”也隨之瓜熟蒂落地發生了改變。他不是如分析派學者所說的那樣站在史詩發軔的最清純的源頭,而是置身于它的由眾多詩段推涌而起的峰巔。荷馬史詩的光輝不是得之于它的始發,而是得之于前輩詩人的積累,得之于荷馬對傳統敘事詩歌有著“一統”的胸懷和能夠體現高超把握能力的提煉。
十九世紀肯定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其他方面如此,在荷馬史詩研究領域自然也不例外。學者們注意到荷馬史詩的源遠流長,知道在它的背后肯定有一個以口頭文學出現的誦詩傳統,知曉這個傳統容納并得益于一套普遍存在著的、對詩人的構詩活動形成強勁制約的模式或程式(他們稱之為formulae或formulas)。德國學者頓澤爾的研究已經逼近到格律的需要與表述程式的產生問題,梅勒特則更進一步,指出史詩中重復出現的名詞短語似乎表明它們的形成沿循著一套“固定的表述模式”。他注意到某些用詞的位置明顯不符合格律的要求,斷言它們的構成有可能完成于荷馬生活的年代之前——那時詩行的格律要求似乎更為“靈活”[6],雖然更顯初樸,卻給詩人的發揮保留了更多的余地。然而,十九世紀的學者們畢竟未能再進一步。無論是分辨派學者還是他們的對手(即統一派學者)都沒有把這看作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分辨派學者從中看到的是古代詩人用詞時的互相“借用”,并以為這只能證明荷馬史詩的最終成篇乃眾多詩人合力所致,而經典的統一派學者也把對這一現象的分析保留在提示語言傳統的層面上,同樣未能抓住機遇,與摘取一項重大理論成果的大好機會失之交臂。
米爾曼·帕里(Milman Parry)的工作在荷馬研究史上樹起了另一座令人矚目的里程碑。帕里曾表示“效忠”統一派,但他也傾向于否認荷馬史詩(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乃由一人所作。如果說前人只是提到語言程式與格律要求之間的關系,帕里則以提供大量的例證入手,從中系統地歸納出一整套頗有說服力的理論。帕里的貢獻還見之于為研究口頭史詩指明了“行動”的方向,并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九二八年,帕里發表了他的博士論文《荷馬史詩里的名詞短語傳統》,宣告了一個成熟的、以研究口頭史詩為指對的新理論的誕生。他明確指出,荷馬史詩所用的是一種“人工語言”,專門服務或應用于史詩的創作,它的制作者是歷代口誦或吟游詩人,其表現力在長期使用中不斷完善起來,逐漸形成套路后成為世代相傳的唱詩的語言程式。帕里的研究表明,受前面音步的重音位置以及停頓等因素的影響,名詞短語polumetis Odusseus(足智多謀的奧德修斯)在荷馬史詩里的位置無例外地均在詩行的末尾,盡管它有著高達五十的出現次數。同樣,polutas dios Odusseus(歷經磨難和神一樣的奧德修斯)的出現和位置也受格律需要的節制。六音步長短短格(及其允許的有限變化)的構詩規則限制了詩人的用詞,使得阿伽門農以外的一些小王或首領級的人物(如埃內阿斯和歐墨洛斯等)也有幸受到aner andron(民眾的王者)的修飾,身價倍增。在他的學生阿爾伯特·洛德(Albert Lord)的協助下,帕里對南斯拉夫口誦史詩進行了詳細的實地考察。洛德繼續老師的事業,以荷馬史詩為“背景”,在系統考察研析流行于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地區的口頭史詩的基礎上,寫出了《故事的唱誦者》(The Singer of Tales)一書,于一九六〇年出版。帕里—洛德的口頭史詩(或詩歌)理論,建立在他們對史詩故事在內容取舍和語言運用方面均嚴重依賴于程式這一基本認識的基礎之上,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要點[7]:
一、口頭詩歌沒有作者和具體作品的個性風格,所用詞匯大都承載文化和傳統的負荷。口誦詩人依靠既有的語言程式構詩。
二、口頭詩歌所用的語言程式構造上由小到大,即由單詞到詞組,再由詞組的聯合形成句子甚至段落。傳統并因傳統的制約而定型(或劃定所涉范圍)的故事主題代代相傳,可以隨時容納枝節上的變動,但不鼓勵“傷筋動骨”。
三、口誦詩人利用既有的積累即興發揮,出口成章,構詩和唱誦常常幾乎同時進行,沒有必須因循的定型文本,歌手和聽眾對此都有共識,形成故事理解方面的“互動”。
四、“成文”是口頭文學的天敵。
帕里和洛德的貢獻有目共睹。但是,他們有時或許稍嫌過多強調了格律的決定性作用,而對詩人的表義需要關注不多。奧德修斯浴血戰場,戰爭結束后又經歷千辛萬苦,回返故鄉,“歷經磨難的”(polutlas)非常準確地概括了這一點,在許多上下文里(比如參考《奧德賽》6.1)也顯得極為協調。奧德修斯是“多謀善斷的”(polumetis),這是他區別于阿伽門農和阿基琉斯等將領的“特點”之一,在眾多上下文里讀來甚是貼切。詩人經常會根據表義的需要選用不同的飾詞。在說到奧德修斯忍受的苦難時,詩人選用了“心志堅忍的”(talasiphronos,《奧德賽》4.241)一語;在需要突出奧德修斯的戰力和強健時,詩人所用的飾詞是非常貼切的“蕩劫城堡的”(ptoliporthos,《伊利亞特》2.278,另參考《奧德賽》8.3)。抵達王者阿爾基努斯宮居前的奧德修斯自然是“卓著和歷經磨難的”(《奧德賽》7.1)。但是,當他即將說出一番睿智的言談以開導阿爾基努斯的心智時,詩人肯定會覺得諸如“歷經磨難的”一類的飾詞不能體現奧德修斯的明智(因此不合“時宜”),所以轉而選用了“多謀善斷的”(《奧德賽》7.207),使之與語境相協調。荷馬不是總能這樣做的,但他在選用飾詞時會考慮表義與上下文相配稱的需要,則是不爭的事實。
過分強調口誦史詩的文化傳統和程式(formulae)特點(有學者比如Norman Austin和David Shive認為帕里和洛德“走得太遠”),無疑會導致對詩家個人才華和創造性的貶低或否定。綜觀史料,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從公元前七世紀起荷馬便被認為是一個有天分的詩人。赫拉克利特說過,荷馬是最聰明的希臘人(片斷56DK)。如果說赫拉克利特是從負面角度出發說這番話的,那么亞里士多德對荷馬的天分和才華的肯定(參考《詩學》8.1451a18—24)則可以被理解為純粹的贊揚。亞歷山大·波普翻譯過荷馬史詩,本身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他對荷馬的評價極高,認為這位希臘歌手的天分遠在羅馬詩圣維吉爾之上,是有史以來最具原創力的詩人[8]。即便同樣以神話和傳說為材料,史詩的質量仍然可以相去甚遠(詳見《詩學》23),足見詩家個人的素質和能力的重要。顯然,我們在足夠重視帕里—洛德理論的同時,不應忽略其他各方對荷馬及其史詩的評價,否則將很可能導致走極端的危險,見木不見林,失去客觀的評審維度。今天,荷馬史詩是一種由傳統積淀而成的口誦史詩的觀點在西方學界幾乎已成定論。大多數學者已不再認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出自同一位詩人的構組。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強調程式作用的口誦史詩理論和肯定荷馬的作用以及詩才之間尋找一種平衡,仍然是一個需要得到妥善解決的問題。畢竟,荷馬不會因為這個或那個原因退出歷史舞臺,歷史既然造就了荷馬和歸在他名下的史詩,也就會堅持它的一如既往的一貫性,直到人們找到確切的證據,表明把荷馬尊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是一個確鑿的歷史性錯誤。只要這一天沒有到來(它會到來嗎?),世人就還會依循常規,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劃歸在荷馬的名下,使他繼續享領此份實際上無人可以頂替接受的榮譽。歷史經常是不能復原的。在源遠流長和同時極為需要最大限度的學力和想像力的荷馬史詩研究領域,人們同樣也只能容忍歷史的出于“本能”的自我“遮蔽”,無可奈何地直面由此造成的不得不憑借人的有限智慧應對棘手問題的難堪。
主要參考書目
Curtius,E.R.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translated by W.Trask),1953.
De Jong,I.A Narratological Commentary on the Odyssey,2011.
Dimock,G.E.The Unity of the Odyssey,1989.
Flaceliere,R.A Literary History of Greece,1964.
Foley,J.M.Traditional Oral Epic,1990.
Knight,J.Many-minded Homer,1968.
Lamberton,R.and Keancy,J.J.Homer's Ancient Readers,1992.
Lefkowitz,M.The Lives of the Greek Poets,1981.
Lord,A.B.The Singer of Tales,1960.
Macausland,I.and Walot,P.Homer,1998.
Meijering,R.Literary and Rhetorical Theories in Greek Scholia,1987.
Morris,I.and Powell,H(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1997.
Mueller,M.The Iliad,1984.
Myres,J.L.Homer and His Critic(edited by D.Gray),1958.
Thomson,J.A.K.Studies in the Odyssey,1966.
Trypanis,C.A.The Homeric Epics,1977.
Watts,A.C.The Lyre and the Harp,1969.
Whitman,C.H.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