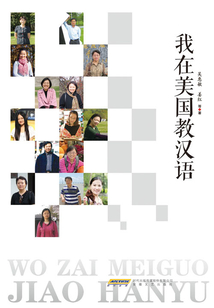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黃—開小道”之“緣”與“道”
惠敏教授和姜紅教授約我為他們的《我在美國教漢語》一書寫篇“序”,欣然應允。一是盛情難卻,二是這本書的內容是關于安徽農業大學與美國罕布什爾學院(Hampshire College)之間師生交流項目的,是由曾參與這一項目的部分安農大教師撰寫的訪美經歷、體驗和思考的文章集成的。星移斗轉,一晃二十年過去。回顧這段歷史,留下一群人的集體記憶,從中悟出一些有益的啟示,還是很有意義的。拜讀了作者們的文稿,覺得大家寫的都情真意切、感悟深刻,說明那段赴美訪教的日子對每一個人都是有益的、美好的、難忘的。
曾有其中一位親歷者把這一交流項目叫作“黃—開小道”,我覺得頗為貼切,無關毀譽。“黃—開”系指兩個人,即安農大的鄙人老黃和罕布什爾學院的老K(Kay Ann Johnson,中文名江開安),老黃和老K 確實是這一項目的“始作俑者”,而“小道”一則指這一項目并不是中美富布萊特交流計劃那樣的官方正規項目,而是一個地道的非官方或民間自發的教育交流活動,二則指走過這條小道的人數不多:每年東飛赴美的少則一人,多不過二三人,而西來中土的師生少則三五人,多不過一二十人。二十年總計也就是一兩百人吧?人們不禁要問:這樣一條默默無聞的“小道”上竟有這些“行者”陸續走了二十年,緣由何來?原因何在?借作“序”之機,我想略作答問。
——之“緣”。
安農大是一所以農科為主的省屬公立老校,而罕布什爾學院則是一所小型私立文理學院,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涌現的一批所謂“前衛高校”(Pioneer College,又譯“先鋒派高校”)之一。顯而易見,這兩所高校并不“專業對口”,卻在二十年前相遇相交,實因那時我與Kay的“緣”——收養。話分兩頭。Kay于中國《收養法》頒布(1992年)之前兩年就從武漢兒童福利院收養了一個叫麗麗(英文名就叫LiLi Johnson)的女嬰(現正在美國耶魯大學讀博士)。作為一個社會學教授和收養母親,Kay自然就對收養(中國人的收養和中美收養問題)這一課題感興趣。這一頭,20世紀90年代初,我參與主持了“中國大陸助孤行動(安徽)”的調研,對安徽十來所兒童福利院進行過實地調查。恰在此時,我在復旦讀研時的大師兄在Kay所在的罕布什爾學院任教,Kay托他推薦一個能為該校一位在北師大留學的女生作畢業論文(題為《中國小保姆》)提供一些幫助和指導的人。當時,安徽的無為縣號稱“中國保姆之鄉”,于是大師兄就想起了當年(1982年)畢業回安徽工作的我,做了此事的搭橋人。該女生就直接從北京乘火車來合肥找到我。后來,我帶她在合肥市和無為縣做了一些“田野調查”,指導不敢說,倒確實幫了她不少忙。因為那時一個洋妞在開放度還很差的安徽農村走鄉串戶做調查尚屬罕見,當地干部都不敢沾這種可能惹麻煩的事,人們仍抱著“非我族類必有異心”的心理。克服了不少困難,終于獲得了所需第一手真實資料,她后來做了一篇相當出色的論文。而此時Kay并不知道我是誰,但這個女生一定向她介紹了幫她忙的安農大的老黃。不久,Kay又一次訪華來肥,我們才見了面。她是我結識的第一個洋教授,沒想到她竟是一個“中國通”,漢語的聽力口語非常好,普通話也比我好許多。因此,我們用中文交流很順暢。這才知道,Kay不知來過中國多少趟,到過多少城鄉。而第一次來華竟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大約在基辛格秘密訪華、尼克松正式訪華那一段,曾有一個美國青年訪華團來華,Kay就是該團成員之一。從她“秀”的一張周恩來總理接見該團時與她握手的老照片可見,Kay是一個金發碧眼、二十出頭的洋美女。這讓我多了一份親切感,同時也不禁感慨,這世上同齡人之間生活經歷和差別竟有如此之大!我那時剛從一個“知青”變成“工農兵學員”啊……
我們相識之后,很快發現一個“交集”——收養。中國《收養法》問世的同時頒發了《外國人來華收養子女辦法》,從1993年起,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其中最多的是美國人來華收養子女。成群結隊的“老外”抱著中國嬰兒走在合肥街頭,一時間成為一道奇異的風景線。而此時,我的大師兄又托我為幾個來自紐約和波士頓的收養團幫忙。按理說,依法收養并不需要熟人幫什么忙,但當時新法剛頒,從北京到各省、市之間收養手續的辦理還很不規范、不及時,這些美國人又是第一次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發展中國家來辦收養子女這樣的大事,當然希望有當地人提供方便。于是那兩年幫了幾個收養團辦一些“民政登記”“司法公證”和訪問兒童福利院這類事情,忙得不可開交,卻也了解了收養和國際收養是怎么回事。最早在中國收養女兒的老K就發現我與她可以在收養問題上進行合作研究。為了回答她“中國人自己是否收養抑或只朝外送養”的疑問,我們在合肥附近及安徽幾個縣城鄉做了一些關于棄嬰和收養情況的調查,發現中國社會收養子女現象非常普遍且源遠流長。以前我對收養司空見慣卻熟視無睹,認為這有什么值得研究、大驚小怪的。從與Kay的合作過程中,我才真正感知美國人的實證方法其實就是“小題大做”,對任何一件事、一種現象都打破砂鍋問到底,務必弄清來龍去脈,掌握具體細節,然后進行分析,最終得出自己的結論。我們以前總是遇事大而化之想當然,選題往往大而無當,叫“大題小做”,空頭議論多于實證調研、科學分析。真慚愧,毛主席“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名言,像老K這樣的“老外”倒是自覺的實踐者!對我而言,這是一次研究方法論的顛覆。從此以后,無論是選擇研究課題、撰寫學術論文,抑或是發表學術著作,我都不折不扣地從“實事”中“求是”了。
在做棄嬰和收養調研,特別是幫助美國父母在肥收養子女過程中,我發現公眾對“老外”為什么來華收養存有諸多疑慮,如是否弄回去“打針”(即像當年日本鬼子用中國人做人體藥物試驗那樣),或帶回家做“童養媳”等。我將一系列疑問告訴了老K,她很敏感地意識到,要消除中國人的此類對外國人來華收養動機、目的和“用處”的疑問,光靠他們自己解釋是不起作用的,必須有中國人特別是像老黃這樣對收養問題有所涉獵的人親自去美國跟蹤這些收養家庭做實地調研,親眼看看這些被收養在美國家庭的孩子的生活狀況,所謂“眼見為實”吧,然后向中國公眾如實報道,才能解疑釋惑。于是,她牽頭向“福特基金(北京)”申報了“美國家庭收養中國兒童問題研究”合作課題,獲批得到一些資金支持。于是,1996年10月我應Kay任教的罕布什爾學院院長Greg之邀赴美做訪問學者,免費在罕布什爾吃住,但我的主要工作是去美國收養中國孩子家庭(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比較集中的地方,如紐約、波士頓、麻州和康州西部、芝加哥、舊金山、亞特蘭大、佛羅里達等州、市、鎮,深入家庭做訪談,發問卷,與這些家庭的中國孩子和他們的養父母甚至親友同吃、同住、同游,深度觀察體驗這類美國家庭的真實生活狀況。調查間歇期間,生活在罕布什爾,當然要接觸Kay的學生,他們對中國語言和文化興趣濃厚,部分學生經常到我的住處“玩”——交談、學漢語、做中國飯菜等,很快我們就成了好朋友,有幾個學生就表達了很想去中國安徽訪問的愿望。罕布什爾非常重視學生的要求,且規定每一個學生四年中必須起碼出國學習一次,至于去哪個國家要看學生的愿望和導師的安排。于是,Kay就和我探討可否安排她的學生去安農大學習。一開始我曾猶豫過,因為人貴有自知之明,我在安農大并不是什么負責人,當時還只是個普通的副教授,說話沒分量,心理不踏實,且安農大又沒有文科學生可對口交流,但心里還是想,如能促成兩校交流倒也是一件好事。于是,我向Kay提出,作為交換條件,可否讓安農大從事思政和中文教研的青年教師來美訪問?誰知一拍即合,她立即爽快答應。于是,Kay和我就很快草擬了一份兩校學者學生交換交流的協議,看來,作為一個資深教授,Kay在罕布什爾說話真有分量,不幾天她就讓Gregory Prince校長批準并簽發了這份協議(草案),傳真給安農大外事辦轉校長,不久竟也得到安農大開明領導的認可(要知道,當時安農大尚無接收外國留學生的資格和權力,即未經省、部教育主管部門的批準和授權)。就這樣,安農大和罕布什爾在1997年秋季學期開始了兩校的交流。這就是“黃—開小道”之緣的梗概。然而緣起之初,“協議”上并未商定有效期,我怎么也不敢想象,這個“緣分”能持續二十年之久,且今后還有擴展的勢頭,這恐怕也是“緣”中有“道”吧!
——之“道”。
記得魯迅先生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前所述,如果當年沒有和Kay因學生論文和國際收養問題合作研究之緣;如果當時沒有積極回應罕布什爾學生來安農大學習的愿望,安農大和罕布什爾交流這條小道就無從談起;如果后來不是走的人多了,且往來于這條小道上的人都十分珍惜并不斷開拓,也就成不了這條“黃—開小道”。時間不倒流,歷史無“如果”。事實既然發生已屬必然,然而必然卻因偶然開路且寓于偶然之中。機會轉瞬即逝、永不再有,機遇只垂青有準備的頭腦。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沒有錯失這一機緣,還算是一次明智的選擇。否則,我自己的歷史就要改寫,本書作者們也就寫不出他們的這段難忘經歷和體驗了。也許這就是因—緣—果的道理吧。
從哲思轉向現實看,“黃—開小道”之所以能開源成溪、拓荒成路還是因為它滿足了雙方的需求。從美方看,罕布什爾學生對中國文化可謂“高山仰止”,如有個叫Lambert(中文名寧蘭波)的學生竟能大段背誦《老子》,實令我驚愕和汗顏。他們自然強烈希望學習漢語,而學好漢語最好的辦法是到中國去學,如同我們要學好英語也只有到英語國家去學(猶如齊人學楚語)。罕布什爾校方恪守“學生是上帝”的辦學理念,對學生們想去中國的愿望和要求真是言聽計從,于是抓住Kay與老黃合作研究國際收養的機遇,主動提出與安農大交流的真誠意愿,并率先簽署我和老K草擬的兩校交流協議,以至我十年中四訪美都是罕布什爾校長親自發出邀請,第一次竟為我辦理了H-1簽證(工作簽證)。美國人是講實用的,總是自身利益優先,并不是因Kay個人的“面子”而對老黃特別優待,而是這項交流首先是對罕布什爾有利有益的,事實也證明,這項交流對他們的學生培養實在是好處多多。從中方看,當罕布什爾提出意向后,我之所以明知能力可能不足卻仍持積極響應態度,是因為我在美各地訪問幾個月后深深感到,如果能讓我的同事們,特別是年輕骨干教師們來美國待上一年半載到處走走看看,那一定是大有益處的。而干我們高校思政教研這一行的和在理工農醫類高校教“大學語文”公共課的教師們出國訪學尤其是訪美這樣的機會一直稀少得如撒哈拉之水。他們也一定有一個不敢想的訪美夢。后來的實踐表明,他們通過“黃—開小道”訪教美國確實也都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提高了自信,改進了教學,安農大人文社科團隊的整體學術水平和在同行中的地位也明顯地提升了,這些都是我方實實在在的“早期收獲”,今后發展也定能獲得更大豐收。綜上兩方面可以明白一個大道理:求同存異、互需互補、合作共贏乃當今世界之大勢和真諦。
我一直覺得,這條跨越太平洋的“小道”,很像中國的“村村通”,一開始只有3米寬,還坑坑洼洼,如今許多村間小道已經拓寬成一條條平坦廣闊的柏油路了。這里蘊含著一個小道與大道關系之“道”:小道須順大道,小道應符正道。30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中美正式建交,中美關系在曲折中發展到今天,無論經貿金融、人文教育還是政治軍事外交都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不可或缺的利益和命運共同體的程度。這就是“地球村”的大道,大勢所趨,順存逆亡。一切小道都必須順此大道相向而行方可暢通無阻,才有生命力和可持續性。看來“黃—開小道”正是順應了中美交往之大道。所謂“小道應符正道”者,是說小道不能是邪道,更不能是黑道,必須是光明正道。說實話,當時乃至后來多年中,我一直惴惴不安,如履薄冰。我們常說一句話叫“外事無小事”。作為此項目的發起人之一和前十年的具體負責者,我深知,無論是我方人員在美還是美方學生在華期間,只要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出一點事,我可就要“自作自受”“吃不了兜著走”了。比較而言,我對我的同事們更放心一些,相信他們不會走邪道,更不會涉黑道。實踐表明,他們確實都表現得很優秀,很守外事紀律,很講人格校格國格,且努力工作、創新教學,與美方師生交友結誼,受到對方學校和師生高度贊譽。這是我最感欣慰之處。而對方的學生則實在令人操心。要知道,美國學生可不像中國學生那么“聽話”。他們的個性化我早已領略。他們總是要do something new,可謂“一個人一個樣”,無論男孩女孩不定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都可能弄出花樣來,那可就“大事不好了”。僅舉一事可見一斑。美國部分州抽大麻合法,即使在不合法的地方人們也普遍認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認為是件大不了的事情。我知道,在罕布什爾學生抽大麻,甚至在宿舍盆栽大麻,不是什么秘密,校方和校警也聽之任之。我就十分擔心他們萬一帶大麻入境被查,或帶進來吸食,按中國法律那是違法的,那就出大事了。謝天謝地,在這點上那些孩子總算還“聽話”,這么多年沒有一個學生為此違規違法。自始至今,由于雙方密切配合,精心管理,從未出過“廣義安全”方面的問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這也說明一個道理:道雖小,正而明,明而順;同時,小道多而順,也助大道直而暢,正所謂“國之交在于民相親”,而民相親則國無戰矣……
二十年前第一次訪美時已近“知天命”之年,如今方知人之要“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何其難啊!而要達“觀自在”之“五蘊皆定”境界,更是難于上青天。
是為序。祈善知識大德指點迷津。
黃邦漢
2016年春
寫于合肥逍遙津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