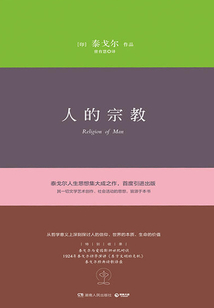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導讀〉宗教的最佳面貌
臺大哲學系教授傅佩榮
“宗教”作為客觀存在的事實,無論就時間的綿延或空間的廣袤來看,都是人類現象的首要特征。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人群聚居之處,必有宗教痕跡。然而,宗教不只是外顯的跡象,它其實是人類生活的核心本質。要了解一個民族,不能不認識其信仰;正如要明白一個人的真相,不能不知道他相信什么。既然如此,借著探討世界各大宗教,不是可以全面而深入地發掘人性的奧秘嗎?
基于此一理念,史密斯教授在《人的宗教》一書中,依序談到了印度教、佛教、儒家、道家、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與原初宗教。這八派宗教可以用“源遠流長”來形容,因為其中最年輕的也歷時將近14個世紀了。在漫長的年代中,宗教所啟發的善行固然使人景仰,但是假宗教之名而犯下的錯誤、不義與罪惡,其數量之多與情節之嚴重,也同樣讓人不敢恭維。史密斯教授的寫作策略很清楚,就是要展現宗教的最佳面貌。因此,本書內容的重點既不是宗教史,也不是對宗教做全盤或平衡的論述,更不是比較宗教之優劣,而是環繞著宗教所引發的“價值”。這種價值,簡而言之,就是促使人性趨于完美的力量。
人性若要趨于完美,就須解除其限制、厘清其定位,并且安頓其過程。說得淺顯些,人性原本是不完美的,因為人生苦多于樂,最后又難免于死亡;那么,人性的潛在能力究竟是神還是魔?要如何使個人定位得恰到好處?然后,落實在具體人生中,應該怎么活出意義?本書所強調的“價值”,正是為了答復這一類重大問題所提供的智慧索引。我們可以從三方面進行解讀。
首先,宗教提醒人類:生命取向要高。取向是指目標而言,宗教無不涉及超越的力量或境界,其目標在于使人與此超越者建立關系。步驟有二:一是在程度上超越凡俗,譬如舍棄世間的享樂與成就,不受人群恩怨利害所牽絆;二是在種類上超越凡俗,亦即在小我中發現真我,從變化生滅中走向永恒本體。這種高遠的目標所產生的效果是立即而明顯的,足以使宗教信徒與凡俗價值分道揚鑣。典型的例子當然是由宗教的創始者所示范的。佛教看來溫和,而釋迦牟尼對于當時的印度教而言,無異于“眾人皆醉我獨醒”,并且醒得十分徹底:不要權威與儀式,排除理論與傳統,不談超自然,解脫則以自力為主。耶穌與凡俗的決裂,更是毫無妥協余地,以致親自成為犧牲祭品,印證了“道成肉身”的奧跡,開創了規模宏大的基督教。
即使是力圖入世淑世的孔子,也與“不義而富且貴”厘清界線,絕不允許有同流合污的嫌疑。本書多次引述一句話:“世界是一座橋,走過去,不要在上面蓋房子。”以生動的比喻來描述信仰的超越態度。但是,“橋”應該是連接兩岸的,我們身在此岸的人如何確知彼岸存在,并且肯定彼岸是今生一切缺憾的滿全?由這個問題必然引致各大宗教如何創立的過程,亦即如何取信于人。
其次,宗教不離修行,因此生命體驗要深。印度教的“瑜伽”包括身心的操練與實際的作為,在此提供了完整的參考架構,就是“知的、愛的、業的、修的”這四種瑜伽。顧名思義,這四條路徑是指智慧、情感、工作與苦修。只要運用合宜,都可以助人覓得真我,不再迷失于大梵之外。
進而言之,不論采行何種修行法門,“回歸自我”都是不可或缺的關鍵。這正是“退出與復返”的標準歷程。以佛陀為例,他在森林中獨自苦修六年,悟道后投入世間弘法四十五年;這段期間仍然按時“退出”,就是每年有三個月雨季的休息與冥想;在積極傳教時,每日亦有三次退到靜處沉思。唯其能夠退出,在復返時才有源源不絕的活力與動力。宗教人物的充電是接上超越界或絕對界的,其經驗之深刻只能以“神秘經驗”來描摹。這種經驗的特征之一是忘我或契合。
依此而論,道家的宗教性格并不含糊。當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時,他心中想的是自己體“道”之后的心得,亦即在心齋與坐忘之后的境界。問題在于這種經驗不可言傳也無法教導,一般信徒只能遵循“退出與復返”的原則,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一個神圣的領域。推而言之,猶太教徒謹守安息日不工作的訓示,基督徒望彌撒或做禮拜的規定,以及穆斯林每日五次朝麥加禱告的儀式等等,無不提醒人收斂心思,回歸自我,再上溯生命源頭。
第三點,宗教鼓勵我們活在世間時,生命能量要強。生命能量是指積極而樂觀地行善愛人。宗教徒的愛的最大特色,就是無私而普遍。其中道理很簡單。依穆斯林的說法,人應該只向神順服,一旦做到這一點,就可以擺脫世間一切局限,帝王將相與販夫走卒并無差異,這樣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可以博愛眾人。
耶穌主張“要愛你的鄰人”,那么“鄰人”是誰?不是專指我們熟識的親戚或朋友,也未必是指我們的同鄉或同胞,而是指所有“碰巧出現在我身邊,并且需要我幫助的人”。為什么應該愛這樣的鄰人?原因有二:一是人人皆是神之子女;二是信徒本身充滿愛心。我們談到宗教的社會效應時,最常聽見的說法是“勸人為善”。這是宗教的必然結果,但并非宗教的本質。宗教的目標在于上契超越者(神、力量或境界),以求得個體生命之解脫。行善愛人不論成績如何,只能訴諸機緣。這是基督教中的新教所堅持的“因信稱義”原則,足以說明信仰的單純性。唯其有單純的源頭,才能因應繁雜的事象,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即是此意。
傾聽了宗教所引發的價值,知道人生在世應該朝著“生命取向要高,生命體驗要深,生命能量要強”這三個目標前進,然后在閱讀本書時,將能獲得充分的資訊與資源。史密斯教授不談宗教史,但是對相關的歷史事件卻敘述得十分生動;他承認自己的論述未達全盤與平衡,但是卻稱得上豐富與精彩;他無意于比較各大宗教,但是行文中隨處引用不同教派的事例與格言來互相印證,使讀者自然體會到宗教的“價值”是相通的,宗教的“最佳面貌”是神似的。
我國讀者看到儒家與道家的部分,也許會覺得意猶未盡,這是因為“宗教”的嚴整形式并非孔子與老子所在意,更不是他們立說的目的。史密斯教授談到儒家時,為“宗教”一詞提出最寬泛的定義:“環繞著一群人的終極關懷所編織成的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不能脫離傳統的祖先崇拜與人際之間的禮儀。重要的不是信什么,而是如何信,以及如何以行動去實踐信仰,由此轉化自己的生命,成為博愛眾人的君子。孔子對祭禮的重視,并不止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更及于“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這種“每飯必祭”的做法,就是較之于其他宗教的規矩也不遑多讓。我的意思是,以宗教角度來理解儒家與道家,在西方是習以為常,在我們自己也不妨重新溫習一遍,或許能有新的領悟。
我初次接觸史密斯教授的作品是18年前,當時的《人的宗教》正是眼前本書的原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位作者竟是麻省理工學院人文學科的教授。理工科的第一流學生能聽這樣一位教授的課并且讀他的書,實在使人有“相得益彰”之感。現在這本名著譯為中文,則是我國讀者的福氣,值得珍惜。本書內容實為知識分子所必備者,但愿這篇短文能促使更多的人一探究竟,共品智慧傳統所廣施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