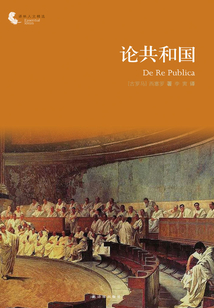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導讀:西塞羅的《論共和國》與《論法律》(1)
薛軍[1]
在絕大多數標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科書中,歐洲古典時代(主要是指古希臘與古羅馬)關于政體、法律問題的討論,是以希臘思想,尤其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學說為核心來展開的。雖然西塞羅撰寫了《論共和國》、《論法律》這兩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著作,但大多數思想史著作認為他是一個缺乏原創性的、希臘思想的淺薄涉獵者,是一個把希臘思想傳輸到羅馬的“搬運工”。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混合政體思想。西塞羅的《論共和國》中對此的確有所涉獵,但被認為是對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思想的照搬,而且他甚至沒有能夠說清楚代表了混合政體各個組成部分的究竟是何種羅馬制度,因此受到塔西佗的奚落(贊譽混合政體要比實現這一政體容易得多)。
果真如此嗎?坊間大多數“思想史”著作,在論述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的時候,在有限的篇幅中所能做的,無非就是蜻蜓點水般地談談其生平,引用其著作中幾段通常會被引用的話,然后順手為其貼上一個現成的標簽了事。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就這樣被制作成一個干枯的標本,陳列在思想史的櫥窗中。要真正進入到一個思想者的思維脈絡中,就必須拋開這些思想史的標簽,去認真閱讀著作本身,只有這樣才能對其思想獲得真切的體會。
歐洲古典時代流傳下來兩本論共和國的著作。一本是柏拉圖的“Politeia”。這本書在漢語譯本中被翻譯為《理想國》。譯名采取意譯方法,不能說非常準確,嚴格按照字面來翻譯的話,應該翻譯為《政制》(或《王制》)。西塞羅將其翻譯為拉丁語“Res publica”(共和國),這同樣是一種創造性很強的意譯,但產生了深刻的歷史影響,成為后世歐洲現代語言中的標準表述方法。西塞羅自己也寫了一本《論共和國》。由于西塞羅的書與柏拉圖的書,至少在拉丁語的表述上,是同名的,因此引得歷代學者試圖將二者進行對比。對比的結果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坐實了西塞羅是個希臘模仿者的說法。
但不能僅僅因為二者具有相同的標題、相同的題材以及在某些方面類似的本文結構,就忽視了二者的重要差別。事實上,只有對二者的差別有足夠的重視,才能夠真正理解西塞羅思想的脈絡和其卓越不凡的貢獻。這種貢獻,即使面對柏拉圖這樣震古鑠今的思想大家,也毫不遜色。我們知道,從人生閱歷看,雖然有過幾次不成功的從政嘗試,柏拉圖基本上是一個純粹的思想者,而西塞羅本人則具有非常豐富的政治實踐經驗,擔任過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最高官職——執政官,做出過涉及羅馬城邦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的決策。在擔任執政官期間,他果斷鎮壓喀提林陰謀,挽救羅馬共和國于危亡。一個具有這樣豐富的政治閱歷的人,對于政治體制的思考,不可能與純粹的思想家完全相同。正是在這一點上,西塞羅表現出與柏拉圖的根本差別。
對西塞羅來說,討論理論問題,進行抽象的哲學思辨,本身不是目的;只有將思考所獲得的成果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才是最終目的。正是基于強烈的現實精神,西塞羅不止一次地在討論國家政體的方法論問題上,對柏拉圖所代表的希臘傳統表現出批判的態度。在《論共和國》(1.36)中,西塞羅借西庇阿之口直接表明了自己對希臘學理傳統的不滿,他強調指出,自己關于政體的思想主要來源于實踐,而不是基于先驗原則的抽象思辨。對希臘政治哲學,西塞羅保持著謹慎的距離,雖然他對希臘思想非常熟諳,但他并沒有毫無保留地將其接納為一種絕對真理。
西塞羅的方法論意識,其實是把自己關于政體的思考,放置在一個與希臘有聯系但也存在區別的學理傳統之中。這一傳統是一種強調實踐理性、尊重歷史的現實主義的知識傳統。與之相對的是則是一種烏托邦的知識傳統。烏托邦傳統不依托于具體的歷史經驗,而是以虛構為主要手段。西塞羅在解釋他為什么必須從羅馬人的歷史起源的角度來討論政體問題時,將二者的區別解釋得非常清楚:“我會回到羅馬人民的‘源流’……向你們闡述我們國家如何誕生、發展、崛起,最終變得如此穩定和強大。這樣做,比起像柏拉圖作品中的蘇格拉底那樣去描述某個想象出來的社會,對于實現我的目標要容易多了。”(《論共和國》,2.3)
西塞羅對烏托邦式的思維所包含的缺陷有著清醒的認識。根據先驗的原則推演出來的政體形態,雖然看上去很美,但是缺乏現實性。而西塞羅認為,現實性是檢驗知識的品質的最根本依據。一個美好但卻與人們的生活和習俗不符合的國家構想,只可能是一種烏托邦。但西塞羅對烏托邦思想的價值并不完全否認,而是站在一個更高的理論層次,合理地承認其理論層面上的價值。柏拉圖的政體理論,是理念、形式意義上的,是邏輯推理的構造物。而西塞羅試圖要做的,則是貫通邏輯與歷史兩條線索,探討“現實的世界”與“可能的世界”。
正是因為西塞羅考察和分析的是“現實的世界”,因此在柏拉圖的“理想型”政體類型的分析框架之下,現實的政體類型就不可能不具有某種程度的“混合”政體的特征。現代的研究者總是強調西塞羅的“混合政體”思想與希臘的混合政體思想的類似,卻忽略了西塞羅的混合政體思想所賴以建立的知識原則,在根本上不同于希臘人的傳統。在希臘人那里仍然是基于思辨的邏輯推演而出現的混合政體思想,在西塞羅這里,已經演變為對一個現實的、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政體之特征的描述。
西塞羅的確在《論共和國》之中闡述了混合政體思想。但是在這種闡述中,已經將來自希臘的思想,賦予了自己獨特的思考。西塞羅意義上的“國家”(res publica)有著嚴格的內涵:“共和國就是公眾的財產。但是所謂公眾,并非指任何一種形式的人類聚集,而是指通過法律許可和共同利益而結合到一起的群體聚居的形式。”(《論共和國》,1.39)
西塞羅的這個關于共和國的著名定義,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希臘人關于政制問題的一般性的分析:個體作為政治共同體平等一員的身份,以及人民作為政體形態分析的基礎,被嚴格地規定下來。在這個前提之下,西塞羅開始分析政體問題,區分了三種政體形態(《論共和國》,1.42),即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在分析了三種政體存在的弊端之后,西塞羅論述了混合政體的優越性(《論共和國》,1.69)。西塞羅的論述與波利比烏斯的混合政體思想存在密切聯系,這一點當然不能否認。但如果把這一論述放在西塞羅政體理論的宏觀背景中,就可以發現,混合政體學說,充其量不過是西塞羅在論述何為最優政體的時候,對政體理論一般性的、導言性質的論述。而他所考慮的中心,仍然是現實的、歷史中的政體,這就是羅馬人的政制。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西塞羅在論述了混合政體理論之后,基本上不再停留在抽象的層面上,而是回到他一貫的歷史考察的思路之中:
從第二卷開始,西塞羅開始討論羅馬政制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關于羅馬政制的產生和發展,西塞羅借助于加圖之口所說的一段話(《論共和國》,2.2)特別值得關注:“……從來沒有出現過什么天才,厲害到可以確信不會忽略任何事情;從來沒有在某個特定時期出現過一群精明能干的人,具有足夠的遠見考慮任何事情;這必須經過相當長一段歷史的實際經驗的積累。”(《論共和國》,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