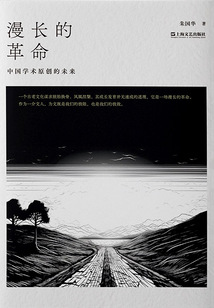
漫長(zhǎng)的革命:中國(guó)學(xué)術(shù)原創(chuàng)的未來(lái)
最新章節(jié)
- 第14章 后記
- 第13章 文學(xué)研究該如何作業(yè)
- 第12章 文學(xué)與文學(xué)研究的未來(lái)
- 第11章 學(xué)術(shù)趣味與理論的“介入”
- 第10章 《訪(fǎng)談》:藝術(shù)生產(chǎn)與中國(guó)語(yǔ)境
- 第9章 另類(lèi)的思想實(shí)驗(yàn):重讀《傷逝》
第1章 勇者不懼——序朱國(guó)華《漫長(zhǎng)的革命:中國(guó)學(xué)術(shù)原創(chuàng)的未來(lái)》
張輝
那天深夜國(guó)華把這本《漫長(zhǎng)的革命:中國(guó)學(xué)術(shù)原創(chuàng)的未來(lái)》(下簡(jiǎn)稱(chēng)《漫長(zhǎng)的革命》)電子版發(fā)給我,第一時(shí)間我就聯(lián)想到他另外幾本書(shū)的書(shū)名。或許這已是他的“朱氏風(fēng)格”吧,明明是一本嚴(yán)肅的學(xué)術(shù)論文集,標(biāo)題卻是《烏合的思想》;明明是對(duì)學(xué)生們語(yǔ)重心長(zhǎng)的“布道”,結(jié)集成書(shū),卻命名為《天花亂墜》。這當(dāng)然是他的朱式調(diào)侃或反諷,但我想,也更是他的自謙與“狡猾”。或者說(shuō),乃是他自己的“社會(huì)學(xué)詩(shī)學(xué)”,不僅與布迪厄相關(guān)、不僅與《權(quán)力的文化邏輯》相關(guān),更與他多年來(lái)形成的對(duì)于學(xué)術(shù)、對(duì)于世界的基本看法相關(guān)。不憚?dòng)谔角笳胬恚珡牟辉噲D占有真理,因而對(duì)任何貌似完美的宣稱(chēng)保持反思乃至批判的權(quán)利,也對(duì)任何試圖在一夜之間完成的“革命”保持警惕甚或抗拒。
悖論式的書(shū)名,事實(shí)上已直截了當(dāng)?shù)赝瑫r(shí)表明了他的耐心和決心。
2023年,國(guó)華有一篇點(diǎn)擊率極高的講演:《仁者不憂(yōu)》,我也曾是對(duì)之再四閱讀的擁躉。這次細(xì)讀《漫長(zhǎng)的革命》一書(shū),我則更多地體會(huì)到的是“勇者不懼”這一對(duì)中國(guó)學(xué)術(shù)思想界而言尤其稀缺而可貴的精神。
讀畢《漫長(zhǎng)的革命》,我讀出了國(guó)華對(duì)中國(guó)學(xué)術(shù)——不僅是他自己所在的文藝學(xué)學(xué)科——之現(xiàn)狀和歷史的強(qiáng)烈不滿(mǎn)。內(nèi)心有這種不滿(mǎn)的人,當(dāng)然不在少數(shù),但敢于說(shuō)出這種不滿(mǎn)的人卻是鳳毛麟角。因而,最讓我感佩的是,我這位“狡猾”的兄弟,毫不隱瞞地說(shuō)出了他所能看到的“真相”。如果他是那個(gè)看見(jiàn)“皇帝新衣”的孩子,也許我們還不需要感嘆,畢竟孩子是天真而幼稚的。但國(guó)華,他已年屆耳順,已足夠“成熟”、足夠“老道”、足夠“established”,卻依然無(wú)畏地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
事實(shí)上,他的一系列反思,不僅指向了當(dāng)下的一些體制性弊端,而且集中指向了更深層的精神秩序,也即他所說(shuō)的中國(guó)文化“認(rèn)識(shí)型(épistémè)”的不足。這無(wú)疑是會(huì)引發(fā)巨大爭(zhēng)論并令許多人不快的問(wèn)題,在泛民族主義越來(lái)越成為時(shí)尚的語(yǔ)境中,尤其如此。
但國(guó)華對(duì)這樣做的“副作用”似乎不以為意。在文集的第三篇文章《本土化文論體系何以可能》中,我格外注意到的是下面這段話(huà):“如果我們認(rèn)為,人文學(xué)科成績(jī)不行,其原因是應(yīng)試教育出現(xiàn)的題海大戰(zhàn)摧毀了想象力與知識(shí)好奇心,是因?yàn)槔砉た扑季S的殖民,將量化考核標(biāo)準(zhǔn)(科研成果發(fā)表刊物的級(jí)別、影響因子、H指數(shù)、發(fā)文的數(shù)量、獲獎(jiǎng)的級(jí)別、項(xiàng)目經(jīng)費(fèi)的總量等等)推行到文科領(lǐng)域里來(lái),是因?yàn)樯鐣?huì)所允許的思考的自由度還不足以滿(mǎn)足這個(gè)學(xué)科的需求,是因?yàn)樵S多學(xué)者因循守舊不思進(jìn)取,等等,這些分析可能都各有其道理,但是我想,最重要的癥結(jié)還可能是我們民族文化的認(rèn)識(shí)型與源于古希臘的西方文化的認(rèn)識(shí)型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而這一差異至今還在相當(dāng)程度上決定著我們的思想與行動(dòng)。”
對(duì)于一個(gè)比較文學(xué)的老學(xué)生來(lái)說(shuō),我一開(kāi)始幾乎是“職業(yè)性地”只能接受他的前半部分判斷。因?yàn)槲液蛧?guó)華一樣身處“卷之又卷”的當(dāng)代中國(guó)學(xué)術(shù)體制之中,對(duì)之可以說(shuō)是冷暖自知。但對(duì)于后面頗具二元對(duì)立色彩的說(shuō)法,則不敢馬上茍同。至少在我看來(lái),簡(jiǎn)單認(rèn)為中國(guó)文化“先天不足”,而我們所遇到的最根本問(wèn)題要由老祖宗來(lái)負(fù)責(zé),不僅是推卸自己這代人的責(zé)任,而且實(shí)際上是在為那些嚴(yán)重影響學(xué)術(shù)思想健康發(fā)展的非學(xué)術(shù)的、乃至反學(xué)術(shù)的干擾提供借口。不是一種魯迅意義上的“幫兇”,也是一種“幫閑”。
但隨著閱讀的深入,我卻也開(kāi)始反思自己的情緒性反應(yīng)和思想慣性。這甚至是我反復(fù)閱讀《漫長(zhǎng)的革命》時(shí)所獲得的最大收獲。
也不知是從什么時(shí)候開(kāi)始,我們和“五·四”那一代人相比,甚至和我們這一代人青春年少時(shí)相比,變得過(guò)于脆弱、敏感起來(lái),尤其是聽(tīng)不進(jìn)批評(píng)的聲音。不僅是來(lái)自外部世界的聲音,甚至自己人的批評(píng)聲音也聽(tīng)不進(jìn)去。似乎只有始終不變地說(shuō)好才是真正的“愛(ài)國(guó)”。否則,就會(huì)惱怒,就會(huì)咒罵,就會(huì)上綱上線(xiàn)。
而國(guó)華的“勇”正體現(xiàn)在這種沒(méi)有畏懼的自我批判之中。《漫長(zhǎng)的革命》,尤其是作為全書(shū)“文眼”的同題論文,不僅提示我們要善于認(rèn)識(shí)中國(guó)文化充實(shí)而有光輝的優(yōu)越之處并將之發(fā)揚(yáng)光大,而且要努力在與外來(lái)文化的對(duì)比中看到中國(guó)文化的不足甚至危殆之處。這也是自王國(guó)維、魯迅、陳寅恪……以來(lái),那些最了解也可以說(shuō)真正熱愛(ài)中國(guó)文化的先賢,所留給我們的最偉大啟示。很顯然,國(guó)華是在有意識(shí)地接續(xù)這個(gè)了不起的傳統(tǒng)。
細(xì)心的讀者一定注意到了,國(guó)華在書(shū)中刻意“反復(fù)引用”的一段陳寅恪的話(huà)。這段話(huà)由于間接出自《吳宓日記(1917—1925)》,其實(shí)并不如陳寅恪的其他論述那樣廣為人知,但卻顯然引起了國(guó)華的格外重視:“中國(guó)之哲學(xué)、美術(shù),遠(yuǎn)不如希臘,不特科學(xué)為遜泰西也……而救國(guó)經(jīng)世,尤必以精神之學(xué)問(wèn)(謂形而上之學(xué))為根基。而吾國(guó)留學(xué)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不自傷其愚陋,皆由偏重實(shí)用積習(xí)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國(guó)之實(shí)業(yè)發(fā)達(dá),生計(jì)優(yōu)裕,財(cái)源浚辟,則中國(guó)人經(jīng)商營(yíng)業(yè)之長(zhǎng)技,可得其用;而中國(guó)人,當(dāng)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guó)人以學(xué)問(wèn)、美術(shù)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
毋庸置疑,這里說(shuō)中國(guó)人具有“偏重實(shí)用”的“認(rèn)識(shí)型”,事實(shí)上并不是在盲目地否定中國(guó)人與中國(guó)文化,而恰恰是對(duì)中國(guó)知識(shí)人的提醒乃至激勵(lì),是我們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前提,也是中國(guó)人文學(xué)術(shù)真正對(duì)世界有所貢獻(xiàn)不可或缺的前提。
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國(guó)華在文中對(duì)王國(guó)維、朱光潛等民國(guó)大師也并非沒(méi)有“苛評(píng)”。因?yàn)椋皬母疽饬x上來(lái)說(shuō)”,受“認(rèn)識(shí)型”和思維慣性的限制,“他們對(duì)西學(xué)并沒(méi)有真正遵循澄懷觀(guān)道、虛己以聽(tīng)的原則,或者說(shuō)阿多諾所倡導(dǎo)的‘客體性?xún)?yōu)先’的基本立場(chǎng),相反,他們無(wú)論是否在意識(shí)層面有所覺(jué)察,客觀(guān)上他們?cè)诟蟪潭壬弦廊徊扇×恕?jīng)注我’的接受態(tài)度,起作用的仍然是傳統(tǒng)文化本位的文化主體性取向。”
也正因?yàn)榇耍瑖?guó)華舉例指出,朱光潛的《詩(shī)論》“就整體格局氣象而言……依然偏安于中國(guó)詩(shī)學(xué)之一隅,不能……參預(yù)當(dāng)代世界學(xué)術(shù)之潮流”;而晚年王國(guó)維不再縈心于西學(xué),甚至在向宣統(tǒng)帝上的奏章《論政學(xué)疏》里,對(duì)西學(xué)進(jìn)行了“極為嚴(yán)厲然而明顯淺薄的指控”,所謂“西說(shuō)之害,根于心術(shù)者一也”,從而完全背離了他在《論近年之學(xué)術(shù)界》一文中所提出的,學(xué)術(shù)之爭(zhēng)需要超越“中外之見(jiàn)”“彼此之見(jiàn)”“只有是非真?zhèn)沃畡e耳”的早年主張。
更可貴的是,《漫長(zhǎng)的革命》不僅提醒我們充分看到中西思想交通中的曲折,而且還希望我們有容乃大地承認(rèn),中國(guó)特有的“知識(shí)型”所可能遠(yuǎn)遠(yuǎn)超出“純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復(fù)雜意涵,以及它對(duì)未來(lái)中國(guó)的深刻影響。如國(guó)華在一個(gè)精微的比喻中所說(shuō):“我們當(dāng)然可以采用各種烹飪技術(shù)來(lái)炮制薇草,例如烤薇菜、薇湯、薇羹、薇醬、清燉薇、原湯燜薇芽、生曬嫩薇葉,但是,薇草究竟是薇草,我們畢竟不能指望單是依靠它,能做出一桌的滿(mǎn)漢全席來(lái)。”(參見(jiàn)《從課程、教研室到學(xué)科:文藝學(xué)的中國(guó)生產(chǎn)》),更何況早在《京師大學(xué)堂章程》中,我們就已經(jīng)讀到這樣允執(zhí)其中的文字:“夫中學(xué),體也,西學(xué),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我想,如果我沒(méi)有理解錯(cuò)的話(huà),怎樣“剛?cè)嵯酀?jì)”、怎樣既超越又融通中西之見(jiàn),正是國(guó)華這本“附帶著”討論文藝學(xué)學(xué)科史、《傷逝》與個(gè)人主義、以及“模特兒事件”等等問(wèn)題的論集,其最中心關(guān)切之所在。
剩下的問(wèn)題是,這個(gè)如此嚴(yán)肅鄭重地討論學(xué)術(shù)“革命”——而且是“漫長(zhǎng)的革命”——的老兄弟,是怎么與他戲稱(chēng)的作為“流寇”的,那個(gè)具有“游戲態(tài)度和娛樂(lè)精神”的“自己”和平相處的呢?(參看訪(fǎng)談《文學(xué)研究該如何作業(yè)》)他的“烏合的思想”,他的“天花亂墜”的表達(dá),究竟遮蔽了什么?又由于這種遮蔽彰顯了什么?
我不敢給出最后的答案。給出答案,也必然會(huì)遭到這位《兄弟在美國(guó)的日子》的作者反唇相譏。
就此打住,就此祝這位幾十年來(lái)亦莊亦諧的好伙伴六十歲生日快樂(lè)。如往常一樣,甚至不用握手和擁抱。
2024年9—10月 草于京西學(xué)思堂燈下,再改于撒馬爾罕之行前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