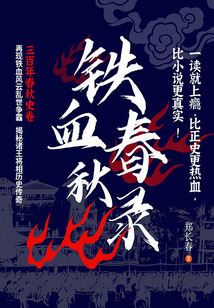
鐵血春秋錄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風云突變》:周室衰微
春秋時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它實際上是東周的前段,起止時間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共294年,因為時間跨度和孔子編著的魯國編年體史書《春秋》的起止時間基本吻合,所以史家就把這一段歷史時期叫作“春秋”。春秋時期是一個大變革、大分化、大瓦解、大動蕩、大融合的時期,社會風雷激蕩,戰(zhàn)火連天,烽煙遍地。據(jù)《春秋》記載,這一時期各諸侯國軍事行動共有480余次,春秋開始時有諸侯國142個,結束時被消滅的就有52個;諸侯中被屬下殺掉的有36位,被其他諸侯國殺死的7位。可以說,這一時期徹底破壞了西周建立的社會秩序,各種政治勢力此消彼長,周王室對天下的統(tǒng)治地位受到根本動搖。
周原是商朝的一個諸侯國,姬姓。在陜西岐山一帶,方圓不過百里,因為治理得當,不斷招納賢才,收留從其他諸侯國流寓去的士民,不斷發(fā)展壯大,后來成為西方諸侯的領袖,稱西伯侯。后來由于商紂王的殘暴統(tǒng)治,使天下民怨沸騰,西伯侯姬發(fā),就會盟天下諸侯,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定都鎬京,追謚父親姬昌為文王。姬發(fā)在位四年就去世了,追謚武王。兒子姬誦[1]即位時才八歲,由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輔政,周公制定了周禮,加上他的勤政愛民,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按當時的規(guī)定,王,也叫天子,天下只能有一個。天子可以擁有方圓千里的土地,萬乘的兵車,所謂“天子萬乘”。也就是天子坐的車要八匹馬拉,諸侯坐的車六匹馬拉,所謂“天子八駿”“諸侯六駿”。一般的車可能兩匹馬拉、三匹馬拉、四匹馬拉,但通常的計量單位是一車四馬,叫作“一乘”,也叫駟,所謂“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就是說這四匹馬拉的車跑得很快。一般的兵車叫“大輅”,都是“立乘”,乘的人都是站著的。御者,就是駕車的在中間執(zhí)轡,兩邊站著甲士,一名執(zhí)戈,一名執(zhí)矛;或一名執(zhí)戈或矛或戟,一名執(zhí)弓。一乘車后還有若干步兵,就像現(xiàn)代坦克后面跟步兵一樣。指揮車叫“戎輅”,也是“立乘”,主帥居中,自掌旗、鼓、金,擊鼓時進軍,鳴金時收兵。左邊一人駕車,右邊一人負責警衛(wèi),叫作“車右”。
天子的家庭及治理天下的辦事機構叫王室,王室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輔助天子執(zhí)政。在地方上分封了一千多個諸侯。有幾類人可以當諸侯:打天下過程中的有功人員;天子的宗親;前朝天子的后裔(象征性地安排一下)。諸侯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可以有不低于方圓百里的土地,伯可以有不低于方圓七十里的土地,子、男可以有不低于方圓五十里的土地。方圓五十里以上的可以面見天子,也有的土地不夠五十里的,不能面見天子,依附于其他諸侯,叫“附庸”。公侯可以擁有千乘兵車,伯以下的可擁有五七百乘不等。諸侯幫助王守衛(wèi)國家,每年還要給王室貢獻自己的賦稅和特產(chǎn)。諸侯統(tǒng)治的地盤叫“國”,狹義的“國”專指國都。大夫也可以治理地盤,叫“家”。諸侯由大夫幫助治理朝政,大夫有家臣幫助管理事務,大夫家里也可以擁有一定的家兵保護自己。諸侯和大夫可以世襲,也可以被剝奪。有諸侯不服從天子,天子就征召其他諸侯去討伐他。天子到各地去巡視,上下和睦,其樂融融。當時的天子很有權威。
但時間一長,問題就出來了。有的諸侯國自然條件好,有的諸侯國自然條件不好;有的地理條件好,發(fā)展空間大,有的地理條件不好,發(fā)展空間小;有的諸侯治理得好,有的治理得不好。所以,有的諸侯國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有的卻像開春后的冰雪越化越小,以至于最后被消滅、吞并。周的統(tǒng)治過程,也出現(xiàn)了不少問題,但基本還維持了下來,到了第13代君主周幽王,荒淫無道,烽火戲諸侯,信譽破產(chǎn),被西戎攻破鎬京,圍殺而死。其子周平王在原地待不住了,只好于公元前770年在一些諸侯的幫助下東遷洛邑。遷都洛邑后,周朝的統(tǒng)治中心就東移了,史稱“東周”。春秋時期從此開始。
在這一時期,周天子逐漸失去了迷人的光環(huán),失去了往日的權威,失去了統(tǒng)御萬方的能力,對王室有功的諸侯得不到獎賞,公然冒犯天子和王室的諸侯受不到懲罰,諸侯不再像以前那樣對王室百依百順,有些諸侯根本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天子名義上是天下的共主,實際上勢力范圍、綜合國力淪為一個中等諸侯國的規(guī)模和水平,甚至還有求助、依附于一些強大的諸侯,成了諸侯的玩偶,甚至是利用的工具。
春秋初期幾個大的諸侯國,鄭國在今河南鄭州一帶,衛(wèi)國在今河南濮陽一帶,宋國在今河南商丘一帶,齊國在今山東淄博一帶,魯國在山東曲阜一帶,楚國在今湖北荊門一帶,晉國在今山西曲沃、新絳一帶,秦國在今陜西咸陽一帶。那時的區(qū)劃并不像今天這樣完整,這中間夾雜著許多中小國,諸如陳、蔡、曹、邾、紀、莒等,楚國周圍江漢一帶也有很多小國。
諸侯的好惡、諸侯的言行,都會引起戰(zhàn)爭,都會影響到國家的興衰存亡。齊、宋、晉、秦、楚幾個國家經(jīng)常混戰(zhàn)自不必說,這里僅從春秋初期最強大的鄭國身上就可看出當時的社會亂象。
周宣王的弟弟友,封地在鄭,爵位是伯,世稱“鄭伯友”,是王室的司徒,在平王東遷的過程中立了大功,獻出了生命,賜謚為“桓”。鄭世子掘突被任為卿士,留朝中和太宰一同輔政,就是鄭武公;鄭武公死后,長子寤生即位,就是鄭莊公,鄭莊公也在朝中執(zhí)政。
寤生出生時驚動了母親姜氏,民間傳說他是“倒生之子”,即脫離母體時腿先出來,讓母親受極大痛苦;還有一種奇怪說法是他系母親睡夢時所生,母親醒來嚇了一大跳。但不管他是怎么出生的,他作為一個新生命都屬于無辜,母親受多少苦都怨不得他,但他母親姜氏硬是不喜歡他,偏愛他的弟弟段。因此,在寤生做世子時,母親姜氏就屢次說寤生的壞話,要武公廢掉寤生立段為世子[2],武公沒答應。寤生即位后,姜氏給段要這里的封地、那里的封地,最后封到共,叫共叔段。共叔段也做了不少小動作,有大臣勸鄭莊公早點對段采取措施,否則會造成嚴重后果,但鄭莊公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任其發(fā)展蔓延,最后到姜氏和段里應外合搞叛亂的時候,莊公出手了。鄭莊公在祭足[3]等大臣的支持下,平定了叛亂,共叔段自殺,姜氏被軟禁。后來在潁考叔的勸說下,母子和好。段的兒子逃到滑國,在衛(wèi)國的支持下要回國替父報仇,后來被平息了。
這樣一來二去,鄭莊公一連幾年沒上朝理政。周平王不滿,就物色了一個人想替換他,結果鄭莊公在朝中安插的耳目來報信,他就去朝中辭職,搞得平王很被動,百般挽留。最后,竟然派太子狐到鄭都滎陽為人質,鄭國派世子忽到東都洛陽為人質。這本來就是王室衰微、天子降格的表示,互相不信任,才會派人質;互相派人質,就說明雙方成了對等關系,失去了君臣的意義。
周平王在位51年,駕崩時,鄭莊公和周公黑肩同攝朝政,讓世子忽歸鄭,迎太子狐回朝中即位。太子狐因沒在父親面前盡孝,哀痛過甚,回到周,還沒接上班就死了。兒子林嗣立,就是周桓王,公元前719年,是周桓王元年。
桓王為他父親在鄭做人質而早死感到悲傷,并且對鄭伯久專朝政不滿,就和周公黑肩商議要奪鄭莊公之權。周公黑肩勸諫不要這樣,但桓王決心已下。有一天上朝,桓王說:“卿是先王之臣,朕不敢再用。請自便。”莊公說:“臣早該辭朝,現(xiàn)在就走。”憤憤出朝,見到人說:“這孩子沒良心,不值得輔佐。”當天就回了鄭國。世子忽和眾官員出城迎接,他就把桓王趕他出朝的事情說了一遍,眾官員都很氣憤。高渠彌當即就要率師攻打周城。潁考叔說不可,等年過半載再去朝覲,周王就會有后悔之心,說不定就又召回朝中了。大夫祭足說,你們兩位說得都有道理,不如兼用,我愿率兵直接到周直接管轄的地方去騷擾一番,玩他一些難看,將來再去朝覲不遲。莊公準奏,就命祭足領一支車馬,見機行事。
祭足先到周王室直接管轄的溫邑邊界,說本國遭了荒年,沒有吃的,向溫大夫求千鐘粟,溫大夫說,沒接到周王的命令,不能給。祭足說:“現(xiàn)在大麥、小麥都熟了,都能吃了,我們自己就能取,何必求他們!”就讓士兵各自備好鐮刀,分頭把田中之麥,全都割光,滿載而歸,祭足自領精兵,往來接應。溫大夫知道鄭國兵強馬壯,只好忍氣吞聲。祭足在邊界上休兵三個月,又到成周,秋七月中旬,早稻已熟,吩咐軍士假扮商人模樣,將車埋伏各村里,三更時分,一齊動手將稻穗割下,五更時聚齊。成周郊外的稻子,全剩下了空稈子。等到守將發(fā)覺,點兵出城,鄭兵已經(jīng)走遠。
周桓王接報,要興兵伐鄭,被周公黑肩勸止,只是告誡邊境地區(qū)要加以提防,不讓諸侯軍隊隨便入境。隨后鄭國我行我素,又干了不少令王室難堪的事情,最后發(fā)展到竟然假托王命,糾集齊國魯國,攻打宋國。宋國雖然多年不朝貢,但要討伐它還得經(jīng)天子同意。周桓王原先只是讓虢公林父為右卿,鄭莊公為左卿,只掛名不做事,這時就徹底剝奪了他的職位,讓虢公林父獨掌朝政。鄭莊公心懷怨憤,一連五年不朝拜。周桓王終于忍無可忍。說:“鄭寤生無禮之極!如果不討伐他,人人都要學他的壞榜樣。朕當親率六軍,去聲討他的罪行!”虢公林父勸諫桓公不要親自去,桓公不聽,召來蔡、衛(wèi)、陳三國軍隊,一同伐鄭。
周桓王讓虢公林父率右軍,蔡、衛(wèi)之兵隨著;周公黑肩率左軍,陳兵隨著;自統(tǒng)大軍為中軍,左右策應。他本想大軍一到,鄭國必然恐懼,俯首謝罪,給個臺階下來,掙回一點臉面就行了。誰知道鄭國也把軍隊分成左、中、右三路來對壘。大夫曼伯率左軍對天子右軍,正卿祭足率右軍對天子左軍。鄭伯親率高渠彌、原繁、瑕叔盈、祝聃等為中軍,和天子對敵。左右兩軍都排成方陣。桓王看到鄭伯竟敢迎戰(zhàn),怒不可遏,兒子竟敢和老子對打,簡直翻天了。所以要親自出戰(zhàn),教訓這個忤逆之子,虢公林父諫阻了他。第二天,各排陣勢,鄭莊公傳令:“左右二軍不可輕動,看到軍中大旗揮動時,再一齊進兵。”
周桓王在朝中精心準備了一篇責備鄭伯的話,專等大軍一到,鄭君出頭磕頭告饒的時候,當陣訴說,來挫一挫他的銳氣。誰知一點也沒用上,鄭莊公給他躲貓貓,根本不給他打照面,不給他發(fā)泄的機會。鄭君雖然列陣,只是把住陣門,絕無動靜。桓王使人挑戰(zhàn),也無人應戰(zhàn)。將至午后,莊公考慮到周王的士兵已經(jīng)怠惰,叫瑕叔盈把大旗揮動,左右兩方陣一齊鳴鼓。曼伯殺入左軍,陳國本來和鄭關系不錯,礙于天子的面子,勉強參與,本來就沒有斗志。鄭兵一沖,當即奔散,反而將周兵沖得穩(wěn)不著陣腳,周公黑肩阻遏不住,大敗而走。
祭足殺入右軍,只看蔡衛(wèi)旗號沖將過去。二國雖然和鄭是死對頭,但兩國士兵看到陳兵已散,祭足一沖,各自覓路而逃。虢公林父仗劍立于車前,約束軍人:“如有亂動者立斬!”祭足不敢硬逼,虢公林父緩緩而退,不折一兵一卒。
桓王在中軍,聽到敵營鼓聲震天,知道鄭兵出戰(zhàn)。后來聽見士卒紛紛耳語,隊伍大亂,又望見潰兵,知道左右兩營有失,中軍也立不住腳了。鄭兵像一堵墻壓過來。祝聃在前,原繁在后,曼伯、祭足前來會合,殺得王師車毀馬死,將殞兵亡。桓王傳令速退,親自斷后,且戰(zhàn)且走。祝聃望見繡蓋之下,料是周王,集中眼力瞄準,一箭射去,正中周王左肩。幸虧裹甲堅厚,傷得不很嚴重。祝聃催車前進,虢公林父前來救駕。正在危急時刻,鄭中軍鳴金收兵。桓王退二十里下寨,周公黑肩也趕到,訴說陳人不肯出力,才導致了失敗,周王羞慚滿面,說:“這是朕用人不明的過失。”事后鄭莊公派祭足去向周王道歉,去營中慰問,周桓王借梯下樓,最后不了了之。
后來鄭莊公要獎賞射中周王肩膀的祝聃,被一些人勸阻,說這種行為并不值得鼓勵,祝聃氣得背部長瘡疽而死。鄭人“射王中肩”是一個轉折,說明周天子的窩囊,周王室的衰微。
后來鄭國內部也出了問題。周桓王十九年,鄭莊公病重,把祭足召到床頭,說:“寡人有十一個兒子。世子忽之外,子突、子亹、子儀,都有貴人之相。子突的才智福祿,在三人中又高出一籌,但這三個兒子又都是不得善終的相。寡人想把君位傳給子突,怎么樣?”祭足說:“子忽的母親鄧曼是元妃,子忽是嫡長子,早就立了世子,并且屢建大功,國人已經(jīng)信從。廢嫡立庶,臣不敢奉命!”祭足不聽令,自有道理,再加上鄭莊公將死之人,不聽令他也沒辦法。只好說:“子突不會安心居于下位,如果要立子忽,只有將子突送到他姥姥家去。”祭足說:“‘知子莫若父’,那就照您的辦。”莊公感嘆道:“鄭國從此麻煩事多了。”就讓公子突出居宋國。夏五月,莊公薨,世子忽即位,就是昭公。派幾位大夫分別出訪各國。祭足出訪到宋,還有一項特別使命,就是觀察一下子突有什么動作。
公子突的母親,是宋國雍氏之女,名叫雍姞。雍氏宗族大多在宋國做事,宋莊公非常寵信。公子突被趕到宋國,與雍氏商議歸鄭的策略。雍氏報告給宋莊公,宋公答應給想想辦法。正好祭足到宋國聘問,宋公高興地說:“子突歸鄭,就在祭仲身上了。”就讓南宮長萬在朝中埋伏甲士,專等祭仲入朝。祭仲來了,剛行過禮,甲士就快步走出來,將祭仲執(zhí)拿拘押。祭足大叫道:“外臣[4]有什么罪?”宋公說:“先到軍府再說。”
當天,祭足被囚禁在軍府。甲士周圍把守,水泄不通。祭足既懷疑,又害怕,坐不安席,食不甘味。當天晚上,太宰華督攜酒親自來到軍府,與祭足壓驚。祭足說:“寡君讓足來和上國[5]修好,細想也沒有得罪之處,不知為何動怒。是寡君的禮品我沒全部帶到,或是禮數(shù)上有什么缺失呢?”華督說:“全都不是。公子突是雍氏所生,天下人都知道。現(xiàn)在子突流落在宋,寡君憐憫他;這子忽性格柔懦,不堪為君。先生您若能廢掉子忽,立子突為國君,寡君愿意和先生結為姻親,世代交好。希望先生考慮。”祭足說:“立寡君,是先君的安排。作為臣子,廢掉國君,諸侯將要討伐我的罪行了。”華督說:“鄭先君寵愛雍姞,母寵子貴,不是也說得過去嗎?況且弒君篡逆的事情,哪國沒有?就看你實力如何了,誰敢問罪!”又和祭仲耳語:“我們國君,也是先廢掉舊君后又立起來的。先生一定要這樣做,寡君會保證您不會有什么閃失。”祭仲皺著眉頭不說話。華督說:“先生一定不這樣做的話,寡君將任命南宮長萬為將,帶六百乘兵車,把公子突送回鄭國。出發(fā)那一天,把先生您殺掉在軍中示眾。我看你的命就到這一天為止了。”足智多謀的祭仲,在這會兒也毫無辦法,只好答應。華督又要他賭咒發(fā)誓,祭足說:“有不立公子突的,天打雷殛!”華督軟硬兼施,搞定了祭足,連夜報告宋公,說祭仲已經(jīng)聽命了。
第二天,宋公派人把公子突召到密室,對他說:“寡人和雍氏有約定,要送你回國。今天鄭國通告立新君的事情,子忽有密信送給寡人說,一定要把你殺掉,愿意用三座城作為酬謝。寡人不忍心,所以私下告訴你。”公子突拜謝,說:“突不幸,逃難在上國。突是死是活,都掌握在君的手心里。若能托君的福,使突能回去見到先人的宗廟,君要什么我給什么,哪里只是三座城呢?”宋公說:“寡人把祭仲囚禁在軍府,正是為了公子的緣故。這個大事離了祭仲辦不成,寡人要讓你們立盟約。”就召來祭足,讓他和子突相見,又召來雍氏,講明要廢忽立突,三人歃血定盟,宋公自為司盟,主持定盟,太宰華督在場,負責定盟事務。宋公讓子突立下盟約,三城之外,一定要白璧百雙,黃金萬鎰。每年給宋國三萬鐘粟,作為酬謝之禮。并讓祭足簽名為證。宋公獅子大開口,子突急于得國,只要讓回去做國君,把國全賣掉也行,反正這會兒不是自己的,要什么就應承什么。宋公又讓子突將國政全部委托給祭足,突也答應了。又聽說祭足有個女兒,就讓他把女兒許配給雍氏之子雍糾,并立即帶雍糾回國成親,給以大夫的官職,祭足也不敢不答應。
公子突和雍糾都是商人打扮,駕車跟著祭足,于九月初一到鄭,藏在祭足的家里。祭足假托有病,不能入朝。各位大夫都到祭府問安。祭足埋伏上百人的敢死隊在壁衣[6]里面,請諸大夫到內室相見,諸大夫見祭足面色紅潤、肌肉飽滿、衣冠齊整,哪里有什么病?大驚道:“相君沒有病,為什么不入朝?”祭足說:“不是我有病,是國家有病了。先君寵愛子突,把他托付給了宋公。現(xiàn)在宋派南宮長萬為將,率兵車六百乘,輔助公子突來攻打鄭國。鄭國還沒穩(wěn)下來,憑什么來抵擋?”諸大夫嚇得面面相覷,沒人答話。祭足說:“今天要想不讓宋兵來,只有廢立可免禍。公子突也在這兒,大家愿意跟從他嗎?請表個態(tài)。”高渠彌因為莊公在世時要提他做上卿,被世子忽阻攔,一向和世子忽不睦。挺身按劍說:“相君此言,是社稷之福。我們愿意見新君!”眾人聽了高渠彌的話,懷疑他和祭足是約好的,又窺見壁衣里面有人影在動,心里都害怕起來,齊聲說行,行,行。祭足把公子突叫過來,讓到上座。祭足和高渠彌先下拜,諸大夫無可奈何,只得一同拜伏于地。
祭足已經(jīng)預先寫就了連名表章,使人送給子忽,說:“宋人用重兵把子突送回鄭國,臣等就不能侍奉您了。”又親自寫了個密信,信中說:當初立您做國君,不是先君的意思,是我祭足主張立您的。可現(xiàn)在,宋國把足囚禁起來要送回子突,還要挾臣給他定了盟,不定盟他們要殺我,臣恐怕自己死了對君也沒有什么好處,白搭一條性命,就親口答應了。現(xiàn)在宋兵快到城外了,群臣都害怕宋國的強大,都商量好了要去迎接子突。主公不如變通一下,暫時避位,給我一些轉圜的時間,有機會再把您迎回來復位。最后發(fā)誓:違此言者,有如日!這個有如日,就是像太陽那樣晚上就落下去。老百姓發(fā)誓,不怎么怎么做,是兔子,是狗,是王八。古代大臣發(fā)誓,稍稍文明、含蓄一點點。鄭昭公接到了表文和密信,知道自己孤立無助,出奔到衛(wèi)國去了。可見那時也是要做官,找靠山,做諸侯也要找靠山。子忽曾幾次推辭和齊僖公女兒文姜的婚姻,錯失了齊國這個大靠山,從人格上講沒問題,從政治上講是不利的。
九月己亥日,祭足奉子突即位,是為厲公。大小政事,都由祭足決定。祭足把女兒嫁給雍糾,厲公又封雍糾為大夫。雍氏是厲公的舅家一族,厲公在宋時,和雍氏往來親密。所以厲公寵信雍氏,不亞于祭足。自厲公即位,國人已經(jīng)安服,只有公子亹、公子儀心懷不平,又怕厲公加害,當月,公子亹奔蔡,公子儀奔陳。鄭國從此變亂不止,受到削弱。
楚國吞并了周圍許多小國,還擅自稱王。還有魯國、宋國、衛(wèi)國等都發(fā)生了弒逆事件,天下的亂象一天比一天厲害。在這種背景之下,春秋諸侯中產(chǎn)生了幾位霸主。所謂霸主,就是憑借自己國家的實力做了諸侯的首領。孟子對此有過分析,他說: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
意思是,憑著國力,再假借一些仁義來做包裝,能夠成為霸主,所以霸主必須從大國中產(chǎn)生。
稱霸往往不是一代的事情,分析霸主的興起和稱霸過程,也要從他們的前代說起。這里,先說第一個登上春秋霸主寶座的齊桓公。
注釋
[1]周成王。
[2]也叫太子、適子,是國君的繼承人。
[3]字仲,一般稱祭仲,是鄭國的一個重要人物。
[4]大臣在其他諸侯面前自稱外臣。
[5]相當于今天稱貴國。
[6]墻上掛的帳子之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