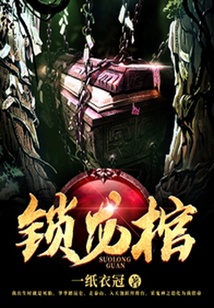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shū)友吧第1章 天道不容
我出生的時(shí)候,是個(gè)死胎。
據(jù)說(shuō)出生的那天,天空中烏云密布,雷霆如龍,仿佛天罰一般,降下九道驚天動(dòng)地的雷柱!
那一日方圓百里,百姓出逃,萬(wàn)獸倉(cāng)惶,天雷滾滾。只有屋中,爺爺顫抖著抱著剛從母胎中降生,卻未能啼哭一聲的我,從門檻走了出來(lái)。
老眼中留下兩道血淚,悲嘆了一聲:“天哪!”
從出生起,我便注定不該活在這個(gè)世界上。
九道天雷,就是警告,告訴爺爺和父親,天威不可逆。身為風(fēng)水奇門四魁首之一的東張君,爺爺自然比誰(shuí)都清楚‘天意’。
但是這一胎的意義非同小可,即使要逆天,爺爺也打定主意要把已經(jīng)是死胎的我給保下來(lái)。他想到的東西只有一樣,而那里是作為魁首的他都九死一生的去處。
“阿巽,我要帶孫子去拜將臺(tái)。你在屋子周圍按天罡位,擺下九護(hù)天罡陣。無(wú)論發(fā)生什么,絕對(duì)不可以出來(lái)!”爺爺滿臉嚴(yán)肅,將皮膚鐵青我包在襁褓之中,“如果三十六天后我還未出來(lái),就去找你師兄劉離,讓他帶上三十六條白蛇去拜將臺(tái),切記!”
父親正為母親十月懷胎生下個(gè)死胎而悲痛欲絕,此時(shí)聽(tīng)到‘拜將臺(tái)’三個(gè)字,頓時(shí)面如土色,連忙跪下哀求道:“爸!你可別做傻事啊!大陰司早就預(yù)言過(guò)我張家三代無(wú)后,此次也只是應(yīng)天命,您何必……”
雷霆過(guò)后,暴雨傾盆。
爺爺在雨中身形挺拔,雖以近六旬,卻如同青松一般。他的聲音混雜在雨中,用只有父親能聽(tīng)到的聲音說(shuō)了一段話后,轉(zhuǎn)身頭也不回地帶我離開(kāi)了家,走入了大山之中。
大山外表看上去平平無(wú)奇,但越往里走,越能感覺(jué)詭異、可怕,好像整個(gè)世界壓在脊背上般的重量!又仿佛有無(wú)上存在俯瞰著自己的恐怖!
走進(jìn)三十里,已經(jīng)鳥(niǎo)聲寂、蟲(chóng)聲滅,走獸絕跡了。
再往前,滿地的骸骨。
分不清是人的,還是怪物的,還是有別的東西,磷火無(wú)盡,飄飄揚(yáng)揚(yáng)。但凡有靈性的生靈都會(huì)避開(kāi)這里,都會(huì)感覺(jué)到這里是片死亡絕地,不該有活物進(jìn)入!
爺爺走進(jìn)這里,一直低頭看路,不曾向左右瞥上一眼。
而這條路的盡頭,是一座古樸、滄桑,泛著黑色,猶如由無(wú)盡鮮血染紅,又經(jīng)過(guò)數(shù)不清的歲月沉淀而變成的顏色。
那是一座拜將臺(tái),矮矮的一座,只有九級(jí)。
但爺爺走到拜將臺(tái)前的時(shí)候,膝蓋已經(jīng)在打彎了,好像承受了無(wú)以倫比的壓力。臉上青筋繃起,邁出一步,都是如此的困難。
普天之下,能在這件死物面前邁開(kāi)步子的人寥寥無(wú)幾。而爺爺不愧是當(dāng)今風(fēng)水奇門最優(yōu)秀的四個(gè)人之一,一步步邁開(kāi)步子,接近拜將臺(tái)。
爺爺最終止步在拜將臺(tái)前,長(zhǎng)嘆一聲,無(wú)限懇求與感慨。
“人皇設(shè)立的……拜將臺(tái)啊。”
三十六聲雷響,環(huán)繞與秦山。直到三十六天之后,聚攏來(lái)厚厚的烏云,一聲聲霹靂,猶如電光火石,一道道閃電,好似裂開(kāi)了天空。
最終一聲炸雷,有九道閃電轟隆劈向秦山的深處。
張家院中,聞?dòng)嵍鴣?lái)的劉離和父親都變了顏色。
沒(méi)人知道那天在泰山的深處發(fā)生了什么,只知道從泰山深處的回來(lái)的爺爺,抱著一個(gè)咯咯傻笑的男嬰。
從那天起,爺爺就此封卦。
那個(gè)男嬰,也就是日后的我。
而我從那天起,就再?zèng)]有見(jiàn)過(guò)我的父母。從我有意識(shí)起,在我身邊的人就一直是爺爺。
我們離開(kāi)了秦山,踏上了周游天下的旅途。一路走遍千山萬(wàn)水,在一個(gè)地方停留絕不超過(guò)一年,即便是留下,我們所用的名字也絕對(duì)不會(huì)重復(fù)。
爺爺告訴我,我和別人不一樣。
七歲那年,爺爺帶我去了昆侖山。那無(wú)垠雪峰,浩浩蕩蕩,縱橫起伏于大地之上,皚皚白雪如天蓋,道道龍脊氣吞山河!
爺爺就帶著我,指著那處最高的昆侖峰說(shuō):“那里便是天下龍脈之祖。”
腳下是皚皚白雪,身后是一條長(zhǎng)長(zhǎng)腳印。我似懂非懂,只出神注視著那高聳入云的神峰,俯瞰著無(wú)數(shù)向整片華夏延伸出去的山脈,我所站的地方,是天下風(fēng)水師向往的龍脊!
八歲的那年,爺爺一身青色布掛,帶我一步步,徒步登上了泰山。那泰山頂上,玉皇觀中的道士對(duì)我們一老一少兩個(gè)行人不屑一顧,甚至不讓我們進(jìn)觀參拜。
爺爺也不惱怒,指著那處高大的山峰,四平八穩(wěn)的巨大石臺(tái)告訴我:“這里是天機(jī)所在,是龍氣上達(dá)天聽(tīng)的地方。是封禪,祭祖,告慰天下九州神靈之處。”
八歲時(shí),我已經(jīng)能懂許多爺爺話中的道理,更是知道爺爺并非常人。因此,我將他的話一一記在心里。
在下山之時(shí),從玉皇觀中恰巧走出一個(gè)白須老道。看見(jiàn)爺爺時(shí),頓時(shí)一驚,上前攔住便想問(wèn),但我看他又閉上了嘴,最后讓弟子送來(lái)兩杯茶水讓我們喝了解渴。
我見(jiàn)此便先謝過(guò)老道長(zhǎng),然后接過(guò)一杯茶遞給爺爺,然后自己接了另一杯。喝下之后非但不再干渴,而且口齒留香,十分奇妙。
爺爺和我喝完還了杯盞,告辭而去。
下到山腳,爺爺問(wèn)我為何接杯?
我正色回答道:“道長(zhǎng)為長(zhǎng)輩,我為后輩。長(zhǎng)輩以禮相待,我自然不能失禮了。”
爺爺笑了笑,贊許地點(diǎn)了點(diǎn)頭對(duì)我說(shuō):“滴水之恩,涌泉相報(bào)。日后玉皇觀有事,你若知道,當(dāng)要出力。”
我不知爺爺是不是算到了什么,但對(duì)爺爺?shù)脑挘乙恢笔巧钚挪灰傻模?dāng)即點(diǎn)頭:“是,孫兒記下了。”
九歲那年,爺爺帶我去了五臺(tái)山,見(jiàn)過(guò)了金佛法相。
十歲時(shí),踏上了普陀仙島,見(jiàn)觀音禪院。
最后一次,爺爺帶我走上了茂密又原始的長(zhǎng)白山,一路走來(lái),神秘的長(zhǎng)白山中萬(wàn)籟俱寂,我感覺(jué)有無(wú)數(shù)眼睛盯著我和爺爺,但什么都看不見(jiàn)。
我感到無(wú)比的緊張,甚至有些害怕,忍不住緊緊拉住爺爺?shù)囊滦洹?
那一年,我十二歲。
爺爺走上了長(zhǎng)白山太白嶺,一身青色布掛,胡須灰白好像一個(gè)老農(nóng)一般,干干凈凈,卻又讓我感覺(jué)那么有安全感。
走上太白嶺,云霧在我身邊繚繞,我隱約看見(jiàn)有一只可愛(ài)的白狐向我張望。
而在這時(shí),從對(duì)面云霧繚繞的七星峰上傳下來(lái)一個(gè)戒備的聲音:“東君,隱匿行蹤十二載,多少能人尋你不到!今日上我太白嶺做什么?”
“向你要一個(gè)承諾!”爺爺鏗鏘有力地對(duì)七星峰上那個(gè)聲音說(shuō)道,這一刻,老農(nóng)的背影竟是如此高大。
我懷疑那七星峰上有一個(gè)巨人,否則他的聲音怎會(huì)如此宏大?我不免為爺爺擔(dān)心。
但那聲音卻沉默了些許時(shí)間,繼而問(wèn):“我能得到什么?”
“老夫的性命。”爺爺鏗鏘有力的五個(gè)字,回蕩在云霧繚繞的的太白嶺和七星峰之間。聽(tīng)的我耳朵嗡嗡作響,當(dāng)即就忍不住哭了。
“爺爺…”
“把眼淚憋回去。”爺爺訓(xùn)斥了我一句,眼神帶著慈愛(ài)和告誡,“以后,你要走的路還很長(zhǎng),萬(wàn)般坎坷,我也只能陪你走上一截。往后,你是男人,記住,男人是不能流眼淚的。”
七星峰上傳下來(lái)一陣?yán)坐Q般的大笑,轟隆隆作響:“東君,好的很!我給你這個(gè)承諾。”
“多謝。”爺爺拱手,轉(zhuǎn)身便走,一個(gè)字都不再多說(shuō)。
離開(kāi)秦山十二年,在十二年后,我和爺爺終于回到了我從未見(jiàn)過(guò)的家鄉(xiāng)。但我沒(méi)能見(jiàn)到我朝思暮想的父母,我問(wèn)爺爺他們?nèi)ツ牧恕?
爺爺嘆息:“以后,要你自己去找了。”
爺爺和我收拾了屋子,在老屋中住下。之后四年,我們不再到處流浪,爺爺將他的一身本領(lǐng)盡數(shù)教給我,結(jié)合十二年走遍天下的閱歷,我學(xué)的很快。
同時(shí)因?yàn)檫^(guò)早游歷于社會(huì)的經(jīng)歷,讓我早早地養(yǎng)成了比同齡人更為成熟的心性。盡管爺爺什么都沒(méi)告訴我,但我相信爺爺肯定有他的道理。
轉(zhuǎn)眼十六歲這天,我照常到堂屋做早課。卻看到爺爺穿的干干凈凈,坐在院子里的青石上,對(duì)著秦山。然后爺爺讓我跪下,對(duì)秦山磕了九個(gè)響頭。
九為數(shù)之極,九個(gè)響頭,除非是救命生身之恩。
“十六年了,爺爺也沒(méi)給你取個(gè)正式的名字。今天開(kāi)始,我就給你取個(gè)吧。”爺爺將我扶起來(lái),“你姓張,從今天開(kāi)始你便叫張秦。這個(gè)名字是爺爺最后留給你的東西,輕易別讓任何人知道。”
“爺爺,這究竟…是為什么啊?”我萬(wàn)般不解。
爺爺搖了搖頭,仰頭看天:“因?yàn)槟愫蛣e人不一樣。”
說(shuō)罷,爺爺閉上了眼睛。我當(dāng)時(shí)愣住了,常年跟在爺爺身邊,讓我第一時(shí)間覺(jué)察出了爺爺?shù)淖兓?
爺爺他去了,走的無(wú)聲無(wú)息。
淚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我強(qiáng)忍著,胡亂抹著臉上的淚。我記得爺爺?shù)拿恳痪涠冢腥耸遣荒芰鳒I的!
但讓我沒(méi)想到的是,爺爺去世的第二天,一輛輛昂貴的汽車如排長(zhǎng)龍般,開(kāi)進(jìn)了這座偏僻的小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