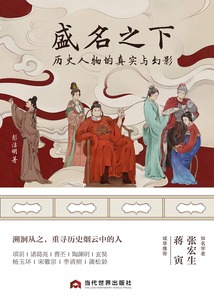
盛名之下:歷史人物的真實(shí)與幻影
最新章節(jié)
- 第12章 蒲松齡:夢(mèng)飲酒者,旦而哭泣
- 第11章 《不遇人生與身后盛名:跨越時(shí)間的回響》:陶淵明:先生不知何許人也
- 第10章 玄奘:心燈一盞,千載孤明
- 第9章 《真實(shí)世界與虛構(gòu)之境:從歷史到故事的“變形”》:諸葛亮:成為鏡,成為神,成為燈
- 第8章 李清照:當(dāng)一個(gè)女子決定成為她自己
- 第7章 《攬鏡自照與“他”的凝視:古代女性的困境》:楊玉環(huán):長(zhǎng)生殿上月,馬嵬坡下泥
第1章 推薦序一 知人與寫(xiě)心
知人之難,自古而然,即使圣賢,也不免有所蔽惑,所以孔子有“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呂氏春秋》)的感嘆,孟子提醒人們論世的重要性:“頌其詩(shī),讀其書(shū),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萬(wàn)章下》)題為諸葛亮所撰的《將苑》甚至給出了七條具體的方法:“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nèi)欺者,有外勇而內(nèi)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jì)謀而觀其識(shí),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彭潔明博士的這部書(shū)稿,主要的動(dòng)機(jī)正在“知人”。她精心選擇了中國(guó)歷史中的九個(gè)人物,有帝王如項(xiàng)羽(從司馬遷《史記》說(shuō))、曹丕、趙佶,有名相如諸葛亮,名僧如玄奘,高士如陶淵明,才士如蒲松齡,才女如李清照,美人如楊貴妃,構(gòu)成一個(gè)有意義的言說(shuō)系列。這些人物都非常知名,而且層次豐富,不少人在歷史的長(zhǎng)河中就有不同的評(píng)價(jià),甚至至今仍有見(jiàn)仁見(jiàn)智的看法。因此,人們理所當(dāng)然會(huì)對(duì)作者如何落筆深感興趣,對(duì)了解作者自己的評(píng)價(jià)體系充滿期待。書(shū)中提到,《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有著強(qiáng)烈的“知音情結(jié)”。這是一個(gè)在個(gè)人奮斗史上前后狀況反差很大的人。早年,他深得知縣費(fèi)祎祉和學(xué)政施閏章的欣賞,曾經(jīng)獲得縣、府、院三試的頭名,自以為青云有路、指日可待,可是此后在科舉的道路上奔波大半生,每次參加鄉(xiāng)試都是鎩羽而回,直到七十一歲才援例補(bǔ)歲貢生。有人說(shuō),蒲松齡反對(duì)科舉制度,事實(shí)上,或許應(yīng)該這樣理解,蒲松齡確實(shí)揭露了科舉制度的一些陰暗面,但從本心來(lái)說(shuō),他并不一定反對(duì)科舉制度本身。他在不少篇幅中予以辛辣諷刺的都是考官,將其不學(xué)無(wú)術(shù)、顢頇平庸,形象地體現(xiàn)在小說(shuō)細(xì)節(jié)中。所以,雖然他想起早年費(fèi)、施諸公的知遇,自嘲后來(lái)科場(chǎng)不順是因自己“駑鈍不才”(《折獄》之“異史氏曰”),但在他的心里,肯定更多地還是覺(jué)得考官是有眼無(wú)珠、不識(shí)真才。從這個(gè)意義看,對(duì)考官的種種諷刺,正折射出他的“童年記憶”。蒲松齡期待知音,這本書(shū)中的其他人物當(dāng)然也是如此,而這正是潔明想要做的事情。
對(duì)于書(shū)中所描寫(xiě)的人物,作者不僅關(guān)注其強(qiáng)烈的個(gè)體特征,而且也注意抉發(fā)其所代表的共性,這些共性,一定程度上就體現(xiàn)了潔明所希望努力挖掘的人性。曹丕和曹植的兄弟關(guān)系是千百年來(lái)人們耳熟能詳?shù)脑掝},圍繞著《七步詩(shī)》,基本已經(jīng)固化出兄弟相爭(zhēng)相殘的思維定勢(shì),不少人恐怕都有著曹丕無(wú)德無(wú)才、得志猖狂,曹植德才兼?zhèn)洹o(wú)辜受害的印象。潔明專辟一章,詳談曹丕,認(rèn)為曹丕不僅政治上更為成熟,軍事上更有才能,而且文學(xué)上的造詣也相當(dāng)突出。這一對(duì)兄弟的較量,最終結(jié)局雖然原因復(fù)雜,但從性格上或行事方式上看,曹植以露才揚(yáng)己敗,曹丕以藏拙內(nèi)斂勝。書(shū)中舉了曹丕在曹操出征時(shí),沒(méi)有像曹植那樣善禱善頌,而只是落淚不舍之事,以及曹操派曹丕和曹植兄弟出鄴城公干,故意讓門(mén)衛(wèi)阻攔,曹丕即時(shí)返回,而曹植卻以王命在身,殺掉門(mén)衛(wèi),破門(mén)而去之事。在曹操心中,兩件事為曹丕分別獲得了“誠(chéng)”與“仁”的印象分。這可能是表演,似乎有“偽”的一面,但這種隱忍的功夫在歷史上不乏其例,如隋煬帝楊廣本有聲色犬馬之好,做皇子時(shí),有一次其父文帝到了他的宅邸,見(jiàn)樂(lè)器之弦多有斷絕,且其上覆滿灰塵,以為他不畜聲伎,心中甚喜。而道光帝衰病之時(shí),曾召見(jiàn)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詢以家國(guó)之事,奕訢滔滔不絕,知無(wú)不言,言無(wú)不盡,而奕詝則伏地流涕,但表孺慕之誠(chéng)。二位皇子的面試結(jié)果,皇四子奕詝以“仁孝”勝出,成為后來(lái)的咸豐帝,而其做法和當(dāng)年的曹丕簡(jiǎn)直一模一樣。這些或者是權(quán)謀術(shù)、韜晦法,其實(shí)也是人性在某個(gè)方面的一種表露。至于曹丕對(duì)曹植的態(tài)度,自然說(shuō)不上好,但潔明也指出,其實(shí)也算不上特別嚴(yán)苛,因?yàn)橹皇菍⑺芸眨屗h(yuǎn)離政治舞臺(tái)而已,畢竟在歷史上,兄弟爭(zhēng)嗣,失敗者失去名譽(yù)、自由乃至生命的情形,并不鮮見(jiàn)。
由此也看出這本書(shū)的一個(gè)重要的書(shū)寫(xiě)思路,即上下古今,縱橫比較。在中國(guó)歷史上,宋徽宗經(jīng)常被認(rèn)為是一個(gè)身份錯(cuò)置的人物,他在文學(xué)藝術(shù)上的成就,恐怕讓他之前的兩個(gè)風(fēng)流皇帝唐玄宗和李后主也相形見(jiàn)絀,而他的崇飾游觀、困竭民力也是很突出的特征。南宋以來(lái),就有不少士大夫反省北宋滅亡之由,其間往往涉及徽宗的窮侈極欲。潔明寫(xiě)這個(gè)亡國(guó)之君,專門(mén)討論了張淏的《艮岳記》。艮岳是秉承徽宗之意興建的,占地約七百五十畝,妙擬自然山川,匯集奇花異石,深得文人雅趣,五年建成,規(guī)模浩大,但在靖康之難中,轉(zhuǎn)眼間化成一片廢墟。作者說(shuō),讀《艮岳記》,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清人孔尚任的劇作《桃花扇》中的名曲《哀江南》,所謂前有周大夫見(jiàn)故國(guó)傾覆、故宮禾黍,作《黍離》之歌,后有孔尚任感南明史事,作《哀江南》之曲,當(dāng)然,中間還可以穿插很多其他的掌故,如杜甫的《哀江頭》、姜夔的《揚(yáng)州慢》等等。將上下幾千年的歷史融匯在一起,當(dāng)然會(huì)引起不一般的感悟。
這個(gè)比較還包括對(duì)后世各種說(shuō)法的評(píng)判。本書(shū)所選擇的九個(gè)人物,大都在歷史上被大量討論過(guò),不同意見(jiàn),所在多有,有的甚至彼此對(duì)立,分歧甚大。潔明充分掌握了相關(guān)文獻(xiàn),通過(guò)細(xì)致梳理,首先展示了一段接受史,在此基礎(chǔ)上予以分疏,可以給讀者提供很多啟發(fā)。比如對(duì)曹丕稱帝,同時(shí)的蜀漢和東吳都予以痛斥,說(shuō)他沐猴而冠,篡奪大位,但魏之后,從晉代以下,歷宋齊梁陳,歷史書(shū)寫(xiě)中就很少這樣說(shuō)了,因?yàn)檫@幾個(gè)朝代的開(kāi)國(guó)君主大都沿用了曹丕的戲碼,往往通過(guò)“禪讓”而登基,所以潔明指出,要對(duì)這樣的問(wèn)題尋找答案,對(duì)和錯(cuò)不一定特別重要,重要的是要明白回答者站在什么樣的立場(chǎng)上。沿著這個(gè)思路,還可以了解到,對(duì)于蜀漢和曹魏孰為正統(tǒng),歷史上也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哪怕是在同一個(gè)朝代,如宋代,北宋司馬光在其《資治通鑒》就尊曹貶劉,認(rèn)為“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tǒng),皆有天子之名而無(wú)其實(shí)者也”,因?yàn)楸彼位蕶?quán)取自后周,也是所謂“禪讓”。而到了南宋,朱熹在《通鑒綱目》中則尊劉貶曹,這又和金人占領(lǐng)了北中國(guó),南宋王朝與當(dāng)年蜀漢及東晉情形相似有關(guān)。意大利史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克羅奇曾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的命題,回看曹魏本身的歷史及其接受史,我們可以對(duì)這個(gè)命題多幾分理解。當(dāng)然,談到這個(gè)問(wèn)題時(shí),本書(shū)又并不局限于政治史,而是擴(kuò)展到生活史和文學(xué)史等。比如陶淵明的詩(shī)風(fēng),在陶的地位真正形成的宋代,三個(gè)論者中,楊時(shí)認(rèn)為是“沖澹深粹,出于自然”(《龜山先生語(yǔ)錄》),蘇軾認(rèn)為是“質(zhì)而實(shí)綺,癯而實(shí)腴”(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shī)集引》),朱熹則強(qiáng)調(diào)“陶淵明詩(shī),人皆說(shuō)是平淡,據(jù)某看他自豪放”(《朱子語(yǔ)類(lèi)》)。而到了現(xiàn)代,朱光潛從陶詩(shī)中拈出“靜穆”,魯迅則針?shù)h相對(duì),指出其特點(diǎn)是“金剛怒目”。潔明介紹了諸家的看法后,指出所謂平淡和豪放、靜穆和金剛怒目,其實(shí)不一定十分矛盾,更重要的是,后人對(duì)陶淵明的發(fā)現(xiàn)和欣賞,既是對(duì)他的作品、人生道路本身的賞識(shí),實(shí)際上也是從不同側(cè)面投射了自己的人格理想,體現(xiàn)的是書(shū)寫(xiě)者的主體性,這樣,作者就能通過(guò)文獻(xiàn)梳理和文本細(xì)讀,抽絲剝繭地還原歷史人物的行為邏輯,也讓這些歷史人物更為鮮活,更為立體。
說(shuō)到主體性,不能不提到書(shū)中對(duì)李清照的論說(shuō)。作者指出,李清照的作品具有不同于一般閨閣女子的眼界和態(tài)度以及“超性別”特征,其經(jīng)歷也反映出不受傳統(tǒng)倫理框限的心性和魄力,因此,認(rèn)為李清照是男性占絕對(duì)優(yōu)勢(shì)的文學(xué)世界的“不速之客”。這個(gè)“不速之客”的說(shuō)法很有意思。若是看李的成就,正如明代大文豪楊慎在其《詞品》中所說(shuō),“使在衣冠,當(dāng)與秦七、黃九爭(zhēng)雄,不獨(dú)雄于閨閣也”,所以潔明說(shuō),她已經(jīng)超越了性別身份的限制。類(lèi)似的看法,還可以舉王世貞《弇州山人詞評(píng)》:“言其(詞)業(yè),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詞之正宗也。”宋征璧《論宋詞》:“吾于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詞透逸;曰子瞻,其詞放誕;曰少游,其詞清華;曰子野,其詞娟潔;曰方回,其詞新鮮;曰小山,其詞聰俊;曰易安,其詞妍婉。”從這些評(píng)論中可以看出,在北宋,能夠和李清照并列的,是這樣一些詞人:晏殊、歐陽(yáng)修、晏幾道、柳永、張先、蘇軾、黃庭堅(jiān)、周邦彥、秦觀、賀鑄等,說(shuō)明至少在這些評(píng)論家的心目中,李清照算得上北宋(甚至也可以說(shuō)是整個(gè)宋代)的大詞人,而并不僅僅是具有性別特征的“女詞人”。把她的詞放在詞史上看,至少有兩點(diǎn)值得提出,一是在突破傳統(tǒng)代言體的過(guò)程中,她和蘇軾等人走在了同一條道路上,以詞體書(shū)寫(xiě)自己的生活和情志;二是她的作品中體現(xiàn)出對(duì)其自少至長(zhǎng),一生感情生活的較為完整的記錄,這是以前的詞體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較為少見(jiàn)的。在宋詞發(fā)展的過(guò)程中,能被本朝詞人稱為“體”的,大概只有“白樂(lè)天體”“花間體”“南唐體”“易安體”“稼軒體”“介庵(趙彥端)體”和“白石體”等不多的幾個(gè),李清照能夠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說(shuō)明她的成就在宋代已經(jīng)很大程度上得到體認(rèn)了。
潔明勤于寫(xiě)作,在其文字生涯中,她至少有兩支筆。一支寫(xiě)學(xué)術(shù)論著,一支寫(xiě)大眾閱讀。在這本著作中,這兩支筆有所交融,其中既有學(xué)術(shù)的嚴(yán)謹(jǐn),又有故事的起伏、文筆的靈動(dòng)。隨著書(shū)中的娓娓敘說(shuō),讀者不僅能夠走進(jìn)歷史,對(duì)話古人,而且也能夠沉思現(xiàn)實(shí),反觀自我。潔明說(shuō),面對(duì)這些歷史人物,她能夠觸摸他們的溫度,聽(tīng)到他們的聲音,感知他們的心跳,因此,講述這些古人的故事,就是講述她自己的故事。讀了潔明對(duì)這九個(gè)歷史人物的解讀,相信讀者也一定會(huì)產(chǎn)生共鳴,進(jìn)而喜歡這本著作。
張宏生
2023年3月5日 于香江片翠山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