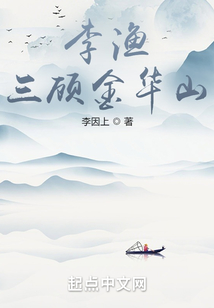
李漁三顧金華山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仙侶降生 名噪五經
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一月二十七日晚,紫禁城深處仍是火柱通明。明神宗朱翊鈞在寢宮,把玩官員進貢的西洋自鳴鐘。
“萬歷十年(1582),張居正薨,海瑞不復官。朝中已無人敢治貪官,朕至此無心理政。雖國庫富余,卻遇萬歷朝鮮之役,退倭兵八萬,折損官軍三萬。萬歷十六年(1588),倭國投降,朝中卻興起太子之爭……”明神宗口中喃喃自語,自怨自艾道。
“皇上,太子之爭轉瞬已十三年,需借外力,方可圖大明復興!”司禮監秉筆太監(東廠廠公)陳矩榮說道。
“何以復興?”明神宗自知朝中皇室宗親勢單力薄,難以制衡文武百官。
“師夷長技,以制百官。”太監回答:“臣向皇上引薦一人。此人已在宮在等候。”
“宣。”明神宗急召。
幾經令官傳述,紫禁城外之人疾步向宮殿而來,不多時,便已至明神宗跟前。
“此為何人?黃發碧眼。”明神宗怕是見到了妖魔。
“此為洋人傳教士,名叫利瑪竇,來自意大利。”太監介紹道:“皇上手中西洋自鳴鐘便是此人進貢。”
利瑪竇曾歷經三年時間,由澳門(已被葡萄牙人租用)入大明帝國,在大明已居住二十年之久。既無妻室兒女,也別無他求,一心信仰天主教,對天文、地理、數學計算頗有研究。
“洋人,為何不遠萬里來此?”明神宗上下打量著他。
“為五炁聚華。”利瑪竇答道。
“何為五炁?”明神宗頓時興致大增。
利瑪竇指向星空,述之:“五炁經人體熔爐鍛煉萬年,由無序、離散之態躍遷為有序、高能之態,含世間萬法萬理,形成自家思想。黑帝生北極之炁,傳共工,主水;青帝生東極之炁,傳句芒,主木;炎帝生南極之炁,傳祝融,主火;白帝生西域之炁,傳蓐收,主金;黃帝生中土之炁,傳后土,主土。五炁后世皆為名人所制。”
“洋和尚對道家頗有研究。”明神宗問道:“上述五炁何在?”
“東南西北四方之炁,盤旋空中百年,已相繼投身江浙一帶,尋明主繼續煉化。唯中土之炁未至。”利瑪竇說道。
“你也懂養生、煉藥之術?”明神宗未曾想,眼前這形貌怪異的洋人,竟能講得頭頭是道,便問道:“何以復興大明?”
“略懂。皇上常煉外藥,而少修金華,易養‘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態。”
“大膽!”太監怕惹怒皇上,便先發制人。
“無事。朕問你,朕若轉而修金華,可否使大明復興?”
“非皇上一人修為之功,需萬萬人修為。”利瑪竇說道。
“華夏上下需秉行大一統的思想,尚可復興?”明神宗思緒敏捷。
“皇上英明!可下令先聚東南西北四方之炁,貫徹天主教義。我如能有機會為皇上服務,將榮幸之至。”
“荒唐。我華夏自有孔子、老子、孟子、莊子等名家,何用洋教?”明神宗怒斥道。
“洋人在大明傳洋教,企圖將漢人同化成洋人,確實不妥。但可借洋人影響,制衡朝中官員勢力。”太監諫言。
“我雖不召集群臣上朝,但也不至于被宦官和洋人蒙騙。”明神宗當即下令,將洋人扣押在會同館中。
利瑪竇被軟禁了幾個月后,被其他洋人救走;明神宗未聽信太監諫言,順應朝中百官,立長子朱常洛(后為明光宗)為太子。
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四炁聚浙江一城。此城因有安期生、黃初平造福百姓,逝后被奉為“大仙”,得名金華。
中土之炁亦離降世不遠,靜待百年終要尋到煉化之人身。朦朧中,有一輪金黃色旋渦,正緩慢旋轉,現金華城五十多里外之蘭溪縣。近看,此旋渦看似一朵花,最里層有六個菱形花瓣,其外又有六層花瓣層層包裹。共有七層花瓣層層圍繞中心原點,各花瓣形態不一,如雪花瓣,如太陽花瓣,如櫻花瓣,如梅花瓣,如桃花瓣,如玉蘭花瓣。層層花瓣皆泛金光,轉速相對獨立,若環繞太陽之金、木、水、火、土等大星,亦或是鎮星(土星)外圍的層層光環。世間之人若是看到這番景象,定會忘卻所有欲界瑣碎。此幅唯美圖案名叫“金華”。
距蘭溪縣城約五十華里有一個村子,名叫夏李村,村中有四五百戶人家皆姓李,先祖李炭,是唐高祖李淵的第十七子李元裕之后,有李燁、李輝二弟。因武氏之亂,三祖從長安避亂至福建長汀,遷至衢、睦之間。炭居壽昌長汀源(現為石門堂、沙墩頭);燁居西安石屏(衢江區峽川鎮李澤村),稱石屏李氏;烣居溪南(壽昌河南里村),稱梨山李氏。
李頻為炭后第9世,中進士,任建州刺史,唐末詩人;李頌為炭后第21世,移居至蘭溪夏李,稱龍門李氏,始為龍門李氏第1世。
中土之炁幻化為一位白發長老,拄拐杖假裝路過此地,見金華之光隱約源自夏李伊山頭一間破舊祠堂內。他向村中人打聽此處住戶。
“敢問幼兄,老夫已年老心衰,今昔是何年?”
村民談吐儒雅,說道:“老人家,今日為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八月初七。”
白發長老道:“嗚呼!這一晃,亦三百年!”
“三百年?”
白發長老打斷了村民道:“敢問對面山上所住為何人?”
“哦,此山為伊山,戶主名叫李如松,長年在江南如皋做藥材生意,夫人在村里做燒鑊娘(女幫工)。”
白發長老以拐杖擊地,問道:“此戶人家,最近是否有異相出現?”
他深知凡人見不到金華之光,但會出現其他異相。
“有,夫人懷胎已十一個月,腹中已痛三天三夜,仍未分娩。”
白發長老微頷之,鞠躬作揖向村民道謝。
村民趕忙上前攙扶,卻見雙手摸了個空,再抬頭一看,白發長老早已不見。他驚慌向四周望去,卻見其已在伊山破舊祠堂門外,深知此人不簡單,趕忙回村中報信。
白發長老敲門欲入,一個男孩開門。白發長老見李如松和接生婆正對著床上夫人干著急。兩人臉上掛著眼袋,已是幾夜未合眼;床腳入土三寸,夫人早已反轉顛頓數日;伊人面無血色、有氣無力地躺著。李如松見白發長老頗有仙風道骨之風,吩咐兩子為他上好茶。
白發長老擺手,棄拐杖于墻角,出門繞屋一圈。他腳踩巨型金色花瓣,心中欣喜,確定已找到人,便進門說明來意。
“夫人肚中胎兒是星宿降地,此間小祠堂屋宇陰暗,按風水相學上說,地盤太輕,載不住‘星宿’。”
李如松聽聞長老建議,頓時茅塞頓開,率人把夫人抬到夏李村中心尋求幫助。村中鄉紳經村民報信,早已得知白發仙人降臨夏李,敞開總祠堂大門,遠出迎圣。
誰知,夫人剛被抬到祠堂門口,腹中便劇烈疼痛起來。
白發長老挺直腰板,對村中眾人道:“此兒非凡胎,乃仙之侶,天之徒……”
話音剛落,白發長老竟憑空消失。而后更令人匪夷所思,有一道金光直沖云霄,卻在九霄云外調轉方向,重新降落夏李村上空,化為一輪金黃色的金華,不偏不倚,剛好降落在夫人腹中。
眨眼功夫,夫人胎中嬰兒降生。
李如松照白發長老所說,遂將其取名仙侶。李家苦受幾世貧寒,就此寄希望于此。
夏李村人多地薄,流寓于外者三分之二,其族中不少人在江南如皋古城經營藥材。李仙侶之伯父李如椿有“冠帶醫生”頭銜(明代末等太醫),受雇于如皋縣唯一官辦醫院,在如皋城內開藥鋪,生意紅火。李仙侶出生后不久,便隨父親李如松、兄長李茂和幼弟李皓舉家遷往如皋居住。
如皋位于長江北岸蘇北平原水網地區,距南通城一百三十里,為南通到揚州陸路交通要道,得水利之便,重商業。
李仙侶自幼聰穎,在襁褓中便能識字,讀“四書”“五經”過目不忘,總角之年便能賦詩作文、下筆千言。父親李如松希望他走科舉之路,好謀個一官半職。
李仙侶每年在自家后院梧桐樹上刻詩一首,以警戒自己勿虛度年華,時年十五歲作:
小時種梧桐,桐本細如艾。針尖刻小詩,字瘦皮不壞。剎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許,人長亦奚怪。好將感嘆詞,刻向前詩外。新字日相催,舊字不相待。顧此新舊痕,而為悠忽戒。
李仙侶從小便有俠客夢,在詩詞中描繪出一位充滿義氣、豪氣、正氣的少年:
生來骨格稱頭顱,未出須眉已丈夫。
九死時拚三尺劍,千金來自一聲盧。
歌聲不屑彈長鋏,世事惟堪擊唾壺。
結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問有仇無?
——李仙侶(16)《贈俠少年》
自古壯士結義生死之交,皆可將頭顱捧在手上,有難同當有福同享,坦蕩如彈劍而歌的馮諼、擊缺唾壺的王敦。
為讓兒子靜心讀書、光宗耀祖,李仙侶母親學孟母“三遷教子”,將李仙侶安置到李堡鎮“老鸛樓”讀書。但正當李仙侶在書山學海中奮讀攻研、學有所成時,父親因病不幸去世。家庭失去頂梁柱,全家人頓陷困境。
時年,李仙侶十九歲,迫于生計,也因要回原籍浙江參加科舉考試,決計扶柩回鄉,在家守孝勤奮攻讀。同年,娶距夏李村約十華里之生塘徐村徐氏女為妻,望白頭偕老,次年得一女。李仙侶好寄情于山水、吟游山海,家中事務都靠徐氏主持有方,得無后顧之憂。
李仙侶成家庭支柱,謀取功名決心愈加堅定。崇禎八年(1635),李仙侶赴金華參加童子試,時年二十五歲便一舉成為名噪一時的“五經童子”,中秀才,入府庠生(月俸祿六斗米),受主考官、浙江提學副使許豸賞識。他將李仙侶試卷印發宣傳。金華知府李一獻為南直隸人,對其才華亦是大加贊賞。
首戰告捷,李仙侶初嘗讀書成名之喜,考取功名信心大增。他游蕩在金華城中,見此城已然發展成為商業城市,與從小成長之如皋有幾分相似。街上偶有讀書人認出李仙侶,或向他招呼問候,或向他表示崇敬之心,也有好事媒婆上前打聽其生辰和家境。李仙侶心里甚是想念家中“山妻”,暫無他娶之意。
金華城考學氛圍濃厚,學術研討頻繁,更有利于個人成長。李仙侶打算在金華住下,積極攻讀“舉業”,備考“鄉試”。他走街串巷,尋找臨時安身之所。
城中有一條街,所住之戶皆為朱姓大戶人家。平日里,此些人家與尋常大戶人家無異,但戶中人白日游手好閑,晚上大門緊閉。
李仙侶好奇,見一后生正在家門口賞花,便慢步上前。
他見此后生身材瘦弱,遇風欲倒,但五官端正,有富家子弟派頭,便上前問道:“鄙人李仙侶,字謫凡。請問兄臺尊姓大名?”
后生聽聞有人詢問,回頭打量李仙侶一番,見其一副書生打扮,便畢恭畢敬地回道:“我名叫朱萬侍,國姓朱,萬字輩,保家侍國之侍……”
李仙侶微頷之,問道:“聽萬侍賢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兄臺過謙,我剛年滿十八,稱我為愚弟即可。家父為金華長山人,進士出身,常年在北方為官,我亦在北方長大,故無家鄉口音矣。”
“金華城中考學氛圍濃厚,是讀書、做學理想之所!”
“謫凡兄來金華可是為童子試?”
李仙侶見對方問到所學專長,興致油然而生,將自己如何高中“五經童子”,一五一十地講給朱萬侍聽。五經是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五部作品。童子試考官根據五經各出一題,考生可選取答題。李仙侶熟讀五經、出手極快,選取一題太過輕松,便干脆把五經之題全答完。自古以來考生皆巴不得少做一題,未見有說愿意多做一題者。李仙侶所為,從古至今僅此一人。
朱萬侍聽完大加贊賞,說道:“我雖無心考取功名,但我爹遵囑我要多看書,多和文人來往,增長見識。謫凡兄文思敏捷、前途無量,有曾想過要在金華安居否?”
“我正有此意,尋思要安住在何處。”
“倒不如,就住在我家?”
“這可使不得!”李仙侶向朱府內張望,府內庭院寬敞、有天有地,黃口、家奴熙熙攘攘,成年男丁和少婦亦無所事事。他心中已知,此非讀書之所。
“環境很嘈雜,非靜心做學之所也!”
李仙侶遲疑后微頷之,有些許不好意思。這竟是大戶人家內院,無非為一處小型市井耳!
“不如我隨你一同租住在外,遠離這喧囂和嘈雜。”朱萬侍抬頭,兩眼放光。
李仙侶心想這位朱萬侍和自己坦誠相對,毫無遮掩,算是可以推心置腹之好友。加之他又算大官之子,和他一起租住,倒是可以學到不少官場知識。李仙侶爽快應許。
“不知賢弟可有理想的租處?”
“金華山鹿田寺(鹿田書院),可有所聞乎?家父嘗在此服喪、求學。”
“人人皆知!鹿田書院位于金華山鹿田村。此處山清水秀,常年仙霧繚繞,文人墨客游此,題詠頗多。宋代潘良貴曾贊賞,自是評吾鄉山水以此為第一;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和東南三賢(呂祖謙、朱熹、張栻)七位先賢曾在這里研學、講課。”李仙侶表現出對此處之崇敬和向往。
“甚好,你我就去此地!今晚就在我家客房暫住一宿,見過家兄。明日你我便可一同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