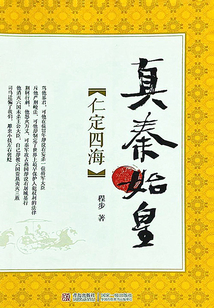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是得多個心眼——程步《真秦始皇》
易中天
程步先生不是歷史學家,我也不是。他寫這本書,我寫這篇序,都有風險。
何況程步先生這回涉及的,還是秦始皇這樣一個敏感的話題。更何況程步先生居然還認為,秦始皇是歷史上有為之君中最仁慈的,是“仁君秦始皇”。天啦!這個結論和我寫序這事一旦傳出去,肯定是罵聲一片。我甚至想象得出那些通欄標題:易中天、程步之流為秦始皇翻案,下一目標鎖定……
這不是危言聳聽,他們干得出來,而且以前沒少干。比如李零先生的《喪家狗》,就被妖魔化。這一回,我們肯定又會被咬得遍體鱗傷。
所以我必須與程步先生“劃清界限”。并亮明觀點。第一,我對秦始皇沒有研究。秦始皇是仁是暴,我不知道。第二,秦始皇與秦政治不能打等號。就算始皇“仁”,也不等于秦政不“暴”。第三,就算秦政不“暴”,也決不可能“仁”。從秦孝公到秦始皇,秦國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先是公國(孝公時代),后是王國(孝公之后),消滅六國、兼并天下之后又成為帝國。但無論是孝公時代的秦公國,孝公之后的秦王國,還是始皇時代的秦帝國,都不行“仁政”,也不主張行“仁政”。當然,他們也不主張“暴政”,至少不公開主張。為什么呢?因為從孝公到始皇,秦的國家意識形態,就是法家學說:秦的治國方針,也是法家的那一套。這個方針,是商鞅在孝公時代為秦國奠定的,以后又在嬴政時代為韓非、李斯所確立。法家的主張是什么?既反對“仁政”,也反對“暴政”。用韓非的話說,就是“仁暴者,皆亡國者也”(《韓非子·八說》),也就是仁政、暴政都要不得。要什么?苛政。事實上,從孝公到始皇,秦公國也好,秦王國也好,秦帝國也好,其“政”都是苛政,其“法”也都是嚴刑峻法。比如商鞅規定,但凡不務農而經商,或者干農活不賣力的,老婆孩子都要被收為官奴(《史記·商君列傳》);治安的要求,則竟是“步過六尺者罰,棄灰于道者被刑”(劉歆《新序》)。這就實在是太嚴峻!沒錯,商鞅執政時,秦國確實做到了“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史記,商君列傳》)。但這決不是為了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而只是為了讓人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也就是只為國君戰斗,不為自己戰斗;只殺外國人,不殺泰國人;只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結果是什么呢?是培養出一大批如狼似虎毫無愛心的殺人機器。正是靠著這些殺人機器,秦王嬴政才完成了他的“兼并事業”,把整個天下都變成了他的家產,把普天之下的人民都變成了他的臣仆。在這樣一個大前提下,嬴政本人是仁是暴。實在已經是無足輕重的事情了。秦始皇這個“案”,我看不“翻”也罷!
那又為什么還要為本書寫序?
真正打動我的,是程步先生“用另一種方法讀史”的主張。程步先生能有這個主張,則又因于他不是歷史學家,而是媒體人。史學家與媒體人有什么不同?不同就在于,前者一般都相信史書,后者卻明白得多個心眼。我們知道,史書記載的所謂“歷史”,無非“過去的新聞”;媒體報道的所謂“新聞”,則完全可能成為“將來的歷史”。這里面,就有一個“如何報道,如何記錄”的問題,也還有一個“如何編輯”的問題。這些問題,史學家不一定清楚,媒體人卻門兒清,因為他們有切身體會。媒體人比誰都心里有數,同樣一件事情,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筆法去報道,完全有可能讓讀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也就是說,媒體人在進行報道的時候,完全能夠做到事件、起因、結果、細節都真實,卻讓讀者的感受不真實,并誘導他們得出不真實的結論。
在這方面。我也是有切膚之痛的。但為了不得罪媒體。我還是舉史書為例。比如赤壁之戰前的孫劉聯盟,周瑜、魯肅、諸葛亮,都起了重要作用,他們也都同孫權談過話。但根據陳壽的《三國志》,我們只知道周瑜的談話在后。魯肅和諸葛亮誰先誰后,就不清楚了。這樣,當后人敘述此事時,就必須進行編輯。把諸葛亮的談話編在前面,給人的感覺就是“諸葛亮說服了孫權”。把魯肅的談話編在前面,給人的感覺就是“魯肅說服了孫權”。這就全看你怎么編輯。根據我和媒體打交道的經驗,編輯比記者更重要。正是他們,決定著輿論的導向,也左右著讀者的感受和情緒。歷史上那些修史的人,包括偉大的司馬遷,就都是編輯,或者是編輯兼記者。他們怎么編。我們怎么讀,怎么信。如果你沒有一點媒體經驗,弄不好就會傻乎乎地被牽著鼻子走。程步先生因為自己是媒體人,深知其中奧秘,便在讀史的時候多了一個心眼。這個我很贊成。我還建議,讀報的時候,也要多個心眼。否則,遇到居心不良的編輯,你上當受騙,他還沒事偷著樂:哈哈!任你精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腳水!
由此可見,程步先生的結論是否成立,可以討論。但他不盲從,則應該肯定。同樣,我們作為讀者,當然也不必盲從,不必認為程步先生所說就是對的。他其實也是編輯呢!他在闡述自己觀點的時候,對史料也有自己的取舍和編排。例子我就不舉了,相信讀者自會判斷。再說一遍,結論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思考。
是耶?非耶?百家爭鳴罷!
2008年9月18日 于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