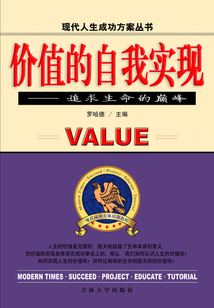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基本需要的滿足
追索價值的真諦
是否可以這樣說,實現(xiàn)價值的真正動力是基本需要的滿足。由于它一直被忽視,我們確實有必要承認它至少是這類因素中的一個,并且是特別重要的一個。在摩爾的著作中詳細描述了需要的滿足和挫折決定興趣的幾種方式。
對態(tài)度、興趣、趣味、價值觀的更深入地研究是可能的,最終必然包括對于道德、價值、倫理的討論,當然,其范圍必須超越禮儀、禮貌以及其他社會風俗。習慣上將態(tài)度、趣味、興趣、甚至還有各種價值觀卻看作是聯(lián)合學習的結果,似乎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即仿佛它們完全是由機體外的任意力量決定的。然而,內在的需要和滿足的效果也在起作用。
假如我們要找到一個對人格分類有用的工具,那就需要將基本的感情需要的層次滿足看作一個線型的連續(xù)體。假如大多數(shù)人都有類似的機體需要,那么在這些需要得到滿足的程度上每個人都能與任何其他人進行比較。這是整體的或有機體的原理,因為它根據(jù)一個單一的連續(xù)體來對完整的人進行分類,而不是根據(jù)大量的、毫不相關的連續(xù)體來將人的各個部分或各個方面歸類。
除去過份滿足以外,究竟什么是厭煩?在這里,我們又可以發(fā)現(xiàn)尚未解決和覺察的問題。為什么與某一幅繪畫、某一首樂曲、某一位婦女相處得久了會產生厭煩?為什么與另一幅繪畫、另一首樂曲、另一位婦女在同樣時間內相處卻產生了更多的興趣和更大的快樂呢?
需要的滿足在健康情緒的產生中起了什么作用?為什么情緒的研究者們長期僅限于研究挫折在感情上的效果?
我們提出的論點是,滿足人的基本需要(以所有條件相同為前提,拋開少數(shù)難以解釋的例外,以及暫時略去匱乏和約束的有益效果),不僅改善了人的性格結構,而且改善了他作為國內和國際環(huán)境中的公民與周圍的關系。這一點在政治、經濟、教育、歷史以及社會學上的意義可能是巨大的、明顯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盡管看起來荒謬),需要的挫折的決定因素是需要的滿足。這是因為甚至要到較低的優(yōu)勢需要滿足之后,較高的需要才會出現(xiàn)在意識里。從某種意義上看,在需要尚未出現(xiàn)之前,是無所謂挫折的。一個勉強維持生存的人不會去奢望生活中的高級需要。幾何學的研究、選舉權、自己城市的好名聲、尊重、價值等都不會成為他焦慮的中心,他所關心的是更基本的物質。只有當一定量的低級需要的滿足使他的需要達到某一高度時,他的需要才會使他在個人、社會和智力的更廣闊范圍內感受到挫折。
絕大多數(shù)人肯定在追求他們一直欠缺的東西,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一種推論,然而又肯定不會感到為眾人更普遍的滿足而工作是無益的。這樣,我們同時又學會不指望任何單一的社會改革,例如婦女選舉權、免費教育、無記名投票、工會、良好的居住條件、直接選舉等,會產生奇跡,但又不低估緩慢發(fā)展的力量。
如果討論哪種挫折或焦慮對社會更有好處,那么為早日結束戰(zhàn)爭的焦慮要好于只關心自己能否活到70歲。明確地提高挫折的層次(如果我們可以談論高級挫折和低級挫折),不僅具有個人意義,而且還具有社會意義。幾乎可以說這對于犯罪感和羞恥心也同樣適用。
很奇怪,科學心理學家一直忽視這一長期為哲學家、藝術家、詩人的議論所充斥的領域。這可能是由于“所有的行為都有動機”這一廣泛公認的教條在作怪。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但這里不準備辯明。有一個鐵的事實可以被觀察到,即一經滿足,機體立即放棄壓迫、緊張、緊迫、危急的感覺,允許自己變得懶散、松弛、被動,允許自己享受陽光、玩耍嬉戲,或者裝飾、擦洗盆盆罐罐,允許自己觀察微不足道的事物,遇事漫不經心,往往無意中獲得而不是有意識地追求,一句話,變得相對地無目的了。需要的滿足導致了無目的的行為的出現(xiàn)。
物質生活的富裕使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疾病。其癥狀包括厭倦感、自私自利、自以為是、“理所當然”的優(yōu)越感、對一種不成熟的低水平的眷戀、人與人之間友愛的喪失等。很顯然,在任何一段時間里物質生活或低級需要的生活本身并不能給人們帶來滿足。
我們也必須面對另一種新的、由心理富裕導致病態(tài)的可能。也就是說,病的起因是由于患者得到無微不至的愛護、關懷、被寵愛、崇拜、歡迎所包圍,被膜拜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被推到舞臺的中心位置;擁有忠誠的仆人,無論在什么地方,各種欲望都能得到滿足,甚至成為人們甘愿為之自我犧牲和自我克制的對象。
勿庸置疑,我們對這些新現(xiàn)象知之甚少,當然更談不上具有任何發(fā)達科學的意義了。我們所根據(jù)的是強烈的懷疑、普遍的臨床印象、以及兒童心理學家和教育家逐漸形成的觀點:單純的基本需要滿足是不夠的,對于兒童來說,他們還必須去體驗堅強、隱忍、挫折、約束、限制等感受。換句話說,基本需要的滿足最好能被仔細地重新定義,否則它很容易被誤解為無限度的溺愛、自我克制,無條件的應允、過分的保護以及奉承等。對兒童的愛和尊重必須至少與對自己作為家長或普通意義上的成年人應得到的愛與尊重協(xié)調起來。兒童當然是人,但他們不是有經驗的人,必須將他們看成是對許多事情不了解、對有些事情一無所知的人。
由滿足引起的另一類病癥表現(xiàn)為可稱為“超越性病態(tài)”的東西,這是指生活缺乏價值觀念、缺乏意義感和充實感。許多人本主義者和存在主義心理學家確信——雖然他們沒有充足的依據(jù)——全部基本需要的滿足并不能自動地解決歸屬感、價值體系、生活目的、人生意義等問題。至少對某些人,特別是年青人,這是在基本需要滿足以外另外需要解決的問題。
最后,我們要重申一個事實,盡管很少有人想到這一點:人類似乎從來就沒有長久地感到過心滿意足。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人類容易對自己的幸福熟視無睹,忘記幸福或視它為理所當然,甚至忽略了幸福的價值。對于許多人來說,我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即使是最強烈的快樂也會變得索然無味,失去新鮮之感。只有體驗了喪失、困擾、威脅、甚至是悲劇的經歷之后,才能重新認識其價值。對于這類人,特別是那些對實踐沒有熱情、死氣沉沉、意志薄弱、無法體驗神秘感情,對享受人生、追求快樂有強烈抵觸情緒的人,讓他們去體驗失去幸福的滋味,從而能重新認識身邊的幸福,這樣做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