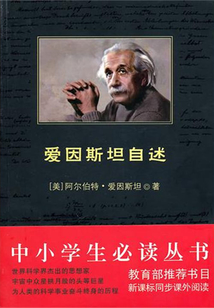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愛因斯坦自述(1)
1946年的自述(片段)
今年我67歲了,來日無多,現在坐在這里打算寫點東西,就權當自己的訃告了。之所以要做這件事,除了希爾普博士的說服外,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也覺得這么做很有意義。我想,給那些奮斗中的人們講一講自己的人生體驗必是一件好事,這些體驗包括了一個人如何看待他當年努力和探索過的事情。不過,我在稍作考慮以后必須事先承認,不要對這種嘗試的結果抱有什么十全十美的期望與幻想,它肯定不會是完美無缺的。因為要把一生中值得講的東西講清楚確實不是簡單事,不論我的一生是怎樣的短暫和有限,且不論其間經歷的歧途是怎樣的占優勢,畢竟現在的我已完全不同于50歲、30歲或者20歲的時候了。由于任何回憶都會染上眼前的色彩,所以有些地方是不能完全相信依靠的。諸如此類的考慮可能會使我產生畏難而退的想法,不過基于心中的一個信念,我覺得我值得一試。這個信念就是,一個人完全將自己的經驗里的一些東西提取出來講給別人聽。
大多數人花畢生的時間去追逐一些毫無價值的希望和努力,這是一個我在少年時期就已深切意識到的道理。不久,我發現這種追逐并不輕松,甚至有些殘酷。不過,這在當年,甚至今天,被精心地用偽善和漂亮的字句偽裝起來。參與這種追逐只是因為每個人都有個胃,這基本上是注定的。通常情況下,這種追逐很可能使他的胃得到滿足。當然,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例外。在這種情況下,選擇宗教便成了第一條出路,每一個兒童正是通過傳統的教育機構得到第一手宗教理論的。因此,我是一對完全沒有宗教信仰的(猶太人)夫婦的兒子,但12歲以前,我仍然深深地信仰著宗教。之所以12歲那年我突然終止了這種信仰,是因為通俗的科學書籍引導了我。通過閱讀這些書籍,我開始質疑《圣經》里故事的真實性。其結果就是染上了一種狂熱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織著這樣一種令人瞠目結舌的疑問:國家用謊言將年輕人欺騙了。這種經驗給我帶來延及終生的影響,那就是懷疑態度。我會對所有權威產生懷疑,敢于對任何社會環境里既存的信念完全持一種懷疑態度。后來,由于要更清楚地弄明白因果關系,我的懷疑精神失去了原有的鋒利性,不過它從未離開過我。
有一點我很清楚,少年時代的宗教天堂就這樣一去不復返了,這是我對“僅僅作為個人”這種桎梏的首次反抗,這是最原始的感情、愿望和希望支配的結果,將實現自我救贖的一個嘗試。有一個不可知的世界在我們之外存在著,它的存在并不取決于我們人類的主觀意愿。盡管它是一個高深而永恒的謎,但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人類至少可以部分地用觀察和思維觸及到它。這個世界深具魅力,有如爭求自由、得到解放一樣,吸引我們的凝視深思。而且不久我就注意到,在這項事業中,許多我所尊敬和欽佩的人找到了內心的自由和安詳。我總是會有意無意地制定一個最高目標,那就是借助一切既有力量與條件,在向我們提供的一切可能的范圍里,我們從思想上掌握這個外部世界。我不乏這樣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囊括了古往今來的各個行業和國度,他們是一群充滿真知灼見的人士。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是非常平坦和誘人的,而指向這個天堂的道路卻不然。不過,我從來也沒有為選擇了這條道路而后悔過,因為它已證明是可以信賴的。
需要補充的是,我的這些說法僅僅在一定意義上是正確的,就好比是對于一個細節混亂的復雜對象,我只不過是作了一幅簡單勾勒了幾筆的畫,所能反映的只能是很有限的意義。對一個思想很有條理的人來說,在付出了其他方面的代價下,他的這一本性會愈來愈突出,并進而明顯地決定著他的精神狀況。故此,盡管他的實際經驗確實是在很多個變化的單個情況中發生的,但在這種情況下,這樣的人在回顧中所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種一成不變的規律的發展。每一個人生活的一種原子化現象之所以會出現,就在于外界情況是千變萬化和多種多樣的,相對來說,意識的瞬息變化則比較狹窄。就我而言,在我的主要興趣方面,逐漸遠遠地擺脫了短暫的和僅僅作為個人的方面,開始轉向力求從思想上去理解和掌握事物,這就是我人生發展的轉折點。這樣看來,盡可能多的真理已經被包含在上述評述里,盡管它們是以一種簡要的綱要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如果要對“思維”作一個準確的界定,那是什么?“思維”并非接受感覺印象時出現記憶形象,也不是當這樣一些形象形成一個系列時,其中一個形象引出另一個形象。不過,在許多這樣的系列中某一形象若反復出現,基于這種再現,它聯結起了那些本身沒有聯系的系列,也就成為了這種系列的支配因素。換言之,這種元素是一種工具或一個概念。我認為,區別自由想象或“做夢”與思維之間的不同,可以從“概念”在其中所起的支配作用的比例來決定。雖然不是說概念一定要同通過感覺和可以再現的符號聯系起來,但沒有這樣的聯系,思維也無法交流。
大家不禁會問,在這樣一個領域里,這個人為什么可以如此輕率地運用觀念,而不作證明呢?我所給出的答復是:我們的一切思維都是概念化的一種自由選擇,而它的合理性取決于我們概括經驗所能達到的程度。所以“真理”這個概念還不能在這樣的結構應用,因為只有在這種元素和規則已經被一致認可的時候,才談得上“真理”概念。很多時候,我們的思維不需要符號也能進行,但很多時候是無意識的,這一點對我來說沒有什么疑問。否則,就不會出現我們有時候不自覺地對某一經驗感到“吃驚”了。當經驗與我們已經建立的概念世界發生沖突時,這種“吃驚”才會發生。每當我們感覺這種沖突很激烈并且不可調和時,它就會以一種決定性的方式對我們的思維進行反作用。在某種意義上,思維的結果就是不斷擺脫“吃驚”。
我記憶中第一次經歷這種“吃驚”還是在4歲的時候:父親給我一個羅盤,它的指南針準確行動方式奇特,令我感到震驚,因為在我既有的頭腦里,也即我無意識的概念世界中,它是第一個根本無法找到其相應位置的事物。這次經驗給我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而持久,以至于現在仍盤桓于我的腦際。我想,當時我就開始思考:一定有什么東西深深地隱藏在它的后面。人們對物體下落、刮風、下雨、月亮或者月亮不會掉下來,以及生物和非生物之間的區別等都不感到驚奇,因為這些事物司空見慣,人們也就見怪不怪了。
另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驚奇發生在我12歲的時候,它是由一本關于歐幾里得平面幾何的小書所引發的。我在一個學年開始時得到了這本書,書里許多具有明晰而可靠的斷言給了我極深的印象,有些命題本身雖然并不明顯,但都被切實地證明了,不能使人產生任何懷疑。比如三角形的三個高交于一點。我并沒有因為它是不用證明就得承認的公理而對它產生懷疑。在我看來是真實的命題,依據有效性就可以證明,這令我完全心滿意足。比如,印象中在我拿到這本幾何學小書之前,我就已經知道畢達哥拉斯定理了,那是一位叔叔曾經告訴我的。我付出了一番艱巨的努力,從三角形的相似性這個角度出發,成功地“證明了”這條定理。當時我就認為,直角三角形各個邊的關系完全決定于它的一個銳角,這是顯而易見的,自然無須證明;只有在類似方式中表現不“顯然”的東西,才需要去證明。而且,那些擺在明處,“能看得到和摸得到的”東西,在我看來,與幾何學研究的對象一樣,都屬于同一類型的東西。之所以存在這種原始觀念,我想根源恰恰在于不自覺產生幾何概念與直接經驗對象的聯系的想法。康德提出了“先驗綜合判斷”可能性問題的觀念,很可能就是以這種原始觀念作為根據的。
想得到經驗對象的可靠知識,用純粹思維是不可能辦到的,否則這種“驚奇”就是以錯誤為依據了。希臘人在幾何學中第一次告訴我們,對于第一次見到它的人來說,純粹思維竟能達到如此可靠而又精確程度是足夠令人吃驚的。
說了這么多,已經和剛開始有關訃告的問題不搭界了,不過既然說到這里了,我將毫不猶豫地用幾句話來概括我的認識論觀點,雖然有些話已經在前面談過了。這個觀點與我年輕時所持的觀點不相同,實際上是在很久以后才慢慢地發展和總結起來的。我會同時注意到感覺經驗的總和與書中記載的概念和命題的總和。概念和命題之間存在邏輯關聯性,而概念和命題之間的相互關系需要一些既定的規則來完成,這是邏輯學的研究對象。概念和命題要想獲得其“意義”和“內容”,必須通過與感覺經驗來完成。這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邏輯關聯性,而是純粹的直覺聯系。這種聯系是區別科學真理與憑空幻想的標準,即這種直覺能得到保證,而非其他。雖然邏輯概念體系本身是完全自由的,可是它們遵循這樣一個目標,即要盡可能對應感覺經驗的總和,又要可靠和完備;其次,它們應當是諸如不下定義的概念和推導不出的命題等,它們都是邏輯獨立元素(像基本概念和公理)。
按照某一邏輯體系,公認的邏輯規則推導出來的命題是正確的。而體系同經驗總和的對應,以及可靠和完備程度,決定了體系真理的內容。正確命題所屬的體系通過其中的真理內容賦予了該命題的共“真理性”。
在休謨看來,諸如因果性概念這樣的概念,是不能從經驗材料中根據邏輯方法來推導的。而康德又完全確信某些概念是必備的,他認為這些被挑選出來的概念為任何思維準備了必要的前提,并且它們不同于那些來自經驗的概念。但我相信,它沒有按自然的方式來正確對待問題,所以這種區分是不正確的……
言歸正傳,現在我們再回到訃告上來。在我12到16歲的時候,我熟悉了包括微積分原理在內的基礎數學。這時,我有幸接觸到了一些這方面的書,它們的基本思想簡單、明了,內容突出,盡管它們有些邏輯上的瑕疵,但還是給了我許多啟發。總的說來,那次學習確實讓我著迷,在我印象中,它絲毫不比初等幾何差,甚至于好幾次達到了頂峰。我當時聚精會神地閱讀了很多著作,包括《伯恩斯坦的自然科學通俗讀本》在內,這個有五六卷的著作是一部卓越的通俗讀物,它幾乎只局限于定性敘述而不拓展。我幸運地從中知道了整個自然科學領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17歲那年,我以數學和物理學的學生身份進入蘇黎世工業大學,其時我已經具備了一些理論物理學的知識了。
在蘇黎世工業大學,我遇到了像胡爾維茲、明可夫斯茨等幾位卓越的老師,照這樣發展下去,我應該在數學方面有所造詣。事實并非如此,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物理實驗室里度過的,因為我對直接接觸太癡迷了。其他時間,我主要用于在家里閱讀基爾霍夫、亥姆霍茲、赫茲等人的著作。為什么我會在一定程度上不在乎數學呢?我想一方面原因在于我對自然科學的興趣遠比對數學的興趣濃厚;其次還由于一次奇遇:在我看來,數學分許多專門的領域,而每一個領域都會耗去我們畢生的精力。因此,我覺得自己很難選擇,為此煩惱不已。數學當然有很多最重要的東西,而且是最根本性的東西,然而由于我在數學領域沒有天賦,以致沒有把它們學好。此外,我對自然知識興趣更濃,作為一個學生,我也不清楚物理學需要最精密的數學方法,這樣才能通向更深入的知識道路。這一點等我逐漸明白的時候,已經是獨立科學研究的幾年后了。
誠然,同數學一樣,物理學也分成了若干領域,每一個領域幾乎都會耗盡研究者短暫的一生,而且還可能得不到令自己滿意的研究成果。況且,已經存在但未建立充分聯系的實驗數據還有很多。與數學不同的是,我在這個領域里很快就學會了怎樣挑選識別東西,將那種有用的知識挑出來,撇下其他多余的東西,尤其是那些只會充塞大腦、并引領我偏離主要目標的東西。當然,還存在考試問題。為了應付考試,即使不愿意,也得把所有這些廢物記住。在通過最后的考試以后,有整整一年的時間,我對科學問題失去了興趣,這都是因為被強迫學習的結果。不過,說句公道話,和其他許多地方相比,我們在瑞士的學習好得多,這種令人窒息的強制少多了。在瑞士,人們只要愿意,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但有兩次考試例外。這讓人們有了選擇的自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目。我有個朋友,他是上課方面的好學生,每次去聽課,都很認真地整理講課內容。我享受這種好處,并認為這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毛病,只是偶爾會有些內疚。正是這樣,研究問題的神圣好奇心才得以保留了下來。因為現代的教學方法就像一株脆弱不堪的幼苗,除了鼓勵,更需要自由;只有自由才能挽救它,使它不至于過早地夭折。我認為,使用強制手段,或給人灌輸責任感,讓學生增進觀察和探索的樂趣,確實是犯了嚴重的錯誤。在一頭猛獸不餓的時候,用鞭子強迫它不斷地進食,特別是人們提供的食物還是經過千挑萬選的,它肯定會逐漸開始厭食的。兩者道理相同。
當時,物理學已經取得了一些細節上的豐碩成果,但教條式的頑固不化,在物理學的原則問題上仍占統治地位。這個教條就是:上帝創造了牛頓運動定律的同時,還創造了必需的質量和力。這個思想統治著一切,其他的所有東西都可以用數學的演繹法推導出來。在這個基礎上,特別是由于偏微分方程在很多方面取得的成績,使得很多人對十九世紀所取得的成就贊嘆不已。牛頓也許是第一個揭示了偏微分方程的功效的人,而且是通過他的聲傳播理論大力宣揚微分方程。其時,流體動力學的基礎已經被歐勒所創立了。但人們仍然認為十九世紀的成就只有作為整個物理學基礎的質點力學。我當時還是一個大學生,對力學在那些表面上同力學無關的領域中表現出來的成就很關注,而對非力學的專門結構或者它所解決的復雜問題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