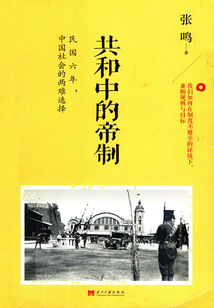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8評論第1章 寫在前面的話
我為什么要寫張勛復辟?這個事,說起來挺簡單。雖然說,這些年一直在晚清和民國這一帶轉,但可寫的東西,其實挺多,不一定非得落到張勛頭上。最直接的刺激,是兩三年前,有人出大價錢,讓我寫民國題材的電視劇,點的,就是張勛復辟。這個價錢,比我寫專欄、出書都高,高到無法類比,不由得我不動心。記得去年(2012年)翻明人筆記,翻到過一則逸事:明代圖書市場發達,好些讀書人是靠寫書掙錢的。有書商找自己熟悉的某小名人約稿,小名人說,先拿一摞銀子來,放在案頭,哪怕寫完了你再拿回去,這錢必須有,因為它提神。這個故事我喜歡。著書為稻粱謀,高人不恥。但我不認為有什么不好,只要寫的玩意兒不誨淫誨盜,煽動殺人放火,搞階級斗爭,或者溜須拍馬,坑政府,坑大人物。寫字賣錢,煮字療饑,或者換來干鐘粟和顏如玉,都沒有什么問題。郭敬明的文字,只要他不抄襲,其實我也能容忍。不高興的,只是某種勢力,想讓作家都變成郭敬明。
所以,我真的動心想寫張勛復辟,是看在稿費的面上。當然,試了一下,發現我沒那個本事,也沒那個膽量,可以放開了寫歷史劇,真的寫出來,連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中途改道,又變成了歷史敘事,而且是規規矩矩的歷史敘事,把注釋也加上去了。此時,讓我埋頭找資料、爬梳史料的真正動力,變成了這個事件本身。無疑,張勛復辟,跟我研究過的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不一樣,在近代史上,是一個沒有多少油水的話題。一碗冷飯,再怎么炒,加多少油或者蔥花,都炒不出名堂來。事太小,又過于簡單,袁世凱搞洪憲帝制,還弄了八十三天,而張勛復辟,從開始到徹底完結,不過十二天。其實,到第三天頭上,就已經結束了。這么點事,原因似乎也簡單,無非“封建軍閥”,無非“歷史倒車”。一個壞人,干了一件壞事,還沒有干成,因為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復辟不得人心。教科書的敘事,也就是研究者的解釋。從復辟結束那日,有話語權的人們就是這樣說的,一直說到今天。
但凡一件看起來過于簡單的事情,你這樣說,我這樣說,他也這樣說,大家眾口一詞,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這樣的解釋,放在辛亥革命上可以,放在洪憲帝制的失敗上合適,放在張勛復辟沒鬧成上,更對路。這樣的歷史萬金油,其實屁也不是,連萬金油也不是。萬金油不能治病,但至少可以緩解一下癥狀,這樣的解釋,連這樣的作用都沒有,充其量,只是某些頭腦簡單的史家,頭腦發熱騙自己的昏話。到了21世紀,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了沒有?我看都不一定。
退一萬步說,就算民心向著共和,如果有權有槍的人都要復辟,民心能擋得住嗎?抗戰勝利,民心思和,不想打仗,仗還不是打起來了?而且規模空前地大,嚇死個人。農業集體化,農民都不樂意,殺豬宰牛地抗議,不還是大規模地集體化了?一直搞到人民公社。原來的宣傳,是說集體化的農村是天堂,所以不能讓地主、富農進去。人們不久就發現,不進天堂,反而是種優惠,所以,只好把地富也拉進去了。后來包產到戶,農民都樂意,都餓到半死了,聽說包了,馬上生龍活虎玩命地干。最后,還不是偉人一句話,就不讓包了?民眾的意向,對于長時間段的歷史進程,肯定是有作用的,但在短期的歷史事件里,他們不是臺上無聊的龍套,就是臺下無奈的看客,對事件的發生、發展以及結束,沒有任何作用。除非,民意被適時地動員起來,形成組織的力量,才會產生影響。但是,在這種時候,民意又往往是野心家的工具,被表達出來的民意,誰知道是不是真正的民意?沒準,是種“被民意”。
客觀地說,民國時期接連兩次帝制復辟,操盤者本質上都是民意論者。他們實行復辟,其實都是著眼于國情,喜歡帝制的國情民意。無論怎樣強調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在袁世凱稱帝和張勛抬出清廢帝的事件中,都找不出底層民眾對此的抗議。相反,老百姓對皇帝又來了,還挺歡迎。尤其是第二次帝制復辟,當北京市民聽說皇帝又坐龍廷了,幾乎是一片歡騰,家家戶戶掛龍旗。這里頭,其實沒有辮子兵挨家挨戶地威逼,張勛的時代,還沒有人想到這樣控制居民。再說,他一共就帶了五干人,想這樣干,人手也不夠。那個時代,是個放任自流的時代,老百姓其實不用這樣表達對政治行為的態度。共和的時候,他們沒掛五色旗,復辟了,他們也不用掛龍旗。凡是這樣做的,都是發自內心。一個小警察在胡同口吆喝一聲,大家就都照辦了。龍旗的市場大好,于是有人突擊用紙糊,小販滿街賣,一個大子一面。吃棒子面窩頭加咸菜的百姓,指望皇帝能帶給他們便宜的米和面。
當然,皇帝回來了,面包也是不會有的。一個有兩千多年帝制傳統的國度,驟然變成共和體制,沒了皇帝,民眾的確感到不習慣、不自在。將中國辦成共和的人們,卻又做不好共和,或者說,根本不會辦共和。所以,舉國上下,怎一個“亂”字了得?掛龍旗,無非是這種不習慣、不自在的反彈。中國需要一個皇帝,民眾需要一個王法。但是,底層社會卻沒法兒推出一個皇帝來,即使推出來,也沒有人認賬。而上層社會一部分人推出的皇帝,另一部分人也不認可。袁世凱做不成,小溥儀,也坐不穩。即使坐穩了,也沒法兒帶給民眾好日子。共和做不好,退回帝制去,又不成。這就是當時中國可悲的現實。
民國好幾年了,民眾依舊留著辮子
對歷史事件,做道德批判最省事,也很痛快,但對于澄清真相,卻只能添亂。可悲的是,我們對于民國的兩次帝制復辟,基本上都是道德審判。凡是提及這樣的事情,可惡的預設就已經有了。等于先有一個標準,把某些歷史事件判定為反動的,然后再加以論述。而這個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成了已經插上死罪牌的被告,接受法官遙控下的群眾審判。這樣的審判,自然會把被告涂成白鼻子的丑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只腳。
進步史觀是個好東西,這樣的歷史觀,讓人們樂觀,也讓人踏實。無論現實多么黑暗,多么無望,人們都會有希望,因為歷史不會倒退,開倒車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們也許忘了,在中國的歷史上,倒退跟進步一樣,是經常出現的。五代十國,相對于唐朝,就是倒退。金與元,相對于宋朝,也是倒退。明清的絕對主義皇權專制,相對于漢唐,當然也是倒退。帝制被國人反掉了,但比帝制還要專制的制度,卻從側門溜了進來,又怎么樣了呢?
其實,兩次帝制復辟,都是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對中國道路探索的嘗試。參與者,不僅有袁世凱和張勛這樣的軍閥,也有很多文人墨客和學問家。兩次,他們都是要回到君主立憲去,復辟的主流人等,沒有幾個覺得君主專制好。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都是代議制,難道說,歷史走到今天,人們還非要說,法國大革命一定優于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和美國的體制,一定比英國的制度更優越?一個有著世界上最悠久的帝制傳統的國家,走英國的道路,也是難免的。
這些年,人們對于當年的某些具有文化保守主義者身份的學者,比如王國維、陳寅恪、辜鴻銘、嚴復、吳宓,已經有了很多的理解和寬容。認同他們的學問,也認同他們的人格,但唯獨談到他們跟皇帝的關系,還是諱莫如深。很多人完全否認,王國維的自沉,確有殉清的成分,好像王國維要是為那個皇帝死了,就一定很丟人似的。跟復辟有關的人物,袁世凱、楊度,尤其是張勛,人們還是難以寬恕。近年來,袁世凱和楊度,在某些場合,評價已經有了正面的聲音,但張勛,卻還是罵聲一片。當年的知識界,就對這個民國了還留著小辮子的將軍沒有好感,到現在,種種惡評依舊。其實,無論講人品,還是論帶兵,此人并不比當年的任何一個將軍更差。辮子軍的紀律,不比其他軍隊好,但也差不到哪兒去。他統治下的徐州和海州,也不見得老百姓就怨聲載道。別的軍閥有野心,張勛也有,別的軍閥愛國,張勛未必就不愛。提到這樣的話題,人們也許會感到奇怪,怎么,張勛也會愛國嗎?那么,段祺瑞愛國嗎?曹錕愛國嗎?吳佩孚愛國嗎?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些人,其實都挺愛國的。也就是說,張勛復辟,不是一群大逆不道的人,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其中的武人,不比其他的武人更壞。其中的文人,也不見得比其他的文人更沒品。無論道德學問,都有可稱道之處。清華四導師,被今人譽為教授中的教授,我們稱道梁啟超,難道就不佩服王國維嗎?這兩個同事,當年可是站在對立面上的。
沒錯,張勛復辟跟袁世凱稱帝一樣,都是干了一件好大的蠢事。即使沒有被人利用,為人火中取栗,也是妄圖翻歷史的烙餅,瞎折騰。歷史不能翻烙餅,正面不對,反面未必就一定對。但這個道理,當時人未必明白。辛亥革命,把中國一下子變成美國式的共和體制,扭曲太過,但簡單地將之扭過來,回復到君主立憲,也是個錯。夾生飯沒辦法加水重煮,因為滿中國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皇帝。歷史不是油畫的畫布,畫錯了劃掉重來就是。如果論扭曲,當初中國正好在異族統治時期遭遇西方,進入近代,本身就是扭曲。最近讀李潔非先生的明史著作,他解讀的那段歷史,正好是整個世界近代史的開端。在這個時刻,中國恰好第二次整體淪為異族王朝的統治。這個王朝帶給中國的封閉和保守,尤其是思想上的禁錮,讓中國在本該轉型的時刻,缺乏創造力和適應性。但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結尾,要等到張勛復辟,才露端倪。一個原本需要帝制立憲的國家轉型,卻因為異族的統治,大好機會被輕易放棄。放棄之后,有些人卻發現還是原來這個異族皇帝好些,想讓他回來。這樣的事,想想都替國人悲哀。當然,這樣的反復拉鋸的故事,實在令另外一些人氣悶,于是再往回拉。因為這個時候,環顧世界,君主國已經日薄西山了。先進的中國人,無論如何,都不肯再容忍頭上有個皇帝了。
辛亥的突變,給中國留下一道難解的題。民國的亂局,就是這難題的展開。這個難題,國人想做也得做,不想做也得做。做難題,要有三個條件,一有知識,二有時間,三有耐心。復辟回到從前,和跨越式發展,走捷徑,都是沒知識、沒耐心的表現,都是動輒來結構性的顛覆。從本質上,文化保守主義者跟后來的激進主義者,犯的是一樣的錯誤,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張勛復辟,展示了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復雜性,卻不幸地被人們大幅度地簡單化了。我寫這個事件,僅僅是想展示這種復雜性,絕非要做什么翻案文字。我一向覺得,所謂翻案文字,限于考據是可以的,但用在道德評價上,則是扯淡。對于過去的人和事,做價值評判和道德審判,很容易,幾乎人人都可以做。有的時候,歷史像個路邊的菜園子,但凡看過幾本書的,都可以進來摘菜。但實際上,干這個活兒,并不那么簡單。要真的想試試,肚子里比從事別的行當的人多幾干本書才能入門,當今之世,能耐著性子做到這一點的,就沒有多少。所以,剩下的事,就別提了。
這幾年,似乎歷史很熱,民間寫史,層出不窮。也有人說,出現了民國熱,微博上,還冒出了好些“國粉”。但說實在的,民國的熱,其實不過是一點兒虛火,若干不滿于現實的人,借題發揮,起一點兒小哄。民國的很多事,還是一筆糊涂賬。人們對于這段開始沒有皇帝的歷史,還缺乏基本的認識。從前說不好的,現在說好,從前說好的,現在說不好。來回翻烙餅,不是這一面,就是那一面。
這些年,寫的歷史隨筆比較多。這玩意兒屬于讀書筆記,亂翻書的時候,偶有所感,寫下來就是,非常輕松而且愉快。只是,我還不能忘情于專題性的研究,隔段時間,就會弄一點兒。累是挺累,大熱天,埋在故紙堆里,汗一身,塵一身,資料從案頭攤到地上,甚至床上,令人落腳幾難。但無論怎么辛苦,只要弄清楚一件事,心里還是挺欣慰的。讀書人本是賤人,君子愛財,但真正錢多的活兒,又不好意思干。一身大汗地折騰,也說不清是為了什么。雖然我還是教授,跟學界卻越來越隔膜。這些年,開始是人家不帶我玩了,后來自己也自覺地脫離了學術界,不想跟昔日的同行們玩了,算是一種自我放逐吧。但愿,沒有了我的學界,能慢慢變得像樣一點兒。
自打1989年出第一本書開始,每本書,我都是自己作序。開始是求不到名人,后來是不好意思打擾,再后來,就成習慣了。自我解嘲,序也是我書的一部分,自己不寫,求人代寫,書就不完整了。
是為序。